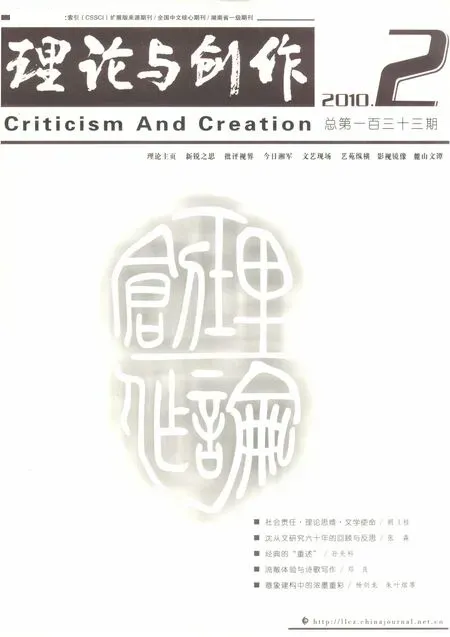在个人与文化的圆融中接续伟大的诗歌星空——汤松波《东方星座》对“主流诗学”的拓展与创设
2010-11-25霍俊明
■ 霍俊明
应该意识到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看似已经相当繁复和多元,诗歌写作也是在差异和多个向度展开,诗歌的技艺也似乎达到了新诗发展以来较为乐观的时期,但是在近些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大是大非的问题已经揭示出诗歌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自身的问题,商业、传媒、大众文化、话语权力、诗歌趣味、诗人身份都和诗歌极其含混、暧昧而又不容分说的纠缠在一起。在一个写作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实际上人们对诗歌写作多元化道路的认识并不乐观。尤其是在“个人化”和现代主义美学视野下,一部分诗人在过分沉溺于“个体”的同时坠入到不及物的迷阵之中;与此同时在新世纪以来更多的诗人投入到底层、打工、草根和弱势群体的“现实主义”的民生写作的时代潮流之中,在不断复制中丧失了诗人的真实体验、知识分子良知和诗歌写作的多样化。不管在何种程度上谈论19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写作中的个人化、个性化特征,这对于反拨以往诗歌写作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写作技法的狭隘性而言其意义已不必多说,但是反过来当个性化和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狭隘化并成为惟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无形中,诗歌写作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就带有了“病态”的来苏水味道。基于此有必要对个性化诗歌写作和诗歌题材问题的误识进行重新的过滤和反思。实际上题材从来都不应该区分为主流题材和非主流题材,然而20世纪中国僵化的美学和文学观念以及强大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却使得题材决定论(素材洁癖)仍然在当下以暧昧甚至强硬的姿势存在。似乎写“民间”、“底层”、“打工”就是进步的、伟大的,写“国家”、“时代”和“民族”就是落后的、堕落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汤松波的诗歌写作,尤其是诗集《东方星座》就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诗学启示性。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因为是在2009出版,更多的人将之视为“献礼”之作,我觉得这低估了汤松波的能力和写作《东方星座》的初衷。当然汤松波的抒写56个民族的《东方星座》是很容易被视为“主旋律诗歌”的,这无可厚非。可问题是在当下的诗歌美学语境之下,有相当多的诗人和专业研究者只要一提到“主流诗学”、“主旋律”和公共题材的诗歌就会在“洁癖”之下敬而远之,想当然认为这些诗不过是肤泛的颂歌和政治刻板的老调。而这种明显的对诗歌题材的道德认知和狭隘的诗歌观念仍然和以前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诗歌认知方式是同构的。基于此汤松波的这部抒写民族文本就带有了明显的诗歌美学和历史意识的双重征候。这部看似是“主流”甚至“主旋律”色彩的诗歌文本在众多研究者和读者的1990年代诗歌写作个性化的幻觉和错觉中可能会招致一些非议甚至批判,但是汤松波所提供给我们和时代的却是带有强烈的个性意识和复杂性的诗歌文本。更为可贵的是汤松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民间姿势重新走入了民族和历史的深处。这就与所有的其他类型的僵化的主流题材的写作拉开了距离。我想这正是我要就汤松波的带有“宏大”题材性质的诗集《东方星座》来重新审视这种类型诗歌写作方式的个性、丰富性和开放性,希望借此对中国诗坛的认知观念和惯性思维起到一些刺激和矫正的作用。
一
众所周知在199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和诗歌写作的变化,个人化写作成为至今仍然被很多诗人奉为圭臬的诗歌趋向,笔者也从来不否认1990年代诗歌所取得的成就及新诗史意义,但是一些新诗批评者无形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认为个人化写作就是拒绝任何诗人的“代言人”特征,也就是诗歌写作是不及物的,诗歌伦理或诗人伦理就是对诗歌美学和技艺的尊重与效忠。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在排除包括公共性题材在内的多元化写作路径的同时使得诗坛生态失衡,而这也正是汤松波的诗歌写作的现实意义和诗学启示。值得注意的是汤松波《东方星座》在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的诗歌语境中独树一帜,而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些诗作突出的抒情性甚至吟唱性质地。众所周知,在1990年代叙事性和口语的冲动下,在日常、口语、细节、对话、事件的所谓复调性的时代美学驱动面前,诗歌的戏剧化、叙事性、复调、张力、戏谑、反讽、冲突、悖论成了新诗现代化甚至新诗后现代主义的必经之途。新诗和戏剧甚至电影的共同作战成了诗人写作的必要常识和思维模式,诗人在普遍的欣快症中迫不及待地加入到日常经验和琐屑的身边事物的漩涡之中,这使得无深度的生活仿写开始泛滥。在此语境下诗歌的抒情性却遭到空前的放逐,甚至抒情被视为低级的小儿科的游戏。而汤松波多年以来的诗歌写作尤其是《东方星座》却在不断的情感渲染和诗人个体主体性不断强化的抒情中,将久违的诗歌情愫和主体的言说在诗意和文化的多重氛围中得到了最为恰切有力的诠释,而且不可替代的真实的生命感在言说和命名中得到了反复凸现。这也有力的证明诗歌的抒情性才是诗歌的本源并且同时接续了中国伟大的古典诗歌的传统。这不仅证明诗歌的叙事化并非诗歌的唯一圭臬,而且证明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和借鉴的。
当后工业社会的物欲消费和虚无主义浪潮漫卷大地的时候,古老而温润的民族文化与根性情怀已经多少显得“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境之下古老民族的文化血脉与原始根性几乎被人们所淡忘,而汤松波却身体力行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调查,致力于民族文化研究并以诗人的敏锐、想象、现代意识抒写出诗人对民族文化的诗意想象和创造。这种创造是古老与当代的融入,别具深蕴、视阈宽远、想象奇特的56个民族的诗歌深切的表达了诗人对生命源始文化、氏族血缘、图腾谱系以及多变的历史和当下时代的探询与致敬。在狂飙突进的科技理性中数字化、平面化和娱乐化的消费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降临。在引车卖浆熙攘难名、涌动的市场的好天气里,在感官膨胀的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时代,在看似流行化、时尚化和世界化的诗歌写作语境中,写作和生存实则都存在着极大被异化的危险。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所保留的民族文化元素也就越少。而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大体就是民族文化元素较少的时代,诗人汤松波正是深切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现代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丧失了自我和本性,而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与冷漠,如何求得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与圆融,如何重新回到人类生存的诗意的精神家园,就成为包括汤松波《东方星座》所探询和挖掘的话题。
在越来越喧杂浮躁、纷扰莫名的时代,也许真正能撼动诗人灵魂的事物和情景已经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诗人沉浸于“个人性”和“叙事性”的虚幻的圭臬,越来越多的诗人抒写所谓的底层、打工、草根的时候,汤松波的这些带有公共性、民族性、时代性同时更不乏创造性、个人性的诗歌言说方式反倒是获得了先锋的性质。当1990年代以来的诗人纷纷沉浸于日常性的小叙事和个人化写作场景中,汤松波的这种返回和瞻望、古老与现代的双重视野,规避了日常化叙述在一定程度上的琐屑宣泄和意义的硬性消解。在一种少有的文化记忆中,诗人使得人类能够依稀看到人类祖先在历史长河中最初跋涉的身影和踪迹。说汤松波的《东方星座》中关于民族的诗歌重新返回人类生存和文化的起点并以宽远和世界性的文化和审美视域进行观照和创造应该是比较恰切的。
汤松波的《东方星座》没有落入以往“主流诗学”的俗套,流于单一颂歌型的缺乏主体真实感受的空洞与乏力,而是在个人化和民族、文化视野中再一次呈现了中华多民族的真实而繁复的根脉,一定程度上有着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在墨脱/这个隐藏着莲花的圣地 /他们的双脚/至今仍未能与全国的公路网/相连”,“门巴人见不得/探险者带入的/任何一个有辱山水与神灵的/字眼和标点//我在想/假如真的有了一条/通往墨脱的大道/蜂拥而至的游客/会让门巴人欣喜不已/还是烦恼连篇”(《门巴》)。我想对于任何读者而言都会在阅读中完成一次陌生化的而又神圣的无以言说的朝圣之旅,俗世的情怀会在一首首关涉各个民族的诗中与诗人一起领受自然的伟大、宗教的玄秘、静穆的神性、人文的力量、文化的根系、民族的情怀。一颗颗尘土掩盖的心灵会在此刻迎接那湛蓝的天宇中漫洒下来的圣洁的白雪来清洗尘世的污垢和麻木的灵魂。汤松波的这些诗歌在建构民族文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蕴涵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精神气韵与文化血脉。汤松波收录在《东方星座》中的诗歌充满了生命力和活力,这些民族诗歌不仅从个人、历史的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民族文化,而且在处理永恒性题材和现实题材上同时展开。诗人将对现实生存境遇的关怀也有机地融入到诗中,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敬畏和良知感,而诗人对工业语境的质疑和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都无疑有着相当的启示性意义。更为可贵的是汤松波的这些诗具有一种开阔的视野和文化使命感。汤松波在回望历史长河中古老民族文化脉系的同时又将视野投注到当下与未来,既保留了原初意义又丰富了当代人的审美和文化诉求。而正是在现代与民族的古老文化的交点上,汤松波的民族诗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的内涵。
二
在疯狂加速前进的后工业化时代,在无限膨胀凸起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景观中,已经很少有事物能够唤醒现代人麻木的内心和自以为是的“自由”,“分明在我们的操场/分明在我们的情场/分明在我们的商场/分明在我们的官场/分明在我们的/人生广场/高高燃起了一座/铸造自我筋骨的/火炉”(《保安》)。也正基于此,多年来汤松波的诗歌写作越来越涉及“公共”题材正体现了诗人深入的对诗歌和文化以及现代性图景的思考,而诗人内心深处对美好、伟大事物的憧憬与渴念也会愈来愈强烈。当诗人历经三年多的时间来准备抒写56个民族的诗歌星空时,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想汤松波的努力是值得嘉许的,因为他所精心营设捧现在我们面前的璀璨的诗歌星空,不仅让我们在面对遥远温热的南方、广袤无垠的沙漠、波涛浩瀚的大海、神秘自然的山寨、静穆神秘的雪山、浩浩延伸的大草原、西北的高塬时感受到了文化和精神的洗礼,而且纯净和安谧的伟大民族景象不能不让读者肃然起敬,屏住呼吸,像一个个领取圣餐的孩子。可以说汤松波诗歌中的“民族”景观是在多样繁复的地域和历史谱系中同时展开的,而与这些民族相关的地域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名词所涵盖的意义,她在此刻已经幻化成一种令人心生敬畏的伟大的居所,因为此刻人、神、自然、文化、历史、民族相圆融的伟大力量已经降临并氤氲开来。诗人内心深处的渴念、敬畏、孤独、安宁、遥想都是与草原、戈壁、雪山、大海、山寨、冬夜、星空、旷野在瞬间契合。由是观之,汤松波的《东方星座》等具有创设性的涉及公共题材的诗歌无疑是具有重要性的,而这对于在长期生活在现代化漩涡中的人来说都无异于是一种梦想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绚烂多彩的童话般的景象,这些景象是那么直接又那么不容置疑地在顷刻间就攫住了人们的灵魂。在诗人的发现性和创设性的审美视阈中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各个民族却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多的新奇和陌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吟诵起来琅琅上口的诗歌在顷刻间让我们回归到人类的本初体验和情怀,任何个体在此刻都会情不自禁的返回到人类最初的生存景象和永远的甚至忧伤的“怀乡”的冲动之中,“走进那达慕大会/一股从历史深处吹来的雄风/会猛然沁入你那/钙质流失得太多的/肌骨”(《蒙古》);“在钢筋水泥覆盖的省会/省不去的乡愁/比遍地的格桑花还多”(《裕固》)。凛冽的冬夜中那漫无边际的雪山、平原和高高直立的白桦林,美丽的让人心痛而失语的草原和河流,这一切所构成的巨大场阈,而其对灵魂的震撼则是难以想见的更是难以言说的。人与自然、人与语言、人与民族、人与地理、人与时代以及人与历史的对话在日常与仪式的融合中都以复调的意向和弦的方式舒展出繁复的空间,如“雪山下一树/怒放的桃花/或许正是这个春日里/最美丽也最坎坷的/词语”(《独龙》)。而在这广袤、安寂的土地之上,在诗人心灵之上的是永恒的夜幕中静静闪烁的星群。在渺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人性与神性、狭仄与高远中,除了仰望灿烂的星群,倾听那来自一个曾经多灾多难现在又无比伟大的家国和民族的声响还能有什么值得诗人反复吟哦呢,“我在格桑花丛里高高地读你/读着读着便变成了喊/喊着喊着/就变成了永不停顿的歌唱”(《藏》)。
面对一个文明古国和现代化视野下的多民族发展,汤松波并没有陷入普泛意义上的颂歌型集体调式的泥淖,而是站在人性、生命、文化、时代和反思的高度。梁平作为诗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使得《东方星座》这部大诗的人文精神、历史意识是相当突出的。在汤松波的诗歌写作进程中,无论是处理个人化的题材,还是在大型组诗《锦绣中华》、《东方星座》等公共性的“主流诗歌”中,他一直秉持了新世纪以来诗人普遍缺乏的一个重要质素,即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一种在时代和写作中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加深问题的手段,是自觉延宕真实指认的(“极限悖谬”,是到达历史真实、个人真实和虚构真实的有力和有效的途径。这种想象力显然是将历史个人化、家族化、真实化,不断用真实的巨流冲刷惯性知识虚幻的尘埃或宏大历史叙事虚假的色彩,还原出与生命、生存更为直接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这在《东方星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曾经的驼队、骡队、马队/联系着新疆的孤烟/通畅于中亚的霜雪//沙海里不知珍藏了他们/多少风干的热泪//一只只仙人掌/至今还在历史的纵深处/标示着他们用血汗撰就的/金黄书页”(《乌兹别克》)。当然由于时间的限制和个人视野的影响,《东方星座》中的极个别诗作略显单薄,挖掘的不够深入。汤松波的这些民族诗歌不是抽象干瘪的文化说教和民族大团结的宣讲团,而是以充满激情和想象的笔触渲染出奇幻而苍莽的民族祖先酷砺的生存景观和现实场景。非常有意味的是,在《东方星座》中,每一个民族的诗歌前都是一幅插图和关于这个民族的文字介绍。这些图片和介绍性文字就与相关的每一首诗之间具有了相互打开的互文性质。二者之间的关系和互补性相当明显,而重要的还在于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换言之汤松波的诗歌话语方式更为灵动、鲜活,富于生命感和想象力。基于此,茫茫天地间蹀躞的庞大身影正暗含着人类这奇异的精灵在自然界中的伟大,莽林、沼泽、草地、洞穴、荒原、海滩、山川构成的生存背景正衬托出各个民族的倔强、坚忍、抗争、乐观、勤劳的精神品性。在诗人繁复的笔触和纷繁的意象叠加中,犹如浑厚的油画相当深切的地折射出一个民族奇异的精魄和幻化的生存景观。基于此,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人文景观在诗人这里获得了一种丰厚的文化观照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彰显了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哲思的感悟。基于此,当我们跟随汤松波的视野不断寻找和发现的时候,那些与各个民族相关的植物意象体系,动物意象体系和自然意象体系不再只是单纯而抽象的符号和人类眼中的客体,而是具有了灵魂和思想甚至宗教意识,具有了生命的热度并承载了人类原初的古老记忆与当代的鲜活想象,“这是山川辉映的/一道道闪亮的灵光/这是大地祖传的/一帧帧生动的底片”(《序曲》)。这些携载着文化感、历史使命感、宗教感、民族感的民族文化诗,重新打开了读者的审美和文化视野,拓展出一片鲜活而神秘,古远而又切近的诗意地域。正是这一地域使得生存的人类扎根于脚下苍凉而丰厚的土地,诗意的生存,艰辛的劳作,又不时抬头仰望浩渺的苍空。这种仰望是穿越大地向天空的仰望,它既扎根向下又秉有了形而上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