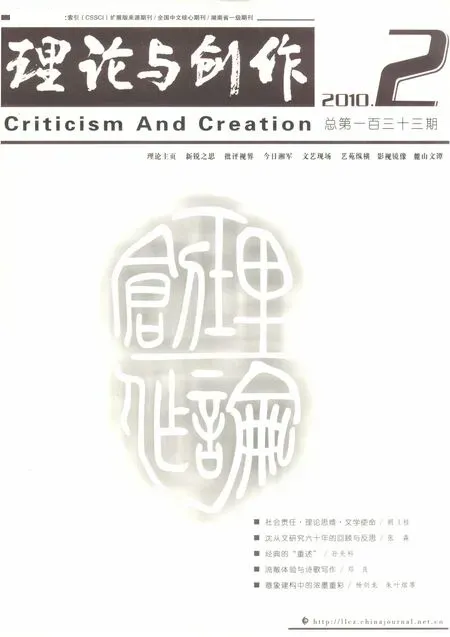关于小说形式美的美学意蕴——以何立伟作品为例
2010-11-25何先慧
■ 何先慧
一
这里说的小说形式,是指文学作品作为“完整的语言结构”,而形成审美反映的枢纽。文学史是作家作品和读者的关系史,文学价值是作家创作意识和读者的鉴赏意识构成的。文学的鉴赏过程在作家艺术构思中就产生了,他要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并在创作和艺术传达过程中不断修改,来适应读者的期待视野。尧斯认为文学作品的接受中,有一个重要的接受就是垂直接受。垂直接受是指从历史考察读者接受的作品,有的文学作品蕴藏的含义逐渐被发掘,几百年也研究不完。①
伊塞尔也是从阅读鉴赏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接受。他认为文学作品有两极,一极是艺术的即作者写出来的本文,另一极是审美的即读者对本文的具体或实现。②他认为,文学作品通过它的文本结构已经暗含着读者可能实现的种种解释萌芽,叫做“暗含的读者”;文学使用的描写语言,包括了许多的意义不确定和意义空白,这种不确定和意义空白,是审美价值的根本点。他把它称为“召唤结构”。
对于这种审美价值的形状,黑格尔也有过这样的描述:“遇到一件艺术作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或内容。前一个因素——即外在的因素——对于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的形状的意蕴,那外在的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③具体到文学鉴赏,鉴赏者必须由语言层面进到作品的形象,在领悟到作品的基本主题之后,他必然还要对内容品评,把玩一番,而这“品评、把玩”的对象,既有内容也有形式,而且常常是作品的形式美给予鉴赏主体很大的审美享受。当鉴赏主体把握了作品的意蕴以后,回过头来再把玩作品的形式美,就会更觉其美了。
以何立伟的作品为例。何立伟小说的结构,我们与其说它是“完整”的结构,还不如说它是“不完整”的,作家正是凭借这种“不完整”来获取一种“完整”的形式美。譬如他的获奖小说《白色鸟》,原本是要写残酷的阶级斗争的,但是作者别开生面,详尽地铺陈出一片姣好美艳、浑然天成的安谧祥和的境界,一直到最后,只是轻轻地又简单不过丢下一笔:传来了锣鼓声和开斗争会的喊声。小说到此戛然而止,但结构中的诗化形象出现了。作者在此处收刹,留下了“不完整”的“空白”,正是诱导读者为这诗化的形象,添上了精彩的一笔。这是何立伟小说中设置的散文诗式的“张力场”,也是散文诗中美丑对立的意境。唯其如此,才能达到艺术结构“诗化”的目的,才能由虚而实,通向作品题旨的丰厚性和含蓄性,而获得艺术、美学的容量。
小说空白是造就“虚而实”即虚实意味的关键。关于虚与实,中国古代画论有精到的描述。清人布颜图说:“盖笔墨能画有形,不能给无形,能绘其实,不能绘其虚。山水间烟光云影,变幻无常,或隐或现,或虚或实,冥冥中有气,窈窈中有神,茫无定象,虽有笔墨,莫能施其巧。故古人殚思竭虑,开“无墨之墨、无笔之笔以取之。”(《画学心法问答》、《画论丛刊》上卷)绘画中这种无墨之墨,无笔之笔,看似空白其实是“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画荃》,《历代论画名著汇编》)上述之《白色鸟》,可谓虚中见实、实中见虚的上品。作品看似整篇实写白色鸟的安详、美丽,大自然的姣好、美艳和两位少年的自由快活,而最后丢下一句开斗争会的锣鼓声响了——这斗争会背后的人间灾难,看上去是“虚”晃一枪,但由于这斗争会是那个时期的读者所亲身经历的,因而暗含着读者可以实现的种种解释,也就是读者对本文的具体化或实现,从而产生“虚生实”的效果。尤其在此美丑、善恶画面强烈对比的“召唤结构”的召唤下,更能调动读者现实世界的经验去填补这“无墨之墨”,从而实现其鉴赏过程的再创造。
为什么说这样的作品比那些穷尽残酷斗争事实的作品更富于意味呢?那是因为它的潜在功能越丰富,读者参与创造的机会就越多,对读者的影响就越大,影响越大,读者的接受就更深刻,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就越强。
类似的例子在何立伟的创作中可说俯首即拾。比如《房客》,其单身男人偶然在宾馆见到一对夫妇中的女人,他始而慌张,继而捂住胸口,最后在心跳中死去。我想,这正是美学家莱辛所指出的“富于包孕的片刻”。即是说,这单身男人死的片刻,一下子在我们面前烘染出一种雾里看花似的情绪氛围,诱发我们去体味这位单身男人和女人属于他们过去生活的“前一顷刻”,而产生“虚生实”的美学效应。这种不可预测的诱发效率,就是作品潜在功能和“召唤结构”的发挥,当然也是意味深长的形式使然。审美思维说到底,就是模糊思维,就是明人谢榛提出的“妙在含糊”,而何立伟的“不完整”和“空白”正是这一审美思维的表现形式。
二
语言,是艺术形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谈谈何立伟小说的语言文体模式。
在对语言文体进行实践的当代小说家中,没有谁像何立伟那样受到频繁的批评。在这当中《白色鸟》和《一夕三逝》可算首当其冲,质疑的文学一度见于当时各种报刊。人们的质疑不是没有理由。因为照常情看来,他的词语的重复、雕琢甚至前后倒置,常常使人觉得有些别扭。用责难的人的话来说,就是他“放着今天的语言不用,偏偏要亦步亦趋地蹈袭、模仿那种‘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时期的语言’,这种初期的现代语言一方面打破了几千年形成的语言桎梏,但另一方面又明显地带着从文言文语言中脱胎的印记和欧化句式影响的痕迹。”④这位责难者还从《白色鸟》中举出这样的句子:
……故而那白皙的少年,也就极喜欢外婆喷喷香香炒的马齿苋干菜……
其时头上的太阳,正如烧红的一柄烙铁。
汪汪地绿着,无涯地绿着,恰如少年的梦想。
责难者主要是质疑其“故而”、“其时”、“如了”以其“设若”、“抑或”之类的古里古气。但是在我看来,这里的“古”气又是不古的。因为它早为现代汉语所袭用。而且,这些词语作为何立伟小说语言结构的一部分,正好与他钟情的“绝句”或小说,与他所陶醉的我们民族文化积淀过程中所形成的抒情气质互为默契。语言是什么?那不就是一种文化形态吗?因此,从他的语言中,我们也感受到古文化及其沿革的一个缩影。这也是他小说中诗的抒情品格和美学价值的主要构成部分。一如何立伟自己所言:“我常常为自己民族语言涨满着感情内容与丰富的表现力而深深陶醉和自豪。实话说,也常常为不少作家将它的作用忽略而扼腕叹息”。(关于《白色鸟》)⑤
因此,这种古气,我们大可不必以为然的。只是他那超越语法规范和倒置的句式常常使我们有点不适应。请看下面的词法语法结构:
忽然来了十几个外地年轻伢妹子,标标致致一个个……
——《影子的影子·水边》
山仍复是峥嵘着,天扼得仍很小,再朝山里走,满耳灌溉着的就是訇訇一派的水声。
——《山洪》
以上两个句子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是将句子倒置,本来应该说“忽然来了十几个外地年轻伢妹子,一个个都是标标致致的”,却说成了“标标致致一个个”。我看这不能说成是语法错误,比方“十来个好汉”和“好汉十来个”都是很正常的语法结构。何立伟的“标标致致一个个”虽然看似不正常,但在“不正常”中,抛弃了陈陈相因的旧气,多了点新鲜,尤其是平添了一种韵律感(何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就说到“起伏了一种韵律感”)。二是着意于实词的推敲和虚词的布设。山“峥嵘”着,天“扼”得如何如何,满耳“灌溉”着……水声,都是巧用实词和虚词,以至超越语言常规的句例,他对实词和虚词的变用,常见的方式是名词和形容词作动词用“山……峥嵘着”,就是将形容词“峥嵘”作动词用,不过你仍把它看作形容词,也无不可。《山洪》中的这一整句,作者通过语言的构设,大大强化了感觉的色彩和情调,显示出语言的个性美来。试想想,如果作者不运用这种词法语法的设置和构造,那么他的语言只能是平淡而俗常了,这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所不乐意见到的。
个性和色彩是何立伟小说语言形式美的主要特征,又如《影子的影子·水边》有这样的句子:“牛和狗也来了。自由散漫得很。只是狗喜欢吠一吠,牛不吠,兀自低头懒懒散步,俨然是一哲学家。狗大约不热爱思想就间常同哲学家玩笑玩笑,惹它发小小一点脾气。夕阳正为青山咬住,一口口吞它下去。”这不啻是充满昂然情趣和妙语解颐的笔墨。《白色鸟》表现少年的乐观这样写道:“还格格格格盈满清脆如葡萄的笑声”,恣意把“笑声”比喻为葡萄,使声和形这两个不相干的东西串连在一起,可谓出格矣。但是“笑声”和“葡萄”毕竟有“甜美”的内在联系,让葡萄为喻,从而获得色彩和味觉的美感,并进而产生一种感觉的芬芳的释放,显示出“这一个”作家殊异的个性和语言效果。
何立伟小说的语言似乎有着一种说不尽的因素。它的独特品性,是由于那种强有力的词汇呢?还是那种超越常理的比喻和句子的组合方式?抑或是贯穿于长段文字中那种显得古怪繁复但又加倍陡增的抒情成分和色彩?他语言措词的古怪,有时简直是远离了我们生活的习惯和常情。但是任何语言的修辞效果,只有当它对读者而言脱离了实用语言而显得新鲜、陌生时才能引起最大限度的注意。“本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派非常注重文学语言的这种特点。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就是要使那些已变得惯常或无意识的东西重新成为陌生的,从而产生新鲜感,吸引读者的注意。文学语言就是把实用语言经过艺术加工后变得陌生新鲜了的话语。他们认为文学其实就是对语言常规的‘有组织的违反’,即依据一定的创作意图使话语脱离实用语言的常规而变得新奇。”⑥
语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群体和心理结构内生衍,它是文学的,但又是文化的社会的产物。语言体系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体系。何立伟,作为有意强化民族文化意识的作家,而着力于对古代语言内质的体味,崇尚古代庄子那种“得意忘言”的境界,实践孔子“情欲信,辞欲巧”的准则,使语言越过实用的和工具功能意识,逐渐显示出语言的独有审美品格来,也显示出摆脱语言困境时的智慧来,这是我们读者所乐意见到的。
三
从何立伟小说的语言和结构相比较,我似乎更欣赏其后者。因为小说那种情绪化的空旷结构,使得他的作品像小溪荡漾涟漪,微风掀起浪花,地壳激荡潜流,轻灵得很,飘逸得很,也深广得很,浩渺得很。不仅是他的《白色鸟》、《山洪》、《水边》,还有他的《小站》、《小城无故事》、《士霁》、《除夕》、《淘金人》等都是如此。譬如《小站》中的“我”,好不容易从桂林乘上一辆到长沙的便车,然而,面对着他那从鼻眼里发出的“呵!——”“喽!——”的颐指气使的派头,面对着他给一对于昏暗中依偎相爱的男女所下的驱逐之令,“我”毅然决然地不等到达终点,就快速下车,从而出色地描绘出一种自尊自重和孤高凌励的心境,将一种突出的印象和闪电般的色彩呈现于世人面前。
作者正是以精湛的才情和质的感受力,在结构和内容上,加以浓缩和浑然熔铸,从艺术总体上把握急剧变化的丰富生活内容。作品中人物那种决不臣服的思绪,不仅显示了速度的节奏,也显示了力度的节奏,让人从中领悟到生活的旋律与转机。
有一些读者读了《小城无故事》对我说,何立伟的作品很像朦胧诗,隐晦得很,有时甚至见不到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内容。《小城无故事》从表面上看,似乎缺少一种新的思想和现实关系的凝结,缺少一种现实感和当代性。然而,故事中的饮食店和摊贩买卖人,对癫女子是那样地古道热肠,即便癫女子把店主送上装食品的瓷碗砸烂,店主依然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怜悯;而店主和摊贩主对两个从外地来的陌生客则冷若冰霜,因为他们看见陌生客对癫女子的调笑无礼,即便上门的生意不做,也要对陌生人表示出愤激之情。这是已经呈现于画面的东西,重要的是,它会让我们想象出画面所无的东西:比如店主和摊贩人对癫女子这番情谊的由来(包括她在政治运动上的悲惨遭遇;她死去的亲人是这一厢厚重的老人),而正因为店主和摊贩人对这一女子及其家庭的怜惜和尊重,他们才不能容忍陌生客对癫女子的丝毫无礼。
这些,都是在“空白”里蕴含着的痛心故事。你能说它缺少现实生活内容吗?那凄楚的情思中分明有着强烈时代精神的贯注和对十年浩劫的反思,可说饱含着直入社会肌体的深度。不过小说使用的,是更见曲尽幽微的艺术笔墨,以及由此而来的耐人玩味的美学氛围。
何立伟是一位非常重视艺术形式,刻意进行艺术劳动和勇于创新的作家。他的艺术感觉极好,艺术想象力极强,他在小说模式、艺术结构、语言文体、表现方式上的刻意求工,丰富了当代小说艺术的表现手段。不过,何立伟也不能因此而过于自得其乐,他必须辩证地看到他对形式的过于讲究而伴生着的形式主义之嫌。而且,小说本身的空间形式也总有疲惫的时候,随着这类大胆切割的小说形式在何立伟的名下催生繁衍,随着这种空间形式的新鲜感一旦消失,也会形成新的概念模式和新的单调划一,进而丧失原有的形式美感,出现艺术创造力的老化和钝化。同时,这种小说由于篇幅所限,当然谈不上具有恢宏气魄艺术典型的创造,难于达到一种荡气回肠和黄钟大吕的史诗性境界。何立伟是热烈推崇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两位文坛老将的,但我们认为,沈老和汪老的艺术境界,与其说他们重视艺术形式,还不如说他们臻至了一种“无形式无意识”或“无形式无技巧”的境界——也就是让形式与内容合而为一,达到了无迹可求之境。
注 释
①②转引自曹廷华主编:《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
③[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4页。
④⑤转引自胡宗健:《何立伟小说形式评估》,见《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胡宗健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181页、第181页。
⑥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