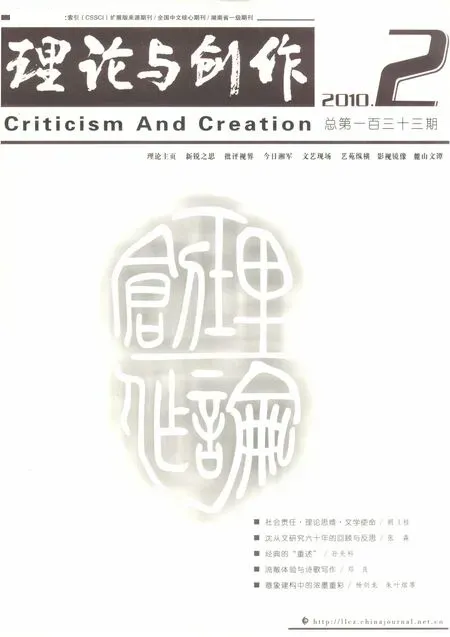池莉小说:时间的大众化与死亡的丧失
2010-11-25肖百容
■ 肖百容
池莉是1990年代初期非常红火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以描写日常生活,以及在这种日常生活中按照日常规程,免不了小烦恼,却也很满足很快乐地生活着的普通人为主题。这个主题颇受读者的欢迎,原因在于,一方面,长时期以来人们看多了英雄主义的作品,可英雄生活毕竟与当前生活联系不大,现在让他们换换胃口,看看普通人的生活,自然有一种新鲜感和亲近感,显得朴素可信。另一个方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中国走向市场化的时期。市场化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功利关系,与大众日常生活是密切相联的,具有大众化的特征。池莉的小说就正好体现了这一时代潮流,因此很合时宜,其中的《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不谈爱情》等尤其受欢迎。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池莉的小说与死亡有什么关系啊?确实,池莉小说是很少写死亡的,比起余华,史铁生,北村等当代以死亡为重要主题的作家是如此,就是与写死亡不太多的贾平凹、苏童等人相比也是如此。恐怕在二十世纪的作家中,池莉是最津津乐道于普通生活的小烦恼小欢欣的作家,她几乎回避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她不仅“不谈爱情”,更“不谈死亡”。既然如此,这里我为什么还要选她为例来进行分析呢?我们知道,死亡这个问题有其特殊性。人们的死亡意识在一般情况下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对死亡会毫不知情。根据心理学家们的考察,一个人到了9岁左右就会自然而然地思考死亡问题①。但是这样一种意识对于不同个体有强有弱。而且就象生理保护机制一样,人们面对死亡意识的恐怖与残酷,会不自觉地用日常生活的鲜活性与现实性将其压抑到意识的最偏僻的角落里去,使死亡显得遥远而模糊,仿佛与我们无关。它成了我们生活的远景,平常很少有人去关注。完成这样一种保护机制的途径主要有二条。一条是用社会事业的创造来转移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古代所谓的“立功立言立德”等三立事业就是如此。人生如能实现这样三个目标,或者完成其中一项、二项,就是有价值的,生死本身则是微不足道的了。古代的士子们,终其毕生精力在追求这样的丰功伟绩,哪里还会整日沉溺在个人的生死意识之中。正如孟子所言:“所欲有重于生者……所欲有重于死者”②。还有一种就是以日常生活本身的美妙诱惑人们,使其将死亡淡忘。中国人所谓的“过日子”就具有这样的功能。而八十年代以来,英雄主义日益退出中国社会。呼唤平凡的生活,强调日常经验成为时代主潮。作家们的创造是这样的,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和池莉的一些小说。批评家们也尤其注重挖掘作家创作中所蕴含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和表现。如果说刘震云还对英雄主义的丧失有点失落,对日常生活的到来有点无奈。那么对于池莉,则是完全的津津乐道,闲适自得。
池莉的小说不像史铁生、余华等人对英雄主义或指指点点,或痛陈其虚伪③,它几乎从不谈英雄主义,而是对其采取漠然的态度。漠然是比反对更坚决更彻底的一种否定态度。其小说《不谈爱情》,命题好象有点对浪漫生活的否定,浪漫毕竟与英雄主义有点关联,而日常生活与之相应的主要特征是物质实在。但作品也没有刻意营造浪漫与“实在”的二元对立。叙述者只是满怀热情的叙述着一个日常生活的故事。另有一篇小说命名《太阳出世》,初看会被其所迷惑。以为又是什么“宏大”叙事,猜测讲述的会是什么杰出人物的故事,其实故事只是叙述了一个名叫“太阳”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前前后后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小孩的诞生过程。这个过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太阳出世”有成千上万,几无特殊可言。
池莉的小说正是现代生活的写照,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的。在一个生产流水线上,只有程序,没有特殊。每一个环节同等重要(必不可少),也同样不重要(不起决定作用)。一个人只是代表生产线上的一个既重要又不重要的环节。他既必不可少,也可被轻易更换。平均化是机械工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也被平均化了。人们没有其他追求,只求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环节。只要能保证自己成为一个环节,他们就会觉得很安逸,很幸福,同时又会觉的很乏味很枯燥。日子就这样平常地过。所有的日子仿佛都是一样,也会一样地永远如此。没有变化会到来,也不去做痴心的妄想。人们不仅觉得所有的日子都是一个样都会一个样,他们甚至认为每一种每一分都是一个样都会一个样。就这样,现代时间观念产生了。
时间到底是什么呢?时间不是一个具体事物,也不是存在者,因此我们无法在经验中表象时间自身,而只能把握住时间的感受。在农业文明中,时间对于人们只是日升日落、春风秋雨、播种收割……那时人们的时间观念是与大自然紧密相联的,跃动着自然的节律,而这种节律也是生命的节律,因为春夏秋冬,草木枯荣就对应了人的少年、中年到老年的过程。当然由于自然现象的循环反复,所以人们在自然中既能感受到生命的“季节性”,又会产生生命无限的想象。现代工业文明以工具理性为基础,它需要的是准确性、科学性,于是产生了钟表。钟表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被广泛使用,其所计量的时间为全人类所认同,所以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时间观念:时间是没有限量的客观存在,它是永恒的,没有尽头;而且全世界共有同一个时间。它可以被精确到无限细微的程度,人们也可以对其进行公平分配。你用两个小时看了一本小说,他在这一百二十分钟里考完了英语,好象对谁都一样,没有亏待谁。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社会里时间观念的公共性、客观性、平均化特征,即一种流俗的时间观④。
海德格尔要追问的是本真的时间。既然时间和空间不一样,它不是客观事物,不是存在者,我们又如何判断本真的时间和非本真的时间呢?海德格尔认为其判断依据在于它是否来自本真的生存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为了一个又一个目标在不停地忙碌,烦忙着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但我们只看到上手的事物,而将过去遗忘了,我们也期待将来,但只是把将来当作一个还未到来的现在。于是我们把时间抹平为无差别的当下时刻。在这样一种时间领悟中,我们把将要来的死亡当成了将来某一确定的时刻了。死亡在时间上本是难以确定的,人们在意识中将其确定化了以后,就使我们躲避了死亡,也就遗忘了死亡。于是,我们觉得每天都会一样,而且将永远如此。而本真的时间观与本真的生存领悟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一个存在者来说,时间是有限的。它是你的一生,是你身上岁月的痕迹,也是将来对于你现在的影响。将要到来的死亡就与你的生命连根而在。它不是将来事件,而是早已存在于你的生命之中,它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在对待自我生命中,以向死而在的态度筹划人生,把自己看成“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⑤,即把存在规定为时间性,我们就会有先行的决心使自己成为自由的别具一格的自己。时间在这里就是源始的、本真的,它使存在具有了意义。
围绕时间和死亡概念绕了一个大圈,我们现在再来看池莉的小说。她的《太阳出世》写赵胜天和李小兰夫妇从结婚到生育小孩的详细过程,有点像家庭纪实,甚至生育记录。小说一开头就是赵胜天和李小兰结婚那一天的描述。什么家庭决策、长江大桥堵车、“麻木”游街,我想这些恐怕是每一对武汉新郎、新娘都会有过的经历。然后是蜜月旅行计划因李小兰怀孕而泡汤,接下来就是关于李小兰孕期生活的详尽的叙述,什么孕检啦怀孕体验啦,每个月如实纪录下来。再接下来的环节谁都清楚,那就是孩子的出世和抚育孩子的辛苦和欢乐。赵李家庭生活过程中也有不如意和争吵,但那些均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烦恼。总之,整个小说按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武汉市一对普通小夫妇最初一年多的家庭生活琐事。他们的生活似乎没有任何特殊性可言,原因就在于无论他们的什么行为,总有一个蓝本可供依据。他们按照武汉市大多数青年人的日常生活模式设计自己的生活样式。结婚和蜜月旅行听大哥的安排,而大哥喜欢的是武汉的”摆显”习俗,生养孩子也是如此。小说最后有李小兰在儿童公园与另几个小母亲交换家庭生活经验的安排。这个安排真是有意思。它让李小兰的生活有了另几个样本,尽管可能在细节上会有所不同,但讲述的都是她们如何进入“初为人母……的轨道”。
这个轨道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烦”的轨道,“被抛”的人进入的轨道。虽然小说也写了赵胜天,李小兰夫妻俩在一件一件令他们疲于应付的生活琐事中感到的快乐,比如孩子成长带给他们的欢欣,因为在生活中学会了一些做人道理而感到的满足。但是这些也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烦”。“烦”是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用以描绘人被抛后的状态。它已不是一种情绪状态的描绘,而是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即一种没有个人选择,也遗忘了死亡的生存状态的描述。这是一种没有自由,非本真的生存状态。人被生活催促着,挤压着去干一件又一件事情,能够开展的可能性是单一的而不是多元的。李小兰、赵胜天的苦恼和快乐都来源于这些日常生活琐事,那不是他们追求到的,而是碰上的,又是必然会遇到的,由不得他们自己进行选择。因此他们的欢欣和满足也是“烦”。“烦”就“烦”在他们的生活遮蔽了死亡的根本的可能性。他们不把死亡这个可能性当前化为整个生命过程之中,而是将其理解为未来某一时刻的某个客观事件,死亡成为一个没有生存论意义的物理事件。这样,在现代人们的当下意识中,时间是公共的,无限量的,个人死亡从生活中消失了。没有了个人死亡,生活似乎永远会是现在这个样。所以,现代又将过去和将来都当成了曾在的或未来的现在⑥。他们认为所有的时间都是一个同样的结构,没有差别。赵胜天、李小兰们就在这个没有差别的时间观念里盘算着日子,筹划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他们的日常意识中没有死亡。池莉的小说关注的焦点是小市民的油盐酱醋,她将她的主人公放置在以死亡为远景的时间图画中,看他们如何按照本能谈情说爱,结婚生子,甚至也看他们的烦恼与痛苦(《烦恼人生》)。他们“在所烦忙的逃遁中有着在死面前的逃遁,亦即掉头不看在世的终结”⑦。他们无意识地又自然地接受了流俗的时间概念,把时间像家具一样做了精心的安排,似乎死亡从不存在。他们天天在“还有时间”的闲适心态下享受当下生活,也幻想着美好的未来。并不是说他们的理性思考中没有死亡,他们也知道有死亡的存在,但在他们那里,死亡很少处于“悬临”状态。只有在面临他人的死亡事件或在烦忙的间隙中,他们偶尔才会想到死亡,可很快又在烦忙中将其遗忘。因此对待生活,他们不会有先行到死的先行决心,甚至连生死无常的荒诞感、痛苦感都没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在做知青时期有过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爱情,却由于彼此都无法说清的原因很快结束了。多年后,当知青好友江南下在来信中回忆起这一切,“他脸上肌肉细微地抽动,有时像哭有时像笑”。不过他很快将“最深的遗憾和痛苦又埋入心底”。但这种“埋入”不是坚忍而是否定,是以日常生活的合理性来否定少年的“梦”。小说里这样写道:“所有这一切他必须去解决,解决了,也没有什么乐趣,没解决就更烦人……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他没有因此感到人生的偶然性与荒谬性。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被妻子的小脾气和生活的艰难弄得十分窝囊,在内心深处“深藏着一份类似遗憾的痛苦,不可言传的下意识的忧郁”,但他常常又很快遗忘了这些。日常生活迅速地改变了他,就在接到江南下的信的这一天,印家厚又因偶然原因失掉了他和妻子一直盼望着的厂里的一等奖,孩子在幼儿园被关了禁闭,烦心事一桩接一桩,可一回到家,“摔掉挎包,踢掉鞋子,倒在床上。老婆递过一杯温开水,往他脸上扔了一条湿毛巾。他深深吸吮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久久不动。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一刻?……此前,花前月下的爱情,精神上微妙的沟通等等远离了这个饥饿困顿的人。”连生命的荒诞感都被日常生活的烦恼和欢乐冲淡了。印家厚当然就不可能再去反思人生了,更别说什么先行到死的先行决心,现代人就这样平常而自得其乐地活着,时间变成了一件可供消费的物质。时间就失去了其时间性,即一种包含了过去和未来的对时间的整体性领悟,一种把生命中的每一刻都作为整个生命来对待的生存姿态。
既然死亡随时都在我们身边,甚至说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能不向它要求全部的生存意义?怎么能不以一种至诚至爱的态度筹划每一分每一秒?当然,我认为海德格尔所说的筹划,并不是常人所理解的计划、谋划,而指一种对生存的本真的、源始的领悟,一种因了本真的领悟而有的存在的态度。这种态度既不是古人所言的“人生如梦”的虚无态度,也不是如赵胜天、李小兰、印家厚似的平常心态。这些都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的生存领悟。因为“人生如梦”的消极态度还是将死亡当成了割断时间的外在事件。而对于个体生命来说,生死同在,每一刻都是永恒,生命的价值就在这每一刻之中,没有一个无限量的时间。古人是在时间无限的观念里追求永恒,他们当然找不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赵胜天所谓的平常心态即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心态。如前所说,这种观念将时间平均化为无差别的每一年、每一月,甚至每一分、每一秒,然后将它们当成物品一样慢慢享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思想,就是要揭橥这种被遮蔽的生活。在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叙述者赞美的就是这种无所选择的,认同一切现实存在的生命态度。小说中的”冷”“热”当然是有所寓意的,不完全指自然现象,而是指人们的生活环境。对生活中迎面而来的一切都失去选择的意志,人的自由又表现在哪里呢?池莉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不会依据自由意志选择生活,而且常常主动迎合现实。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你以为你是谁》中的宜欣。印家厚似乎有点无奈,宜欣就显得很有“远见”,她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离开她深爱的陆武桥,与德国男友结婚。她的说法是“这与爱情没有关系”。是的,她的决定确实与爱情无关,而全是因为生活。池莉轻描淡写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如何失去了情感的乌托邦,完全退回到现实的理智之中时那种自欺欺人的生活态度。如果我们还相信爱情的非现实意义,又因为现实的逼迫不得不与之诀别,那什么时候才能谈谈爱情呢?宜欣似乎还有另一辈子可以分配给爱情,她对时间存在一种永恒的幻想,至少死亡的意义没有进入她的当下生活。“与……无关”是池莉小说中的人物做出太现实的决定时找到的共同借口。实质上,与他们无关的是永恒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一种可以沟通当下与过去以及将来的东西,而有关的全是公共化的要求,即对世俗的认同。这种公共化的要求让人们按照公共的时间生活,一起过有滋有味的日子,一起出国,一起忍受寒冷,一起感受酷暑,一起在日常生活中烦忙。他们承载着池莉八、九十年代小说中的生命观念和她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和审视。
注 释
①⑥孙利天:《死亡意识》,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③肖百容:《直面与超越——20世纪中国文学死亡主题研究》,岳麓书社2007年版。
④⑦[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⑤孙正聿:《超越意识》,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