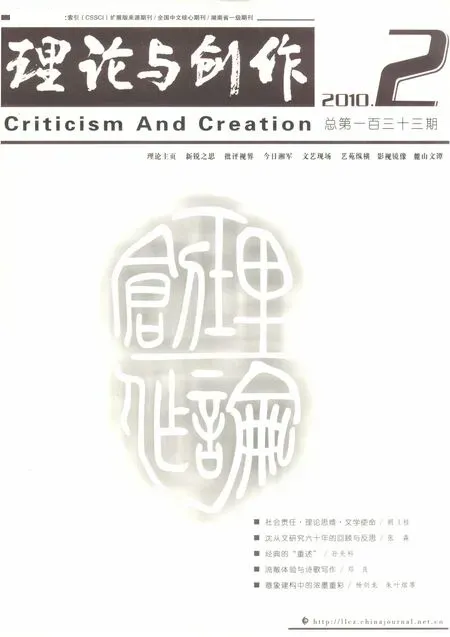意象建构中的浓墨重彩——重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
2010-11-25杨剑龙朱叶熔陈鲁芳
■ 杨剑龙 朱叶熔 陈鲁芳 赵 磊 张 欣
杨剑龙:文学需要经典。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回首新时期文学走过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使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莫言作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我们研究其作品就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诚然,张艺谋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使莫言迅速走红,但是他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因其与众不同的风格而成为新时期文学史的经典。莫言的代表作《透明的红萝卜》故事情节虽然很普通但不乏耐人寻味之处,下面我们以讨论的方式来发掘这篇作品独特的价值。
一、儿童视角下的人物形象
陈鲁芳:《透明的红萝卜》是按照两条线索展开叙述的,一条是外在的故事发展线索,即小石匠和菊子姑娘的朦胧感情发展,另一条是内在的线索,即主人公黑孩的心灵世界的发展变化。作品从黑孩这个儿童视角中去探讨和揭示那些通常被成年人视角所忽略的、孩子心中的黑暗和苦涩,探讨关于生命意志的问题。黑孩缺少家庭的关爱,又经常被人们所欺负。他的生命意志是顽强的,活着是他的本能,对于一切生存的机会他都牢牢把握。他看上去瘦弱不堪,他是卑微的一个小生命,却也有自己的尊严和坚韧。黑孩是一个原始而朴素的形象,莫言在他身上注入了自己的满腔热血,莫言曾说过,黑孩与他在心灵上是相通的。从小缺少关爱的莫言,在匮乏的物质生活中,童年的生活让他感到黯淡,于是在想象中倾入了更多的感觉和幻觉,这可能也是他对于黑暗的挣扎,是心灵的抗争。有时候童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童年的一切感受,都会在他成年后更加明晰起来。我们可能会遗忘最近的事情,遗忘掉很多细节,但是,发生在很久之前的童年往事,却是深深植入你的心灵,这可能构成一个作家写作的风骨与灵魂。此外,故乡也是莫言写作的源头,他对故乡的情感是爱恨交织的,他自己在故乡的经历常常进入小说中。他十三岁时曾经给桥梁工地当过小工,给一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生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黑孩的饥饿和悲苦是十三岁莫言心灵的写照。
赵 磊:《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是饱受虐待、异常沉默的孩子,同时他又有着非常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莫言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视角来讲述故事,首先是因为在小说里融入了其童年时的生活体验。莫言经常提到自己在童年时悲惨的经历,曾经说“我所以写作,不过是为了传达一个怕挨饿的孩子,对过好日子的渴盼”,那么他只有通过一个和他经历相似的孩子的眼睛和思想,才能把他的那些感受真实地再现出来。从小说的创作过程来看,莫言由一个梦获得了“透明的红萝卜”这个美丽奇特的意象,萌发了一种感受,这个意象不断膨胀、感受渐渐发酵,莫言结合自己童年的生活经历,又用想像弥补了那些生活中不足的部分,最终写成了这样一部小说。这样的创作过程是由内向外的,首先是作者的心灵受到了触动,在这种触动的驱使下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发挥想象,与那种由外向内的创作方法相比,这种构思方式更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他的写作对当代小说由过分观念性结构所形成的文体模式是一次冲击。莫言的小说总包含有对生命力的体现和渲染,这一点可能在他的“红高粱系列“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但是在《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有人把沈从文和莫言的小说放在一起比较,说沈从文是把人性纯化了,而莫言是把人性强化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张 欣:“黑孩”是家庭暴力、成人暴力的受害者,父亲的出走、后娘的虐待、饥饿的折磨、成人的欺凌,让原本“说起话来就像竹筒里晃豌豆,咯崩咯崩脆”的孩子,“话越来越少,动不动就像尊小石像一样发呆”。黑孩的言说功能因压抑而退化的同时,他的视、听、触觉感官却异常发达,黑孩以沉默拒绝成人世界的同时,他向大自然敞开了心扉,他凭借发达的感官和丰富的想象,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童话世界。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完全可以把这部小说看作是儿童文学的一种,或者说是一种变形的儿童文学作品,这种变形具体表现在黑孩眼中的美好的童话世界总是遭受成人世界的野蛮践踏,总是被成人世界的各种丑陋人性所毁灭。每当“黑孩”迷醉在童话世界中时,总会被来自成人世界的尖利刺耳的话语所惊醒。童话世界和成人世界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不停地交替出现和对抗,这种充满冲突的儿童文学是充满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但是在与命运的不幸和残酷的成人世界抗争过程中,却又真切地让读者感受到生命力的顽强、生命意识的张力,这与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提到的“酒神精神”,那种高昂的生命意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常常流行这样一句看似矛盾的话“痛并快乐着”,在痛苦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欢乐,只有经历过挫折打击的人才会更加珍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光。童年叙事和儿童视角在莫言小说创作中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除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之外,《枯河》、《红高粱》、《第四十一炮》等作品中,也都有明显的童年叙事和儿童视角存在。
朱叶熔:我们发现这篇小说的三个支点是黑孩、自然和记忆,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先说说黑孩这个形象,他是饥饿的载体,头很大、脖子很长,皮肤里嵌满了黑黝黝的煤渣,身子看似羸弱不堪却又异常敏捷和顽强。这个形象饱蘸着作者深藏的情感,黑孩的故事中有着当年作者的影子。莫言在1993年第2期《当代作家评论》上的《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一文里曾提到了这一点。另据发表在2003年4月19日“网易文化自助餐·读书论坛”上的叶开的《莫言:在高密东北乡上空飞翔——莫言传》记载,莫言小时候曾有过因为偷别人地里的萝卜填肚子而被批斗的经历,这给他留下了一个无法褪去的伤疤,也使他自此而善于以饥饿的种种表现来展现人间的苦难和抒发对不幸命运的同情。黑孩默默承受着没有父爱和母爱的残酷生活,他的父亲离家出走,被丈夫抛弃的贫穷的后母常常毒打黑孩,于是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亲情的丧失和沦落。作者如此描写和他的童年记忆有关,莫言1956年出生,1958年遇上了大跃进,紧接着文革,作为中农的莫言一家始终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莫言的父亲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就发泄在亲人身上。据1993年第8期《作家》中的一文《与莫言一席谈》记载,莫言说:“我确实没有感到人间有什么爱。我始终认为,家庭对任何孩子来讲,绝对是种痛苦,父爱和母爱非常有限度。所谓父爱、母爱,只有在温饱之余才能够发挥。一旦政治、经济渗入家庭,父爱和母爱就脆弱得犹如一张薄纸,一捅就破。”该小说以文革为背景,黑孩承受着更多的世态炎凉。公社干部刘副主任对黑孩的态度可以说明黑孩当时的社会处境,他是人们眼中可有可无的人,如果黑孩活着就把他当成一个干活的机器,死了也不会掉一滴眼泪,反而认为这是一件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事情。人们以一种看客的心态议论甚至嘲笑他,虽然偶尔也会表现出一丝怜悯,但更多时候仅把他作为无聊时候解闷的素材。黑孩没日没夜卖命地给铁匠炉拉风闸,却还要常常忍受小铁匠的无理打骂,听从于他的无理要求。面对生活的不幸,黑孩没有用激烈反抗来回应,而是用沉默和儿童特有的乐观天性来将所有的苦难咽下。
杨剑龙:儿童视角的叙事往往显得更为真实,也常常充满着奇幻色彩,儿童可以驰骋想象甚至幻想,使作品充满着浪漫色彩。就连鲁迅的《故乡》由于有了少年闰土的出场,使这篇压抑的悲苦的作品有了亮色。
朱叶熔:莫言从儿童视角来表现黑孩超常的心灵感应能力,这使得看似不足为奇的儿童视角兼具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质——用一种非常态的审视眼光去观察世界。于是,世界充满了不断变幻的色彩、光线和图象,从而又进一步使人感到黑孩心中难以抵御的忧郁和孤寂。他承受的精神压力和体力完全可以压垮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然而他没有倒下,其幼小而又惊人的生命耐抗性简直令人怀疑他是一个刀枪不入的石头里蹦出来的小孩。为什么他能坚强地活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拥有的这个美丽的梦幻世界使他超越了恐惧、忧虑和肉体的被摧残。
杨剑龙:从莫言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童年和故乡记忆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曾经有论文很细致地谈作家、艺术家的童年与创作的关系,其中谈到了莎士比亚和达芬奇。我们也可以从国内很多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他们深刻的童年记忆,比如冰心童年记忆中的大海,沈从文童年记忆中乡土的杀戮,这些对作家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也构成了他们后来创作的基本情感基调,甚至形成了他们的叙事方式。莫言的故乡——高密乡也是他创作的基本素材。
二、“透明的红萝卜”意象分析
赵 磊:《透明的红萝卜》这部小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写实作品,它包含了想象的成分,充满了一种梦幻的色彩。它写于1985年,这一时期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中国,中国小说界的创新意识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莫言在创作过程中也进行了艺术上的实验和尝试,我们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他很明显地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透明的红萝卜”是小男孩希望和梦想的象征,承载了他寻找精神家园、渴望关爱直至希望破灭的心理流动过程。而作为主人公的黑孩,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特点,也代表了底层人们承受生存困境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对生活依然抱有的期待和向往。莫言对象征、变形、通感的灵活运用和感官化的叙事,使这部小说没有像“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那样粗糙直露,莫言的小说突破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给我们以无穷的遐思空间和审美可能性。就像“透明的红萝卜”这个意象,它具体的象征意义到底是什么?小说结尾的处理方式蕴含了什么样的寓意?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这就是莫言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莫言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的表现技巧的同时,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中。他和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一样,站在乡土文化的立场上表现人性丰富的内涵,发现其中蕴含的强大的生命力。从莫言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底层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民族品格。
杨剑龙:魔幻现实主义传入中国后,新时期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受到了一定影响,很多作品都从“我爸爸”、“我祖父”、“我奶奶”等长辈的角度开始叙事。不仅如此,从某种角度上说也影响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比如常常会出现像《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韩少功《爸爸爸》里面的丙崽等弱智形象。这与“五四”时期的小说有些类似,“五四”时期作家们也塑造了很多疯子形象,例如鲁迅、丁玲笔下的人物。新时期弱智形象的出现或许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它的背后有什么文化的、文学的和社会政治的缘由?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文学手段、文学形式去塑造这些弱智形象?这些论题值得我们研究。
陈鲁芳:莫言是个善于写感觉的作家,他把感觉看的很高。他用感觉的语言来宣泄一些自我感受,用一些奇异变幻的感觉描写,来表达一些深层的含义。在《透明的红萝卜》里,黑孩是个内心十分敏感的可怜孩子,他孤苦伶仃,渴望温暖,渴望关爱,莫言没有直接写他对于爱和关怀的渴望,反而有些地方还写到黑孩对于关心有些反叛和潜意识的逃离。当他看到了那个泛着金光的红萝卜的时候,红萝卜象征了爱、希望、温暖和对美的追求,象征了理想的精神家园,甚至象征黑孩自己。他外表看上去和红萝卜一样执拗而且固执,但内心却剔透;看上去是傻傻的,但其实看得很准,感觉也是十分灵敏。
张 欣: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可以理解为一个缺少家庭关爱和温暖的十岁小男孩内心深处的“恋母情结”的象征。黑孩从小失去母亲,后母根本不关心他,对他非打即骂,只有遇到了筑坝工地上的菊子姑娘以后,黑孩才第一次被一个女性像母亲和姐姐一样的温暖所关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早就指出这种“恋母情结”在男性成长过程中的普遍性和重大意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黑孩要小心翼翼地珍藏菊子姑娘给他包扎伤口的手绢,为什么他要咬阻止他去铁匠炉帮忙的菊子姑娘一口,为什么他会对菊子姑娘亲手洗过的红萝卜发生幻想,当小铁匠与小石匠打起来时为什么他不去帮表面看起来对他友善的小石匠,而是去帮助对他十分粗暴的小铁匠,为什么黑孩喜欢坐在菊子砸石子的座位上,为什么他在黄麻地无意中看到小石匠和菊子姑娘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猛烈冲击着他”,为什么当他看到有“一片黄麻倒地,像有人打过滚”时,他会用手擦擦眼睛抽泣一声。深层原因就在于黑孩对菊子姑娘的感情是一种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他不愿意让任何人夺走和占有他的“母亲”,所以才会有上述看似奇怪的举动。
朱叶熔:《透明的红萝卜》呈现出一种朦胧形态,莫言将现实因素与非现实因素融合在一起,运用类似白描的手法将那些作为心灵对应物的景物勾勒出来,故意拉大象征体和象征义之间的距离,设置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意象,也导致了小说主题指向性的模糊,这与过去所倡导和理解的“清清楚楚,爱憎分明”的小说截然不同。如果用通常的主题分析和概括方法,在这里恐怕会受到阻碍。“透明的红萝卜”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有人说,这象征了一种美,一种精神的亮色,与黑孩周围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并否定着周围的世界,但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代表一种不易察觉、转瞬即逝的希望,一种用来逃避现实的精神寄托,超脱尘世的终极幸福等等,不一而足。小说多义性的原因一是由于作者根据梦境来构思作品,梦本身是朦胧模糊的,这对于依梦而成的作品来说会有一定的影响,作者从一种意象开始,其余情节都由此发出来的思维方式,被一些评论家称为“内省式思维方式”。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作品中纯化生命感受的需要。
三、语言特色:浓墨重彩的民间语言
陈鲁芳:《透明的红萝卜》里的语言来自民间,并且是色彩化了的。民间语言是滔滔不绝、生动而有乡土气息的,通常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说出来的话可能是最简单的,但是活灵活现的。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他们所说的话根本不真实,但你听的时候却沉湎于其中,莫言称之为“一场听觉的盛宴”。他写《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些人对黑孩的嘲笑、队长的话语,写他对黑孩的呵斥和辱骂,最真实地还原了他们本身所应有的特色。莫言任意搭配着这些语言,夹杂着大量的方言俚语或是城市里的流行话语,用这样一种状态来深刻地表达出他内心的痛苦和纷扰。色彩的运用则使得他所要描绘的感觉和意象诗意地表达了出来,文章里常常有一些色块和明丽的色调,他用这些单纯绚丽的色彩夸张地抒发自己的感觉和体验。有人说,哪里寂静一片,哪里就渗透着莫言的感觉。莫言多次写到哑巴或者近乎于哑巴的孩子,如《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枯河》中的小虎等。正如莫言自己的名字一样,他提醒自己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但很多时候他是不得不说的。他通过其他的灵敏感觉来传达,用手势和眼神来表达感情,因此反而更加生动和丰富。他通过个人感觉的传递而将听觉功能转换成视觉或其他感觉,最典型的例子是《透明的红萝卜》里黑孩的眼睛。尤其是最后队长对他的盘问,他先是“迷惘的眼睛里满是泪水”,然后“清澈如水”,又“满是惊恐”,最后“两行泪水从黑孩眼里流出来”,这些是如此生动,让人读了觉得有一种永远的痛,最单纯的眼睛触痛了读者的心灵。
朱叶熔:莫言全然不顾艺术的成规旧律,用一支神奇的笔描绘着自己记忆和想象中那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北方土地,他的小说如歌如画,他试图动用人类的一切感官资源,例如视觉、听觉、触觉来诠释某种复杂的思想和体验,就像一个怀着六弦琴的行吟歌者,用自然的灵气和生命的骚动弹拨出一个色彩与音符交织的梦境。他对感觉的理解与苏珊·朗格有相似之处,即把感觉视为生命力、生命体验的最高形式。苏珊·朗格认为,人类语言是推动形式的符号,而人类内在生命形式即情感活动则永远在难以捉摸地运动着,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相互容纳、相互沟通,形成一种无序的状态。对于再现和表达复杂的生命感受语言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包括绘画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绘画用色彩和形状来表现思想。莫言则试图将绘画的作用发挥在小说中,他多次运用了醒目色彩的词语,例如小石匠火红色的运动衫、菊子姑娘紫红色的方头巾、小铁匠右眼上鸭蛋皮色的疤、白里透着绿的钢錾、金色的红萝卜……寓意无穷的颜色给人遐想的空间更大,当斑斓的颜色代替了描述性的语言时候,文本的内涵也变得无限起来。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着重描写的是上海的都市生活,表达东方大都会的城与人的神韵。莫言的小说虽然也可称之为新感觉小说,但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有很大不同。他的小说时常和故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透明的红萝卜》就是一个例子。作品里浓郁的乡村气息不仅体现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上,还体现在小说语言上,它和民间口语一脉相承,是从农民的嘴巴里挖出来经过锤炼的语言,夸张,流动,充满乡土味。小说中的比喻也令人回味,喻体都是农民们常见的事物,例如把柳叶比成蜻蜓,把拍巴掌的声音比喻成摔死青蛙的声音,老铁匠的鼻子比喻成熟透的山楂,小铁匠右眼的伤疤比喻成“萝卜花”等等,不仅贴近生活,而且也为文章增添了不少趣味和活力。
杨剑龙:从某种角度上说,莫言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的风格,他那种通感式的叙事手法、语言表达方式和新感觉派相似。然而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感觉派作家大多描写城市人生,展示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心态,而莫言的作品则大部分讲述的是乡村故事。莫言的小说语言俗中透出华丽,质朴中闪烁着亮丽的色彩。在这一点上,张艺谋和莫言是一拍即合的,张艺谋也是追求大红大紫的绚丽色彩,不知是莫言影响了张艺谋,还是张艺谋影响了莫言,总之电影《红高粱》中华丽的色彩衬托了影片的基调,也充分反映了莫言创作的色彩感。我们讨论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实际上是以它为切入点,回溯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说在形式和语言上所具有的创新趋势。莫言的视角不是封闭的,他用开放的眼光借鉴和汲取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养料,故其作品是世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同时具有民族性,它始终扎根于故乡,关注故乡,聚焦民族精神。莫言的成功印证了鲁迅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他通过故乡高密构建了自己心目中的乡土世界,这构成了他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