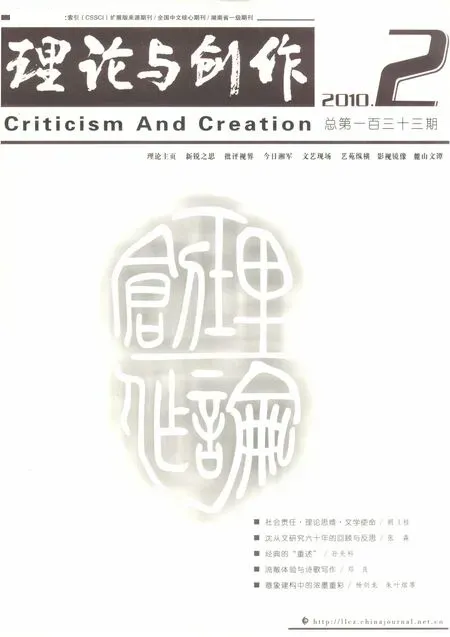革命体验与红色书写❋——论建国初期“十七年”作家的创作特质
2010-11-25龚奎林
■ 龚奎林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不仅是一种认识的差异,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和政治分野的象征,这就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命名谱系、话语原则与文化资本。因为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民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急需精神文化的辅助,因此,唯有借助新文化建构才能把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和信仰价值观进行普适性传播,以鼓舞新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许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战争的参与者,积蓄了大量的战争素材。当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战争经历和稳定的和平环境使他们渴望通过小说创作把昨日战争的艰难和今日和平的来之不易以及革命意义诉求表达出来。于是,革命战争文艺应运而生,成为一种社会主义文化资本,进而确证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合法性、有效性与优越性。而这些文艺工作者都是从战火中走来的年轻的老革命,不仅具有革命知识分子化的政治党性,更具有少共精神、军人规范、侠客梦和青年气质的特质,这种身份使他们完成了革命起源和革命意义的经典化文化资本的生产,其主体建构也就具有了如下特质:
第一,乡村政治的迁徙和少共精神的改造。现代文学名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田汉、张爱玲、张恨水等大都经历过传统私塾教育和新兴高等教育,从地域上来说很多来自江苏、浙江、四川、北京等经济文化发达之地,这些地方本身就是新文化起源的地方,而且他们的家庭财富颇为殷实(当然有不少贫寒之子通过自强不息而进入上层知识分子群体中),在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诗教传家的文化传承下,都具有高学历或者海外留学背景,因此,他们的知识背景、阅历视野、人文素养、思想人格等方面都已经形成独立的传统,自然,他们在文学创作或创造成熟的时候大都远离乡土进入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都市或者海外,这使得他们的创作视野和写作技巧方法都先胜一筹。而“十七年”作家大都来自与革命的发生地非常密切且颇为贫穷的农村,朱毛井冈山会师之后转移到江西赣南、福建闽西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随后长征经过贵州等地到达陕西,国共合作抗日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联军等大都在华北如山西、河北、内蒙古、河南和东北等省以及安徽苏北等地;而解放战争的几大战役又大都在东北、华北、陕西等地开始,这些地方都是最为“乡土”的地方,费孝通曾经以“乡土中国”作为研究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历史框架,他认为乡土中国带有极大的封闭性和自足性,并由此带来了中国乡村文化鲜明的特色:“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①“十七年”作家恰恰大都来自这种古老的不流动的乡土中国,极少数经历过私塾教育和高等教育,海外留学和国内读完大学的非常少,大学肄业的也不多,而且多是农村贫寒之子,家穷无法读书,兵荒马乱之中也无以为生。因此,当革命潮流一旦汹涌潮起,这些年龄小的年轻人在阶级观念的导引和革命战争的裹挟之下离开家乡、走上前线、奔走全国,即使是城市青年,也开始乡村化改造,把自己的一切都上交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说,每个个体有自己的局限和困境,特别是面对生存的偶然、荒谬、脆弱与无妄之灾时,个体往往将自己置身于群体之中,以获取群体价值、意义与勇气,进而面对生死逆境。这些参加革命军队的个体进入群体之后自然获得了群体的力量支撑。由于他们很多是农村无产者,走投无路之际与财富拥有者阶层也就有了对立的一面,当这种对立无法和解的时候,那么,革命是这些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本能反应。因此,从省籍来说,与那些在文化传统浓郁省份走出来的现代文学作家完全不一样,“十七年”作家都是在以上各省的革命洪流中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组织并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游离于传统的都市空间和乡村空间,在战场空间中去经历恐惧、死亡,把自己献给了革命的战火。经过考察,可以发现长篇战争小说作家基本上都是十八九岁成为了共产党员,而到了解放后他们虽然大都是老革命,但年龄却并不大,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年轻心灵上,充满了改造人类和世界的勇气与决心,形成了为民请命的少共精神,因此,围绕中国革命历史的的文学叙述和艺术想象自然就是一种少共精神的青春想象。
由于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少共,也就具有了党性的恒定性。冯雪峰曾对党性进行了界定,认为党性“是宇宙观的最高表现,也是人民性、阶级性和革命实践性的最高的集中表现”②。这种党性就赋予了作家的功能是通过文艺叙事培养民众的“工农兵”本质和话语主体性的言说权力,使外在于民众的某种意识、文化和国家话语主体的观念积淀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并在他们头脑中成为某种习俗和无意识,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我们可以用如下几个术语概括他们的等价职能:文艺工作者/革命知识分子/灵魂工程师/知道分子/布道者,而且这种价值符号系统和身份识别话语系统也走入日常生活和文本世界中,任何人都受此管辖。同时,这种政治党性可通过作家的重新命名来管中窥豹。在现代文学中,绝大部分作家为了呈现与传统封建关系的决绝,都是笔名或者改名创作,以致读者对其笔名的知晓度远远大于对其真名的认知程度,如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皆是如此。而在“十七年”时期,依然有很多作家通过笔名或者改名进行创作,尽管有的改名是他们在经历了残酷战争之后对敌斗争中保存自己的一种策略,但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新生,既是与封建关系的决绝,更是与过去的决裂,隐喻着作家找到共产党后在政治各层面的新的追求,其新名更加昂扬、光明、激越。如《东线》的作者寒风原名李运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潮。年仅19岁的李运平决心投身疆场,改名寒风,以此表达坚强决绝的抗日志向,不仅参加战斗,而且写了很多作品,陈赓大将曾高度评价他:“要了解我们二野的战史吗?看寒风的作品吧,他都写了。”许多作家都是普通的工农兵,他们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慢慢成长为坚强革命战士和人民作家的,他们感受到一种“阶级”的温暖,因此通过改名来确立和证明自己的志趣与追求,表白自己的革命向往,从而建立新的革命目标认同,这种认同往往又是与政治认同相一致,因而新的命名也就具有了可阐释的空间。例如孙犁原名孙树勋,抗战初期,革命干部盛行改名,孙树勋希望自己要像牛犁地一样在文学中默默耕耘,为革命添砖加瓦,于是改名孙犁。孙犁的朋友张学新就曾经对孙犁的笔名进行探究,认为:“犁,耕具,耕犁用牛。像老牛耕田一样,他意识到文学事业也是一种艰苦的劳作。人们知道有个孙犁,谁也不管他原来的名字了。”③所以,从旧名字到新名的确立,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经过革命和战争历练之后的成长过程。白刃是王寄生的笔名,1940年八路军攻打山东白彦,战斗异常惨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肉搏战,让随军记者王寄生深受感动。随即他在《时事通讯》上发表了以此为素材的通讯《在观察所》,因为在白彦这地方,又是白刃战,为了纪念那场激战以及英勇献身的战友,就署名叫“白刃”。这名字在战报上迅速传开,而本名却逐渐淡出了受众视野。
第二,兵作家的军人规范和学养资源。“十七年”作家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写作训练和知识储备教育,只是在革命战争的集体生活中逐渐学会了识字和一般文化,极少数人接受过良好的中学、大学教育。但是他们大都是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亲历者,真人真事和亲身经历是这个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源泉。杜鹏程在解放战争中曾作为随军记者,深入连队底层,亲历了延安保卫战以及西北战场上其他重大战役,从而为《保卫延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说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解放战争初期曾亲自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牡丹江地区的林海雪原进行剿匪,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斗争,才歼灭了顽匪,这是作家创作的重要生活基础;刘知侠与鲁南地区的铁道游击队曾一起战斗、生活过,下笔也就更加有声有色;而当过军区文化部长的吴强写出了《红日》;有着地下党斗争经验的李英儒写出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贾政率领的敌后武工队,神出鬼没,敌军无不闻之丧胆,作者冯志本人就是抗战时期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小队长,当年曾屡立战功,小说中的人物多以他自己的战友为原型。可以说,他们的人生经历都是在革命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走向革命的成长的,成为兵作家的军人同时又是军队体制规范的执行者,他们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文艺工作者,大部分作家都是军队的战斗员、宣传队员、文工团员以及随军记者,这种短促、紧张的战争状态只能要求他们创作一些短小、生动、活泼和有鼓动性、宣传性甚至煽动性或对敌人讽刺性的文学艺术如歌曲、快板、评书等。如赵树理在谈到他的职业转换时就说:“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是作农村宣传的,后来作了职业的写作者只能说是‘转业’。从作这种工作中来的作者,往往要求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而且要求速效。”④因此,他们的学养资源只能在艰苦战争中通过马列理论、上级文件、鼓动性宣传文字材料、革命具体实践以及通过故事性非常强的战斗故事作品如战争小说或话剧等尤其苏联文学自学而来的,这种政治导向型和鼓动实用性特点注定了他们的学习或创作都是从简单开始,而且注定了其实用性、战斗性和鼓动性的特点。正如王愿坚在1978年7月参加“当代文学”学术讨论会筹备会议所说:“我们这一茬子人,大体经历是共同的,开步走的情况也大体是相同的。我是宣传队员、文工队员、记者;杜鹏程当过记者、文书等;王汶石很长时间是文工团员;茹志娟也是文工团员。都不外是宣传员、记者等,这种经历势必使他们和战争生活结合起来,亲身参与这生活,在这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工作,就必然接触那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⑤所以,这些作家自身的人生体验和革命成长记忆与文学叙述中的革命者成长产生了重构,吴强、刘知侠、杜鹏程、曲波、徐光耀等战争小说作家都是经历了革命战火洗礼的兼具革命文艺工作者与革命战士于一身的革命战争亲历者,当年那种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生活以及奋勇抗敌、转战疆场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他们独具特色的人生记忆,也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具有天然优势的文学素材和创作资源。在战争年代战士与作家的这两种职业的互动强化了他们的革命经历和为革命服务的体制化反映,这样就促使这些作者在时过境迁的创作中优先考虑文艺鼓动的宣传作用,因而在素材处理、人物塑造等方面不自觉的向优秀革命者典型形象靠拢,许多作品也都具有生动的故事、曲折的情节、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革命形象。
同时,他们也学习苏联文学的创作技巧,其阅读视野也是苏维埃化。例如《日日夜夜》等苏联小说曾作为解放前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战争必读书目,而《铁流》等小说又成为这些半文人性质的革命者的阅读来源。所以周扬1952年就认为:“现在苏联的文学、艺术和电影已经不只是作为中国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学习的范例,而且是作为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广大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中国人民新的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内容了。苏联的作品,如《铁流》、《毁灭》、《士敏土》、《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俄罗斯人》、《前线》等,早已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习。苏联的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苏联人民的高尚典型,已经不仅被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所热爱,而且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了。保尔·柯察金、丹娘、马特洛索夫和奥列格已经成为我国无数青年的表率。”⑥这也就是说,很多以苏联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主题的战争作品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流传,除周扬所说的作品外,其它还有《保卫察里津》、《夏伯阳》、《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恐惧与无畏》、《团的儿子》、《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优秀战争小说经典,苏联的这些小说在人性的悲剧层面往往独树一帜,它们积极对战争进行反思,正视战争对人性的价值剥夺与残酷毁灭,对人的命运、灵魂和日常生活及其合理欲望进行探索。应该说,一直以苏联文学为圭臬的新中国作家尽力向苏联文学学习,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塑造技巧方面和故事的胜利结局方面,但同时有意忽视苏联卫国战争小说中战争对人性的毁灭以及面临战争的恐惧的积极反思,忽视苏联文学的独立价值取向。所以,他们学养资源有点先天不足和后天不足,这也注定了“十七年”文学具有概念化和呆板化等缺陷。
第三,作家的侠客梦。对于知识分子或作家而言,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启蒙情怀和拯救天下苍生的英雄情结总是搅荡着自己的心灵,尽管“文人士大夫”情结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儒教传统影响下的最梦寐以求的目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们夺取功名之前的志向,但一旦金榜其名,行政权力机构的潜规则以及其它各种因素又改造着这些知识分子,公权力与政治公信力开始无效,他们的原有志向由此灰飞湮灭。事实上,如上所述,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侠义的情怀。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很多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处满足,而不得不求助于文学虚构中的愿望实现,人永远向往英雄梦想,当自己没有经历的时候可以幻想,当自己经历那种传奇色彩的战争的时候,英雄梦想就成为自己进行文学创作的一种原动力,而这种原动力又契合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
1950年8月1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第2卷第4期登载了读者徐康的来信,他认为应该多写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因为“革命战争的英勇史迹和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对于一切工作岗位的人们都有莫大的教育意义”。这其实就向作家提出了读者的要求。因为读者也具有侠客梦式的英雄崇拜情结,战争小说一方面具有真实性,另一方面具有英雄性,故能够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攻击性、嗜血性和阅读快感,对人类潜存的欲望进行替代性补偿。因此,平民对于英雄的期待与仰慕,满足了人们对未经历过的心理补偿以及当下生活的精神超越。《林海雪原》中“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土匪黑话满足了读者的心理欲望需求,而铁道游击队的江湖好汉和兄弟义气的风格使民众为之钦羡,他们深入敌穴,短兵相接,出奇制胜,其传奇性战斗事迹和侠义豪爽的个人风格更是让读者兴奋不已。可以说,通俗易懂的战争小说一直是读者对文艺工作者的革命诉求。
第四,创作者的青年气质和故事讲述的教育功能。战争创伤赋予了这些青年战士作家一种英雄情结,因此,激情、豪迈、刚强成为这群经历战火烽烟的青年人的革命气质。同时,对死亡的战友的悲痛、感伤又成为他们刚中有柔的青年气质。因此,青春的记忆与抒情在革命中获得同质化的建构,从而建构起革命的新青年。所以,这些长篇战争小说可以说是作家的回忆性创作,具有对战友的缅怀情结和思念补偿的功能。徐光耀认为:大家在救亡图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光辉理想照耀下,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把流血牺牲当做家常便饭。英雄故事,动人业绩,日日年年,层出不穷,昨天还并肩言笑,挽臂高歌,今儿一颗子弹飞来,便成永诀,这虽司空见惯,却又痛裂肝肠……对先烈的缅怀,久而久之,那些与自己最亲密、最熟悉的死者,便会在心灵中复活,那些黄泉白骨,就又幻化出往日的音容笑貌,勃勃英姿,那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巨大声音,就会呼吼起来,震撼着你的神经,唤醒你的良知,使你彻夜难眠,坐立不安,倘不把他们的精神风采化在纸上,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于是,写作欲望就难于阻止了。”⑦在战争当中,每个人必须面对死亡,这是军人的前提,那么必须“勇猛”“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在战争中看到了很多为了革命战争而牺牲的英雄,他们的英雄故事自然激励或者感染了这些更加敏感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是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励了他们,这些兵作家以战友和自己的行动为故事主题,创造出很多作品,使战争文学发挥了空前的组织、宣传、教育与鼓舞人民和战士的作用,成为军队和人民的武器。所以,军人出身的这些作家自然愿意把自己以及周围的战友的革命英雄事迹进行叙述,而且写作的目的也是十分鲜明明确的。古立高回忆自己文学创作时说:“作品必须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促进并提高部队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斗志,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我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我什么体裁都写,只要它发光,发热,能起战斗作用……我的这些作品,绝不高超;但我忠实地记述了这个伟大军队的部分生活,描绘了一些可敬可爱的指战员的形象。”⑧因此,缅怀激情的浪漫记忆页总是出现在许多革命作家的心理机制中,王燎荧在谈论革命传奇小说时认为:“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常常出现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异常勇敢的人物和异常出奇制胜的行为等等。就是当事人也往往事后吃惊,非在平常的日子里所能想像。这种人和事随即传播开来,听者当作神奇的故事来听,传者当作神奇的故事来传,因而被赋予了传说的性质。”⑨
总之,为了让革命后代牢牢记住打下江山的不易,牢记革命者的鲜血和革命的艰辛,具有独特革命体验和创作特质的“十七年”作家本能地成为新中国话语的维护者和创造者,实践着无产阶级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合法性和天然性功能,通过文化资本向读者种植各种历史记忆。因而,作为一种为革命排忧解难的职业工种的文艺自然就成为一种“历史记录”的方式,因为记录革命、记录战争、记录战争下面的英雄、牺牲者和幸存者就是记录历史,历史是这些革命者创造和改写的。革命战争小说成为革命历史教育的教材,已经替代了正史的意识形态普及功能,成为历史通俗化的传播方式。
注 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②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1952年第17期(9月10日出版)。
③张学新:《孙犁笔名浅识》,《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2期。
④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⑤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关于当代文艺问题的内部讲话》,内部参考材料1979年7月印,第345页。
⑥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⑦徐光耀:《〈小兵张嘎〉是如何写成的》,《文史精华》1994年第1期。
⑧古立高:《永远向着前面·后记》,解放军文艺社1981年4月版,第430-432页。
⑨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