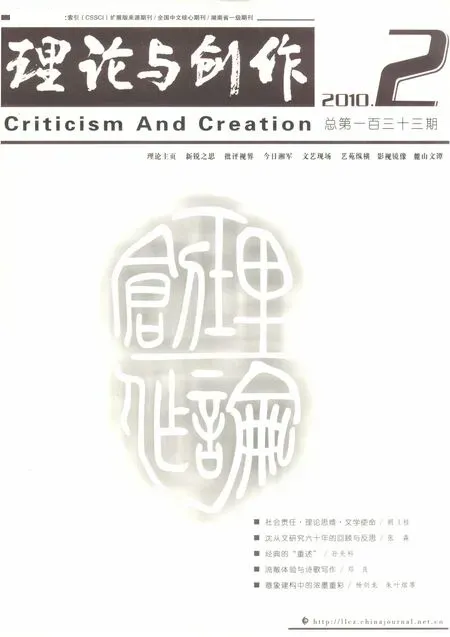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重返八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研究❋
2010-11-25赵黎波
■ 赵黎波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及其研究的清理和反思显然成为了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显然,这个问题已非始于当下,199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研究的升温、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纯文学”概念反思和“底层写作”的兴起等思想文化事件中,一条反思1980年代的知识脉络已经清晰可见。2005年“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命题的提出和实践,更是将这一反思活动全方位整体展开,并上升到方法论高度和文学史反思的层面上来。
“重返八十年代”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它将1980年代搁置在一个开阔的文学场域,“尝试通过将八十年代历史化和知识化,探讨何种力量以何种方式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建构。”①通过对重要作家、批评家的走访,对1980年代重要文学现象、作家作品、重要期刊和文学制度的分析,对核心概念的梳理,试图还原出一个复杂的80年代,从而揭示“80年代文学”及我们今天的文学史是如何“形成”的。探寻80年代知识立场、文学成规、文学史叙述的形成,成为“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学术活动的核心层面。
正是在这个发生学意义的命题上,“重返八十年代”和“十七年文学”产生了紧密联系。正如一位“重返”的研究者所言:“对1980年代文学的反思研究必须建立在对‘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反思研究的前提下进行,只有重新发现‘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的复杂建构才能‘理解’1980年代文学的复杂建构,这之间是一种同构关系。”②如果要从“起源性”的角度谈论“新时期文学”的话,如何面对“当代文学”的“遗产”,如何认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不仅是“八十年代文学”首要面对的问题,同样也是“重返八十年代”面对的重要问题。
一、“十七年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的关联性研究
在“文革”后至今的文学批评中,可能从没有一个时期像80年代批评那样热衷于对行进中的文学进行主题概括和归纳。“人的发现”、“人道主义”、“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民族灵魂的重铸”、“现实主义的复归”、“反封建”等等,不一而举,在新时期之初,这样的总结显然有它独特的意义,就像刘再复所说,“新时期文学是在清除极左血污中开拓自己的道路的,它首先要赢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批评家的发现和呐喊“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文化动力之一”。③但是,这样急不可待的总结和呐喊除了使新时期文学“不惮于前驱”之外,本身还意味着一种姿态、一种心理、一种热切的渴望,那就是急于显示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绩和新的特质,从而将其与之前的文学彻底划清界限。
一切都是在对立中显示出意义,为了发掘、建构新时期文学的“新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者采取的通行策略即是将它和“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区别开来。新时期文学被视为一种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清算、反拨、矫正和超越并向着“文学本身”回归的文学形态。“新时期文学”正是以这种潜在的“进化论”观念来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本质化的“50-70年代文学”,特别是“文革文学”,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和历史价值。这就是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断裂论”,“十七年文学”也因此和“新时期文学”被人为地构成了一种非常紧张对抗的历史关系。
较早关注“50-70年代文学”的洪子诚曾对这种“进化论”色彩的文学观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这种不断划分阶段,不断把每个阶段宣布为‘新的起点’,不断掩盖新的阶段与过去关联”的一清二楚的“断裂”实际上掩盖了文学史的“历史性的关联”(冲突、承继、改造、转化),这显然极大地妨碍了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深入研究。④1990年代末,不断深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也越来越显示出这一阶段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面貌,同时,越来越多的文学史事实也在说明了“新时期文学”和之前文学史阶段的复杂纠葛。
从“起源性”的角度谈论二者的关联性,昭示了“重返八十年代”崭新的问题意识。它不再致力于发掘“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或“现代性”因素,并以此来将之纳入当代文学叙述的整体视野之中。而是探究“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资源如何参与到“新时期文学”的建构中的。
“重返八十年代”的倡导者之一程光炜在这方面做了相当的努力。他通过切入具体的文本和文学现象,清理出了一条80年代文学如何“不断拒绝、重返、清理或挑选‘十七年文学’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新时期文学”在强调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一方面拒绝、批判和排斥前者极左的思想思潮和激进性文学试验;但同时又将“十七年文学”中被压抑的因素吸收、消化和转换到“新时期文学”中来。它建构起来的第一个文学经典——“伤痕文学”,就是直接从“十七年文学”中派生出来的。二者在文学观念、审美选择、主题和题材诉求等问题上,都显现出同构关系。从作家王蒙、张洁、张贤亮等重要作家的题材记忆、写作经验和叙述方式中,也可以细查出十七年中所受的文学教育、接受的文学观念的影响。这表明“十七年”作为一代作家的历史经验和文学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想象与建构过程。“80年代文学”对“十七年文学”的态度也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1985年前后,它日益主动表现出与“十七年”历史剥离的倾向。现代派、文学自主性等新的文学观念的兴起,“十七年”已经成为被刻意“遗忘”的对象,成为附着于政治的“非文学性”文学形态。⑤
伴随着“十七年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的动态关系的,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立场、经典建构、文学观念、文学体制等的不断形成。新时期文学在树立新的文学经典、建立自己的文学成规时,它需要恢复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某些仍未耗尽的活力作为补充,但是它并不是“照单全收”的,而是有着自己的鉴定、甄别、排斥与肯定。⑥“十七年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参与,是通过“改头换面”的形式使自己“合法化”。⑦随着“向内转”、“文学的主体性”、“文化热”、“现代派”等一系列核心概念的提出,“80年代文学”终于逐渐建构起了自己“去政治化”、“回归文学自身”的主流文学史叙述。而这一建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强化“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政治化”和“非文学化”来得以完成的。
当然,在今天,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80年代文学”建构的知识立场和它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是,在当时,这些命题都是作为真理性的不证自明的命题存在的,这种带有“启蒙现代性”特征的文学史叙述作为一种话语霸权对其他文学形态起到了排斥和压抑作用,这在1980年代现实主义的遭遇和先锋文学的经典化中,体现得再也鲜明不过了。
这种关联性的研究使得“重返八十年代”有效地揭示出了“80年代文学”知识立场和文学史叙述的形成。“80年代文学”也是经过复杂的冲突、经过对其他异质性的文学现象的压抑和排斥才建立起来的,从建构方式上来说,它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这种建构不仅掩盖了80年代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本质牢牢地固定在了“政治”这个“文学”的“对立面”上,这两个历史阶段的文化/文学在80年代的历史叙述中被整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学史事实,其复杂的历史面貌在相当长时间内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程光炜的尖锐质疑才是有启发性的:“也许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新时期文学’排斥、替代‘当代文学’的历史性的‘丰功伟绩’和某种‘进化论’的因素,而是1976年以前的‘当代文学’何以被统统抽象为‘非人化’的文学历史?……假如说历史性反省80年代与50至70年代文学的关系,是基于摆脱固有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深度干扰,使其呈现出更为丰富、复杂的研究维度,那么究竟该如何重新识别被80年代所否定、简化的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文学?它们本来有着怎样而不是被80年代意识形态所改写的历史面貌?另外,哪些因素被前者抛弃而实际上被悄悄回收?哪些因素因为‘新时期文学’转型而受到压抑,但它却是通过对历史的‘遗忘’的方式来进行的?”⑧不仅如此,他又提出了“十七年文学”作为“重返八十年代”的参照系的说法,也就是说,只有重回“十七年文学”才能看清楚“80年代文学”和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这不只是对于80年代文学的评价问题,同时还是“80年代文学”的起源性问题的深入。
二、突破80年代“新启蒙”文学史叙述
“断裂论”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述,不能不说和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对“文革”发生原因的一种阐释,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成为了新时期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既然五四“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那么“新时期”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使命就是继续被中断的“启蒙”精神。作为八十年代的“元叙事”⑨,它也主导了80年代文学研究者理解、阐释、叙述“新时期文学”的知识框架和批评立场。通过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搁置,80年代的文学批评在启蒙的层面上将自己的理论资源、价值立场和五四文学接轨,从而形成了以反封建、人性解放和现代化追求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价值观念。在文学范畴内则衍生了一整套与此相关的核心概念、人道主义、主体性、向内转等。“新启蒙”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史叙述和研究显然成为主宰“80年代文学”的评价体系,“80年代的文学史,是以‘新启蒙’为中心的知识分子文学话语方式贯穿始末的”,是“精英文学(或说‘纯文学’)对其他文学样态的‘话语霸权’”。⑩
“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对“新启蒙”文学史叙述话语霸权的颠覆是从解构制约80年代人文知识的“元话语”开始的。李杨认为,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将“启蒙”和“救亡”加以对立,实际上隐含其中的是“现代”和“传统”的对立。这种论述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将50-70年代的历史剔除“现代”之外,把“新时期”理解为启蒙的复活。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李杨认为,“救亡”并不是“启蒙”的对立面,而是“启蒙”这一“现代性”得以生长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在这一意义上,“50-70年代”文学并没有割断“新时期文学”和“五四文学”的联系。11在接下来讨论的有关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系列文章中,12批评者进一步解构了建立在这种“元叙事”基础上的文学史“断裂说”。不仅如此,它还从创作群体、文学建构、批评思维等角度,举出种种例子来揭示“新时期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提出了“没有‘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这种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问题。13
“新启蒙”叙事不仅是一种知识框架,还是对80年代文学研究影响至深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即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它将八十年代理解为逐渐摆脱政治回归自身的文学,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整体本质化为“政治性”的“非文学”,这不仅将“新时期文学”和“50-70年代文学”对立起来,将“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对立起来,同时还派生出了一系列的诸如政治/文学、革命/审美、中/西、传统/现代、文明/愚昧等二元对立结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建立在“整体论”和“本质论”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牺牲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样也简化了“80年代文学”的复杂进程。
“重返”研究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高度本质化的二元对立”。在研究者看来,只有揭示出80年代文学的政治性,才能有效地化解这种二元对立:“如果政治对文学的‘规训与惩罚’指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规定作家如何写和写什么,那么,80年代针对文学的规训同样无处不在。”14通过对“纯文学”、“现代派”、“先锋小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80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的分析,“重返”研究梳理了80年代文学现象的知识谱系,有力地揭示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15
“重返”研究警惕的不仅是八十年代的研究思维方式,而是这种思维方式在90年代以至今天的延续,在他们看来,80年代文学研究的评价系统仍然在制约着文学研究界,这使得很多的反省并没有有效地进行。今天的很多研究者仍然是在八十年代的知识框架来谈论“80年代”、谈论文学。“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就是说,八十年代建立起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化政治的理解框架仍然是八十年代奠定的。”16“一些形成于80年代、未曾被充分意识和反省的思考框架/文化逻辑”仍然“制约着人们指认90年代社会现实的方式”。17
具体到199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我们看到上述的“政治/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很多研究中延续,不少成果仍然在重复着1980年代“新启蒙”语境中产生的研究思路。这种研究大致顺着这样两种思路在延伸,其一是固守80年代的启蒙立场,整体上将“十七年文学”界定为“人”与“自我”的失落,18这种研究,显然是将80年代“主体性”文学作为评价、衡量“十七年文学”的依据和标准,它的非历史性特征非常明显。其二,通过文本细读、资料的重新发现,寻找、放大“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因素,以此来证明它是有价值的。“民间”视角、“潜在写作”概念和思路、“启蒙文学”形态、“个体精神”碎片等等这些研究成果,19极大拓展了“十七年文学”的研究空间,发掘出了“十七年文学”中被压抑的文学形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认知。但是,这种研究,且不论它是否存在着过度阐释的成分,就思维方式上看依然没有走出80年代启蒙文学史叙述的“价值预设”。在这些研究中,“十七年文学”的价值是依附于80年代文学而存在的,因为它同样具有了符合80年代文学趣味和“个体性”、“启蒙性”文学观念。
由此看来,“十七年文学”研究如果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真正将它的复杂面貌、自身特征、文学史意义呈现出来,就必须在研究的方法论上有所更新,尽快扬弃这种产生于80年代但是至今仍制约着我们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重返八十年代”的方法论启示。
三、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整体观”和“历史化”
“重返八十年代”显然有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可以说“80年代文学研究”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面向,一是“作为问题的80年代文学研究”,另一个则是“作为方法的80年代文学研究”。20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论可以归结到两个相辅相成的层面:“整体观”和“历史化”。
在对于“十七年文学”和“80年代文学”的关联性研究中,我们不难体察到“重返八十年代”学术研究的整体性视野和研究观念。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真正的文学史研究实际上已经暗含了整体性的观念,缺乏“整体观”的研究也很难说是一种有效的历史研究。“重返八十年代”的这种整体视野致力于发掘文学史各个阶段的内在联系,有力地解构了文学史叙述的“断裂说”。
这种“整体观”和80年代的那种强调“宏观研究”方法的整体观是有区别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的整体观”在当时用一种新的切入角度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这种“整体观”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当下的文学研究界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研究范式运用的普遍性。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晰地看到这种“整体观”的研究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当代文学各个阶段的“断裂”问题,反而将这种断裂进一步深化。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种“整体观”是有着潜在的价值预设和立场的,这种价值预设使它在进行文学史的整体观照时是有取舍和甄别的,有学者曾戏称为“捡好的拿”。21这种“排斥性”理解问题的方式把历史整体性缩小压瘪,变成了一种狭隘的整体观。22“重返”研究采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通过“重回八十年代”,以整体性的视野把“被‘新时期叙述’强行拆解、撕裂和断开的若干个‘文学期’,在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寻找它们之间的关联点,进而“重建各个文学期和文学现象的‘历史联系’”,23在对“十七年文学”和“80年代文学”关联点的研究中,体现的就是这样的充满包容性和理解性的“整体观”研究思路。
和“整体性”的研究思路并行不悖的,即是将问题放在“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的“历史化”方法。在研究者看来,“始终没有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历史化’,是困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24应该说,将“历史化”这一带有后现代理论色彩的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当代文学研究并非“重返”研究者的首创,90年代末洪子诚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就体现了将“文学历史化”的意识,并认为这“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25这种意识在“重返八十年代”中得到充分彻底的贯彻,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方法论意识形成的前提是对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敏锐体察。“重返”研究者认为,当代文学研究“批评化”倾向和“当下性”特征是其没有充分“历史化”的重要原因。而“批评化”的形成和当代文学对“当下性”的迷恋又是分不开的。不断变化的当下文化语境能够激活已经“沉睡”的文学史问题的同时,也使得文学批评和研究很难摆脱当代文化语境的制约。尤其是在面对已经成为逐渐“经典化”的文学史阶段时,这种过于强烈的当代意识,常常会干扰、阻碍甚至破坏我们对研究对象本身的认知和把握,从而陷入以今律古的迷津。如今不断升温的“十七年文学”、“左翼文学”研究中,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以当下的文化语境来重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这种作家作品“当下化”的问题普遍地存在于左翼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如从民间的、底层的角度将赵树理再次经典化;从个人化、女性主义的立场对丁玲小说的褒贬;将孙犁从革命文学的精神谱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多余人”;对郭小川诗歌中的“不和谐”因素的过分强调等等,这些研究在揭示这些经典作家“另一面”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既定的“经典”性结论的“颠覆”。程光炜通过对孙犁“复活”这一代表性现象的分析,认为,这种研究的“当下性”实际上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需要,把研究对象从“文学史”中“拎”出来以支持“当下”文学的构建。强调孙犁小说的“人性美”、突出他作为革命队伍中的“多余人”形象、高度评价他的晚年写作,这些都是将他从“革命文学”中剥离出来做法。但是,这种根据当下消费文化语境重新“定义”并给予积极评价的做法是否能够更接近于研究对象的真实?对此,程光炜进行了质疑:“与‘革命文学’相‘剥离’也许并不出自孙犁本人的真正意愿……这种‘剥离’,在很大程度仍然只是文学史研究的需要……他们并没有真正‘碰’到历史的关节之处。”26这种研究归根结底依然是80年代形成的“文学性”文学史观念所致。
“重返文学现场、还原历史语境”,将所有的文学史问题置身于其所处身的特定语境中去考察它的发生发展,“历史化”的方法也能够使我们警惕用一种恒定不变的“普遍性”的文学观念去评价文学作品的方法,真正走出“文学/政治”、“文学/非文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80年代”的语境中谈论“80年代文学”,同样在“十七年”的语境中谈论“十七年文学”。“重返”研究者不妥协地贯彻了“文学历史化”的思路:“文学作品的好与坏常常并不由作品本身决定,而取决于评价作品的理论和方法,更取决于我们讨论这些文学的语境。——如果我们因此承认‘个人性’本身并不是‘好文学’的理由,那么,是否我们也应当因此放弃将‘模式化’、‘公式化’的文学视为‘坏文学’乃至‘非文学’的偏见呢?”所以研究者“不应该把‘文学’剥离出具体的历史进程和权力关系,而应该把‘文学’历史化,——或者说将‘文学’作为话语对待。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不会再以是否与‘政治’有关作为判断‘好文学’的标准,而是转向追问这种文学表现的是‘何种政治’与‘谁的政治’。”27
如果说,今天的当代文学研究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文学的政治性有着足够的警惕和反省,但是往往对“新时期文学”中形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却缺乏足够的认知,“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总是习惯于依凭着自己的文学史知识来评判之前时代的文学,而对自身所处身的文学语境缺乏自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浩然对新时期作家和批评家的愤怒:“有些人千方百计地糟蹋我。当前中国文坛野草杂生,妓女、土匪充斥书摊,他们认为理所当然,而且自己迷醉于描写旧中国最落后最愚昧的女人裹脚缠足等等破烂货的展览,而对我写的反映建国后农民运动、群众斗争的作品恨之入骨,不仅大动肝火,还‘以势压人’地对我大加讨伐。对于这号所谓作家、实际小丑,我是最看不起的。”28参照系的确立也是相互的,在80年代的研究者眼里,“十七年文学”尤其是“文革文学”是根本没有什么“文学性”的文学,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在后者的眼里,“80年代文学”的价值又体现在何处呢?即便是“纯文学”理想真的能够得到实现,这种文学就一定是“好”的文学吗?而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一定是没有“文学性”的文学吗?按照80年代进化论理念,是否个人化、主体性的写作就一定比政治性的宏大叙事更进步?这也许很多新时期的作家从来没有也不屑于思考的问题。
所以,“历史化”并不仅仅是将研究对象历史化——探寻它们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不同意义,同时我们还要将自身“历史化”,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自身研究也同样处在“历史化”过程之中,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力地不断对自己文学研究的知识框架、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调整,真正做到在“研究80年代”的同时“走出80年代”。
注 释
①程光炜、李杨:《主持人的话·“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专栏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②杨庆祥:《如何理解“1980年代文学”》,《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③刘再复:《文学八年·序》,见阎纲:《文学八年》,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④洪子诚、静矣:《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意义——洪子诚访谈录》,《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
⑤参考他的系列论文:《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转型》、《“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革命文学的激活——王蒙创作自述与〈布礼〉之间的复杂缠绕》、《经典的颠覆和再建——重返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之二》等。
⑥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⑦程光炜:《革命文学的激活——王蒙创作自述与〈布礼〉之间的复杂缠绕》,《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⑧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⑨11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⑩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12主要有《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没有“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文学史意识与“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文学》、《文学史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等。
1316李杨:《“文学史意识”与“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
14李杨:《重返80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80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15参看贺桂梅和程光炜关于“80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研究的系列论文。
17贺桂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
18丁帆、王世城:《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这一类研究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较为常见,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张光芒关于十七年文学中启蒙碎片的发掘等,可以说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20参看《文学、历史和方法——程光炜教授访谈录》,程光炜、杨庆祥,未刊。另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80年代文学研究丛书中,程光炜将他的讲稿命名为《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这都可以看出他们自觉的方法论意识。
21郜元宝:《批评五嗌》,《文艺研究》2005年第 9期。
22 23程光炜、杨庆祥:《文学、历史和方法——程光炜教授访谈录》,未刊。
24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分歧和建构》,《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2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6程光炜:《孙犁“复活”所牵涉的文学史问题》,《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27李杨:《“好的文学”与“何种文学”、“谁的文学”》,《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28蔡诗华:《历史是一面镜子——浩然及其作品评价》,《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