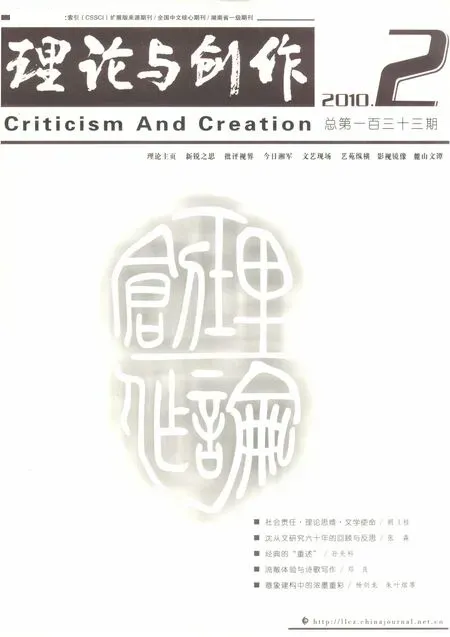政治与思想革命的不平衡关系的表现——“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种基本关系的还原研究
2010-11-25张喜田
■ 张喜田
“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由于作家的深入扎根生活、事件的亲历性、社会担当精神,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使他们的作品较大程度地实现了“形象大于思维”,让人可以不停地阐释,每次均有新发现。接受者的解读参与了作品的建构,膨胀了作品的内涵,虽然时有误读误判、自说自话的一厢情愿。
一、两种革命:一个被忽略的常识存在
“十七年”的农民经历着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全面转变,那就是摆脱个体劳动走向集体劳动,这是一场未曾有过的政治革命。伴随着这场政治革命,他们的思想也将发生一场革命,即所谓思想革命。政治与思想之间有交叉重合之处,因为,政治由行动和思想所组成。但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农民的特点,农民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呈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我们所说的政治与思想的不平衡性着重表现在,一是农民的思想并不一定随其政治行动的转变而转变,即历时意义上的不同步性;二是政治行为的进步并不预示着思想的先进,即共时意义上的不同质性。“十七年”的农民的政治革命着重有合作化运动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其实政治革命就是集体化的实现与巩固。农民的思想与农民的文化并不一致,此处的“思想”着重指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与交融中形成的对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财富与权利的追求、社会发展、家庭处境、自己命运的思考、理解、持守等。在现实中,农民们的政治行动虽已符合社会主义政治精神的要求,如加入集体、参加阶级斗争等,但他们的思想却常常没有同步跟上来。或者说,他们的思想虽然不合于当时的政治标准,但是却仍有历史的进步性。……思想与行动的节拍常常不合拍,正是在这种合拍中产生了张力,既影响了农民前进的步伐、历史命运,也影响了作家对农民的表达。
不管“十七年”的政治革命功过是非如何,但这的确发生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亲历了,几代人、多个阶层的人都受其影响,尤其是农民的思想。政治革命可以带动思想革命却不能代替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是长期的、连续的、远比政治革命艰难和复杂。思想具有构成性作用,政治若不被思想认同,政治也将困难重重、失误连连。因此,欲使政治革命取得成功,政治革命一要正确,二要时刻注意思想革命。这个问题当时的工作者、作家也注意到了,即常说的“关键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就是说要想让农民政治上进步、跟上党的步伐必须关注他们思想上的问题。这是“十七年”农村工作、农村叙述的一个基本问题,具有本体性的地位,但在近几年的“重评”、“回归”的文学浪潮中却常被忽略或避而不谈。
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乍一看是一个比较清晰的关系,但细究起来却又不太容易说得清。我们通过重返经典,细读文本,还原一个文本的乃至历史的现实,去看一看农民、农村工作者、作家在这两种革命中的处境与行为,从而实现农民的处境与表达、身份与建构、诉求与误读的历史还原。此处的“还原”是在中国人的常识意义上的运用,不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即恢复原状,尽量贴近、符合对象的历史真实性。
二、文学表达的“显”与“隐”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基本主题是如何让农民走上集体和发展集体,而后期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也是围绕集体而展开的。
(一)思想进步的滞后性(欺骗性与反动性)
合作化运动变个体私有为集体公有、变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集体生产。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同农民的历史文化积淀、同农民的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道德准则发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
作家表现了农村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斗争的起因是由对互助合作的不同看法造成的,斗争的内容是走不走合作化道路。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们对此不理解,心理上觉得参加合作化是失去财产。“穷人”(贫下中农的大部分)因为贫穷无什么可失,也就无什么可顾虑,参加互助合作还可以获得一些东西;而且他们没有个人发家的条件和资本。对个人发家也就不抱什么幻想,他们就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中农稍有资产,参加互助合作资产有可能失去,但个人发家条件又显然不够,抵抗不过富裕中农。党的宣传使他们对互助合作抱有幻想,但又怕合作化搞糟了不但得不到东西反而连老本也会赔了,因此他们就动摇徘徊。富裕中农是农村资产较多的人,他们有个人发家的条件,他们入社明显地是把财产“归公”,而且合作社的美好蓝图毕竟还没有兑现,农民务实的心理使他们不相信没见过的东西,因此,他们就强硬地抵制合作化运动。由于现实处境不同,农民各阶层对合作化的态度也就不同,可见,这种不同是农民们的财产欲造成的,而不是政治觉悟。“穷人”愿意得到财产,“富人”不愿失去财产,正如同《暴风骤雨》中“赵光腚”之所以革命是因为他“光腚”一样,他们的思想根源相同。然而,作家在表现时却因为前者合于合作化的需要而进行歌颂,后者因不符合而进行批判。这种思想判断是简单的,只看到了表面的与合作化的对应,而未看到深层次的与合作化的对立。这几类人的思想可以发生对立,也可以发生斗争,但这种对立、斗争很微弱,因为二者没有质的区别,没有调和不了的矛盾,而且他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任老四没有钱时积极跟梁生宝走,一旦有了钱就不愿意。这说明“穷人”“富人”的思想是相通的,并且很容易转化。
作家受狭隘的政治视角的限制,片面夸大政治革命同思想革命的同一性,而无视其不平衡性,小说中出现了壁垒分明的局面。农村中各个阶层、各式各样的人物政治与思想上均分为左、中、右。合作化的带头人和积极分子是农村这场政治革命中的左派,其思想也是社会主义的,他们身上或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私有观念和农民的精神负担。合作化的反对派是这场政治革命中的右翼,满脑子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他们是私有观念和农民精神负担的体现者。这样,农村的政治革命就成了梁生宝们“革”别人的命,郭世富们只有被别人革命的资格,而农民的思想革命就成了梁生宝们教育、改造梁三老汉、郭世富们。
作家虽然因政治视角的限制,使他们简单地看待农民的行为与思想的关系,但是他们在不经意或不自觉之间暴露两种革命的不平衡关系,这也许是现在流行的显性主题与隐性主题的表现之一吧。两种革命的不平衡表现和显隐性表现的典型代表莫过于梁三老汉了。
梁三老汉的思想和行动是传统的农民发家思想、与梁生宝的继父子关系以及现实处境综合作用的结果。长期统治着农民的自发意识使他对合作化运动不理解、不支持乃至消极抵触。他的经济状况是富而不裕。他有发家的可能,并不是一无所有,因此对集体化、共同富裕不满、对儿子不满。他又不太富裕,经济地位低下,在现实生活中不被人尊重,有着卑微屈辱感。一方面逆来顺受,一方面对富人有着本能反感。与富人不站在一条线上,与党在精神上相通。(不过,这种“相通”是用党的阶级路线压别人、抬自己,实现新的不平等,而不像作家理解的那样是思想觉悟的体现。)个人发家人力不足(儿子异心)、财力不足(生产基础差)、政治又不允许,这些堵死了他个人发家的路。这种境况迫使他不得不与党、与互助合作保持一致,这种“一致”不是心悦诚服,而是形势所迫。但是因为有梁生宝的关系,他的转变又有很大的“自愿”成分,这种“自愿”也很难说是思想觉悟的提高,更多是农民心理的一种调剂。他认识到自己对生宝的对抗只是发牢骚而已,不能左右他的行动,也只有多关心儿子的事业。他把自己的发家梦转移到儿子身上,让儿子成功,从而“光宗耀祖”,从而使自己因不能发家而造成的心灵空虚用儿子的成功来填补。他把互助组的成功归于儿子,把互助合作事业当成儿子的个人事业。由于儿子使互助成功他才对互助组满意,他也因为儿子的成功才觉得脸上有光。可见,他的转变并不是有了思想认识,并不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只是农民思想、心理的自我调节,某种程度上也带有阿Q的“精神胜利”的特点。
同样,梁生宝的政治行动与思想基础也有很大的不同质性。他身上有很重的农民的落后性。在处理素芳的问题上,表现了梁生宝身上农民文化对素芳的合理追求的压抑和摧残,但作家却以此体现梁生宝的品德纯正、人格高尚,这无疑是对梁生宝身上丑陋的东西加以美化。在与改霞的关系上,也显示出了梁生宝身上的农民文化对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的压抑和批评。梁生宝有着浓厚的故土难迁的恋土情绪,而改霞则是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下,具有新的追求、新的意识的现代女性,但梁生宝却贬低、责斥改霞,这是农民文化对现代文化的排斥和压抑。作家对梁生宝这种思想和行为进行肯定,这是因为梁是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合作化有用人才,他的思想和行为便都是正确的。
作家表现了一些领导人的“青天意识”,也把他们做为“青天”来表现,并对这种“青天”意识进行歌颂。刘雨生坚信“吃饭的一屋,主事的一人”,把合作社的“一篮子”工作全归自己管,成功与失败全由自己负责,他不启发大家对社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只靠个人包打天下。柳青虽然反对郭振山的“青天”意识和“恩赐”观点,但又把梁生宝做为救世主来塑造。活跃借贷时,人们依靠郭振山失败了,靠梁生宝得救了,度过春荒。他俨然成了救世主。在任老四退组时,梁生宝与任老四的一段对话已点明了他具有“青天”意识。萧长春也成了偶像,人人崇拜。如果对他们的一些思想不加警醒与改造,这些合作化的领导者,发展到后来不知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郭振山、范登高们真实地体现了农民革命的动机和发展过程,他们革命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利益。一旦革命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时,他们便不革命了,甚至反对和阻碍革命。他们的革命合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历史上农民起义往往如此,“打皇帝”是为了“做皇帝”。郭振山们的革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是作家们却把他们孤立地看待,不能与其他阶层如梁生宝们联系起来看,也不能发展看。
郭振山们大多是老革命者,“老”革命落后,说明了农民革命的规律性,有一种可怕的历史循环。农民革命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做保证,其结果很可能走向革命的反面,这也揭示了梁生宝之辈的发展前景:郭振山们的昨天就是梁生宝们的今天,郭振山们的今天也就是梁生宝们的明天。但是作家塑造郭振山们是为了给梁生宝们建立对比物。这种对比不是互相见证,互相联系,互相参照,从而寻找两者的相似性和临界点,而是简单对照,片面地肯定和否定,两者一优一劣,肯定一方,否定一方。对比之后不是出现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对农民的革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是把两者孤立分裂,由“坏的”映照了“好的”可贵与强大,从而产生了乐观的情绪。他们的对比不是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去进行,而是单一地从当时的政治、阶级的角度入手。作家只批判郭振山们思想落后不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一心搞个人发家,而对他们如此革命的历史根源、文化积淀注意不够,也就陷于就事论事,而忽视了他们的典型性、代表性,也就对整个农民阶级革命的复杂性注意不够。其实他们与阿Q们的革命何其相似!
(二)思想的劣质化(恶化、丑陋化)
在行为上合于时代需求的人,其思想作家不无溢美,相反,不合于时代要求的,则极尽“集丑”与恶化。
落后人物身上荟萃了农民的“恶”,作家很少表现他们身上“善”的因素。农民身上的二重性到他们身上只剩下了“恶”的一重性。他们自私、狭隘、顽固,甚至剥削他人,疯狂抵制和破坏合作化运动。“糊涂涂”一家里里外外,男女老幼均无一是处。作家对他们全是批判,缺少赞扬,这种状况越来越突出。郭世富、王菊生只是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而被批判,到了《艳阳天》中的“弯弯绕”、“马大炮”则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由阶级斗争转化为两条道路的斗争。他们不仅受批判,而且也要消灭。
农民身上的确有很多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农民思想是相通乃至相似的,差别只是五十步百步之别,但是由于政治行为的不同,就把优劣截然分开,显然不合适。同时,这种“不利于”只是放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方可看出,一旦离开,也可能有其他的历史价值,他们身上的一些因素也值得借鉴。如把郭世富们的勤劳致富、劳动创业的行为全作为资本主义的自发行为加以批判,把个体生产中的计划谋略、经营管理水平看作是奸诈、阴险而极尽嘲笑。正是这些层次间的张力和不连贯性,露出了隙缝,使后人能够不停的解读。叙事是最高的调和机构,具有构成与再生作用。正是由于作家的如实叙述,使我们感觉到了这些落后农民身上的可贵之处。当然,作家有时也意识到了这些价值,如《山乡巨变》对王菊生夫妇、张桂秋夫妇的勤劳、俭朴、爱惜农具加以赞扬,比较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农民,尽管作家也在批判他们的政治落后。
从当时农村的中心工作出发表现一切裁决一切,这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它提供了未来社会秩序的蓝图,却忘记了背后的历史动力,所以有时对农民的落后性的批判又具有很强的历史反动性。如对范登高跑买卖、郭振山窑场入股、郭世富囤粮的批判就值得商榷。他们之所以受批判,一方面因为他们这是个人发家的行为,与当时共同富裕的政策不合,另一方面,这也是长期的小农经济产生的“重农轻商”的农本思想的流露。“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著作家,自然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谈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最后结论”,是“农业中的宗法经济”。①商品经济是封建社会后期新生的经济形式,比农业经济先进,它受到封建经济的排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农村是通过打倒封建经济建立起来的,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因此仅仅以反对个人发家的资本主义思想为借口反对个人的商品经济,实际是从农业经济出发反对商品经济。如此批判的作家,与马克思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著作家”一样是反对历史潮流的。
三、底层的无语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留下了一系列农民形象,身份虽然被后人不停地评说,但给后人留下的印象还是基本固定的。
“十七年”的生活与文学中,政治处于至上地位,具有很强的统摄性,而对政治的阐释、贯彻掌握在权力者手中,即掌握在政治权力(执政者)与知识权力(作家)手中。农民的处境、命运、思想,农民自己无法表达,即使有所表达也常被人误解,他们总是“被表达”。在被表达的过程中,他们的“真实”往往是被改写的,他们的合理诉求得不到表达与尊重,更不可能实现。比如农民们发家致富的思想被丑恶化反动化,郭世富、王菊筋,甚至姚士杰的渴望富裕和经营策略被作为自私、奸诈消灭掉。《风雷》中因羊秀英卖狗肉就把她从生活到人品全盘否定,孰不知这不就是另一个胡玉音(《芙蓉镇》)吗?
身份创建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权力问题。身份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对自我的界定包含着对“他者”的价值、特性、生活方式的区分。作家在与叙述对象的权力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利用自己的话语霸权对农民进行了改写与重塑。政治权力为突出自己的正确性,强化农民的落后性与反动性。知识权力为了突出自己的文明与现代,强化农民的愚昧与野蛮。总之,政治的统摄性,遮蔽、过滤、改写、弑夺了农民思想的复杂性与合理的历史诉求。
尤其在对女性的描写中,显示出了比较典型的特征。在赵树理的创作中,大家一直公认,赵树理的妇女观比较落后。在作家的落后人物谱系中,妇女占比重大,并且妇女形象中,落后形象比重大。如此描写,是因为妇女们在政治上比较滞后,其原因不做过多分析。但是,妇女除了政治特色之外,还应有其他的权力诉求,不应因政治的落后而否定其他的诉求。如素芳虽然是被诱奸,但是却获得了性的快感,但这被作家当作政治背叛道德堕落进行了非常厌恶的描写。刘雨生的前妻离婚也有自己的原因,刘只是尽到一个领导的责任,而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所谓“大公无私”其实正是把家人(妻子、儿女)当作了男人的私有财产。
问题最大的当属知青的表述,如对知青的城乡选择的表达就显示了极大的权力在场。“十七年”作家大量涉及这个问题,如《春种秋收》、《创业史》、《韩梅梅》等。作家处理时往往采用一边倒的倾向:知青回乡务农是热爱劳动、热爱家乡,而向往城市、奔赴城市是好逸恶劳、忘本叛家的表现。这种模式是农本思想的体现,也是“十七年”简单的意识形态划分造成的,更是一种城市权力的在场。作家、政策制定者都是在城里,并且大多是由农村到城市里的定居者,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农村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美好之处,但对于接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来说,农村毕竟是闭塞、狭小的,外面的世界好大、好有诱惑力。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如何,城市是人类进步的标志”②,所以,走出农村,奔向城市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冲动。这些城市利益的既得者,却往往以政治、农村建设、合作化运动的需要而阻止甚至诅咒农村知青进城。
在农民身份叙述与构建的过程中,构建者的身份也显现出来。知识就是权力。乡村叙述中知识者时时在场,即权力总在场。政治权力、知识权力,甚至与城市权力合谋,打压农民,尤其农村妇女、知识青年的合理要求,农民的正义呼声他们听不到,甚至听到了也装做不知或误听误判。因为乡村及农民的文化及文物话语表达的机会欠缺,总是处于失语状态。农民不能说话,即使能说,也往往被误听或误解。在叙述与被叙述中,农民处于不对称的地位,没有话语权,任凭他人评说。
但作家毕竟出身于农民,与农民有天然的血缘亲情,并且亲历了农村的变化,体验了农民的酸甜苦辣,在他们葡蔔于政治权力的同时,他们还有意无意地对政治权力表示些许的龃龉,对农民表示微弱的理解与同情。“个别的叙事,或个别的形式结构,将被解作对真实矛盾的想象解决。”③虽然有某种误解,毕竟也只有他们能为农民说话。《山乡巨变》表现了种种粗暴、简单化的做法。邓秀梅用“外交手段”(不能不说含有奸诈和欺骗的因素)使人们入了合作社,她不是以使人放弃旧思想、旧生产方式为目的,而是以动员入社为目的,因此不管怀着什么动机和心理,只要一入社就万事大吉。她(包括朱明)已明显地暴露出了上级领导的那种左倾、机械命令的官僚作风。陈大春、陈孟春、盛淑君等人富有朝气,充满活力,嫉恶如仇,但是在他们的正义下面却掩盖着一种专制、独裁、粗鲁、甚至野蛮和残酷。他们不把对手当人看待,听不进别的意见,容不得别人的思想,一切唯自己正确,并把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些人发展到后来,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必然是“土皇帝”。陈先晋的入社,是被邓秀梅的“外交手段”胁迫入社的。在外受着政治舆论的压力,在内又家庭不和,他也没有了发家的可能,他只好狠狠心加入了合作社。这说明了革命的残酷与野蛮,对农民最神圣的情感(家庭的和谐、亲人的爱与诚信等)进行亵渎与摧残。作家如实地表现了这种处境,虽然态度有时暧昧,甚至有点赞同,但在评价与叙述过程中却留下了农民“革命”的辛酸。这类文本的真正功能则表现出了“层面之间的干涉,一个层面对另一个层面的破坏”④。
《“锻炼锻炼”》对“小腿疼”、“吃不饱”、王聚海们与杨小四们的冲突的表现作家便有较多的保留。这种冲突与力量的不对等,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后来的群众批斗会。这是变相的刑场,它使每一个参加批斗会的群众都失去人性,成了盲从暴力的帮凶。本来是干部们诱民入罪,然后利用群众的盲目性来整治落后的农民,是典型的“钓鱼”案件。即便是“小腿疼”真的偷了棉花,又是多大的罪?赵树理自己也说:“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了什么法。”⑤
作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们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农民就是这样“被入社”,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侮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性的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⑥。他们只是想反映农村真实的历史现状,而且从当时可能表达的方式来看,他们也只能站在邓秀梅、杨小四们这些所谓新生力量的一边,但“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⑦。正是这种叙述的相对独立性,正是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之间的“张力或不连贯性”,为文学阐释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这种张力的扩大使作家们维护农民的立场得到曲折的表达。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74-276页。
②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③④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页、第45页,第68页。
⑤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页。
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