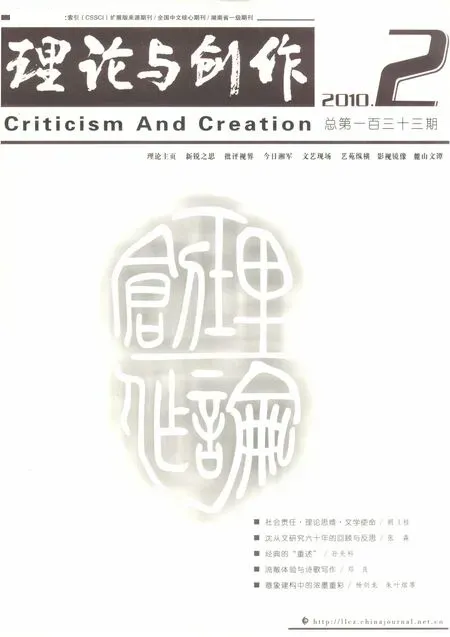解读新都市小说:在市民文化精神的视野中
2010-11-25肖佩华
■ 肖佩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新的市民阶层,中国新都市小说迅即崛起,带来了新都市小说的繁荣。这些作品表现出对新市民生活理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认同,充满市民文化精神。然而,当前许多的研究忽略了它们生成的本土性——中国语境,大多硬套西方时髦理论来解读新都市小说。其实中西文化、文学、历史等迥异,我认为应该回到新都市小说生成的本土性语境,充分注意到我国传统市民文化精神和市民文学对新都市小说的重要影响、作用,当然,这其中也有西方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融合,正是中西合璧,土洋结合,从而构成了当代新都市小说具有新质的当代市民文化精神。
一、城市化浪潮:新都市小说崛起之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加速推进市场经济进程,带来了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较快发展。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新的市民阶层的兴起,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市民文化精神正渗透着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正因此,我国新都市小说遽然崛起。新都市小说实际上已一跃成为当下的文学主流。一扫传统的“都市文学”萎靡不兴的局面。众所周知,由于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起步较晚,受乡土中国文化的制约,故我国都市文学较之乡土文学逊色不少。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学曾掀起过一阵浪头,然而由于救亡与内战,加之缺乏都市文学发展的必要的土壤,都市文学遂昙花一现。而从1949年直至1980年代前,国家采取高度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权威意识形态,都市文学更没有成长发展的空间。“乡村被美化为带动人民的精神之源,而城市则是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腐朽思想的泛滥所在。《霓虹灯下的哨兵》(1963)就体现了这种将城市置于乡村对立面的‘时代思想’。”①1990年代以来新都市小说的崛起,正应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阐释过的观点:任何文学艺术流派、艺术品的产生与流变都是当时当地之“时代精神”与“风俗习惯”进行“选择”与“自然淘汰”的结果。这里的“时代精神”与“风俗习惯”既是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的总体体现,又是以上众多因素融合共生的产物。社会时代的变迁必然引起“时代精神”与“风俗习惯”的相应变化,进而引发文学艺术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当代新都市小说的崛起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与变化了的“时代精神”的产物,是社会转型期的客观产物,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对当代新都市小说的研究、评论角度很多,其中多以西方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时髦、热点理论来解读我国新都市小说。笔者以为见仁见智很为正常。而当我多次阅读这些新都市小说,又觉得恐不尽然。西方社会与中国并不一样,现代化实现也有不同的路径。我国新都市小说的崛起、解读也应有自己的情况(语境)。为此,我尝试提出“市民文化精神”命题,以此观照、解析当下中国的新都市小说。
二、解读新都市小说:在市民文化精神的视野中
文学的生命本源在于它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当代中国新都市小说正是在中国当代都市土壤上适应我国当代都市市民的需要而产生的。从历史上看,我国有悠久的市民文学传统。从宋代开始,市民文学颇见兴盛。可以这样认为,市民文学的发展几乎与市镇商业的演进同步前进,也即:“市民与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乃是市民文学滋生的土壤。”②明末清初,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伦理与功利观念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更加冲突动荡,从而掀起了一股具有近代崭新的市民资本主义特质和启蒙意义的新思潮。与此相应,“随着印刷业的兴盛,市民自我表现和娱乐的文学样式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和传播,说话、表演等时间艺术借助书面文学的存在形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行和赏析。一大批文人雅士染指其间,或取其谋获利之径直,或因其叙事抒情之简便,从宋元话本到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从讲史话本、英雄传奇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长篇章回小说,从元杂剧到明清传奇,从魏晋六朝文人短篇小说到《聊斋志异》,如此种种,构成了一股汹涌跌宕、兴旺发达的通俗文学洪流,传统的诗文词赋相对地反而不那么显眼注目了。”③宋元话本所具有的民主精神和社会进步意义,所表现的富有现实人情味的世俗生活,对于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的向往,在明清通俗文学中得到了扩展、弘扬,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这中间特别重要的是市民文化精神的凸显,反映市民阶层要求的理论逐步形成,王学左派,李贽掀起了人性解放的启蒙思潮。他们抨击儒家圣人理学文化,弘扬个体价值,返回人生真相,大胆践踏了僵化的儒家礼教,为形而下的民情民欲正名。于是,在明清市民通俗文学中,我们看到一幕幕商人们追财逐利的艰难历程,市井间家庭的悲欢离合,市民对情与欲的大胆拥抱。这些包含着市民的人生体验以及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生动事件在作品中显得生气盎然。从而完成了把人作为个体的人,从礼教的牢笼中,从军国大事中,从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中解放出来,而放进日常的平凡生活中,展现了人性的本来面目。它们所表现的正是市民阶层的愿望和审美趣味。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国当代新都市小说的兴起与明清之际的市民文学大体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其一,是社会转型和商业性文化环境的形成;其二,是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的反拨和纯文学性的消解。建国近30年的国家权威话语的膨胀,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压,情与欲的禁忌,十七年文学的宏大叙事,特别是“文革”文学的彻底政治化和乌托邦化,文学与现实生活出现了裂隙,文学疏离了现实大众的真实生存,即便是“文革”结束后,这一趋向并没有彻底终结,知识分子话语与大众话语间的裂隙还存在。个人生活和情感的被消除,使大众疏离拒绝着如此“惯性”的文学。当然,最重要的乃是改革开放促成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各种禁忌的被打破,私人生活空间的自由度的扩大,城市化、现代化浪潮的迭荡,市民社会得以逐步形成。按照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市民社会是与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具有明晰的私人产权及其利益并以契约关系相联结的,具有民主精神、法制意识和个体性、世俗性、多元性等文化品格的人群共同体。而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与旧、民主法制与专制特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但即便如此,一个已迈上现代化征途的大国前景仍被看好。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当代新都市小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崛起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当代中国的市民文化精神一方面继承和弘扬了中国自宋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的传统市民文化精神,即追求“个性自由、闲适享乐”,反映在文学中的“直面世俗性”,这也是主要的一面。其二,当代市民文化精神也吸收融合了西方市民社会精神,理性和个人化是现代都市最大的文化特征;西方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对中国市民也冲击不小。一定意义上,现代化就是世俗化。但与中国传统市民文化相比其影响要小。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马克思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或许很能说明这一点。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也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其他能力和形成的习惯。”④美国学者C·克鲁克洪也认为:“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具体形式;文化基本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⑤这里充分说明民族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与渗透性。而当代中国新都市小说便渗透了更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市民文化精神。正是中国传统市民文化精神与西方当代城市文化的融合,才催生了中国当代新都市小说。并且从当代新都市小说的主题和艺术形态上看,它的确更多地承继了我国市民文化传统。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中西文化有着根本的迥异,先哲们早已认识到这种差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为中国文化一大特征”。⑥诚然,中国文化以儒道为主脉,但其哲学观与人生观却都是世俗的。由于中国农耕文明悠久,民众“重实际而黜玄想”,很少生发那种超出实际生活之外的欲求与愿望,故以儒道为主脉的本体论都是将人的注意引向现实人生而不是引出现实人生,即立足于世俗人生建立宇宙观和本体论,而非总是以彼岸世界为参照,设计宇宙与人生图景。中国传统哲学带着这种内在的“此岸”情结,故对世俗生活一直持认同与肯定态度,即使孔孟儒学从来也没有否定人的正常与合理的生活欲求,“它所要求的只是人应当将自己的欲求置于理性框架之中,在伦理规则的约束下实现内在的和谐。”⑦所以说中国文化根本上是一种世俗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认为,人类此岸的生活微不足道,它不过是彼岸的准备,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恪守原则,死后才能升入天国,否则就要在地狱中受煎熬。所以在西方,人与神、人与上帝的交流、沟通就成了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人们在生活中常常进行反省与忏悔,力图通过承受肉体与心灵上的痛苦清洗据说人类生来就有的原罪,以便皈依神性,获得精神上的救赎。西方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的超越性,使其不可能将价值取向定位在一种世俗的追求上,尽管西方历史在神性与世俗生活的两极之间也常发生摆动。如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期间在反抗神性、张扬人性旗帜下的世俗生活,诞生了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巨人传》等作品。但基督教文化毕竟根深蒂固,已作为一种天启的戒律深入到人的无意识中。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西方文学对神性与精神超越性的认同被大大超过对世俗性的兴趣,他们不断探索、追问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正是西方文学区别并高于中国文学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文学大多缺乏西方文学这种宗教性精神意义的永恒叩寻,而多沉溺于世俗情怀、日常生活意义之中,这根本上也是由中国的世俗性文化特点所决定的。所以,反观中国当代新都市小说,往往也难逃脱此“窠臼”,尽管我国新都市小说已取得巨大成就,然而扪心自问,当下中国新都市小说哪一部能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卡夫卡《城堡》等媲美一下?当然,文学的情况很复杂,不能硬性这样比。中国有自己的语境。但同时更能说明这样的道理:文学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是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都受到后者很深的影响。正如汤学智所言:“一种文学,之所以可以区分为这一民族或那一民族的,关键在于其不同的民族风格,而决定这种民族风格的关键,则在于不同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学正是以自己独具的文化精神为灵魂,为内在的生命。”⑧的确如此,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是作家在生活中积累的体验、感受的提炼与升华,所以作家所处的物质生活环境、历史传统、时代特点,自然、人文景观、风俗人情等等特点自然而然会在其创作中反映出来。在此意义上,作家确实是本土文化的代言人,文学则是对本土文化的艺术表达。因此,文学必然是民族的,它的躯体中流贯着民族文化的血液、精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本民族文化的鲜明印记。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奇怪地看到:首先,市民文化精神影响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中国当代新都市小说家,他们的身上更多地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市民文化之血液,尽管许多人本身并未感觉到这些;其次,当代新都市小说家所反映的客体——都市景观、市民生活,也主要是中国市民社会、市民文化传统之积淀,加上外来文化——西方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之影响。遂造成当下中国新都市小说喧嚣多彩奇特之“景观”,它们呈现目下都市的种种景观,市民生活“物”与“欲”的沉迷,乃至堕落,进而展现出现代都市的生命哲学意识。
三、叙事策略:世俗化欲望化图景
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激活与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率,同时也把适者生存的原则带进了社会生活,这是一个被物欲所驱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以物的名义,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为所欲为,物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圣经》。脱贫致富便是这种世俗精神的实现目标和实践形式,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新都市小说在1990年代就逐步确立起欲望化的叙事法则。我们知道,新都市小说的主力作者被称为“新生代”,像北京的邱华栋,广州的张欣,江苏的韩东、毕飞宇、鲁羊,上海的唐颖、殷慧芬,东北的刁斗、述平,湖南的何顿,广西的凡一平,海南的李少君等。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初,在文革期间处于儿童时期,没有经历过严峻的政治时代,他们形成自己世界观的时候正是中国开始加速城市化的时候,可以说,他们是第一代完全意义上的都市人。这些作家深知新市民的审美趣味,在大多数新市民眼中,文学是消费,是娱乐。在为金钱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拒绝崇高,也不需要沉重,因而他们的阅读取向标准是传统民间文学的“快乐原则”。为了迎合普通市民阅读中的“快乐原则”,新都市小说将作品反映的重心投向平民生存原相,投向人自身生存的各种庸常现实层面,并建立起一种“欲望化”的叙事法则。这种欲望化的叙事法则,具体表现为叙事对于“物”与“性”的依赖。“性”在小说中成了情节发展的动力和情节的枢纽,整个叙事围绕着“物”与“性”展开。其主要代表性作品有邱华栋《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韩东《障碍》,朱文《我爱美元》、《尖锐之秋》,何顿《生活无罪》、《我不想事》、《无所谓》,张欣《爱又如何》、《岁月无敌》,唐颖《糜烂》、《红颜》等。这些作品描绘的主要形象是一群走上市场竞争的城市平民,他们是改革成果的享有者,也是经济转轨、市场竞争中的“悲欢离合最直接的体验者”。小说的作者们以近乎平行的视角展现新时期这个庞大人群的生活方式、欲望和追求,展现现代都市的纷繁、绚烂、动荡、充满挑战性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小职员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乡镇,从穷乡僻壤来到城市,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边缘人员层——流民。他们无户籍、无固定工作与居所,希望有一天能被欲望燃烧的城市接纳,这些“闯入者”成为了新都市小说着意描绘的对象。“闯入者”一进入城市,便被五光十色的都市繁华迷惑,欲望的都市点燃了他们内心蛰伏已久的欲望:“我必须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社会迅速分层的时期,我必须要过上舒适的生活”。⑨为此,“闯入者”们使出了各种手段,《音乐工厂》里的杨兰离开乡村到城市打工,一度陷入困境,于是这个小姑娘便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青春的肉体来赚钱,获取金钱上的最大满足成了她生活中的唯一目标;《新美人》中的那些漂亮女人更懂得充分利用她们的优势资源——身体,娇嫩靓丽的脸蛋,妖娆苗条的身材,来换取她们的享乐、金钱与地位。《我爱美元》更极力描摹了性欲的饥渴状态,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慈子孝的完美关系,具有反文化的色彩,这些作品体现了城市的光怪陆离。“欲望的叙事”成了当代文坛一道眩惑的风景线,而从这些新都市小说中我们既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西方现代都市旋风,同时又分明嗅着了我国古代《金瓶梅》等明清市井艳情小说的遗味。
总之,从新都市小说热潮中,我们可明显看到我国市民文化传统精神的承续和弘扬,当然这是结合了新世纪新时代风尚的具有崭新特质的当下市民文化精神。而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国家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压抑、攻击、蔑视市民社会,动不动就斥为“小市民”,市民意识被戴上庸俗、功利、简单的帽子,这种观点,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市场。殊不知,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就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相伴随的城市化、世俗化的过程以及市民社会的崛起过程。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市民开始大步跃上社会舞台,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强行操纵松弛后,在知识分子话语中心位置偏移后,市民的意识和精神空前的活泼,城市的空气到处可以嗅到他们自信的气息,可以预言,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秩序中,市民意识是可以与主流意识、知识者意识对等发言的。正是中西合璧,土洋结合,使得当下中国的市民文化、市民意识庞杂纷乱。但我们应该看到,“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政治民主、人性的解放、思想自由、学术繁荣,都有赖市民社会的壮大和市民意识的完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传统与现代、中西碰撞的语境中对话、磨合。当代新都市小说以极大的热情反映此种变化着的如万花筒似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意识,新都市小说所开启的充满市民精神的文学空间,愈来愈活力四射。当然,我们也毋庸讳言新都市小说中的狭小、平庸乃至恶俗的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身份也许会成为历史,但对人类精神性因素的追问和对平庸现实的抗拒,则永远应该是文学不可推卸的职责,须知文学作品的精神高度与市民文化精神并不相互抵牾。在此我们深切期待新都市小说创作有更大的突破。
注 释
①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②钟婴:《明末清初市民文学与江南社会》,《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
③许建中:《论明清之际通俗文学中社会价值导向的嬗变》,《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
④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⑤邹广义:《文化·历史·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8页。
⑥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华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⑦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⑧汤学智:《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⑨邱华栋:《环境戏剧人》,《上海文学》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