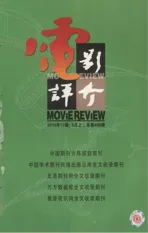《茉莉花开》:男性“缺席”的女性叙事
2010-11-16魏斌宏
侯咏的导演处女作《茉莉花开》已经公映七年,影片播出后,一直好评如潮,最近,笔者再次观看了该片,发现该片在表达其“女性主义”的叙事策略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侯咏和顾长卫一样,也是“摄而优则导”,但摄影师“有镜无片”的毛病却暴露无遗,许多优美成功的镜头无法掩盖故事的空疏与做作。相较于《孔雀》,《茉》剧的缺陷则更为明显,从电影叙事的角度而言,《茉》是缺钙而经不起推敲的。
《茉》剧用平行三段式的结构方式讲述了一家三代茉、莉、花在不同历史时期(20世纪30、50、80年代)的婚恋悲剧,欲图“表现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把握过程,表达对女性勇于把握自身命运的期望。”[1]这种初衷无疑是非常好的。因为一直以来,在中国传统的婚恋中,男权中心主义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观念中,女性依附于男性并受男性宰制的局面随着时代的进步虽有所改观,但却并未完全打破,所以女性主义是应当提倡的,时代也迫切呼唤更多优秀的“女性主义”影片的诞生。但是,遗憾的是,在中国堪称典型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的影片却少之又少,戴锦华教授就认为,迄今为止,在新时期大陆拍摄的电影中,女导演黄蜀芹的作品《人•鬼•情》(1987年)是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女性电影”的唯一作品。[2]
不可否认,拍摄“女性电影”是有相当难度的,尤其对男性导演而言。因为,一不小心,男性导演的叙事视角往往会陷入“男权”的叙事泥淖中而浑然不觉,从而使得其“女性叙事”变成一种男性视角下的“女性想象”,变成一种点缀在男性话语下的奢侈附丽。《茉》剧的问题恰在于此。《茉》剧的叙事主体似乎对什么是真正的“女性主义”拿捏的不是很准,或者说,他对“女性主义”理解过了头。我们知道,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出发点首先就是反对“男性中心说”,要求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同男性一样的权力。但是,女性主义中并不是要把男人囚禁起来,让男人仅仅成为女人的背景,平等才是“女性主义”追求的第一要义。笔者认为,悬置、虚化进而使男性“缺席”的叙事策略的采用是造成《茉》剧在表达其女性主义主旨上失败或不完满的症结所在。
其实,男性“缺席”并非男性“不在场”,而是一种叙事主体在行使其女性叙事时一种先入为主的制作观念。他有意识地将男女主人公置于一种男/女完全对立的二元话语模式之中,在将男性角色概念化、符号化、淡化和歪曲化的过程中来完成对女性角色的塑造,而不是把女性的婚恋悲剧放在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中,让其遵循故事情节发展的应有逻辑。在《茉》剧中,可以看到,男性不是促进情节发展并使女性角色形象逐渐丰满起来的有效因素,而仅仅是作为陪衬的道具出现的,因此贬抑男性的视角始终主导着整个剧情的发展,男性成为导致女性悲剧的唯一根源。统观全剧,无论是孟老板、王师傅、牙科黄医生还是“负心汉”小杜,“花心”与“好色”构成了近乎所有男人的两大基本特征。叙事主体似乎一再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叙事主体后来也的确通过茉之口明确的表达了这一观点。侯咏曾说,他想“传递一种客观的女性主义思想。”[3]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尤其是像《茉》这样的叙事电影,动人的故事和丰满的角色塑造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它不是赤裸裸的理念传达物,“理念先行”的创作方法注定是收不到良好的艺术效果的。
诚然,在《茉》中,造成茉、莉、花三代女性悲剧的因素中男性是主导性的因素,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因素,其它诸如自身性格的、社会的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人作为复杂的社会综合体,是绝对不可以条块分割加以分析的。但作者为了强化男权的宰制,却矫枉过正,他有意识的在其女性叙事中加入更多人工思维的因素,其实并没有达到作者所说的“客观的女性主义”效果。影片时时让我们都能感觉到主观的存在,感觉到作者的眼睛,感觉到电影的虚假,这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其实,所谓“客观的女性主义”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既然提“女性主义”,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何谈客观?或许,效果与初衷的相悖也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作者以为然,读者未必以为然”的接受法则是作者所无法控制的。单方面的强化女性反而弱化了对男性角色的塑造,因此也就无法在男女角色的矛盾冲突中形成一种叙事的张力,进而收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在《茉》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茉与孟先生、莉与邹杰、以及花与小杜的婚恋当中,如果再算上茉的母亲,整整四代人的婚恋都是悲剧性的。而且这些表达都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对男性角色的处理,更是浮浅而虚幻,性格不鲜明。通过这些,侯咏也似乎一直在向我们传达着另外一个信息:爱情是不可靠的,爱情只能是使女人受伤的东西。男人和女人是对立的,女人是受男人宰制的工具,用茉的话说就是“世界上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在茉、莉、花的“爱情”中,唯一可以和两个“负心汉”(孟先生和小杜)形象形成一定反差的莉与邹杰的爱情塑造中,也是不能让人感到满意的,至少对爱情的表现是拘谨而不舒展的。特别是让莉怀疑邹杰猥亵花最终逼死邹杰那一段更是大煞风景,更让人怀疑他们曾经自由相爱基础的坚实性,并且也超越了伦理的惯常界限,显得非常牵强。这样的处理方式对男人也多少有些不公平。其实观众对于这种悲剧的造成恐怕感受更多的应该是女人性格的悲剧(比如茉的幼稚、犹豫、爱慕虚荣和莉的多疑)而跟男人没多大关系吧!侯咏的“爱情悲观主义”态度告诉已经“很受伤”的女人们,应该远离男人,才能避免受伤害,女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因此,远离男人和虚化男性角色的主要叙事策略的过分运用,导致了男性角色性格塑造的模糊化和电影语言的理念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观众理解上的极大偏差,同时这种刻意的强化和淡化都使影视艺术的“更高真实”化为一片泡影。
在《茉》的剧末,作者刻意的安排了花乔迁新居的一个镜头,意在表达新时期女性的独立自醒,花还特意告诉他的小女儿,“你将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英国女权主义作家伍尔夫就曾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个所谓光明的尾巴的象征意味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铺垫,这样的结尾让人感觉是突兀而做作的,难道在没有爱情、没有男人的世界里,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归宿么?而谁又能保证身处单亲家庭环境中的花的女儿就不会延续祖辈的悲剧呢?不要忘了,鲁迅先生在数十年前发出的“娜娜预言”可一直还在我们耳边回响呢!
正是这种男性 “缺席”的女性叙事策略,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真实的“缺席”,《茉》剧让我们感到其时代气息是很微弱的,侯咏曾说他是故意的,难道离开环境的人物就能够自足吗?如果放逐了时代和自身的因素,把悲剧仅仅归结为男性的欺骗和压制,是缺乏说服力的,而且在我们的社会中,男女和谐相处的社会基础不是“对立”,而是“共谋”,谁也离不开谁。对此我们不必讳言也不应矫枉过正。
笔者一直认为,电影不应该承载伦理的说教或是赤裸理念的传达,电影的力量在于使观众在美的享受中接受潜移默化的伦理熏陶和体悟某种生活的哲理。正如美国电影学家布鲁斯•F•卡温所言:“电影是种建构的启示”,[4]而这,恰恰是《茉》剧所最最缺失的。
[1][3]侯咏:《茉莉花开》[J/OL],http://r.book118.com/files/article/html/8/8302/691892.html。
[2]戴锦华:《〈人•鬼•情〉:一个女人的 困 境 》[J/OL],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3872。
[4][美]布鲁斯•F•卡温:《解读电影》[M],李显立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