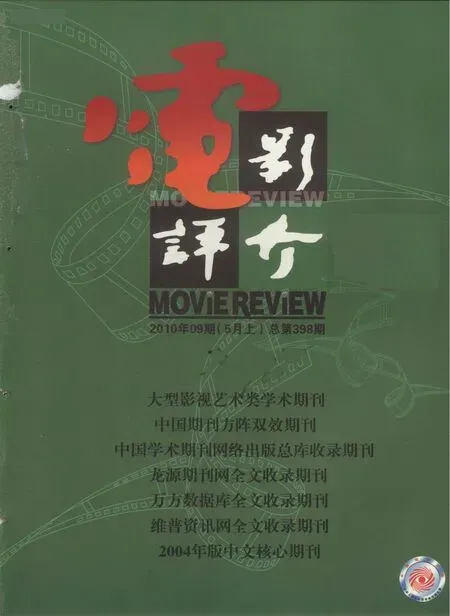女性叙事的影像建构:马骊文电影解读
2010-11-16廖小西
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从最初的强调发展对抗电影,逐渐转向弱化两性之间的表面对峙,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造成两性不平等的深刻根源。而当代女性电影也由最初单纯的“对抗电影”长大成熟,表现主题也由批判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和描述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境遇,拓宽为对社会、人性、生命等等问题的关注与审视。然而,女性电影创作者却依然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对女性重新定位,具体表现为:对女性情感的理解,对女性内心渴望的讲述,对女性悲惨遭遇的人文关怀,对女性权利的现代性思索等。”[1]这意味着女性电影关注于表现女性视角下的爱情、亲情、友情、事业、家庭,并加入女性创作者自己的思考与感受。女性电影的叙事由对性别压迫与歧视的控诉的单条主线,转变为多条主线,其中充斥着对人生、社会、生命、爱情等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而“新生代”的青年女导演马骊文先后拍摄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和《我们俩》就是其中的代表。 新时期的女性已经不再是一味的反抗,她们拥有了独立的经济、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独立的人格。因此马骊文抛开社会的大环境,在镜像中构建了一个纯粹由女性组成的空间世界, 塑造有主体性的银幕女性形象,强调女性经验,用新时期女性的视角,女性的叙事方式,女性的电影语言来关注作为个体存在的普通女性,深入到她们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世界,把现实的问题归结为观念的问题,从而提升出超越两性对立的人生价值观。这两部作品都是在马骊文的视角下,通过马骊文的眼光来塑造老、中、青三代平凡普通女性的生活、情感体验。影片中女性的独立自主、自强自重,在男性形象的缺失下,将人物置于男性文化之外,刻画和呈现女性自身的命运遭际,情感特征等,带有很强的客观性与明显的女性意识。影片围绕着这几个女性,在一个相对封闭狭小的空间里叙事,构建了一个纯粹由女性组成的空间世界与女人自身的精神世界。影片中时间的连贯与轮回,空间的封闭与独立,都体现着作为女性独特的时间与空间感受,为女性电影语言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时间与空间逻辑。
一、女性叙事的视点选择
马骊文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和《我们俩》都是因其自己的感动和经历而进行创作的,渗入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理解与体悟,在丰富的生活化细节中,透露出一种感性与理性交织的观照,对于女性之间的感情(母女、老人与女孩)和关系变化进行着客观化的记录;在颇为冷静而温软的记录中;对女性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度的开掘,审视着自身也关注着身边的世界,用悲凉苍茫的叙事基调写下女性真实的体验,直面女性自己的感受。
马骊文说,“不管是谁的经历,它的故事及情感必须是我能了解,能把握,也能体会的。要首先能打动我触动我,我有激情才愿意做。这两部电影都从个人角度反映了个人的真实体验及感情,但也折射了社会及现实,而且潜意识有社会责任感在,尽管我没有用这样的目的在拍电影,但电影本身潜藏着这样的意义。”[2]马骊文就是作为一个新世纪具有女性自觉意识,有女性独立人格的个人,用她的眼睛去看,用她的心去感悟剧中女性的角色,在她的电影语言中带观众走进女人的世界,女人的心理,阐述主流文化下新世纪女人的真实生活、情感。
在对女性个体心灵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对人类群体社会的探悉和洞察的基础上,她坚持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感知,捕捉着有意味的物象,诉说着来自心底的诸种感慨。或许就如19世纪英国文学家萨拉•艾丽丝所体察的那样:女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重感情而轻行动的。马骊文在这两部作品中运用女性独特的视角与叙事风格把人物的内心感受通过细节描述,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阐述的叙事视角,是指所涉及到的是谁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是透过谁的眼光传达出来的,在本文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受到谁的眼光的“过滤”,或者在谁的眼光限制下被传达出来。影响视点的因素有很多,而叙述者的性别则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美国心理学家珍尼特•希伯雷•海登等在编著的《妇女心理学》中曾作了这样的表述:“女性对人和内心世界的关注能力和体察能力优于男性”,“女性的情感不仅细腻、深沉、而且更容易移情,具有易感性,因此,更富于同情心,比男性有更多的‘亲社会情感”’。黄蜀芹也曾形象的比喻,她认为“视角就象房子的朝向……如果把南窗比做千年社会价值取向的男性视角的话,女性视角就是东窗。阳光首先从那里射入,从东窗看出去的园子与道路是侧面的,是另一角度。有她特定的敏感、妩媚、阴柔及力度、韧性。女性意识强烈的电影应当起到另开一扇窗、另辟视野的作用……女导演恰恰在这里具有了一种优势,也就是说,平时没人经意一个女人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你有可能用你独特视角向观众展示这一面。人们将惊奇地发现:原来生活里有另一半的意蕴、另一种的情怀,它将使世界完整。”[3]的确,女性电影正如从“东窗”看出的风景,具有另辟蹊径的独特视角,而决不是与所谓“男性”电影相对立的。
《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采用了女性第一人称的画外音实施叙述。影片中,女主人公诃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母亲因病离去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心理:爱、恐惧、焦虑、愤怒、缅怀、疼痛、煎熬等等,从诃女士的经历与感受,来重新诠释母女关系。男性眼中的母亲是中国传统美德――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呈现者,她的全部意义与价值在于贡奉、牺牲,以成全男人的生命与价值。而在马骊文的影片中,母亲是作为女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不依附于男人,不挂上“伟大”的标签。由于受到病痛的折磨,母亲吵闹、任性等行为,都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这里女人视角下所呈现的母亲形象还原了其女性感受的真实原貌,不再是男人们附加给母亲的沉重符号而处于家庭的从属地位,失去女性自我的印象人物。影片传达的母女关系,通过同为女性的马骊文的眼睛过滤给观众,自然会引发女性群体的强烈共鸣,同时触发男性们的警醒。
《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采用倒叙之后的顺时空叙事形式,影片的开始 ,就以叙述者的“妈是含冤而死的 ,而且是我害了妈 ,是我的刚愎自用害死了妈 ,是我把妈累死了”的旁白 ,定下了女性主观的情感基调,女性真实的心路历程由此开始。从诃女士发现母亲已经老了,到诃向大夫咨询母亲的眼疾 ,诃陪母亲雨中乘出租车上医院检查 出母亲的垂体瘤和脑萎缩和尿道感染 ,联系治疗的医院 ,母亲向邻居告别入院 ,诃在医院上下奔跑办住院手续 ,在手术单上签字 ,术前母女交谈(实则是母亲交代后事) ,术前备皮 ,备皮前母亲拍照留念 ,做手术 ,因术后反应母亲闹人 ,诃因母亲的折腾人和母亲闹别扭发脾气,诃在医院陪伴并服侍母亲 ,出院后买跑步机让母亲锻炼 ,诃因参加出国颁奖母亲入托老所 ,回来后接母亲回家继续要求母亲锻炼 ,直至母亲临终。在这一连串的简单的事情中以叙述者的心里和情感活动为轴心结构,让我们跟着诃去经历去感受。电影采取线形散文式的结构方式将文本内容组织以来,把一个个细节构成的场面进行有效的积累,着重展现人物之间的细节,细致的描绘这对母女之间的感情。追述使叙事本身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女性意识通过“我”— —叙事人对于画面的编织得到完整的体现。影片中大量的细节也体现了马骊文细腻的叙事风格 ,例如:诃因操劳过度 ,疲乏地趴在桌上睡着了 ,母亲为她悄悄地拔下早生的华发;诃接母亲出院下台阶时扭了脚 ,忍疼屏息 ,佯作无感觉 ,一直拿捏着搀扶母亲坐进轿车 ,才舒一口气;诃怕母亲因吃饭慢而吃不着咸鸭蛋 ,将一块咸鸭蛋放入母亲的盘中 ,而母亲又将最后的一块夹给女婿;诃与先生在医院病房的走廊里,因母亲的新房未能如期装修完毕 ,母亲出院后不能入住的问题而争吵时 ,走廊上走来了住院的患者 ,两个人暂停争吵 ,待人走过去后,争吵又继续;诃因母亲的固执 ,一边数落母亲 ,一边擦眼镜 ,她没有接过小保姆递过来的纸巾 ,而是用衣襟擦拭;母亲洗澡时用水喷头当电话打给外孙女;母亲因手术反应折腾人 ,诃赌气离去时 ,母亲叮嘱诃“外面在下雨 ,出来进去的别忘了多穿些衣服”,以及母亲临终前对诃的“明天变天了 ,天凉 ,出门多穿点衣服”的最后唠叨等等细节。
马骊文的第二部作品《我们俩》,看似平淡的叙事、对话与生活,却在影片最后以老人的去世撕开一道伤口,揪住你内心最软弱的地方。一个古老被遗忘的四合院,通过一个四季的变幻,悄悄的诉说着她们的故事,悄悄的没有任何方向目的的刻画着人物的心灵。年近80的金雅琴把一个北京老太太的孤独,戒心,精明与渴望交流,刻画得活灵活现。小女生宫哲的风风火火与老太太的迟缓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角色中两人的心态反差很大,马骊文在最大限度地纯净关系的同时,来展开人物之间复杂的心灵交往。整个电影由一些对水电费的计较,对使用电话的争执,以及冰箱的使用,还有小女生试图对老太太的屋子进行改造,爬上老太太屋顶挑鸟窝,给老太太拍DV等段落组成,让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也不由的随着微笑,起伏,感动,怅然。影片的结尾,中风的老太太搬出院子后,女生接到一个无声的电话,此时电影将所有声音切掉,只有女孩在天桥上慢慢地蹲下,无声地流泪,虽然电影中什么也没说,但观众都已经知道,老太太已经去世了,马骊文准确地将电影人物的情感传递给观众。她没有对生活作任何结论,让观众始终沿未知的方向随着人物走去。不强调戏剧性,而力图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表现,节奏虽然比较缓慢,没有指向,不讲道理,无辨是非,而正是在所有的发展都超乎俗套的意外中,我们却渐渐走近了真实的世界。
上述两部影片,马骊文用感性、细腻、平实,带有个人经验的叙事风格,运用细腻圆熟、精雕细刻的手法着力表现女性的内心感触 , 多方位地直抒女性的喜怒哀乐 , 立体化地描摹女性的生存境况,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电影独特的写意 (抒情) 视角 ,探索着新时期女性独特的叙事风格;同时着重表现女性内心的自我对话,让女性历史、女性时间、女性空间、女性语言从男性话语的牢笼中脱逸而出,形成不同以往的女性叙事。显示了当代女性电影范式的内向化趋势,以及创造一种自觉、自主、自由的女性电影语言的努力。
二、女性时间和空间建构
时间与空间的重新编织体现了女性电影语言的新向度,电影本来就是一个空间控制与时间控制的影像编码系统,“电影的编码利用作为控制时间维度的电影(剪辑、叙事)和作为空间维度的电影(距离的变化、剪辑)之间的张力,创造了一种目光、一个世界和一个对象,因而创造了一个按欲望剪裁的幻觉”[4]。电影通过对空间与时间的编码获得有意义的形式,从而构成了电影语言。新生代女性电影无论在题材还是视觉的表达形式上,都提供了与之前的女性电影不同的影像实践,初步建立了一个新的类型女性电影语言范式。
马骊文的这两部电影都强调时间上的完整性和意义上的模糊性,较少采用分析式的蒙太奇手法。《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由母亲去世这一事件开始,追忆主人公从发现母亲衰老到母亲生病,给母亲治病,一直到母亲去世,时间是连贯的,导演按时间顺序一步步推进,没有花哨的拍摄手法,于平淡中让观众随着故事的情节被感动。《我们俩》按照一年四季的时间顺序来安排情节的发展,为了在影片中展现真实的四个季节变化,这部小成本电影最终在一年半时间里才拍完。这部电影的导演手法和影片结构一样简单,基本不玩花样,一场一场的叙事、对话,小女孩风风火火进出,老太太端坐屋前默默端详,彼此之间从不信任地相互抗争到自然而然如同家人,感情随着四季发生、生长、成熟、消失,最终留下了伤感,也留下了一些挥之不去的印记。
马骊文这样的时间安排与女性本体有着神秘的联系,女性就是在这个时间维度中识别自身的。电影《我们俩》的时间安排具有自在的规律性和节奏性,小马与老人相处的一年就象征了女性的一生,季节性场景的复沓将自然节奏与女性的生命节奏同构起来,女性的生命周期原来就是自然的周期。另外一个周期是女性生命的循环往复,女性与“自己”在生命尽头的相遇在四季轮回的背景中拥有了特别的意义。少女获得了女性经验的启示,从此开始认识自己的女性命运。老妪则重温了青春的朝气与梦幻,把自己灵魂寄托于崭新的女性生命,生命不会在死亡时终止,而将在另一个身体中延续。同样情况也出现在《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女人在母亲弥留的短暂时间里明白了生命的秘密,最后在自己的身上发现了母亲的身影。一切都在循环之中,生命的始终,季节的变化,瞬间的轮回。马骊文电影都是关于内在时间逻辑的展示,女性对死亡的发现也是对女性内在时间的领悟。这是对于女性生命的时间新体验,它指涉女性存在的源头并象征了女性无限自我更新的生命机能。时间本是父亲规定的刻度,历史是关于父亲的书写,在男性价值系统的建构中,时间的概念是有计划、有目的、呈线性展开的历史时间。马骊文这种对女性时间的别样逻辑,独立于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之外,女性时间也从“他者”的时间规定中脱离出来,获得了女性较为完整的影像再现。一种新的女性时间叙事,女性时间视角被发掘。
其次这两部电影在场面调度、画面构成上强调了女性的空间感觉,倾向于室内空间或室外小空间的拍摄。显示了女性营造自我空间的渴望,公共空间的隐退和私密空间的浮现是其电影的重要特征。在80、90年代的女性电影中,核心主题在于表现女性的社会实现与女性性别自我之间的矛盾,女性在公共话语层面的成功是女性政治表达的主要策略,女性的社会空间取代了女性的自我空间。《人•鬼•情》的主人公最后决定嫁给舞台便是个突出的例证,没有比舞台更为夸张的公共空间,上面的每个人都不是自己。《我们俩》的电影空间几乎没有离开屋子和庭院,只着力于表明女性与自我、还有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主体性的女性空间。而《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也主要是室内剧的套路。女性空间的发现就是关于女性存在的体验, 略显局促的室内空间带来了如同心理空间般的局促与压抑,女性的潜意识活动是这个空间的主要内容,女性的内心之镜在这里现身。脱离大的公共空间,女性体会到作为女人的存在感,女性在自我空间与自己对话,是女性最真实最自我的存在。 我们看到,马骊文对影片中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不同于男性的逻辑,这是作为女人独有的感悟与体验,从女权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女性在男权文化掌控的时间与空间话语权之外,拥有了属于女人自己的思维与逻辑,建构了自己的时间与空间体系,摆脱了一直以来作为“他”者存在的状态,体现出明显的女性意识与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
三、女性主题及价值建构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主题聚焦于对“母女关系”的探讨,这一主题也是中国电影中女性主题的重要表达层面。影片颠覆了社会历史因素侵入性别叙事和消解女性的传统,只是从女性的视角极纯粹地解读母女关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因而丰富深刻,更为重要的是它被不加曲解地袒露出来,从电影史的角度来说,这是女性导演的性别叙事自黄蜀芹以来的又一个高峰。作为文本的叙事策略之一,影片在母女关系这一主题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刻的诠释,将其中蕴含的女性主题在充满爱与焦虑的现代女性世界中加以表述,作者关于女性自我的表述使得女性话语看来纯粹和自足。影片中,诃与母亲、女儿以及女友构成了一个自足的女性世界,这个世界由肝胆相照的温情和体贴构成,其核心是母女之情。影片表现了母女关系的本质——女儿对母亲永远的欠缺与愧疚,无论女儿付出多少,母亲的爱都是无以回报的,因而作为女儿就永恒地处于悔恨之中,也因之忏悔成为女儿终生必须背负的情感和原罪,女性的自我挣扎和困顿都取决于这本就矛盾的情感之源。它讲述我们的感情,折磨我们的感情……以一个特殊的视角揭示最为隐秘的情感和生存关系,展示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地带。没有哪一部电影比《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可以告诉人们更多的,我们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父母。电影中的事件、人物、矛盾、细节,充当了现代社会亲情意识觉醒的代言人。影片的可贵在于,提出了我们正在面对和经历的复杂问题:我们都是父母的子女,我们都会长大,我们都有可能成为父母,我们不再为物质而挑剔,但是,我们要求下一代人给我们更多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安慰。电影通过银幕形象,使观众超越了自己的生活,化为银幕上的那个女儿,能够使我们重新感觉内疚、自责、忏悔,体验曾经熟悉、经历、忽略了的东西,唤起我们的良知。
《我们俩》的主题没有《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那么鲜明和有所指,在马骊文独特的视角下,在其感性、细腻的叙事中,影片执着于对女性心灵世界的探索,富有浓厚的人文精神。马骊文的表达是温和的、散文化的,微微弥漫着一种诗意的,爱的柔光。非常写实的框架里包容了思想交锋的巨大含量。生命与人的有限性、孤独感,情感精神的无限性、审美性交织在一起,节奏明快情节跌宕起伏,主题广泛而具有普适性。她着眼于人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凡人小事背后的心灵动荡的阵阵涟漪,小影片大波澜,小制作大人生,小故事大道理,小叙述大胸怀。该片折射了社会现实中传统家庭的萎缩,人际需求的变化。生命多数情况下注定是孤独的,但是人际关系的温暖元素,生命的必要靠近和交流使生命的价值和美凸显绽放出来。人生,往往就是在无奈的悖论中走过。小马对于老人的感情更趋近于“孝”—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推崇的一种情感和关系。这种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无奈,和人们对人际关系这种温暖元素的渴望。也正因为如此,它产生得如此自然又如此深刻。《我们俩》没有对生活作任何结论,始终沿未知的方向随着人物走去。惟其没有预设使命的附着,才有面对性格和人际关系的诚实。看惯了那种以规定的价值判断,把生活编排得一清二白,开头几分钟后便知结尾,观众没有感动自己已经先感动得不行的电影,在金雅琴扮演的老房东和宫哲扮演的女学生面前也许会一阵茫然,因为它实在没有指向,不讲道理,无辨是非,而正是在所有的发展都超乎俗套的意外中,我们却渐渐走近了真实的世界。 马骊文的在《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和《我们俩》两部作品中,将女性独特的“东窗”视角和叙事风格运用到女性电影中,从男权中心的话语场中突围,重新拥有自己的镜语,以女性的敏感和对生活的独特体验,注重从人物的内心世界来透视社会的变迁。对于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挣扎有着混合的心态,或焦灼或忧郁。在个体意识与历史时空、在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穿梭”或“徘徊”,关注着女性的生命困境。
新时期女性在女性意识获得的同时又面临着被重新欲望化、客体化和商品化的危险,期待女性电影能寻找到自己的突破口,走向更广阔、更深邃彼岸世界。
注释
[1]李毅梅:《女性电影的情感视角》,《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http://www.southen.eom/ent/movie/ehinesemovie/200603090634.htm
[3]黄蜀芹:《女性,在电影业的男人世界里》。《当代电影》,1995年第5期
[4]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周传基译,载《影视文化》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