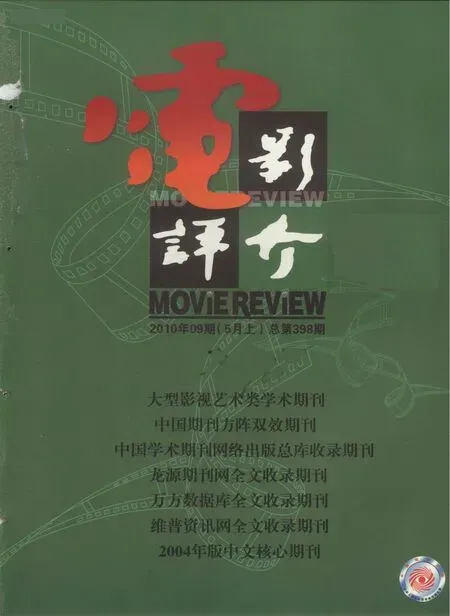莫言《红高粱家族》叙事艺术研究
2010-11-16高志,赵静
莫言1986年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随后,他又连续写了相关的几个中篇,并将其结集为《红高粱家族》。成为莫言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对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其为“寻根派”,称莫言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骁将”[1]。李洁非认为莫言是先锋派,“在莫言哪里,小说写作超越于‘讲故事’这个层面’……”[2]《红高粱家族》的叙事模式成为以后小说写作模式暗流,其中叙事特色达到了写作的高峰,彻底颠覆了以往传统小说写作的规范,他不仅汲取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叙述特色,还结合了中国传统野史的写作特点,从而使《红高粱家族》成为一个经典的文本,对其进行细致的剖析,对理解其他作品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虚构叙事和历史叙事
1985年,当代文学开始了“寻根小说”的创作潮流,莫言也深受其影响,开始创作文化寻根小说,《红高粱家族》成为其文化寻找的起点,《红高粱家族》作为“新历史小说滥觞的直接引发点”,典范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从‘启蒙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3]的审美过渡,从而极大地开拓了现代中国历史叙事的文学空间,作者从此开始从历史沉积中寻找文化活力因子,那么,莫言就找到了民间本土文化,但民间底层文化存在处于自由意识状态,很少留笔于正史写作,所以莫言的叙事存在虚构叙事和历史叙事两难境地,如何处理民间存在和正史写作、人物行动和人物思维、场景虚构和真实情态的写作悖论成为作者叙事的关键点。
首先,莫言在创作完声称,《红高粱家族》里,“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4]可见作者认为自己的创作完全是虚构的,作者的言论可能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也可能是作者的真实创作实态,此话真实与否,都说明作者创作存在着虚构的叙事,所以陈思和教授评价《红高粱家族》,“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把全部笔墨都用来描写由土匪司令余占鳌组织的民间武装,以及发生在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中的各种故事。”[5]无论是小说的经典场景“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地”,还是小说中爱绝狠绝的爷爷和奶奶、狡诈至极的冷支队、执着至极的江队长,都有作者虚构因素的介入,所以作者坦白“我确实不曾看到过如此浩瀚的高粱地”、“小说中的世界是我创造的”[6]。小说中用了大量修饰词、排比句式来突出高粱及其组成的场景,通过写高梁的颜色、气味、冲击力、诱素,利用丰富字词复沓来创造出超越物体实际存在实态的氛围和意象,使叙事效果更加突出,予读者的印象更深。
作者远取古代传统的侠义英雄写作模式,近取十七年文学中革命英雄写作型范,综合变异,写出奶奶爷爷的大爱大恨,超越了世俗,在中庸文化为主流意识中国,这样的书写只能是凤毛麟角的,最多只是文学作品的美好愿景;而爷爷的的土匪(引寓侠义)之爱—杀死单家父子—单家做活计—不被奶奶认可—耍懒混日—出酒显胜—接纳为主人—继续土匪生涯—与恋儿同居—奶奶怒找黑眼—爷爷与黑眼拼命—奶奶原谅爷爷—奶奶抗日牺牲——爷爷为其出大殡,这个叙事流程可明显看出有传统英雄传奇、才子佳人的故事影子。而作者借华北平原民间的叙事资源来写这个“英雄”传奇,20世纪上半叶多如牛毛的土匪,旱涝保收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地,民主思想的政府官吏,民间制酒业的兴盛,娶亲财礼的看重,鬼狐故事流播,作者在这些民间资源上取舍夸贬,使虚构叙事有了一个真切的具体可感真实细节,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境,真实的模型,从而写就了一个非历史的历史。“把西方重表现的现代艺术与我国重再现的传统写实艺术结合起来,用最现代的叙述手法表现最中国化、最民族化的生活。”[7]
作者对一些涉及战争团队的历史,则采取民间视点,以底层文化底蕴、文化积累为见解的基础来评判,把国民党、共产党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历史,土匪的斗争史、八路军的战争史渗入了其小说叙事之中,但作者从民间的立场对历史进行了新的阐释,“我们心目中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民间状态是与‘红色经典’中所描写的历史差别非常大的。我们不是站在‘红色经典’的基础上粉饰历史,而是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4]作者从自己的角度、民间角度出发,虽然言辞有所闪烁,但把自己模糊等同于民间,也透露出一个信息,《红高粱家族》从正史相对的立场为基点去写,有了野史的意味,虚构性、意狎性随即而生,也使叙述真正有了诱惑力,有了多维理解叙述历史的角度,凸显了陌生化效果,作者巧妙地处理了民间存在和正史写作间的关系,也唤醒了文本的生命力。
“爷爷”——余占鳖的行为完全背离了他的日常思维,骂失信的冷支队为“狗”,但还是孤军伏击日本兵,损失惨重,但还是坚持到底;说不给胶高支队枪,但最后还是赠与了很多。这些用戏仿的叙述手法塑造了人物形象,从人性的发展趋势角度度测了人物性格的发展,使虚构叙事在大的历史语境中自由的穿梭,也渗透了叙事者的观点,叙述者以崇拜其祖父的话语倾向来结构叙事,使叙事话语意识形态更加民间化;但作者身为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修养,叙述者的声音言语中也受到正史熏蚀,叙述的言语呈现多声部。
小说所叙述的场景脱离本土的真实情态,升华了日常高密东北乡地理风物、乡俗生产、人物性格,带有极具夸张化、极端化、神秘化的特质,使小说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卓异。这样叙事创造了典型的场景,但也有风物真实情态做基础,但有异于此,使真情事态涂上一层对比鲜明的油色。“如果说此前的长篇写作一直是以主流社会生活为写作空间的话,那么莫言则是建立起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民间世界,并将这一世界的精神价值作为了主题与艺术的最终旨归。”[8]
二、事实时间和叙事时间
《红高粱家族》有其独特的时间叙述结构,结束中国以往传统线性叙述范式,开创了新的叙述形制,这是作者借鉴了中外名家的叙事策略,尤其西方新叙事理论,使其更好的处理了事实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关系。
《红高粱家族》贯穿了一条主线:爷爷的一生经历,即上文介绍的叙事流程,围绕这条主线,是一条条的侧线,说明相关人物的情况、行为、风物、传统,通过插叙、倒叙、补叙的手法杂错来结构全篇,使事实时间在叙事时间的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从而叙事时间和事实时间有效统一起来。小说中的五章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但总起来才能隐现一条完整的时间流程,但章序是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放在一起组成集子的,所以每一章中有一总体的时间段,即事实时间,每一章事实时间还是较为明朗,符合阅读传统习惯,但从整个小说时间来看,每一章并没有按事实时间来排列:红高粱(A)—高粱酒(B)—狗道(C)—高梁殡(D)—奇死(E),其事实时间是:B—E—A—D—C,这种叙事错置了事实发生时间,为读者造成了陌生化效果,适合接受美学信息抑制、断点理论的要求。
在每一章里,作者叙事时间中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以事实时间为主,同时插叙、倒叙、补叙,转换视的焦点,使事实时间移位,在叙述中导致信息延宕和全知叙事暂时断点,引起阅读障碍,同时也诱起阅读期待,因为《红高粱家族》采取的是全知叙事,读者对未来叙事可然性充满期待。华莱士•马丁认为:“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递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的后加上去的,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9]
同时,章内的叙事时间考虑到读者的阅读疲倦长度。叙述者在一定长度的叙述后,进行插叙、补叙、倒叙,一方面转换叙述视角,体现陌生化效果,一方面解决阅读疲劳,造成信息断点。如在“红高粱”章节中,开始叙述奶奶送爷爷父亲去伏击日寇,在315字后,转换到“我”的成长对高粱感受,460字,转入队伍行进793字后,插入王文义故事,193字后叙述时间开始,余占鳖队伍行进,661字后插入父亲捉螃蟹的趣事,972字……这种不断插入的叙事时间,使时间呈现多维性,同时带动了空间变换,造成新鲜的场面、新的叙事信息,就像作者的语言修饰词一样丰富多姿,体现了现代社会陈置庞杂信息的特点。具有现代叙事的明显特征。并且插入的叙事多为趣事、风俗、残酷的事实、乡土文化等,有力支撑了事实叙事,使主线叙事丰满起来。
小说内的信息断点大部分能够在以后的叙事中连接起来,但也有一部分信息断点成为永久的断点,留下一些悬念,“暂时断点丰富了阅读体验,譬如悬念就是暂时断点的结果,它在阅读过程中激起欲望而尤抑制满足。”[10]但大部份信息断点问题的随后解决,为小说提供了一个整体的事实时间,为完整的故事提供了可能;而少量的永久的断点则为阅读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事实时间和叙述时间都走向了未来,具有了永久生命。
《红高粱家族》的叙事艺术独特新颖,与以前的中国小说的叙事大相径庭,并开创了小说叙事的新纪元,作者在历史叙事和事实叙事、时间叙事上既有西方的理论影响,又有中国民族特色,为以后的叙事提供了经典的仿效范本,本论文就从这两个角度进行了新的分析,以期对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同时,限于篇幅,本论文没有对莫言的语言进行分析,其语言不同于其他作家,辞藻繁复,修饰丰富夸张,戏仿幽默,大量使用通感,地方土语混用,对此分析本文将在新的论文中进行剖析。
[1]“新时期小说流派研究”课题组•新时期小说流派[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4):128。
[2]李洁非•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史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4):98。
[3]王彪•新历史小说选•序言[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5。
[4]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J].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2(1):10-14。
[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17。
[6]莫言•与莫言一席谈[J].北京:文艺报,1987年1月17日。
[7]金汉总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543。
[8]张清华•《红高粱家族》与长篇小说的当代变革[J].广西:南方文坛,2006年第五期,P50。
[9]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58一159。
[10](美)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