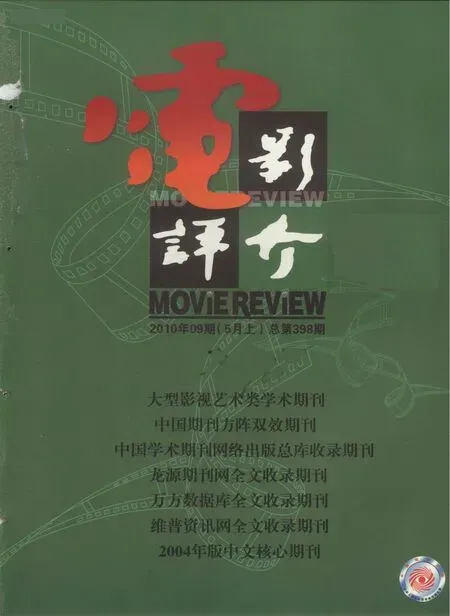莎剧《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一场的内涵与审美价值
2010-11-16王宏刚,穆亚一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一场的地点是在教堂墓地。观众往往认为“墓地”这一场的前半场与全剧没有关系,是多余的。因为,看起来这部分确实与剧情的发展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假如将这一部分删除,也不会影响剧情的完整性。但是,也有不少批评家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部分与全剧有关系,并给出相应的理由。索天章先生在论《哈姆莱特》时说:“可能由于我们理解不够,认为某些段落是多余的,其实不然。”[1](P196)确实如此。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批评家所给出的理由,也并不充分,他们缺乏对作品本身的深入理解。所以,重要的是需要领会作品、考察已有的各种观点,深入而合理地阐释“墓地”这一场的内涵,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它对于塑造人物、表现主题的意义,说明它的审美价值以及它与全剧的关系。
一、丑角对生存之境的戏谑式揭示
我们先来看“墓地”一场中的小丑。小丑甲问乙的问题是:“谁造出东西来比泥水匠,船匠或是木匠更坚固?”小丑乙回答说:“造绞刑架的人;因为一千个寄寓在上面的人都已经先后死去,它还站在那儿都不动。”而小丑甲的答案是“掘坟的人,因为他造的房子是可以一直住到世界末日的。”他们的问答荒诞而机巧,细想又似乎有道理。哈姆莱特和霍拉旭上场后,小丑甲且掘且歌,断断续续的唱了一首滑稽而玩世不恭的歌曲。[2](P398-401)
一些批评家注意到了剧中小丑的作用。孙家琇认为哈姆莱特从掘墓人的态度领会了死亡是人生必然的终结和自然现象,感到死亡本身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不白做人,关心自己的名声。[3](P57)卞之琳认为掘坟人唱的民歌流露出了“人生如朝露”的感觉,表现了热爱生活、抓紧生活的时代精神和要求。这种人生观也影响了哈姆莱特,给哈姆莱特的下一步行动,“打稳了哲学基础”,因此,到下一场临死的时候,他泰然面对死亡,又那么在乎自己的“名字”会受到“伤害”。[4](P72-74)两位评论家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是合理的。不足的是,他们都主要是从掘坟人的态度对哈姆莱特的影响,来看这一场戏,而较少对小丑本身展露的意义进行分析。尤其没有明确阐释小丑的荒诞问题及答案。从剧情看,哈姆莱特只是惊奇小丑“在掘坟的时候还会唱歌”,我们看不出小丑所唱的歌曲使他特别在意。并且在小丑甲和乙问答的时候,舞台上只有他们俩,哈姆莱特还没有上场。所以,仅从小丑对哈姆莱特的影响这一角度看问题是不行的。
小丑的问答和歌曲看似荒诞滑稽,实则有着深长意味,有着真理性。诙谐与严肃往往是正反同体。索天章先生就认为,莎士比亚描写的下层人物一般给人的印象是粗俗可笑,但是有许多一针见血的话是通过他们之口传出来的,“尤其是他的丑角,有时成为作者的代言人。”[1](P273)其实,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许多作家就是借“小丑”或“疯子”,传达真知、真理。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就指出,拉伯雷把小丑和愚人描绘为圣徒和先知。小丑[1]摆脱了官方世界的评价体系及其严肃性,摆脱了个人物质私利,摆脱为家庭和个人事业斤斤计较的小算盘,故他们能够说出真理的语言。[5](P234)
两个小丑的问答到底展露了什么意义?他们的答案是说:造绞刑架的人、掘坟的人造出来的东西,比泥水匠、船匠或是木匠造的更坚固!换句话就是,绞刑架、坟墓,比房屋、船或家具更坚固。显然,我们若真去比这些东西哪个更结实耐用,是比不出来的,会觉得这样的比较太荒唐。不过,我们换一换思路再去想,就会触及到一种严肃的意识。绞刑架和坟墓都与死亡有关,是死者的寓所;房屋、船和家具与生存有关,是生者的器具。那么,小丑的问题莫不是对生与死的隐喻式的述说和比较吧?死者的寓所比生者的器具更坚固,死比生更“坚固”[2]。死亡是必然的、不可移改的、给人强烈的触动,是永恒的题目;生则是暂时的、易受损害的、易被忽视的、颠沛而痛苦的。
小丑的问答不是符合科学认知的推论,而是从谜面到谜底的隐喻。小丑的谐谑中暗藏了玄机。它是对人的生存之境的戏谑式揭示。
莎士比亚常常利用独白,或者利用对话,或者偶而的只言片语,达成了对人的生存之境的深刻彰示,悲剧人物就是置身于此境之中沉吟或前行。“小丑的问答”这一段正是起这样的作用。
二、哈姆莱特对虚无与意义的探问
掘坟人在墓坑里且掘且歌,先后掘出三个骷髅[3],把它们扔到地上,骷髅里塞满了泥土,颇为触目。
面对此番情形,哈姆莱特痛苦的心灵又亢奋了起来。他推想死者生前是心机算尽的政客、朝臣、律师、地主,或者是最会开玩笑的弄臣;感慨和嘲谑他们死后都成了一无所能的、脱掉了下巴颏、塞满了泥土的小小的脑壳,任放肆的工役用肮脏的铁铲敲来打去。接着哈姆莱特推想古代的亚历山大和恺撒死了、被埋葬了,也化成了尘土,变成了泥巴,被人们用来塞酒桶口或填填破墙上的窟窿。
哈姆莱特的这些推想确实让人觉得是奇思异想,而且出言不逊、亵渎死者。霍拉旭就认为这样想“未免太想入非非了”。哈姆莱特的言语似乎不像是出自于冷静理智的心里,倒像是疯人的妄言谵语。但是,只要我们不迷惑在虚妄之中、不欺骗我们自己,敢直面人世的罪恶、庸俗和虚无,哈姆莱特所说的又何尝不可能是事实呢?“疯子”[4]常常正是真理的宣讲者,残酷的事实令他发疯,世故昏昧的人则常把讲真话的人说成是疯子。孙家琇先生就认为,哈姆莱特面对社会黑暗而上下求索时,有时他的“想入非非”,达到了哲理的深度。[3](P49)
正因如此,评论家们都很重视对“墓园”一场中哈姆莱特的“想入非非”进行阐释。孙家琇说:“(这一场)借墓地骷髅挞伐政客、朝臣、讼师、地主、风骚女人等等的钻营和无耻。”[3](P32)卞之琳说:“哈姆莱特借坟墓里挖出来的骷髅的题目,痛快淋漓地发挥了对于社会罪恶的控诉。”[4](P74)陈惇也认为“哈姆莱特与两个掘墓人的插科打诨式的对话中,更是集中揭露了社会上种种不义的现象,……”[6](P124)综观几位评论家的观点,我们会看出,他们都是从批判社会现实的角度,看到了哈姆莱特对“社会罪恶”的“揭露”、“挞伐”和“控诉”。
几位评论家的看法确实有道理,不过,他们的看法并不全面。试想,哈姆莱特嘲弄了政客、律师、地主的不义和无耻,可他并没有说出一个词语来“挞伐”亚历山大和恺撒,说他们不义或无耻。那么,为什么哈姆莱特要由政客、律师、地主和弄臣推想到亚历山大和恺撒?为什么要将他们都相提并论呢?为什么要推想亚历山大在地下“也是这副形状”、“也有同样的臭味”?为什么要推想“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2](P404)显然,哈姆莱特的推想并非着意于“挞伐”不义者的丑恶、赞赏古代英雄的高贵,相反,哈姆莱特以敏感的神经意识到了世人的相同终局,这正是他“想入非非”的兴奋点。上述几位评论家只是看到哈姆莱特的话所起到的一种客观作用,而没有注意到他的主体意向。
在哈姆莱特的推想和沉思中,他意识到了世人的相同结局便是“死亡”,化成了泥土,甚至被作了“下贱的用场”。哈姆莱特较多的是从现在的时间点上,目击或推想一个个死去的人“现在的”、“如此的”或“可能的”形状和下场:“现在却让蛆虫伴寝,(指朝臣)……”“他(指律师)的玩弄刀笔的手段,……,现在都到哪儿去了?”“现在你(指弄臣)还会挖苦人吗?你还会……”“现在他的脑壳里塞满了泥土,这就算是他(指地主)所取得的罚款和最后的赔偿吗?”“恺撒死了,你尊严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5][7](P228-236)[2](P400-405) 在哈姆莱特捧着塞满泥土、发出臭味的骷髅时,他看到每一个人的结局是相同的,都是“现在”“这副形状”。不管是高贵的人,还是低贱的人,不管是高尚的人,还是卑鄙的人,伟大的人也罢,平庸的人也罢,死后一切皆为泥土而已。
在哈姆莱特的推想和沉思中含藏的一个问题,就是,人能不能超越死亡、实现超越个体有限生命的价值?灵魂能不能不朽?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哈姆莱特。在不同时候他似乎有着不同的考虑。他有时看到反抗的价值和灵魂的不朽,有时看到的则是生存的苦难和虚无。在“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里,他认为生存是无涯的苦难,死亡是未知的噩梦;在他要“重整乾坤”的时候,他看到了个人的伟大价值;在他放弃杀死正在祷告的罪犯时,他相信地狱和天堂的存在,相信灵魂的得救和永生。在“墓园”一场,面对骷髅,他没有仰慕和向往亚历山大和恺撒的伟业,没有言说灵魂在肉体化为泥土后会继续永存,他只是看到每个人的终局都是“这副形状”。他似乎看不到个体生命超越死亡的终极意义,他的思想陷在虚无感的深渊之中。
哈姆莱特是悲观的,还是不悲观?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他在沉思时流露出虚无感,就认定他是悲观的,或认为他否定人生的意义。虚无感本身就是对意义的探问的表现。生命在延续,就会向不同的方向探询,每一个方向上都可能是险滩或深渊。哈姆莱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并不仅仅因为他歌颂人是“宇宙的精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作为人在沉思和探问人自身、在行动。
三、庄谐同体、沉潜动人的审美价值
莎士比亚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大师,“墓园”一场就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独具的一些艺术方法,和沉潜动人的多重审美效果。
这一场的前半场中,小丑和哈姆莱特的话既有谐谑的风格,又有严肃深刻的内容。谐谑与严肃同体共存,具有双重的审美效果,适合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审美趣味。一个观众,如果他喜好喜剧性的谐谑,他可以从中得到娱乐和快意,如果他倾向于严肃的思索,他可以被引向沉思和体悟。正如塞万提斯所说,在一出精心结构的戏里,诙谐的部分使观客娱乐,严肃的部分给他教益。
有的评论家认为,莎士比亚善于在悲剧里放进喜剧成分,用以对照,使悲剧性更突出。他们就以墓园一场为例:哈姆莱特和掘坟人在还不知道是奥菲利娅的坟头上开玩笑,加强了他后来在知道了就是奥菲利娅的坟头上发作的痛苦。[6]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其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哈姆莱特和掘坟人的话单纯是喜剧性的,认为喜剧性的成分和悲剧性的成分是前后分开的,分属不同的情节,而没有认识到在同一情节内诙谐与严肃、喜剧性与悲剧性是共存的。卞之琳就批评了这一观点,并指出“这里也不是纯粹的轻松”。[4](P72)
小丑的怪诞的问答和歌谣,哈姆莱特面对骷髅的推想,都有着民间诙谐文化的风格,他们无所顾忌、任自己的心思发挥,决没有宗教家或道德家的腔调。小丑的“什么人造出的东西更坚固”的谜语及答案,无须逻辑学的证明。小丑掘坟时一点也不需要严肃行事,他唱着俚俗的歌曲,他把歌曲的一些片断乱搅在一起,还不时夹入由于干活用力而发出的“喔”“呃”声。哈姆莱特面对骷髅,既没有想它们有灵魂,也没有敬畏他们活着时的功业,只是快意的嘲讽它们,嘲讽它们活着时心机算尽、煊赫一世,到“现在”都化为泥尘。我们可以想象,剧中的这些诙谐的动作,无所顾忌的言谈,一定引起了观众的笑声,观众被带“动”了,甚至也蠢蠢欲动地想要加入到这狂欢放任的举动中来。但许多观众随即可能会沉潜下来,剧中人物的话语透射出的严肃问题,使他们在狂欢的队列中放慢脚步,他们随小丑看到了死亡的永恒、生存的易损,随哈姆莱特似乎看到了生命的虚无。就这样,一些问题在明澈地浮现。
第五幕是全剧的高潮和结局,从掘坟人和哈姆莱特言说死亡,到奥菲利娅的葬礼,再到险恶的谋杀、复仇、意外的屠戮、陷人自害的结局。它给人的感觉是激烈的、痛苦的、阴毒的,但又是沉静的、安详的、明澈的。它言说死亡,也在呼吁再生的意志,其主题是毁灭、也是再生。“墓园”一场正是这一幕的序曲,在诙谐狂欢式的行动中呈现着这样的悲剧审美特质,孕育着这一崇高的主题。
注释
[1]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小丑”是艺术形象,他不是一般的日常意义上的怪人或傻子。巴赫金认为在文艺复兴时代,在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的作品里都有怪诞形象,这些形象是中世纪诙谐文化的典型人物。参考《巴赫金文论选》第154页、第103页。
[2]坚固,莎士比亚用的是stronger这一个词。(可参考《哈姆莱特》原著英文版。)这个词还有多种含义:不易损坏、伤害,强烈的,有力的等。
[3]在希腊,有一位演员曾把他的头骨献出来,作为上演《哈姆莱特》中掘坟一景之用。(据《罗念生全集》第9卷第144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4]这里的“疯”并非一般日常所指的发疯或病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疾患,而是指一些言行疯癫怪异,但有着敏锐深刻的思想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和文学作品中都并不鲜见。索天章评论《李尔王》时说:“李尔是个真疯,……他的疯话充满了深刻的真理。”(参考索天章著《莎士比亚的悲剧》。)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表现这样的人物的经典之作。
[5]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加着重号的词语都是朱生豪先生从原著中直译过来的。
[6]阿达姆斯的《<哈姆莱特>诠释》(1929)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例。陈惇的《莎士比亚的生平及其剧作》也认为莎士比亚在一个剧本中“把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结合在一起,这也加强了情节的生动性”,并具体说到,《哈姆莱特》第五幕“就以掘墓人的插科打诨式的场面开始。”
[1]索天章.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及其时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2][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五)[Z].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孙家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4]卞之琳.莎士比亚论痕[M].北京: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1989.
[5][俄]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陈惇.莎士比亚的生平及其剧作[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7]Shakespeare, W.HAMLET [Z].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