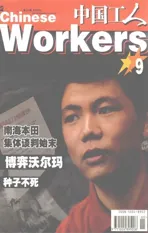种子不死
2010-11-15人与自然编辑部主任
《人与自然》编辑部主任 赵 彦
种子不死
《人与自然》编辑部主任 赵 彦
人们有着美好的面孔,血淋淋的欲望,贪婪,不耐烦的装模作样,热爱真诚的掠夺——这样的芝加哥,在1968年的诺曼·梅勒看来,应是美国最后的美好城市之一。当商业巨头们忙着修改城市的高度和宽度的时候,艺术家们开始忙着修复人性了。
2010年,人们仍旧有着美好的面孔,血淋淋的欲望,贪婪,不耐烦的装模作样,热爱真诚的掠夺,艺术家们仍旧在忙着修复人性,商业巨头却开始疲惫地拍拍手中的泥灰,在狭小的郊区田埂上曝席而坐,虚胖的肥脸以与足球和同世界杯的球门相等的疏离度与安全帽底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听说全部要零碳了,是真的还是假的?
据说,这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要讨论的主题。
我假装自己是一名真正关心环保事业的媒体人,在再三犹豫之下洗去文学爱好者脸上通常都会有的模糊的愁苦和低能的自恋,喜气洋洋地来到了人头济济的世博园。我可疑地琢磨着自己是否真正对这样的主题有兴趣,是否真正关心一些城市的未来,是否真的相信“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从某种意义上,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因为现在有点话语权的人全部生活在城市,因为他们自己正被城市所折磨:时间被壅塞的交通零打碎敲,情感被网络的快捷压缩和磨损,肺部被污染,孤独被放大,精液被稀释,子宫被囊肿,死亡被精确估算以至于正在渐渐失去神秘性。生存整整齐齐,就像产品。但另一面,他们看到周围的世界又是如此不稳定,恐怖事件、石油危机、核试验,人们的行为模式变得如此堕落,人与人的关系没有深度,草率,令人无法捉摸。与此相适应的是,艺术家们对现实的把握也开始变得很不坚实,偏执、厌恶和情感的放纵有时候成了他们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
很多年前,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就开始感慨了,他觉得现在的城市已不再是一个地方了,而仅仅是一个环境。比如南布朗克斯、克利夫兰、底特律、圣路易斯,都一样,不再是地方了。所谓地方,就是有地域性的环境。其实,反思城市文明的命运不止贝娄一人。现在,我估计最没有见识的中国农民都会感慨我们的城市已经变得没有特点了,当他们来到上海后,发现所有的城市都一样,包括北京和纽约,都是高楼和公路、人和机器,不再有陌生感;相反,另一种存于人内心的陌生感却在扩大和加深。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园内,修筑在美洲区的智利馆是其中一个很不起眼的国家馆,说不起眼是因为智利这个南美国家的经济活动在全球几乎没搅起过什么波澜,世博游客的势利惯性会将一个国家馆的热闹程度与它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等同起来,几个动辄排四五个小时长队的“大馆”总是和它们的国家在经济领域及文化生活在全球的享誉度不无关系的。但是智利馆却做得一点也不第三世界,几乎全木结构的内装修,钢管废料和木板废料叠加的一个螺形空间,甫一进门,一条猩红色的滚动电子问话立即让人沉静下来:我们把城市称为大街、高速公路、楼宇,有时候还称为我们的家园。什么是城市?当今的城市为我们提供什么?
是啊,什么是城市?当今的城市在给我们提供什么呢?
说到城市,不得不提到城市的历史。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往往以建成的历史开始。在西方的古代,人们以神定城邦,幽灵、魔鬼、英雄,都可成为他们的护邦神。每一座城邦都有一个神,神护佑他们,使他们免受灾害和外邦的侵扰。但是古人并不太相信神的友谊,因为神多欲且易怒,既不够忠信也不甚友好,动不动就与人发生争执。于是,惟恐神抛弃他们,人们要取悦他们,贿赂他们,这样,渐渐地人们有了敬畏。这些神,全部是自然的化身,如阿波罗神就是太阳(驱夜或者除恶神),福玻斯神就是闪电,波塞冬是海神,赫斯提亚是炉灶和火焰女神,伊丽丝是彩虹女神,阿尔忒弥斯是月亮和狩猎女神。一方面,大自然的瑰丽使人心仪,另一方面,大自然的威力也使人怯懦。人与神有史以来就这样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关系中。现在,我们的城市没有城邦之神已经有很多年了,很多年前,人们就与神分道扬镳了:人们发明了电,驱走了用来阻挡黑暗的太阳神和月亮神;发明了船舶,征服了性情乖戾但魅力知性的海神;发明了网络,废黜了传递信息的彩虹神。十九世纪之后的城市彻底成了人们自己统治自己的城市,人们更加相信自我的力量而不是自然的力量。但是工业机器虽貌似完美却内蕴着令人抓狂的错误设计,因为它假定资源可以被无限利用这一个前提。城市被我们自己统治了两百多年之后,又变成什么样子了呢?这也是这届世博所关注的主题——虽然我对此次世博会许多主题馆颇有些微词,觉得多数教化痕迹太重,但不得不承认它们在表现各类主题时用尽了心思。在浦西城市地球馆的“地球危机”展区里,策展人就非常巧妙地用“金、木、水、火、土”五行作为展示元素,演绎了地球的“五大变形记”。他们用仪表、漏斗、水龙头等道具,形象地表现地球的有限资源正在不断减少,揭示地球的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现象。换句漂亮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曾经居住在我们城邦里的神病的病,倒的倒了,我们面临的将是一种将护佑神变成敌人的危险。在城邦里,本来人与神之间就应该订有一个契约的,人神互惠相通,人若只是无度地索取而不供养,神就不再护佑他们。我们普通人都是肉身订制的,并不高贵,多数人被欲望束缚,被身体所限制,无法自觉地启用这个世界用来操控我们的诸如理想和义务等修辞手法,误以为不可触摸的东西不可能有意义——于是,神就来惩罚我们了。
神对我们的惩罚有两种,一是自然对城市的环境惩罚,二就是城市对人的心灵惩罚。前者的修复寄希望于科学家和环保学者们——这也是2010年世博会的最急切要讨论的,各种层出不穷的低碳和零碳居住方式,正是出于对先前挥霍的一种纠正。但实际上修复自然比我们想象要容易,只要人类一放手,物种的恢复和壮大数年甚至数月之间就可以发生。美国亚利桑纳大学的阿兰·魏斯曼教授曾经预言过如果人类消失,一年之后,分布在城市中的柏油路面会被生长的草木所侵蚀和破坏,被废弃的房屋很快会被霉菌和苔藓所覆盖,而由于工厂不再运转,空气将会重新变得清洁起来;五年之后,城市街道和公路会布满裂缝且其中充斥着绿草;二十年之后,曼哈顿这样的城市将会重新变为沼泽和湖泊,植物重新繁盛的城市将会被野生动物所占据,其中不但将包括狼、野猪和鹿,还将包括重新“野化”的牛、猫和马;一百年之后,原先连接各个城市的道路将不复存在——残存的沥青和水泥将会被沙土和落叶所覆盖,曾经的田野将变为森林;五百年之后,处于温带气候条件下的城市中将只能看到茂密的森林;一百万年之后,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拯救似乎不费什么力气,只要人类知趣一点,自行消失。可是人类能消失吗?
有人将现代生活比作是一个使用外语的异国他乡,在熟悉的土地上,自己成为了陌生人。城市生活让我们成为陌生人,成为一群最及物的人,成为失去家园的人。就这个文学主题而言,没有谁能写过卡夫卡了。可以说,卡夫卡制服了我们对于现代城市的可疑的想象。不知是不是因为布拉格城市(那时候布拉格属于奥匈帝国)出产过卡夫卡的缘故,捷克馆一直是我努力在向朋友们推荐的国家馆——我一直对捷克、波兰这些小国家抱有好感,因为这些东欧国家经历过深重的民族苦难,更懂得自省和救赎,更有绵长的人性深度。捷克馆不大,但处处是细节,有动漫,有科技,有文化,有历史。其中有一件叫做“大都会”的装置艺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件牢牢地被钉在天花板上的“大都会”作品是一座由废手机壳、电脑键盘、电线、铁丝、玻璃等组成的“城市”,这个“城市”与我们生活其间的城市何其相像:机械,苍白,荧光,过度加工,理性,无用,不性感,不甜蜜。这个“大都会”一诞生就被迫具备了废墟的气质,散发着某种占有和控制的气息,毁灭与新生俱存,一切都是即时的,令人绝望。的确,城市化进程对人类心灵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异化和戕害:技术导致抹杀差异,人被物化,心灵变成了可度量之物,忧郁成了避难所和安慰剂。平克·弗洛伊德在《迷墙》里的唱词:
我们该用什么去填补剩余的空间
我们过去在哪儿交谈
我怎样去填补最后的空白
我怎样才能完成筑墙
现在这个时态已经被工业所毁灭了,妥帖一点的未来时态又怎样呢?未来看样子也已被技术所牢牢地掌控了。在世博会的未来城市馆里,世博专家为我们所设想的我们的未来是这样的,城市以后将是一座“生态之城”、“智慧之城”、“水之城”、“太空之城”、“能源之城”。特别是智慧之城,我相信这对所有惧怕高考的学生来说是一种解放。根据城市未来馆设计者的推想,未来我们市民的大脑是用装载了各种信息的芯片来构成的,不用学习就可以据有知识,知识就像基因一样,可以继承也可以植入。这让我想起前年意大利学者艾柯与法国电影泰斗卡里埃尔的一场精彩的对话。当这两位大师在聊到人们如何保存记忆的时候,卡里埃尔说,将记录和更新知识的任务交给机器当然很省事,这样人们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认识上,只剩下智慧,会很轻松!可是事实上,这是最不可靠的一种记忆存储方式。只要稍稍来一场生态灾难,或人类因意外或损耗而消失,人类文明就会被清零。这样,现代人又被变成原始人了。我固然也想通过大脑芯片变得像艾柯和卡里埃尔一样博学,可我觉得这里边有一种比有可能发生一场生态事故将人类文明直接清零的灾难还要可怕的灾难:如果人类大脑变得同一,若干年后,我们的图书馆将不再由多位作者的作品构成,而只剩一本书。思维的千变万化将由一部机器代替。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提到技术的时候,我像所有那些保守派一样表现得很悲观,我固执地认为技术是对所有看得见的事物的一种描述,而像死亡、爱欲、幻想、梦境那样的东西永远不能被设计和描述。我有一位文学修养不错的朋友有次颇得意地对我说,除了电灯,其余电器他一概不知道怎么使用。他的自得里有某种示炫的成分,好像文学和科学是一对劲敌,承认一方弱就是表明另一方强大;要表明自己在某一领域的天赋必定要以另外一领域的弱智作牺牲。虽然我讨厌他的矫情,可我知道他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不想把自己的生活降低为技术,他不想把除肉体之外全部变成工具。可在世博会上对于未来城市的几乎所有的描述只让我看到技术:我们关心的不再是思想,我们关心的也不再是凝视。
我只在英国的种子圣殿跟前流下了眼泪。这是唯一能让我流泪的展馆。在其他馆,我的时间都被好奇了、惊叹了、羡慕了、折服了、缭乱了、明天了,唯有英国馆让我在进去的第一时间感动了。在由长达7.5米的60858根“触须”亚克力光纤构成的这座种子圣殿里,内嵌了英国千年种子银行自从1990年代以来收集的上万颗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植物种子。“种子拥有着无限可能,蕴含着无限变化,也代表着希望和创意,通过各种各样的种子,英国馆体现的不仅是现在,更是拥抱未来的理念。”设计师的解释通俗而简洁,据说这也正是英国托马斯·赫斯维克建筑设计事务所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夺标的原因。《新约·约翰福音》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种子给予我们未来,这未来不仅仅是技术的未来,更是思想的未来。种子,是给予我们犯错后纠正的机会的。我们之所以有出生,是为了来纠正我们的父辈的缺陷,为了修正,为了更新。我们不仅是用种子来保存和恢复物种,更是用它来传播理念和理想。
因为有了种子圣殿,一切都还来得及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