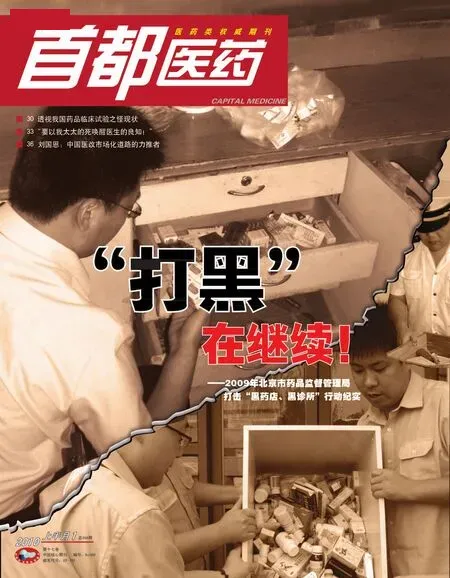“要以我太太的死唤醒医生的良知!”
——对话北大医院事件受害者熊卓为之夫王建国
2010-10-20

49 岁的北大医学教授熊卓为因腰椎骨关节病病发到北大第一医院就诊,2006 年1月31 日,即脊柱手术术后第7 天,北大第一医院宣布,熊卓为因发生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熊卓为的丈夫王建国认为,参与抢救的主治医生是无行医资格的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且熊卓为的病历多处被修改。
2007 年10 月,王建国将北大医院诉至法院,控告该院“非法行医”,索赔500 万元。2009 年7 月,法院一审判决北大第一医院存在医疗过失,与熊卓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由该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王建国及其岳母共计70 多万元。但一审法院并未认定北大医院存在“非法行医”。一审判决后,双方均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11 月5 日下午2 点,“熊卓为案”在北京市高院二审。对此,本刊记者邀请了熊卓为的丈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国参加本期对话,请他谈谈对这一案件的看法。
记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
王建国:2006 年1 月13 日,我太太在下出租车时腰扭伤后开始疼痛。先在北大第一医院门诊接受了10 天的保守治疗,从发病到1 月23 日入院前这段时间,入院的病历本上写着腰痛10 天,其中加重8 天,其实并没有加重,门诊保守治疗的效果还不错。有几点可以证明:门诊医生没有建议她休假,她仍每天提着装有资料和笔记本电脑的两个大包上班,还参加了科室组织去密云的活动。当时我太太所在研究所的副所长张宝娓的丈夫就是李淳德,是张宝娓推荐她找李淳德诊断,李淳德吓唬说“不手术会瘫痪”,并说“这是小手术,开刀后4 天即可下床,7 天即可出院”,“手术费只需4 万元”等,随后让助手不断打电话催我太太住院。在李淳德的反复劝说下,我太太同意接受手术治疗。于是,在2006 年1 月23 日中午,我和她的学生10 多人陪她走进了北大第一医院,而没有被封存的护理记录里却写着她是坐轮椅住院,以支持“病情加重”。
术前检查非常仓促,我们怀疑很多都是造假的。肝功和血常规下午2 点17分就全部出来了,她是吃了中饭入院的,做肝功检查是无效的。第二天我8 点不到去的医院,但没有见到她,她已被推去动手术了,上午11 点多我太太被推回病房。
2006 年1 月30 日晚上10 时左右,我太太下床只走了几米远,就突然摔倒在地,恶心呕吐,呼吸困难。我大喊救命,先来了护士,然后是于峥嵘,再后来是刘宪义和一个内科大夫。他们把我太太抬到病床上抢救,我太太喊了最后一声“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妈妈”,就没有自主呼吸了。他们当时手忙脚乱,连氧气罩都找不着。有人喊口对口呼吸,他们没人做,我说我来,他们不同意。他们既没做口对口呼吸,也没插气管,只是罩上了氧气罩。同时于峥嵘去做胸部按压,随后是刘宪义做。然后推她去二楼ICU 急救室,于峥嵘骑在我太太的病床上按压。我跟着进了急救室,这时来了一些医师,包括李岩、丁文慧等,然后是院长。他们让我出来,我一直跪在外面祈祷。晚上11 点多,我打电话给胡盛寿求救,因为是大年初二,当时没找到他,后来值班医生在凌晨找到了他。我要求他来,开始院方没同意,过了半个多小时又同意他来。凌晨1 点多,阜外医院院长胡盛寿和副院长刘力生来医院会诊,胡盛寿说太晚了,即使救活了也是植物人。我说那我也要救,这时院方就决定开胸探查,1 点半院方医生李岩开始动手术取栓,胡盛寿在旁边看,在开胸时发现肋骨断了,心脏和肝脏都破了,打开腹腔满腹都是鲜血。胡盛寿出来跟我说,已经没救了,节哀吧。
记者: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而且是本院的一名专家,您爱人当初是否知道术后容易出现并发症?而且像腰椎骨关节病这样一个常见病,只有5%病情较严重的患者须选择手术,而熊教授的病情诊断是腰4 滑脱 (I 度)伴峡部裂,这种轻度滑脱是没有必要手术的,您当时为什么签字同意手术呢?
王建国:我太太是做实验室基础研究的,研究脂蛋白和心脏病的关系,隔行如隔山,对于临床完全不懂,你们可以这样想,如果她真的懂,她会去动手术送命吗?她长期在国外生活,非常相信临床医生说的话。入院当日,术前同意书是于峥嵘让我太太签字的,没有告知可选择非手术治疗方案,也没有告知她具有深静脉血栓和肺动脉栓塞的高危因素。于峥嵘当时没有受聘于北大第一医院,也没有取得执业资格。但我太太以为他是正式医生,相信了他就签了字。
记者:手术后您观察您爱人的情形如何?有没有什么不良症状?
王建国:术后第二天我太太就有了不良症状,右腿下胀痛,当时我就问李淳德是什么原因,他说是伤口引起的神经疼痛。后来又出现无力、呼吸不畅,他答复说是体位低压。我太太喊痛,他们就给她大量地开奇曼丁、泰勒宁等止痛药,这在我们的住院费里都能反映出来。李淳德24~26 日都来过病房,27 号离开的,但他没有签任何字,把一切字都让于峥嵘来签。30 日中午12 时,我太太出现呼吸困难,于峥嵘仍然没有排查和监控,只在临时医嘱中嘱护士给她吸氧6 小时。我们都以为这样处置是对的,病人怎么会不相信医生呢?
记者:我看到于峥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都是按指导医生的指示做的。那是不是说,整个术后的监测,李淳德还是在指导于峥嵘?
王建国:什么事都要讲证据,既然你说指导了,拿证据来,签字就是证据。有李淳德的签字吗?没有!他指示学生这样做又不签字,这不是害学生吗?这不是想逃避嫌疑吗?整个病历里除了开刀他签了个字,他什么都不签。在签字里他把I 度滑脱改成II 度滑脱,以掩盖没有手术适应症的事实。
记者:悲剧发生后,您怎么发现北大医院有医疗过错?
王建国:最开始是我的代理律师卓小勤研究病历时发现了问题:第一,我太太是腰椎I 度滑脱,病情仅10 天,经保守治疗已好转,没有手术适应证,然而医师却违规为她实施了手术。第二,她属于容易发生深静脉血栓的高危病人,应该密切注意发生术后并发症的可能性。
记者:但院方说熊卓为教授并不属于含高危因素的患者群,可以不用抗凝药。
王建国:北大第一医院麻醉科吴新民主任在《围术期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一文中写着:“围术期导致DVT(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大于40岁”、“显著肥胖”、“大的创伤”、“全麻>30 分钟”。我太太入院时年龄49 岁,患糖尿病、高脂血症,体态肥胖,术前有骨折(峡部裂),且术前阿司匹林停药(术后没有恢复用药),医师为她实施的是大手术,植入了人工假体,术中失血,全麻术,病人术中俯卧,手术时间2 小时43 分,这些都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从李淳德、于峥嵘等人发表在《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的论文《脊柱手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与预防》里显示,李淳德是知道不用抗凝药的后果的。其中第一组是2005 年的62 个病例,有2 例出现静脉血栓,第一人没事,另外一人术后5 天猝死,抢救切开右肺,发现混合血栓。在我太太入院前,已因深静脉血栓并发肺栓塞死了一个人,李淳德却仍然不警觉。如果他拿抗凝药使用有争议来反驳我们,我们也可以退一步说,按邱贵兴院士的说法,面对容易发生深静脉血栓的高危病人,即便不用抗凝药物,也该采取如弹力袜、间歇充气压力泵等物理预防措施!
记者:但是北大医院二审的上诉状说,医院当时没有弹力袜,2007 年才有这些设备。
王建国:如果不是看到吴新民的论文,我们还真会相信。在这篇《围术期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论文里写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麻醉科观察了40 岁以上的胸外科、泌尿外科及肝胆外科肿瘤根治术的患者240 例。于术后3~8 d 超声检查深静脉血栓形成情况,分级加压弹性长袜加间歇充气压力泵术后应用组为23.3%,而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的对照组为49.3%。论文收稿日期是2006 年2月10 号,从这个描述可以判断,北大医院一直有这些物理设备却宣称2007 年才有。
记者:您认为北大医院在对您太太的治疗过程中存在哪些过失? 主要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王建国:我们认为,至少有三点明显的过失:一、没有手术适应症,却做了这个手术。没有门诊大夫的手术推荐就做手术是违法的。法院要求医院负举证责任,医院到现在也不把门诊病历拿出来,说明根本没有手术适应症。二、我们不争论是否该抗凝的问题,但术后没有任何防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发生的预防、监控、排查措施,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有监控和检查,就可以随时发现是否发生肺栓塞,恰恰相反,他们开出大量的止痛药掩盖了肺栓塞的症状。三、即使这样,如果不是由无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参与抢救,我太太还有被救活的可能。抢救一开始是由于峥嵘做按压,而急救常识告诉我们应该先口对口呼吸打通气管,再戴氧气罩。气管没有打通,罩上了氧气罩又有什么用?
这一案件,我认为主要的责任者是李淳德,于峥嵘并非完全不知情,三个医学院学生比较,对我太太的死亡负最大责任的于峥嵘是第一,段鸿洲第二。术后出现肿胀疼痛、呼吸困难的临床表现,这时如果不是擅自处置,而是严加监控检查诊断,及时进行溶栓,我太太就不会死。吴新民的论文也提到,急性溶栓,死亡率会从36%降到8%,早期积极进行碎栓或取栓,也能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记者:悲剧是2006 年1 月31 日发生的,而您到2007 年10月才将北大第一医院起诉至法院,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决定打这个官司?
王建国:我太太去世后,我当时不愿意打官司,因为我自己都死去活来了。2006 年4 月我给北大第一医院的领导的信里,阐述了我当时的态度,要求院方承认错误,赔50 万,我捐给我太太的研究所,研究所以我太太的名字命名。再捐筹一些钱成立熊卓为基金,建立流程管理培训中心,以改善医院的管理水平。我找了北大第一医院的副院长和医患处,一直跟他们沟通到2007 年10 月前,他们说,如果不打官司,可免你的医疗费,但态度强硬,拒不承认任何错误,最后说,你要打官司你就打,你要告就去告。
后来我向卫生部投诉,信访单位为我召开专家咨询会,其中一个法律专家叫邓立强,是中国医师协会医院维权委员会的主任,他当时极力主张通过诉讼解决。我说请他帮我打官司,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律师,叫吴俊。吴律师拟了起诉状并要求了500 万的赔偿金。其中死亡赔偿金400 万,索赔标准是户籍所在地澳大利亚上一年度当地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乘以20 年。按澳大利亚公民的标准,就是400 万。精神抚慰金法律没有封顶,我太太是国际顶尖的华裔外籍专家,新加坡国立心脏中心首席科学家,精神抚慰金主张100 万并不过分。钱不是打官司的目的,早在2006 年写给北大医院的信中我就说了我所得的那部分死亡赔偿金将以熊卓为的名义全部捐赠希望小学。
记者:您的律师为什么认为北大医院是“非法行医”?
王建国:吴俊律师当时准备按医疗事故打这个官司,因此他没有主动研究病历,只是等待医疗事故鉴定结果。2008 年1 月我辞掉了吴律师,请来了卓小勤律师。“非法行医”是卓律师主张的,这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卓律师是77 级医学院校临床医学的本科毕业生,2006 年到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做法律顾问,医政监督执法主要就是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医疗广告,因此,卓律师对非法行医这类案件及相关法律文本很熟悉。卓律师把医嘱单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医生的姓名在卫生部的网站上进行了查询,发现他们3 人在事发前没有注册,没有医师执业资格。我们当时向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做了非法行医的举报,他们经过调查取证后,确认了北大医院非法行医的事实,并提出了一个整改意见,但一直到中央电视台去暗访时,他们仍然在非法行医。
记者:您耗日长久地打这场官司,目的是什么?
王建国:我的目的很简单,第一,我太太已去世,但我希望通过这件事能唤醒医生的良知,提升医生的职业道德,救活其他人。第二,必须为我太太讨回公道,她到底是怎么死的,责任人要得到应有的惩罚,不然他还会害别人。太太去世后,她的导师给我的信里说:卓为的死,这个悲剧的后面一定有某种使命感的存在。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就是一直为此在努力,我一定会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记者:医学是个经验科学,有其特殊规律,是个高风险行业,同时也有其探索性的一面,既然是探索,就难免有失败的例子,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王建国:风险包括可预见和不可预见。民事过错的认定,通常是看是否尽到了谨慎注意和充分说明的义务,谨慎注意就包括了风险预见和风险防范的义务。腰椎手术术后出现深静脉血栓,引起肺栓塞,从2006 年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临床上已经有死亡病例的出现,2005 年李淳德已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也出现了死亡病例。麻醉科主任吴新民的研究更早,规模更大,医院应该早有预见和防范。李淳德和吴新民的论文都显示,采用抗凝和物理方法,可把产生深静脉血栓的风险降到很低。如果医生采取了防范措施,最后患者仍然死亡,那可以不承担责任,但问题是在对我太太的治疗上,北大医院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太太的死完全是不该发生的。归根结底,这还是个医德问题,而不是医疗风险问题。
记者:对于这一事件,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王建国:我总觉得我太太死得有些蹊跷。我太太一死,她单位的那个副所长张宝娓就辞职去了美国,接着又把段鸿洲和肖建涛也弄美国去了。在我太太的案件里,李淳德是主要责任者,但医院把他保护起来了,保护李淳德是北大医院的现任院长刘玉树,他和李淳德是好朋友,当年是李淳德把这个院长推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张宝娓我太太的直接领导,她们之间有利害冲突,研究领域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我太太一去世,她申请下来几百万的基金和成果全都到了张宝娓手上,她在研究所是很有地位的,我太太来之后却黯然失色。
记者:如果有机会面对面,您想对北大医院说些什么?
王建国:在打官司时,虽然我很愤怒,但我的表现仍然很平静。我不想对他们说什么,我是相信灵魂的,他们这一辈子都会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