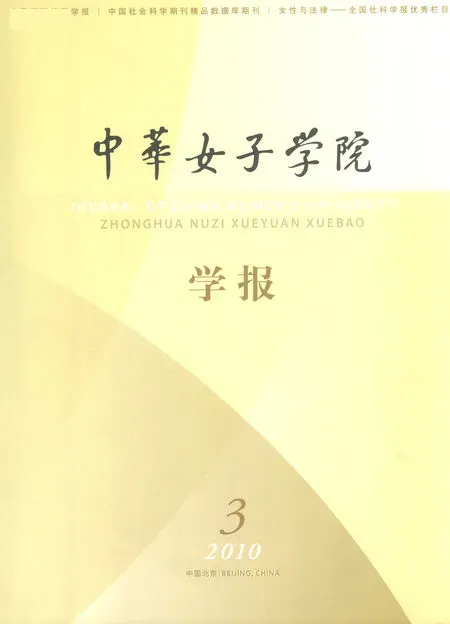变化与秩序:基于河北H村社会舆论中性别关系的研究
2010-09-18王冬梅
王冬梅
(中国农业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北京 100193)
变化与秩序:基于河北H村社会舆论中性别关系的研究
王冬梅
(中国农业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北京 100193)
婚姻关系、婆媳关系和妯娌关系是妇女在家庭和村庄层面中最重要的三种社会关系,这三种社会关系中性别规范的某些内容和形式可能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某些变革,但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婚姻关系、婆媳关系和妯娌关系中的性别因素如何变化,这三种关系赖以存在的根基——“父系、父权、夫居”的性别权力结构始终未变。
社会舆论;性别规范;性别权力结构
社会舆论(本文指乡村普通民众的舆论)作为社会多数人的意见,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较之其他意见具有压倒性效力。它既能够造成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心理气氛,又能谴责背离社会规范和群体意志的越轨行为,两种功能经常同时发生作用。只不过对村庄男女作用的程度不同,而使舆论的社会控制带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女人长期居住在村庄,女人之间交谈的次数、时间和深度远远超过男人,交谈的内容大多以村庄自我的生活为中心,而不是像男人一样过多关注村庄外部世界,因此女人在形成自己的女人社区的同时,也营造了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从而对女性自身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婚姻关系、婆媳关系和妯娌关系是社会舆论中对妇女在村庄和家庭层面评价的核心内容。本文以河北H村为例,对上述三种舆论中性别关系存在的历史、现状及其变化进行探讨。这种基于乡土社会的事实,将“社会性别”赋予中国语境性意义来作为分析工具[1],已为多数学者所实行。
笔者在2006年11—12月、2007年8月和2010年2月曾三次到河北H村,运用个人深入访谈、小组访谈、关键人物访谈及参与观察等方法,进行了深入调查。H村位于河北省东北部,离县城较近,约有15华里。H村东、西、北三面环山,只在南面有一条路与外界相通。村庄有228户,2005年人均纯收入为2440元,是所属乡镇中唯一的贫困村。H村土地贫瘠,每人只有半亩地,此外种植核桃和安梨有一些微薄的收入。据说该村1989年以前一直不种粮食,靠吃国家返销粮生活。后来返销粮停止,才开始种植玉米。20世纪七八十年代H村生活相当艰难,90年代中期后,村里90%的男人到县城打工维持生活。2003年村附近的服装厂开业后,约20—30名妇女去服装厂做工。H村以前的路相当难走,在村里走路要上下爬河沟,“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以至于外人都不愿来 H村。直到2005年申请“文明生态村”建设后,才开始修桥、垒护坝、硬化道路。H村比较重视礼俗和民情,家族内部和亲属之间在婚丧等人生仪礼和节日仪礼中往来频繁。从整体上讲,H村是一个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交通比较闭塞,但原初的礼俗和民情较好地得以保留的村庄。
一、舆论之一:供养关系
尼采说,“没有任何制度有可能建立在爱之上。”作为限制和规制人的性冲动和异性间感情的婚姻制度除了满足基本的性和爱的需要外,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因婚姻而形成的家庭的生育、生产及社会保障功能。在这些功能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妇女劳动价值的隐蔽性,中国大多数家庭尤其是乡村家庭夫妻之间出现一种供养关系。
乡村的民俗中流传着最为广泛也最易理解的方言:“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种方言不知存在了多久,也不知曾被多少人反复地诉说。当H村的老年妇女回忆起心酸的生活史时,“穿衣吃饭”竟是一种奢求,他们谈到那时无论自己怎样辛苦地劳作,仍不能保证过年时每个孩子都穿上新衣。在物品极度紧缺的时代,“穿衣吃饭”成为亿万人共同的生活理想和愿望,妇女的劳作也被遮蔽在这愿望中,成为极普通、极自然的一种生活。
社会发展到新时代,人们喊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口号也让H村的妇女像中国所有乡村的妇女一样出工劳作,跑到离村70里地的地方参加炼钢、修水库。这种热火朝天的生活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朦胧的印象:仿佛原来的婆娘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然而,这种如疾风骤雨般刮起的政治口号驱动的是人的行为,在H村男女的内心深处烙下的仍是“穿衣吃饭”的印痕。笔者第一次到H村时,问原妇女主任英现在的妇女和以前的妇女有何区别,她谈到,那时的妇女整天下地干活,挣公分,天天开会,一点也不闲。可就在这繁重的劳动和开会之余妇女仍无法摆脱沉重的家务负担。“福的媳妇是第一个做绝育的,做完了自个捂着伤口给猪喂食。”“喜的媳妇生了七个孩子了,一年一个,让她做结扎,她男人还跟她打架,说不让她做手术。她刚做完手术,就硬拉着她下地、做饭,一时也不让她歇。”在这种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的相对“去性别化”的环境里,“男外女内”的性别意识仍然根深蒂固。
20世纪90年代后,H村的男人出外打工,女人成为田间的主力,也有些女人成了服装厂女工。“穿衣吃饭”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不少穿着时髦的女人在刚铺好的水泥路上悠闲地溜达。村里的复员军人存说:“现在流行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说男同志只有让女同志过得幸福,才是男同志的本事,村里好多女的天天打麻将。”这种“男人让女人幸福”风气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穿衣吃饭”的翻版,从温饱的解决到生活的享受都在诉说着一个同样的内容:男人供养女人!当然,这种供养的形式和内涵随男人的阶层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形态:暴发户或包工头之妻可能不从事任何田间劳动,收入较低的打工族之妻大多从事农田劳动或外出打工,然而即使打工妇女,其工资收入也远远低于男人。在H村访谈的88名妇女中,16人外出打工,16人中女工的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45%的只有5位,约70%的妇女外出打工的收入只占家庭年总收入的20%—40%左右。按照一般的标准,妇女收入占家庭收入的45%—55%被认为是经济独立,而收入在45%以下属于经济依赖[2](P105),因此绝大部分打工妇女在家庭经济中仍然处于依赖地位。
从上述可看出,男女供养关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无论这种形式如何变化,男女供养关系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的符号结构,成为人们头脑中固定不变的文化图式。
二、舆论之二: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是乡村社会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养儿防老”的观念把儿媳推向了照顾老人的前台,婆媳关系在这种照顾和被照顾者的角色中出现彻底的转换,“婆权”从至上到衰微到遗弃,其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
第一阶段:绝对服从
H村人谈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婆媳关系时,对那时儿媳对婆婆的尊敬记忆犹新,点烟、盛饭、早晨侍奉洗脸、倒尿盆等,媳妇不敢不干。家里来客人,婆婆跟客人吃好饭,媳妇吃孬饭——喝菜汤。对婆婆的这种尊重和服从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严格的等级服从,一种侍奉式的服从,这在堂的媳妇身上体现最突出。堂媳1962年嫁到H村,婆婆当时只有40多岁,堂媳嫁来后给家里的13口人做饭,从未跟小姑计较吃穿,遇事完全由婆婆做主,不认识钱,不知道钱咋花,从来不赶集,不上店,从那时到现在,一直照顾婆婆50年,被村里人称为“最孝顺的媳妇”。这种称号可以说是以对婆婆、对丈夫、对小姑的绝对服从和无偿的劳动换来的,它实践了村民所熟悉的传统伦理文化的规范:“媳妇是伺候人的”。堂媳和婆婆的关系是 H村的一个特例,也成为旧时婆媳关系的一个缩影。
第二阶段:摆脱控制的斗争
旧时婆媳关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婆婆的尊严与媳妇的自主存在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八九十年代以经济冲突、价值冲突、道德冲突等各种方式反映出来,婆权的威信慢慢降低,直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路一辈子都忘不了跟婆婆的冲突,她1982年来到H村,当时H村生活还很困难,她没经婆婆的同意,擅自吃掉了留给小叔的午饭,婆婆骂她,她就跟婆婆打了起来,小叔和小姑就来跟路打架,从那以后路跟婆婆开始分家。芹的丈夫在煤矿上班,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时经常找村里人打麻将,住对门屋的公婆非常看不惯,与公婆大打了一场后,芹在村里找了一个屋子,搬出去住了6年,直到公公生病才回来。存的媳妇和婆婆住一个院15年了,但从不说话,他们的冲突是缘于一次在院里用暖水袋接水时,儿媳没有让婆婆先接水,婆婆气得把水管拔了。路、芹和存的媳妇与婆婆的冲突让我们看到八九十年代因经济匮乏、两代人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等引起的冲突,婆婆仍要求媳妇遵从孝道、敬重婆婆、维护婆权的尊严,但年轻人的个人意识不断增长,他们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寻求更独立自主的生活,由此出现了婆媳之间试图控制和摆脱控制的斗争。
第三阶段:经济的理性供养
经过八九十年代婆媳之间尖锐的斗争后,近几年这种冲突已渐渐趋于平静,婆媳之间出现了一种理性的经济供养关系,有无赡养费用及居住方式由儿媳决定。下表11位单身老人中,有6位老人完全没有赡养费,有赡养费的老人其数额也不高,大多一个儿子一年100元,最高的一年有300元。居住方式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异,H村现在几乎没有婆媳住对门屋的情况,婆婆或轮住,或单独居住,轮住的周期最长一年,一般一个月,最短的3天。轮住方式的选择大多与儿媳有关。村民玉是服装厂的工人,因住房问题跟公婆发生过矛盾。“公婆原来住我们的旧房,旧房是我们自己盖的,公公四个儿子,为啥只在这儿住?后来让他们哥仨拿钱,他们谁也不拿,气得我把公婆赶走,从那以后公婆在四个儿子家轮住。”公婆独立居住的愿望与玉的意愿发生强烈的冲突,玉最后采取了强硬的方式让老人同意了轮住。

表1 单身老人的赡养费和居住方式
存在的问题:“虐婆”现象的出现
赡养费和居住满足了老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但这种需求以什么方式来满足直接体现了人的尊严。H村老人的赡养费勉强维持温饱,半数以上的老人因轮住丧失了自己的固定住所。独立空间的缺失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力的缺失,婆婆们以各种形式表示对这种居住方式的不满,但遭到了媳妇们的坚决拒绝,因为单独租房不仅要让媳妇们承担房费、水电费、炉灰费等各种费用,而且还要找时间去看望老人,否则会背“不孝”的罪名。对有劳动能力的老年妇女来说,也没有拒绝为儿子家劳动的权利,田老汉和他的媳妇70多岁了,一直给儿子家种地,连核桃都是每年由田的媳妇剥皮、洗净,最后卖了钱把钱交到儿媳的手里。田的媳妇说,“儿媳来了后从没下地劳动,被子都不拆,你要不管她能骂死你,她的自留地我们替她种,收了东西都给她。”
从对婆婆的绝对服从,到与婆权的尊严和控制权进行斗争,再到今天H村老人中的经济供养关系以及“虐婆”现象的出现,婆媳的位置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婆权”被颠覆,媳妇占据了原来婆婆的位置,出现了乡村前所未有的变局。如果深入分析这一变局,我们会发现婆权至上时期婆媳之间的关系是以对婆婆的服从和侍奉为本质特征的,这是因为传统家族等级制的三大原则(性别、辈分和年龄)对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辈分原则作为第二大原则使妇女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晚辈的尊敬和抚养,使婆婆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有相当高的地位。[3]但随着现代商品经济在乡村的渗入,对婆婆的服从和侍奉被经济赡养的方式所取代,这其实是完全颠覆了传统养老方式的核心内容,以简单的“金钱”代替了具有深厚道德内涵的供养行为,这种经济供养所带来的也必然是婆婆人格的丧失和非人性化的对待。然而在这大变局的背后,我们会发现支撑婆媳关系变化的基轴始终存在,这个基轴就是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男性继嗣制度。表面上,对婆婆的服从和“虐婆”完全不同,实际上两者只不过是由男性继嗣制度而派生的两种极端形式:前一种是以婆婆对儿媳的索求作为特点,而后一种则伴随着个人主义的观念,媳妇要求提前从婆婆身上得到对给婆婆养老的补偿。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由父权体系所设立、由妇女自己来操作的制度。这种制度使婆媳关系始终成为养老舆论的中心,舆论将矛头直接指向婆媳双方,男人在婆媳双方的冲突中,或隐退,或直接介入,但不管怎样都未进入社会舆论评价的视野。清的例子说明了这点。清在外开出租,他母亲原来在他的旧房里单独居住,村民说,“清的媳妇对婆婆很好,婆婆不知足,麻烦事多。有一回,清出门回来,清的母亲对儿子说媳妇对她这不好,那不好,结果儿子回去把媳妇打了一顿,气得媳妇把婆婆的被褥扔了出来,从那以后婆婆开始轮住。”清家发生的这场冲突,儿子、儿媳和婆婆都参与其中,而且儿子殴打妻子,但村民在议论时都把事情的罪责推在婆婆身上,对她的儿子并没有丝毫的责备。婆媳关系成为人们评价家庭关系的一个焦点,男人即使介入其中,也很少受到舆论的责备和惩罚。
三、舆论之三:妯娌关系
妯娌关系是家族关系评价的关键要素,妯娌之间是否和谐,直接关系到家族关系能否长久维持。妯娌关系从矛盾、摩擦、甚至相互仇视到双方和解,社会舆论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而这种舆论得以发挥作用的关键,则在于家族关系中的性别规则对妇女的内在约束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H村一般没有钱给每个儿子单独盖房,只能是两个儿媳住一座平房,每个儿子分一间半。居住空间过近带来了很多家庭妯娌之间的冲突:维伍的媳妇在婆家排行老五,老大在东北,她和老四维真媳妇曾在一座房子里住了十年。当时两个媳妇只有一台缝纫机,维真媳妇只要回娘家就把缝纫机的梭子卸掉,不让维伍媳妇使用,维伍媳妇不知为此与她打了多少次,后来谁也不理谁,最后维伍媳妇搬出老房单独住。关系何时和解的呢?是从东北的大哥来H村后,据说东北的大哥得了脑血栓,维真把大哥接回来后与大哥住了不到一年,维真媳妇就因一些家庭琐事把大哥从家里赶了出来。村里人对维真媳妇议论纷纷,家族的几位长辈想狠狠教训她,村民说家族不和都与她有关。在舆论的指责和家族势力的压力下,维真媳妇在村庄越来越孤立,后来只好主动和维伍媳妇往来,才平息了以前的风波。这一事例说明,家族观念对妇女有很强的约束力,妇女只有搞好妯娌关系,维护好家族的和睦和团结,才能免受村庄舆论的指责。
近些年,妯娌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相比紧密接触的时代明显减少,只有遇到一些事情需要帮忙或婚丧往来时家族成员之间才发生关系,在这些事件的处理中家族观念仍根深蒂固。维伍的媳妇讲到了村民继真盖房摔伤和自己让别人撞伤的事,她说,“继真给村里人盖房,不小心把腿摔坏了,房主给钱赔偿,继真媳妇嫌给钱少,整天吵吵闹闹,到现在这事也没解决好。你看我这条腿,前些天让人撞伤了,但没过1小时事情就了结了。怎么解决的?出事当天我把娘家哥、老四维真等几个家族兄弟全都叫过来了,他们坐在一起商量,事主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有百年当家子(父系家族的成员),没有百年亲戚,家族哥们能力再不行,也要有这个‘角’在那儿摆着。”维伍媳妇真实、生动的讲述阐明了一个最朴实的道理:家族的哥们即使不能发挥实质的作用,也要在一些重大事情上有自己的象征性权力。在笔者听到珍的故事时更加明白了家族对一个女人的意义。珍和弟媳都是从东北来的,弟媳家庭生活贫困,2008年珍的小叔子(丈夫的弟弟)得病去世,珍提议村民捐钱资助,不辞辛劳地操办丧礼,之后又给侄子交高中的学费,拿侄儿当自家人看待。这其实反映了珍是将自己看作家族的真正一员,甘愿为家族成员努力,在这种努力中来凸显自身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七八十年代,H村妯娌之间的冲突大多是因贫穷而引起的对物品的争夺,之后妯娌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以事故性摩擦(盖房发生的摔伤或其他事故等),日常仪礼往来(婚礼、丧礼、看病人等)中发生的各种矛盾为主,但不管冲突的原因如何,在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时,家族关系中的性别规则始终是他们遵守的牢不可破的法则,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意识是一种隐约却有力的制约。[4]这说明无论妯娌之间的冲突随社会情境发生何种变化,从夫居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父权至上的家族权力结构始终未变,社会舆论也在对这些事件的评价中将宗族观念进一步强化。
四、性别关系图式的变化与稳定
婚姻关系、婆媳关系、妯娌关系是妇女在家庭和村庄层面中最重要的三种社会关系,这三种社会关系中的性别权力结构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在各种风俗仪式中形成规制社会秩序的性别“符号”,只不过这种“符号”的控制功能在近20年有所弱化。婚姻的供养关系中,从“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到妇女内部阶层分化,出现打工妇女但仍在经济上依赖男性的现实;婆媳关系中,从婆权至上到衰弱到被遗弃,最终形成对婆婆的经济理性供养;妯娌关系中,由原来住对门屋的矛盾、摩擦、相互仇视到如今和解的增多,这些都显示了性别关系的某种变通,显示了性别关系随社会经济、政治、风俗等社会形势的变化出现的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无论供养关系、婆媳关系和妯娌关系中的性别因素如何变化,其赖以存在的根基——“父系、父权、夫居”的性别权力结构始终未变。这种性别权力机构只不过改变了以前极其露骨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代之以更隐晦、更易变通的方式。
上述状况与新结构主义人类学家萨林斯的主张很吻合。萨林斯的新结构主义中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结构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一方面,结构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断转换其形态,呈现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结构的深层固有模式仍通过事件而延续,始终保持不变。萨林斯对文化变迁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社会文化的变迁实际是本土文化结构对外来文化吸收和改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本土文化的意义发生了改变,但本土宇宙观和本土文化结构并未改变。二是文化对物质活动的决定性。相对于形形色色的“实践理性”,萨林斯提出了象征理性或意义理性,主要表述如下:“人的独特本性在于,他必须生活在物质世界中,生活在他与所有有机体共享的环境中,但却是根据由他自己设定的意义图式来生活的——这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因此,这样看来,文化的决定性属性——赋予每种生活方式作为它的特征的某些属性——并不在于,这种文化要无条件地拜伏在物质制约力面前,它是根据一定的象征图式才服从于物质制约力的,这种象征图式从来不是唯一可能的。因而,是文化构造了功利。”[5](P3)新结构主义为社会舆论内部性别关系形式变化而深层结构未变的事实提供了理论根据。
[1]杜芳琴.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六十年述评:理论与方法[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5).
[2]Morris Lydia and Stina Lyon E.Gender Relations in Public and Private-New Research Perspectiv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1996.
[3]笑冬.最后一代传统婆婆[J].社会学研究,1999,(3).
[4]张悦红.性别意识演变与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生存现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3).
[5]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M].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董力婕
C913.68
A
1007-3698(2010)03-0050-05
2010-05-04
王冬梅,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农村妇女发展。
本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09-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