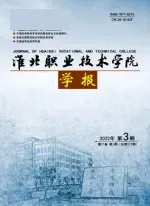从前后期创作看外国文学对余华的影响
2010-08-15闫加磊
闫加磊
(江南大学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从前后期创作看外国文学对余华的影响
闫加磊
(江南大学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一批年轻的先锋小说家登上中国文坛,特别是余华,他以血腥的暴力叙述、颠覆性的语言、令人绝望的意境和黑色幽默情节,挑战着读者的视觉和感觉机能。九十年代,余华由先锋向写实转变。这种转变并非人们所认为的先锋作家在中国当代遇到了写作困境和精神危机而转向而实现的自我救赎,而是在借鉴西方写作模式和传统精神而实现的写作方式的成熟转变。所以,纵观余华创作,外国作家、理论及写作方式对余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余华;川端康成;卡夫卡;暴力;温情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如今,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文学青年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阵营,同时中国文学也迅速融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中。在总结回顾历史文化发展的同时,一些青年作家将触角伸向外国文学及理论,余华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为何写作》中余华说:“这是无数人汇集起来的饥渴,是一个时代对书籍的饥渴。我置身其间,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一样,……我要面对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最后我选择了外国文学。”[1]21对余华而言,对西方的借鉴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也并非简单的技巧和框架的学习,而是将西方先进的文学理念巧妙地融入自己的文学机制之中,成为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审视余华小说创作母体的演变,夏中义、富华在《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中将其概括为:“困难”与“温情”[2]。陈少华在《写作之途的变迁》中将它描述为:“世界上冷漠与温存并存。”[3]所以,我们大可将余华前后期小说创作基调概括为“困难”与“温情”,围绕这两基调,我们可以发现余华前后期创作的与外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余华早期受川端康成影响颇大。在《“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中余华讲:“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是《伊豆的舞女》,我吓了一跳。那时候中国文学正是伤痕文学的黄金时期,……我一直迷恋川端康成……”[4]36俞利军在《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中认为余华和川端有着相似的童年,而童年的经历对于作家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川端康成出生正值日本经济萧条,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以后就和祖父一起生活。而余华也有着不愉快的童年,他出生时中国正遭受自然灾害,外科医生的父亲经常不回家,余华的童年不仅缺少父爱,还遭受兄长的欺压。两位作家前期的作品表现的主要是卑贱的小人物,川端的《十六岁的日记》、《致父母的信》、《参加葬礼的名人》、《篝火》,主要描写其个人经历与体验,而《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就主要表现社会下层等小人物悲惨的命运。余华从处女作《第一宿舍》到《小站》,也是反映小人物的恩怨忧愁,并且在这些小人物身上也多少有余华自己的影子,在《兄弟》和《呼喊与细雨》中充满了对父亲的负面描写与反抗,父亲成了邪恶的化身,这种写法在陈晓明的《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中被认为是“胜过父法”。[5]而这部作品堪称余华坦诚而又令人震惊的心理自传,余华用非成人化的视角向读者讲述幼年那些令人绝望的生活事实。《呼喊与细雨》对“父亲”孙广才进行了解构与颠覆,孙广才不再是传统那种父亲形象,成了一个十足的无赖。在后期的小说《兄弟》中,“父亲”也遭到了极力的贬低,未出场便因为偷看女厕所而淹死。父亲形象再也没有传统“父亲”的光辉与高大。
此后,余华小说中更是充斥着暴力与黑暗的叙述,这多少又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有关。余华说:“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的童年的经历有关。……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到了1982年,我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罪与罚》,我被深深震撼了。”[4]25在1986至1987年余华写下了《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等极具先锋特色的短篇小说,其中充满了对混乱的现实世界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混乱的人的描写。此后,余华又发表一系列冷酷之作,将人性中最黑暗、最丑恶的一面暴露在人们眼前,正如朱玮在《余华史铁生格非林斤澜几篇新作印象》中所说的“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的,一定是冰渣子。”[6]费樊星在《人性恶的证明》中认为余华小说中人物残忍的本性是人类的生存本性,这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记下的一个思想史多么相近:“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7]25陀斯妥耶夫斯基却还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宗教,到尼采那宗教也没落了。从卡夫卡、福克纳到卡内蒂、戈尔丁,人类之没落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主题,于是余华告别诗意,走进艺术的地狱。《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作物》、《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就具有了悲剧的宿命感。陀斯妥耶夫斯基给了余华启迪,余华以荒诞的手法写出了当代人生存的困境。但余华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又是有区别的,余华对人性的挖掘仅停留在描述阶段,并不能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将现实的人性分析上升到哲学层面。
余华的前期小说中还有一些黑色幽默的荒诞成分,这多少借鉴了福克纳的写作经验,但据余华讲卡夫卡是其创造力的第一发掘者。如果说川端康成教会了余华最基本的创作,即细部的描写,而卡夫卡则带给余华以思想之解放,这种解放即是他对残忍的令人惊异的叙述忍耐力。在《论余华小说的黑色幽默》中,余岱宗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中的暴力与欺骗,《河边的错误》中疯子的连续杀人事件,《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的自戕,《现实一种》中一家人之间的相互残杀,《古典爱情》中令人胆寒的人吃人与变态的爱情,《鲜血梅花》中的荒诞戏剧的模仿,等等,都设置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具有一段距离的叙述语境。余华小说之所以具有黑色幽默色彩,暴力导致所以具有荒诞性,是因为这种力量根源于人们内心的渴望,而单纯的语境更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突兀”的感觉,而达到一种滑稽的效果。尽管余华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多是一些疯子或自虐狂等反常人物,我们在这种荒诞的场景中很难看到幽默的成分,但反常的文本场景却让幽默“突转”而出。《许三观卖血记》是学界公认黑色幽默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小说。这个故事讲述一个小人物的具有悲剧性的一生,所涉及的也是江南小镇人们的琐碎生活,在这里,黑色幽默是人们超越困境的一种无奈的态度,许三观想要摆脱困境,可困难却如影般的纠缠着他,这就使许三观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忍耐成为他的精神良药。
二
在余华的转型后期,他创作了《兄弟》、《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著名的长篇小说,其风格与文笔迥然大异。如果说我们从前期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余华对国民生存状况和人性本质的揭露与批判,那么虽然在后期的创作中也延续着人生苦难的主题,但是我们隐约看到他对人们残存的一丝希望与期待,这种创作风格多少与余华第一恩师川端康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的文学道路》里余华谈到:“所以读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以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人家写伤痕是这样写的,不是以一种控诉的方式,而是以非常温暖的方式在写。”[8]同时他也认识到作家的使命并非向人们展示罪恶与黑暗,而是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与希望。尽管《兄弟》中处处充斥着死亡叙述,但这它占据作品的主导地位,李光头在亲人全部失去之后,刻苦学习俄语,希望有朝一日搭乘俄罗斯飞船,把宋钢的骨灰盒送上太空轨道。李光头用俄语说,我的兄弟宋钢就是外星人啦。所以我们在《兄弟》中读到了希望。昌切、叶李的在《困难与救赎》中将之称为:“对人的生活的拯救。”[9]当余华对人类生存世界解构为虚无之后,他着重处理人类心灵的任务,他在无意义的空虚中找到了人真正的存在意义。
小说《活着》的创作多少与美国民歌《老黑奴》有着一些关联。余华说过,美国民歌里的老黑奴经历了一生苦难命运,家人全都离他而去,但他亦然乐观地看待世界,没有任何抱怨。这个民歌深深打动了他,于是写下了《活着》,阐释人类在经历各种令人绝望的苦难后亦保持着令人敬畏的心理承受能力,保持着乐观的处事态度。所以“苦难与承受”就成了《活着》的基本主题。《活着》中福贵面临着一次次的命运的打击;妻子家珍死于疾病,女儿凤霞在难产中失血过多而死亡,而女婿最后被水泥板活活砸成肉饼,唯一的儿子在医院中被强迫为老师媳妇捐血而死,最后,与他相依为命的小外孙也因为饥饿吃豆子被胀死。在这里,死亡不再是抽象的现实事件,而是现实存在的境况,福贵亲人们的接连死亡并不是人为的暴力事件,更不是人性恶的结果,死去的亲人处处显示了人性之光辉,家珍的善良、凤霞的质朴与贤惠、二喜的憨厚,哪一样都感动着人们,残酷的人生命运造成了福贵的生存困境。余华用《活着》表达了他的人生态度与真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10]所以《活着》就像是一部寓言,渗透着余华对人生的看法。九十年代的余华不再把死亡看作是令人绝望的事件,而是应以“活着”的态度来面对苦难的生活。所以,福贵个人对命运的处世态度就不仅仅是一个农民的个人体验,而升华为普通人们对悲剧命运的态度。福贵经历次次苦难,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生活和家人的亲情,但是最后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可福贵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期望,他依然以一种对未来生活的乐观主义和超越绝望后的平静心理悠然地生活着,以穷尽生活苦难而“活着”的生存态度拯救了自己。所以,《活着》尽管是一部悲剧作品,写的也是主人公的悲剧历程,但是人物的生存态度才是这部作品尽力去刻画的主题,只有“活着”才是人生关键,带着这样的生存哲学才能在充满悲剧的世界里获得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纵观余华前后期小说的创作,可以看出,转型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与当时中国思想界提出的“将苦难化为精神资源”这一命题相辅相成。千百年来,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同时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处于“个人精神”之遗忘与缺失状态。余华小说极力强调对自我世界的感知,去生活深处挖掘人的生存价值,于是暴力得到了有效缓解,忍耐成为余华处理生活困境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许三观卖血记》里,悲剧命运得到了戏剧化的处理。也正是因为前期余华特别关注人们的苦难状况,所以余华后期的长篇小说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转型前,余华很容易将人们的各种生存困境归结为人类本性之恶,但是在后期的创作中,这种情形悄然发生变化。人不再是一个符号或简单的注解,而成了活生生的主体,特别是在与困境的对抗中现实了自己特有而又坚韧的意志,也正是这种意志使得人何以生而为人。于是余华在对人之强大精神韧性与现实的非逻辑性的对抗的展现中,直接将矛头对准那看似合理实际却不正常的种种现实。
三
从余华前后期文学转型中我们可以看出,余华虽立足于中华名族的文化土壤中,他自己也承认如果早点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那么此后的余华便是具有鲁迅色彩的了。但是在他运用传统的写作方式的同时,也借鉴了众多外国文学的理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写作,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理念。
佛洛依德认为人的意识主要由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潜意识,潜意识是人之未被压抑的心理状态,是最真实的。在《“我只要写着,就是回家”》中余华说:“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经常手提着一桶血肉模糊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4]童年的经历潜移默化地镌刻在了余华的潜意识里面,于是心理对暴力的渴望加上对外国作家对暴力描写技巧的借鉴,这双重因素造就了余华前期那令人骨寒的死亡叙述,但是后来余华自己也意识到仅仅对现象的揭露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后期写作中暴力叙述虽然还存在,但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变成暴力与温情并存,在《虚伪的作品》中余华说:“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意义。”[11]于是余华后期小说创作的语言离事物本身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贴近现实,即中国社会的现实。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七八十年代余华以其极具先锋色彩的叙述方式登上中国文坛,到九十年代其艺术道路悄
悄开始转型,也开始他对中国现实、自己的创作理念的反思。我们不能把余华的转型看成是逃避世俗的方式,也非技巧到了末路的逃亡,相反,余华后期的转型是他对艺术的自觉选择,让艺术回到单纯而又质朴的阶段。所以纵观余华前后期,实际上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同时更是余华创作技巧逐渐成熟的过程。
[1] 余华.我为何写作[M]//余华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 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J].南方文坛,2001(04).
[3] 陈少华.写作之途的变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9(04).
[4] 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M]//余华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5] 陈晓明.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J].当代作家评论,1992(4).
[6] 朱炜.余华史铁生格非林斤澜几篇新作印象[J].中外文学,1988(03).
[7]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余华.我的文学道路[J].当代作家评论,2002(04).
[9] 昌切,叶李.苦难与救赎[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02).
[10] 余华.《活着》前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1
[11] 余华1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坛,1989(05)1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on Yu Hua from His Works of Earlier and Later Stages
YAN Jia-lei
A batch of avantgarde novelists came to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ver the 70s and 80s in china,especially Yu Hua.He challenged his reader visually and sensationally with bloody description of violence,subversive language,desperat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plot of black humor.But there is a conversion of the avantgarde writing style to a realistic writing style over the 90s for redemption.This is,however,not for the reason well-accepted among most people that the avantgarde novelist encountered some difficult situations and spiritual crises during writing,but for the reason that he wanted to achieve the conversion of his writing style by taking the western writing style and traditional spirit for reference.So we may find Yu hua have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foreign writers,theories and writing style from the works he created.
Yu hua;Kawabata Yasunari;Kafka;violence;tenderness
I209.4
A
1671-8275(2010)04-0078-03
2010-05-06
闫加磊 (1985-),男,江苏无锡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之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