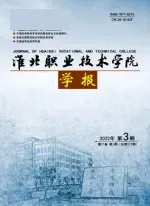论柔石小说的典型化
2010-08-15王吉鹏丁宝晶
王吉鹏,丁宝晶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辽宁大连 116029)
论柔石小说的典型化
王吉鹏,丁宝晶
(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辽宁大连 116029)
柔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才华的青年作家。他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柔石从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塑造人物时特别注重典型情节的描写、典型环境的选取和典型性格的刻画。情节和环境充分典型化,对人物性格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提供了人物得以表现自己性格的各种有利的机会,从而更好地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
柔石;小说;典型化
柔石是一位难得的天才作家,他虽然英年早逝,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作品,塑造了许多震撼读者心灵的人物典型。如《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的“人鬼妻”和《二月》中的文嫂等苦难深重的劳动妇女形象;还有《二月》中的萧涧秋、《三姐妹》中的章先生和《旧时代之死》中的朱胜瑀等抑郁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典型。本文主要从情节的典型化,环境的典型化和人物性格的典型化三个方面来论述柔石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艺术技巧。
一
情节、环境和人物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情节是由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结构成的。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结构成作品中的情节,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塑造典型,这里有一个集中概括、取舍、提炼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如何使作品中的情节典型化的过程。[1]文学作品反映生活主要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形象实现的。也就是说文学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应该以广阔的人民生活为基础。柔石小说典型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取材于广阔的人民生活,并严格遵循生活的逻辑发展,进行严格的提炼,以充分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柔石从小就生活在贫苦的人民大众之中,和淳朴勤劳的人民有天然的联系,他亲眼看见了劳苦大众的不幸遭遇,亲身体会了他们的痛苦。“童年的柔石每次走到方祠前,总是看见一簇簇兴高采烈地坐着闲聊的公公、伯伯、叔叔们,偶尔从旁听听,感到很有兴味,不知不觉中,方祠又成了他听故事的好去处。”[2]自己的亲身感受和长辈们的故事成了柔石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短篇小说《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写的是就是贫苦的农民仁贵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变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3],因此,人们都叫他“人鬼”。在那个腐朽的旧社会,勤劳俭朴的劳动人们辛勤的劳动,希望可以通过劳动改变贫苦的生活现状。但阶级的压迫却让他们变得更加更加贫穷。柔石以当时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为素材,加以概括、提炼,通过“人鬼”这个苦难人民的代表,写出了黑暗腐朽的社会对劳动人们的压迫及残害。柔石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升华,描写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被摧残、被损害的劳动妇女“人鬼妻”的不幸遭遇。“人鬼妻”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无奈之下只能给人家做童养媳,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但不久她的丈夫去世了,婆婆整日对她非打即骂,过着垃圾堆里死老鼠一般被弃着的日子。她以为嫁给“人鬼”可以摆脱自己过去苦难的生活,但没想到却陷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人鬼”每天只知道喝酒、抽鸦片、吃饭、睡觉,对妻子连起码的生活照顾也没有,更不用说体贴、温暖了。婆婆对她更是冷嘲热讽,百般凌辱,“人鬼妻”如行尸走肉般生活着。阿宝的降生重新燃起了“人鬼妻”对生活的希望,她以为看见了光明,可“人鬼”却说孩子是“野种”,将孩子打得惊吓而死。“人鬼妻”悲痛欲绝,愤怒地指责“人鬼”应早些死去。最后“人鬼妻”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走向了死亡的道路。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人鬼妻”不但要受到阶级的压迫,还要受到“人鬼”这个社会畸形儿的压迫,可谓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倍受剥削和压迫的群体,连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都没有,柔石正是看到了广大劳动妇女的苦难与煎熬,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因此选取了富有典型性的情节加以渲染,使得“人鬼妻”的形象更加打动人心,更加震撼读者的心灵。鲁迅在回答自己为什么撰写小说的这个问题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柔石继承了鲁迅的思想,通过对典型情节的选取,意在表达社会的腐朽以及苦难人民的不幸的主题思想,以引起社会的重视与“疗救”。《没有人听完她底哀诉》、《摧残》中都从不同程度,不同侧面表现了黑暗社会对底层劳动妇女的摧残及伤害。
情节充分典型化,会对人物性格的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从而更加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动人。当然人物性格发展的深化也作用于情节的典型化。“情节显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发展也推动了情节的展开。”[5]某一情节合乎生活的规律,也对人物性格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凸显人物的典型。如中篇小说《二月》中,有一个各式公子大谈主义的情节,当问道萧涧秋是什么主义者,有什么主义时,萧涧秋微笑地答:
“我没有。——主义到了高妙,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
可见萧涧秋苦闷彷徨的心理状态。萧涧秋从小接受进步的思想,有理想、有抱负,但又找不到救国救民的出路,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却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而感到十分彷徨痛苦。这个情节就表现了萧涧秋苦闷抑郁的心情和彷徨无助的性格特征。而在这个情节中,陶岚却冷冷地平峻地几乎含泪的答:
“我么?你问我么?我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社会以我为中心,于我有利的拿了来,于我无利的推了去!”
从陶岚的言谈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热情似火而放纵坦率的时代女性形象。她不像那些虚伪的公子哥们大谈理想,大谈救国方针,她直率地说出了每个人都不敢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人都存在的问题—自私。这个情节为我们活画了一个直白坦率的知识女性形象。随着矛盾的不断深化,作品的情节也进一步发展。萧涧秋在得知革命遗孀文嫂的艰难情况后,决心帮助文嫂,并资助采莲上学。但镇上却谣言四起,侮辱与诽谤也随之而来,这让萧涧秋和文嫂都十分痛苦。不久文嫂的儿子死去了,为了挽救文嫂,萧涧秋放弃了对陶岚的爱而决心娶文嫂。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性格得到不断深化,萧涧秋由苦闷彷徨的知识分子深化到了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时代青年形象,使萧涧秋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尤其是最后萧涧秋出走这一情节更是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三姐妹》中则通过章先生对三姐妹由热恋到遗忘的过程,刻画了章先生这个自私虚伪的知识分子形象。《会合》中王老爷和李少爷的对话这个情节,活画了自私虚伪的知识者形象。这就说明了典型情节的提炼不但促成了人物性格的发展,而且让作者看见了丰满可感的人物形象。
二
环境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外在条件的总和,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狄德罗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5]也就是说环境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在不少小说中,自然环境充分社会化了,这使得它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成为现实社会的某种象征,并且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作品主题思想的突出。这一点在先秦的表现说中就有所表现,我国古代山水诗人往往寄审美情感于山水。从六朝一直到明清的山水诗的移情作用都进一步发挥、体现了这一发展着的审美传统。柔石继承了这种用自然景物移情的手法,来突出作品的主题以及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在《二月》中当萧涧秋知道了革命遗孀文嫂的艰辛后,第一次拜访文嫂的景物描写:
雪上的脚印,一步步地留在他底身后,整齐的,蜿蜒的又有力的,绳索一般地穿在他的足跟上,从校门起,现在是一脚一脚地踏进她们门前了。
可见当时萧涧秋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仿佛这雪上的脚印如绳索般牵绕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实施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但终将被这“绳索”绊倒,可见萧涧秋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但当萧涧秋从文嫂家返回学校的时候又这样写到:
萧涧秋在雪上走,有如一只鹤在云中飞一样。他贪恋这时田野中的雪景,白色的绒花,装点了世界如带素的美女,他顾盼着,他跳跃着,他底内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微妙的愉悦。
在文嫂同意接受萧涧秋的救助后,萧涧秋仿佛在这个小镇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一种自豪的、喜悦的心情倾泻而出,同时一个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跃然纸上。《二月》开头有这样的景物描写:
是阴历二月初,立春刚过了不久,而天气却奇异地热,几乎热的和初夏一样。
这段景物描写挣象征了芙蓉镇当时的气氛,芙蓉镇看似一个“世外桃源”,却到处弥漫着封建旧势利的气息。这里的天气很热,让人感到很躁动,这里的封建旧势利更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作者借自然景物的描写,暗示了当时的时代大背景,这更显示了萧涧秋帮助文嫂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难能可贵。
柔石小说不但注重自然环境的渲染,也十分重视社会环境的真实再现,使得人物形象在环境的渲染下更加形象化,主题也更加突出,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如《为奴隶的母亲》写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外有强敌的入侵,内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杀戮,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贫病交加,生活无依,卖儿典妻,甚至饿死冻死。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柔石描写了春宝娘这个苦难的母亲形象,她身为母亲却没有做母亲的权利,照顾秋宝就得放弃春宝,和春宝在一起就永远也看不见秋宝,作为一个母亲这种痛苦生不如死。柔石将春宝娘放在那个黑暗的社会环境中加以描写,更加突出了那个时代底层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同时也深化了春宝娘这个苦难母亲的形象。而《疯人》则写的是封建家长对男女青年恋爱自由的压迫与扼杀。辛亥革命虽然给腐朽的旧中国沉重地一击,但是并没有动摇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封建思想仍然深入人心。作者将疯人的爱情悲剧放在封建旧社会的背景下加以表现,更见疯人的悲惨际遇,也更有力地批判了封建势力对男女青年爱情的镇压与迫害。在《三姐妹》中,作者将三姐妹与章先生的爱情悲剧放在动荡、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去表现,更突出了社会环境对美好事物的扼杀。《爱的隔膜》则表现出旧社会青年对社会自由的向往,写出了封建旧社会对妇女思想的毒害。柔石不但注重情节的典型化,也十分重视环境的选取与渲染,使环境富有典型化,进而在典型环境中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
三
情节的典型化和环境的典型化都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它们之间有辨证的依存关系。情节的典型化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的典型化,而典型环境又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柔石不但注意通过典型情节的描写和典型环境的渲染来突出典型人物的性格,而且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对话、肖像等来突出人物的典型性格。心理描写是披露人物内心的秘密,刻画人物性格的极为有效地一种手段。《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在为秀才地主生下儿子后,秀才地主想了好久也没为孩子起个好名字,而春宝娘说,“还是叫秋宝吧”。作者描写春宝娘含泪想“我不过因春宝想到罢了”。这一心理描写,写出了苦难妇女对儿子的思念,以及黑暗的封建制度造就了这个不幸的母亲,有力的抨击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当三年典期将满时,春宝娘的内心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她一方面想念旧家的春宝,另一方面又不愿离开秋宝,实在想在这个新家永远地住下去。她想,春宝的爸爸是活不长的,等他三五年死后,要求第二个丈夫把春宝接到新家来,这样就可以和两个儿子在一起。即使地主婆百般侮辱虐待,她也愿意。可见春宝娘的愚昧麻木,她只想在忍让中暂时坐稳她奴隶的地位,从不想去反抗,去争取她做母亲的权利。这样,一个可悲而又愚昧麻木的旧中国母亲形象便跃然纸上,深入人心。
对话在刻画人物性格中显然是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作者善于描写人物的对话,在对话中展示人物的性格,使得人物形象更加栩栩如生。看文嫂与萧涧秋一段对话:
“先生!我总感谢你底恩惠!我活一分钟,就记得你的一分钟。但这一世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我只有等待下世,变一只牛马报答你罢!”
“你为什么要说象这样陈腐的话呢?”
这两句对话把文嫂的善良﹑真诚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别》中青年与他妻子的一段对话:
“你去好了!”
“你这样,我去不了的。”
“我什么呢?我很快乐送你去。”
“不要你送,不要 ;你睡下,好好地睡下,你睡下后我还有话对你说。你再不睡下,我真的明天要在埠头留一天了。”
“那末我睡下,你去吧。”
这段对话把妻子对丈夫的依依惜别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虽有不舍但更富有牺牲精神,形象刻画合情合理,入木三分。《侩子手的故事》中从小酒馆的听众与侩子手的不断对话中,一个凶残、麻木的侩子手形象便呼之欲出。
肖像描写在柔石的小说中总是显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如《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人鬼”的肖像描写:“一副古铜色的脸,眼是八字式,眼睑非常浮肿,所以目光倒是时常瞧住地面……,神气的倒像一位哲学家,沉思着生死的问题。”一个麻木不仁、痴痴呆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人物形象便显现在读者面前。《为奴隶的母亲》中写秀才的大娘子只有一句“脸孔肥肥的,两眼很有心计的约莫五十四五岁的老妇人。”一个刁钻刻薄,心计很深的老妇人形象便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曾说:“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无论优点或者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6]柔石正是有意识地将我国传统的写意画的方法运用到肖像描写上,只是寥寥几笔简略地勾画,人物的形象特征便了然于心。
[1] 陈鸣树.鲁迅小说论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 王艾村.柔石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 柔石.柔石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I207.4
A
1671-8275(2010)04-0070-03
2010-05-03
王吉鹏(1944-),男,江苏东台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丁宝晶(1986-),女,黑龙江绥化人,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之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