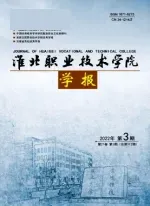回漩与突进
——论苏曼殊文学中的现代性品格
2010-08-15崔鑫婷
崔鑫婷,丁 颖
(大连民族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回漩与突进
——论苏曼殊文学中的现代性品格
崔鑫婷1,丁 颖2
(大连民族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将苏曼殊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中,阐释其诗歌、小说、译作中所体现出的个体独立精神,探讨其作品的悲剧意识对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生成的作用,在其小说艺术手法的现代性倾向的综合分析中,发掘苏曼殊的极富魅力的精神探索历程,归结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品格。
苏曼殊小说;主题;悲剧意识;艺术价值
苏曼殊(1884、10~1918、5)短暂的一生如一颗划过天空的耀眼的流星,在20世纪初这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结点上飘落下“五四”黎明前“苦涩的清新”。这种“清新”给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期的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那个充斥歧路与选择的时代,对于旧时代的眷恋和新时代的想象同时存在于正在蜕变中的旧中国的文人心中,苏曼殊小说的根底就在于他个体精神淋漓尽致的彰显,这种个性表达在主题模式方面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精神境遇和文化选择的困惑的充分描述。他那“断鸿零雁”的人生境遇、“披发长歌”的洒脱骏逸、“白马投荒”的探索追寻、“袈裟点点疑樱瓣”的情道困惑以及去国远行的拜伦式的自由情怀,让处在一个世纪后的我们感受到了曼殊在新旧时代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那追寻人生终极价值的鲜活的生命体验。那么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视野下来重新烛照苏曼殊,他却是一个先锋式的开拓者,“末代文人”这一论断显然掩盖不住他绚烂的光彩,作为20世纪文学的创辟者之一,他同时也是当时启蒙语境下的另类叛逆者。就整体创作风格而言,他是与那个崇尚金戈铁马、气势磅礴的大革命背景相牴牾的,但是其优美而忧郁的作品却真实地再现了人们在世纪之交之时无所适从的痛苦,也就是“近现代人才有的那种个体主义的人生的孤独感与宇宙的苍茫感。”[1]428尽管他自己是浑然不知身后事的,他的情之所至的“虚无主义”、“颓废主义”,他和所谓香艳脂粉气浓重的鸳鸯蝴蝶派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等等都让他长期被文学史所屏蔽。
一、逃往自由——追寻自由人格
(一)独立人格的追寻
自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中,很多思想家都对“自由”这个哲学命题和人生命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在萨特眼中,“人的选择即自由”。在曼殊的人生轨迹中,畸零的身世使他如“断鸿零雁”般飘荡在人世间,孤傲倔强的他偏偏要挣脱被抛弃的命运,在生命的旅程中力意迸发出“生命力的突进”,已经显露出现代人文精神的品格。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自由选择,创造着自己的本质,向着未来的道路自我造就自己。所以,曼殊的这种独立人格的找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自我人生创造的过程,自我生命突进的过程。
由于苏曼殊身世经历的传奇性以及思想的多维性,他短暂的一生在人间舞台上扮演了众多角色:革命家、启蒙主义者或佛门高僧。曼殊纷繁的人生体验有着追求真我,探索人生终极价值的执著与倔强。但其彰显的如浪潮般涌动的个性,任性而为地放浪形骸并不是为了标注一个新旧时代启蒙者的光辉形象,而是其天然个性的自然流露。可以说,曼殊不是一个能“肩起黑暗的闸门”的坚定的革命者,也不是一个“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理性的启蒙者,更不是一个“断惑证真、悟入真如”的佛家高僧,这些角色是无法框架住他的,对于这些人生角色,曼殊却始终有种漂泊感,一种在渊深的海里不断挣扎、回漩之感。他是一个新旧时代文化与文学转型期的浪漫歌者,一个在震撼心灵的时代浪潮中进行回漩与突进的时代歌者,但他的歌不是宏大的历史的歌,不能够站在万人之上地引吭高歌,而只合在月华如水的夜色里随着微风静静歌咏,或许那歌者的歌声并不嘹亮悠扬,甚至是略带嘶哑的颤音,但那每一个音节的颤抖都是来自曼殊灵魂深处的悸动,都是曼殊心灵的回漩波荡,正是这样一个“歌已哭,哭复歌”的歌者将胸中的不平、怀中的郁结以及牵绊他一生的“爱的涅槃”如幽泉流于深谷般静静地注入他的文学作品中,他像一座外表平和静谧、内里却动荡不定的活火山,随时都会爆发也随时都会寂灭。
(二)找寻精神上的“因缘”
曼殊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洋溢着的青春、生命的激情,以及特殊的身世经历都促使他找到了精神上与之契合的拜伦。如冯至所说:“我不迷信,我却相信人世上,尤其在文学方面存在着一种因缘。”[2]34曼殊在《潮音》序中写道——“他(即拜伦)是一个热烈的,真诚的为自由而献身的人,不论在大事业和小事业上,也不论在社会的或政治的每件事情上,都敢于要求自由,他认为自己无论怎样做,无论做到什么程度,都不过分。拜伦的诗,象是一种使人兴奋的酒。——饮得越多,就越觉得它甜美、迷人的力量,他的诗里,到处都充满了魅力、美感和真诚。”[3]50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近代》中在论及二十世纪初中国文艺时说道“正是这位(拜伦)出身高贵、满脸傲气、放荡不羁、难容于祖国俗议的叛逆诗人,在二十世纪初成了中国青年革命者、知识分子所顶礼讴歌、有着强烈共鸣的对象。”[1]430就是在这个历史转折期,以拜伦为象征的西方浪漫主义大潮向中国知识分子袭来,那号召个体独立的思想情感方式给古老的文明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同时进一步促进了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形成。拜伦对苏曼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气质上,拜伦那如大海般汹涌澎湃的生命激情,拜伦性格中的敏感、自尊、好强、孤傲、暴烈、反抗、悲观、阴郁等特点,都使曼殊感到一种天然的契合。尽管苏曼殊对拜伦充满了崇敬之情,与拜伦产生了共鸣,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并且在诗歌创作中着力仿效拜伦作品所具有的浪漫主义气质和个性主义特征。但在形式和内容上,他仍然选择了中国传统的诗歌表达,基本运用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字典故。曼殊所译拜伦的《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如鲁迅所评价的“显得古奥”,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传达出拜伦那叛逆的生命激情,倒是曼殊借译作传达出他漂泊于人世间的壮怀豪情与孤独悲愤。
曼殊用追求独立自由的人生姿态和他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知识分子自由人格、自由精神的向往,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燃起黎明的光。他用诗人的幻想和浪漫构筑的文学作品也就成为他最后的逃亡地,一个灵魂可以最终安然栖息的精神家园。
二、“爱与死”的主题——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生成
如李泽厚所说的:“苏曼殊描述的爱情已不复是《聊斋》里的爱情,也不是《牡丹亭》、《红楼梦》里的爱情,当然更不是《悔海》里的爱情。”[1]430在感伤的气氛中重新反思“爱与死”的人生和文艺的永恒主题,在世俗的故事中追求一种超越性的爱之体悟与死的冥想,祈望着“超越爱与死的本体真如世界”,而这个本体真如世界实际上只存在于这个世俗的情爱生死之中,但这种对于爱与死的体悟与冥想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逃于禅”的佛学观念,而是包蕴着西方浪漫主义点燃着“爱与死”的沸点。在20世纪初,理性、乐观的启蒙主义与拜伦式的非理性、狂热的浪漫主义促使“逃于禅”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为新旧时代的各种思想文化在敏感的知识分子心灵上留下的巨大撞击。从这个层面上,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苏曼殊作品中“爱与死”的主题所体现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以及从中展露出的中国现代文学悲剧的生成。
在世纪初通俗文学言情小说的潮流中,“情”是其“不死之魂”,而我们看到无论哀情、苦情、悲情……,“死亡”却是大行其道的情节模式。如李金发《有感》中“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苏曼殊对死亡主题情有独钟,他的全部小说没有一部不以“情死”或遁入佛门而“善终”,可见多愁善感的苏曼殊有着浓厚的悲剧意识。
苏曼殊小说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小说的题材内容上,他的小说几乎都是荡气回肠的悲剧爱情故事。《绛纱记》中昙笃与五姑的悲剧则因昙笃舅父破产而五姑家父退婚。《断鸿零雁记》中三郎与雪梅的爱情悲剧因雪梅父亲见三郎家道中落而悔婚,致使三郎遁入东门,雪梅以死殉情。《非梦记》海琴与薇香的爱情,因婶母贪图财钱百般阻挠演化成悲剧。年轻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脆弱无力,理想之花的绚烂与现实处境的残酷之间的矛盾必须会使爱情走向毁灭终结。进而,小说通过揭示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源,对封建宗法制和门第观念对人性的毁灭与摧残给予了有力的抨击。
三、艺术形式的现代性倾向
(一)自叙性小说的开创
从叙事角度来看,曼殊的小说也颇具现代意味。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叙事不同,苏曼殊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或第一人变式的叙事方式。《断鸿零雁记》以第一人称手法,展现了三郎内心的冲突与斗争,道出了人物的真情实感,可以成为我国第一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碎簪记》亦以第一人称手法,通过“余”的所见所闻来展现庄提与灵芳、莲佩的爱情悲剧。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并且增强了对个人主体情绪的渲泄和自我个性的张扬,而这正是现代性在人的个体生命中的显露。“只有人的独立价值被重视的时代,自叙传性的作品才会大量产生。”[4]546这要等到五四时代孕育出的创造社,郁达夫、郭沫若、郑伯奇等一批作家创作了一大批自叙传小说,特别是郁达夫,他那“沉沦”在性灵深处的情欲的挣扎,大胆地呼喊着“灵的觉醒”。
(二)浪漫抒情小说的发端
曼殊小说的艺术价值,不仅仅在于“自叙性”,更多地在于叙述方式的主观化、抒情化和由此开拓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的潮流。我们回顾20世纪初中国的小说,苏曼殊以其独抒性灵的文字自成一家,他的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便是“情”字,以主观心绪的流动构成作品的空间结构。“曼殊的文学,是青年的,儿女的。他的想象,难免有点蹈空;他的精神,又好似有点变态。”[5]57实际上,这是郁达夫、郭沫若、倪贻德等抒情群体的共同特质。曼殊那带着感伤的爱与自由的浪漫主义,的确与五四青年产生了天然的感应,尤其是五四落潮期,那些一度热情奔走,将家国使命置于自我生命之上的青年,猛回头之后,梦醒了无路可走。
在五四小说史上,除了《狂人日记》,在发表之初引起文坛大地震的可能就是郁达夫的《沉沦》了,它对于“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的描写无疑一声惊天春雷,炸出了文坛的千姿百态。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上,从小说而言,对于人物的理解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一)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二)人物性格化的展示阶段;(三)以人物内心审美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化展示阶段。”[6]33苏曼殊一改传统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主线,而以人物情感流动变化作为推动小说发展的动力。《断鸿零雁记》就是以三郎在灵与肉、情感与理智、出世与入世间的回旋与冲突的心理来组织全篇的。事实上,中国的小说从来就不是个体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承载体,正因为如此,苏曼殊的小说在现代文学的源流处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才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三)审美风格的转变
在美学风格方面,苏曼殊小说也同样具有超越意义的。他的小说既没有早期新小说的板滞的面孔,也没有后来者鸳鸯蝴蝶派小说彻底的媚俗,而是悠游于其间。周作人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是客观精当的,他认为∶“正如近代文学史不能无视八股文一样,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就不能拒绝鸳鸯蝴蝶派,不给它一个正当的位置。”[7]76并认为苏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大师“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在以后文学史著中,苏曼殊也屡被提及,例如:1958年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史》,1959年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这和一直以来对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的非公允的认识有关,其用意是要切断早期革命家的苏曼殊与媚俗的鸳鸯蝴蝶派的丝丝缕缕的联系。苏曼殊的小说不同于鸳鸯蝴蝶派之处在于他的文字更为纯净清新,没有那种“近乎色情的游戏描写”。
更为重要的是苏曼殊的小说人物形象虽然有很多怀有悲观的人生情愫,但并不绝望,曼殊笔下人物如他本人一样在人生的多重选择和诱惑中回漩与突进,在人生的歧路中不断判断与选择,并不是世人所谓的“颓废者”、厌世者,而是坚持不断向内心深处探索,有着认识自我的勇气。“认识你自己”是篆刻在阿波罗神庙的一句箴言,千百年来的智者都在这句箴言的光照下摸索通向自我内心的曲折的道路。尼采在《道德的系谱》的前言中,也针对“认识你自己”来大做文章,他说:“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8]6
曼殊短暂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寻找自我本真,这不仅仅表现为他对于自身“断鸿零雁”的身世的执著探寻,更深层次地体现在他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探寻,在这过程中伴随着曼殊“生命力的突进”,但更多地则表现为精神世界探索进程中的回漩。这新旧时代交替时期回漩困惑着千百年来的知识分子,但丁把他的回漩与突进谱在了《神曲》中,每一个跳跃的音符都是他精神世界激烈挣扎与矛盾的外化;歌德将其困惑与探索熔铸成浮士德这一上天入地的探索者形象;曹雪芹用其余生残力将人间多少浮华烟云都幻化成一曲《红楼梦》……从这种意义上看曼殊作品,外在的审美风格的转变而具有的超越性,在不媚俗与不革命的外在审美风格下跳荡着不安的灵魂与思想,不断回漩与突进的生命力。“回到现场、触摸历史”,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进程,发掘那些深埋于历史和文学史中具有丰富生命力的资源,毫无疑问,苏曼殊就是这类资源中的一部分。苏曼殊对于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近现代形态转换的创辟作用,尤其是在新旧时代转型期的精神世界的回漩与突进是十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同时,他的精神的困顿与挣扎也给他的文学作品带来了“苦涩的清新”,这对于20世纪初中国文学现代性是十分具有启发性意义。
[1]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2] 冯至.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J].世界文学,1989(01).
[3] 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 郁达夫.苏曼殊全集·杂评曼殊的作品[C].北京:中国书店,1985.
[6]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7] 周作人.答芸深先生[C]//柳亚子.曼殊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
[8]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尼采文集[C].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之 者
I207.64
A
1671-8275(2010)06-0123-03
2010-10-18
1.崔鑫婷(1988-),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人,大连民族学院中文系学生;2.丁颖(1975-),女,辽宁大连人,大连民族学院教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