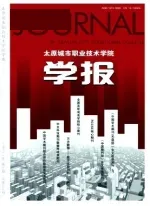森林中的彼岸世界
——从《挪威的森林》中透析村上春树的生命态度
2010-08-15张文彬
张文彬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森林中的彼岸世界
——从《挪威的森林》中透析村上春树的生命态度
张文彬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此在世界与彼岸世界是村上春树作品中永不消歇的主题,通过对这两个存在的探究以实现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审美化的观照。在《挪威的森林》中彼岸世界被设置在了茂密的森林中,其所传达于读者的是无尽的孤寂、迷茫以及举棋不定的游移。本文将通过对《挪威的森林》中生活在此在世界与彼岸世界人物的深入剖析来透视作者村上春树的生命态度。
《挪威的森林》;此在世界;彼岸世界;归属感;生命态度
一、强烈地无归属感的存在
“内里精神无归属感”,这个带有一定哲理意味的话题在众多作家尤其是日本现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屡见不鲜,但唯有在村上春树(以下称作村上)的作品中它才得以全景聚焦式地呈现。村上于1987年出版的青春小说《挪威的森林》(以下称作《挪》)中作者就为我们勾勒出一群内部精神极度缺乏存在感的灵魂。他们是一群以“边缘人”身份真实地存在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的东京或神户,但是精神却无处归依。
主人公渡边厌恶那个社会,那种既定的体制,希望大学遭到学潮的肢解,而当希望落空后他无奈道:“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决定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物料的忍耐力”,他的心绪烦乱,无奈集中在其精神世界对既成的一切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反感以及无可奈何,而对某种不清晰、不明确的目标又似是而非地执着着,“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以便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是不是向空间浮动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都触不到。”作品中主人公不止一次地找不到精神的坐标“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心不知所措所以迷失。
直子,一个属于过去的死亡世界的阴柔美的化身,是一个非现实的存在,具有明显的“存而不在”的性质,患有严重的精神断绝症,除了死去的恋人木月外,不能与其他所有人沟通甚至是交流。“我觉得自己周身仿佛紧紧贴了一层薄膜,由于薄膜的关系,我无法同外界相融无间,而同时他们的手也无从触及我的皮肤。”直子与木月,一对完美的恋人但那种完美近乎病态,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毁灭。他们将除其二人之外都垒起了高不可测的围墙,从来不出来与人交流,也不放外人进去,偶尔进去的渡边也只是维系他们与外界的虚弱的纽带,而当木月不期然地“离去”之时,直子的世界便顷刻崩塌,理想覆灭,精神领域一片黑暗,内心被死去的木月吞噬致成了巨大空洞,最终抵挡不住死亡的诱惑。在日本现代社会,人们因承受不住幻灭感所带来的精神无归属感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去追寻自我存在的意义,一旦理想破灭,人会以自杀来反抗无归依感对人精神的腐蚀。
具有非凡气质,春风得意,所向披靡的永泽同样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途中,以声色犬马来抵御精神孤独的痛苦。他内心一样充满了沉重的失落感和无归属感,只能用压抑和玩弄别人来证实自我的存在,其精神也一样在流浪。“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他们想摒弃旧理想,旧信仰,却又未能建立新理想,新信仰。丧失善恶美丑的标准,于是无所适从地怀疑一切,他们对现实不满感到幻灭,可又无力改变现实,便彷徨在虚无和绝望中,企图寻找某种方式来暴露他们这种幻灭的悲哀和现实的痛苦。”精神无处安置时所表露出的强烈无归属感充斥着每个人的内心。
二、致命残缺的彼岸世界
《挪威的森林》虽然是村上春树反复强调的“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但依然秉承了村上“两个世界”的创作理念。作为与此在世界对极存在的彼岸世界在《挪威的森林》中却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村上春树的其他作品,但相同的是都代表了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具有浓重的非现实色彩。
早在我国古代就有五柳先生陶渊明的理想之国——“桃花源”,那是人类最理想的彼岸世界:淳朴的人们、如画的风景,纯洁却充满生机的环境,俨然一方脱离残酷现实的所在,而《挪威的森林》中作为彼岸世界的“阿美寮”却是一个拥有致命残缺的彼岸世界,它是一所坐落在深山老林之中的精神疗养院,具有与世隔绝、得天独厚的现实条件,这种凌驾于喧嚣俗世之上的虚假的优越感使得身在其中的人忘记现实之中无法承受的种种,但也阻隔了人与最本质的存在的交流与互动,它是一把双刃剑,在刺穿现实复杂性的同时也斩断了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由于过于悠闲,有时我甚至怀疑这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阿美寮”在本质上无异与直子和木月周围的高墙,通过拒绝外界来维护围城内部的“安全”、完美,然而这种病态的完美却拥有最致命的缺陷。人,一种被定义为社会存在的存在,若拒绝与外界的对话而固执地将其自身与现实隔绝,就无法获取人之为人的意义与价值,而人又无法丧失意义而存在。所以,阿美寮虽然是一所以治愈病人为其本质精神的疗养院,但其实是一座美丽的坟墓,一点一点蚕食着一个人向往现实生活的勇气:“这所疗养机构的问题在于:一旦进入这里,便懒得出去,或者说害怕出去。在这里生活,心境自然变得平和安稳,对自己的反常也能泰然处之,感到自己业已恢复,然而外部世界果真会如此接纳我们吗?对此,我心里很不踏实”,这是已入住阿美寮的直子写给渡边的信,活在自我虚假的完美之中,最终她用死亡无言地证明了乌托邦式的疗养院无助于都市人困惑的实际解决,生活于其中的人将其作为一个不受外力粗暴伤害的所在,并用以逃避社会、责任和成长所应付出的代价。其中最能体现逃避哲学的人物是石田玲子,她在“阿美寮”疗养已达七年之久,绝少与外界联系,甚至连亲人都不理,三十一岁时遭到一位前来向她求学钢琴的仅有十三岁的女同性恋者的恶意陷害,而致使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内心遭到了重创:“我们精心构筑的一切在那一瞬间彻底崩溃了,完全化为泡影”,之后玲子近乎武断地逼迫着丈夫,最终离婚并离开仅有四岁的女儿,只身龟缩在“阿美寮”,事实上,她也并不承认这所疗养院可以让她在面对现实挫折时拥有坚不可摧的“免疫系统”,而只是关起高大的门阻隔一切外界的病菌侵入罢了。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和痛苦,不是选择让自身变得强大,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不去触碰那些必经的挫折,这便是“阿美寮”的疗养理念,一种不是把人指向生而是将人引向死的治疗理念。
“阿美寮”是一个比现实世界更为荒谬、怪诞,甚至更为阴森恐怖,含有病态成分和死亡气息。它无法给病人带来生的希望以及面对未来的勇气和支撑存活的坚强信念,无法给予病人所需要的真实的阳光和盎然的激情。
三、依稀可见的生命态度
《挪威的森林》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村上春树生于1949年,而《挪威的森林》成书于1970年,即:主人公渡边21岁,也正值村上春树本人21岁,由此可见,村上春树本人与主人公渡边拥有一样的社会成长环境:共同经历了日本二战后经济神话般的飞速发展,“全共斗”的大学潮,学潮失败后的精神空白。就个人方面来看,村上春树与渡边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酷爱爵士乐、欧美文学(特别是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的美国作家菲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样厌恶日本的大学制度。大学时代村上春树所住的名叫“和敬廖”的宿舍也极似小说中渡边所住的学生宿舍。关于学潮,他们也秉承一样的态度,即:一直同所谓的集体运动完全绝缘,喜欢一个人行动从不依附任何政治体制,村上春树曾说:作为个体,自己很享受学校的“骚乱”。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而认定村上春树就是渡边的原型,但渡边对生命的本质态度村上春树本人是有理由认同的。以下我们将通过渡边来窥看作者村上的生命态度:
在作者设定的两个世界中,渡边是穿梭于此在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一条纽带,充当连接现实与非现实桥梁的作用。他让两个世界产生了对话与交流,在现实与非现实两个世界不断的撞击之中,超越了此在世界,在饱览和遭受由彼岸世界的致命缺陷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后,对其进行否定而后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孤独与迷茫回归此在世界。渡边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既不愿参加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残酷的竞争,也不屑于手拉手一道游行以肢解大学,同时也不隶属于或认同于以“阿美寮”为代表的病态的彼岸世界。与此同时,渡边的这种生命态度,通过村上春树在作品中另一位女主角——小林绿子的设置,也在依稀之中透露了渡边的内心世界。
小林绿子,一个标准现实里真真切切的存在,她和直子代表了两种美的极限,直子固守着彼岸世界幽怨孤寂的灵魂,象征着一种阴郁之美;而绿子则热情爽朗、坚强,寓意着阳光之美,她全身迸发出了无限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来的一头小鹿,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或笑或怒或惊讶或泄气。绿子和直子都同样经历过亲人的离世,但绿子却能坦然面对,作品中的绿子始终保持着盎然的生机与活力,无论与人交往还是面对拮据的生活,她总是激情澎湃,对爱情和友情永远投注最大的热情。渡边第一次做客小林书店时,我们从渡边的视线窥看到绿子对于厨艺的由衷热爱,对于爱情,她并不执著于过去而是只求内心的契合,因此绿子亦然决然地选择了渡边。这与静静地活在死去男友余韵之中的直子截然相反,她们是将一个女人的阴阳两面分开来最大限度地烙刻在自己的灵魂里。渡边与绿子交往的过程中被绿子身上所散发的阳光味道以及内心所传达的鲜活气息所震撼,渡边在给玲子的信中这样描述着内心的感动“而绿子方面则截然相反——她是站立着的,在行走在呼吸在跳动在摇撼我的内心”,绿子以巨大的冲力打开了渡边犹如坚果一样的心门,那是一缕现实阳光的穿透。
作品中对于彼岸世界的否定是通过直子的自杀以及玲子走出“阿美寮”来实现的,直子是一条作茧自缚的蚕,始终活在自己为自己设定的虚假围城之中,“阿美寮”却无法将其送回现实,直子也无法以坚强的姿态来迎接来自此在世界的一切挑衅,最终她只能孤独地走进黑暗的森林深处勒紧自己的脖子,她的自杀使渡边清醒地认识到那个彼岸世界的致命缺陷。
关于玲子的结局,村上春树安排她最终选择离开疗养院而回归现实,回到七年前离开的现实,她从象征死亡世界的“阿美寮”走出来,想重新回到曾经让她千疮百孔的现实世界,这使得玲子既紧张又迷惘,但如同渡边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只能是如何活下去,除了祝你幸福,还要幸福的活下去”,于是,玲子带着渡边的祝福与期许走入了能带给她新生的此在世界。送走玲子的渡边,如同玲子决心考虑活着的问题一样,他也选择了活着,选择了现实,选择了绿子,尽管“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在回来的途中迷失了,但“我”呼唤着,向一个满身充溢着希望之光的人——绿子求救。渡边经历了此在世界的无归属感的存在,目睹并承受着彼岸世界对人身心的蚕食,而最终决定结束精神的流浪,真诚地回归此在世界。
[1]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D106
A
1673-0046(2010)01-019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