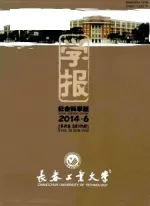浅议国民素质普提时代下我国教育的法治环境
2010-08-15刘蓓
刘 蓓
(长春工业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
浅议国民素质普提时代下我国教育的法治环境
刘 蓓
(长春工业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透过德国国内教育的相关法律政策与制度以及对我国国内教育现有相关法律政策与制度,说明了国民素质普提时代来临,教育面临更多更复杂问题。为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遭遇的国民素质亟待普遍提高的难题,教育法治环境的改善应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有关教育的政策、法规、制度应全面跟上。
国民素质普提;教育法规;教育政策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自建国起,我国的领导人就特别强调要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始终如一地高度重视共和国的教育事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为推进我国的素质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1917年4月2日,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更系统地阐述了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的思想。他说:“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以此耳。”“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此耳。”“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1](P67)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他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P340)他60年代中期又提出:“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
邓小平曾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从恢复和振兴教育事业抓起。1977年8月,邓小平亲自作出了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的决定。197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全局中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地位树立了第一块里程碑。到2008年底,“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3%。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576.07万人,毛入学率74%。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3]国民素质普遍提高的时代已然来到,这必然要求教育的法治环境也要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与制度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教育传统的文明古国。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教师和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问题。孔子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孔子倡导“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他提倡不分长幼,不论贵贱,不认种族,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孔子之前,贵族阶层垄断了文化教育权,平民阶级没有受教育的可能,教育仅仅是局限在最高统治阶层范围之内的事,办教育的目的,也只是为统治者培养接班人。学校的贵族化,阻碍了文明的普及与发展,也扼杀了平民百姓的求知欲望。孔子从三十岁左右开始,便打破历史的陈规,创办私学,明确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思想。这一教育思想的提出,开创了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的新道路,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创举,也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很有革命意义的突破。这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与”学在官府”相对立的“学移民间”、“学术下庶人”[4]的划时代的标志。
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出现在德国。德国地处欧洲心脏地区,自古即为人文荟萃之地。二次大战后,于短期内由废墟中复兴,成为目前欧洲经济力量最强大之国家,更居欧洲共同体之领导地位。此一成功之事实,断非偶然,实乃民族性所致。1619年德意志魏玛邦国率先公布了“义务就学规定”,规定父母应送六至十二岁的男女儿童入学,否则政府强迫其履行义务,这就是“义务就学法”的开端。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应致力于人类关系的改善;所有的人,同样由上帝创造,便彼此均等;不论男女,不分社会地位的贵贱,他们都应拥有受教育的同等的机会。这就是最初的教育机会均等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的传播,使普鲁士在1717年成为第一个实施“义务就学法”的国家,此法规定:所有男孩、女孩不论出身贫富都必须接受教育。类似的法规在法国1880年才开始制订,在英国则是1882年。义务教育一开始就渗透“政府强迫其履行义务”的观点,因此也被称之为“强迫教育”。
与德国相比较,我国的义务教育起步较晚。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国民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两部分,同时实施。依据张惠芬、金忠明编著的《中国教育简史》记述:“由于采取强行措施,据全国实施该制度的19个省市统计,至1946年底,受教育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百份内之七十六强;历年共扫除文盲人数约占文盲总数百分之五十七强。”中国最早的义务教育的年限为四年,因此直至解放初期我国的小学学制中有四年初小,设立初小的原因就是民国期间曾经推行过四年义务教育。民国期间的义务教育在普及方面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是中国义务教育的雏形。
建国后,政府推行的是政府倡导下的普及教育。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样中国的义务教育从政府倡导下的普及教育转变为“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20年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行修订。新版《义务教育法》突出三个明显的特征:公益性: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不收学费、杂费”,并且强调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国家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体;统一性:强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义务教育,这个统一包括要制定统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设置标准、教学标准、经费标准、建设标准、学生公用经费的标准等等;义务性:强制性又叫义务性。强制性不仅是接受适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教育,还体现在政府是举办义务教育的主体,这也是有强制义务;家长和学校也有强制义务,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法律问责。这部法律的修订还体现了以下六方面的进步:首次明确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以法律形式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法律规定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学校乱收费主管人员将受罚;立法明确实施素质教育;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保障校园安全写进法律。这部法律是我国普及义务教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义务教育是关系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长远大计。我们要坚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各项规定,切实加快义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义务教育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从我国人口众多、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偏低的基本国情出发,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确立了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地位,作出了有步骤地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决策。到2000年底,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奋斗目标,全国85%的人口地区基本实现“普九”,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1%,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88. 6%,青壮年人口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残疾儿童入学率也有较大提高,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从80年代初期的不到5年提高到目前的8年以上,使基础教育长期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在我国教育史上谱写了辉煌篇章。
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从全国看,“普九”工作在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大部分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基础还非常脆弱,巩固和提高的任务十分繁重;还有15%的人口地区,主要是边远、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普九”攻坚任务相当艰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阶段,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义务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首先落实到义务教育上来,继续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义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当今人类社会所处的全球化、信息化、科技化时代要求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普遍提高,否则将被世界抛弃。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要颁布实施。“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制订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规划,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意义。”[5]由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将进入长达10年的战略机遇期。到目前为止,我们建设了一个教育大国,但还远不是一个教育强国,大而不强的教育绝不可能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由此,2020年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而继续完善教育法制,实现教育管理行为的法治化,这将是我国教育改革不得不面对的一道坎。
温家宝总理不断强调指出的:“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当今世界,知识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人才培养与储备成为各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占据制高点的重要手段。我国是人口大国,教育振兴直接关系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振兴。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国家。”
推进中国教育改革一定要加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领导,建立和完善教育执法、监督体系,解决教育事业有法不依,教育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还要推进教育行政问责,解决教育事业违法不究、有责不问的问题。随着国家教育领导力的不断提高,我国教育改革会尽快走出困境、进入健康和谐发展的轨道。
二、我国教育法治环境有待改善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管理精神和价值追求,是伴随西方文化产生的。西方社会的法治可以追根溯源至古罗马的城邦文化。经过几百年的教育跋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管理行为法治模式已经逐步确立并且稳定下来。在走向21世纪的过程中,教育管理行为法治化的新趋势是,政府教育管理行为自身的权利制衡和法制过程中的民主保障得到加强。
教育的去行政化,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在国内,教育行政化已成为了教育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离不开长期官僚作风影响。“学而优则仕”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所走的路线,也是一种无形的知识分子价值观,普遍而实惠。读书为了什么?升官发财。读书功利化,不应该归咎于人们对教育功利追求,而是来源教育长期被扭曲的价值观。温家宝数次公开批评教育行政化,并明确表示“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面对国内教育法治环境充斥众多问题的现状,我们可资借鉴的西方国家政府教育管理行为法治化基本经验,总结如下:一是行为法规,即政府的教育管理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二是保障公平,这是政府教育管理行为法治化的基本原则;三是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和救济制度,这是政府教育管理行为法治化的保障机制;四是更加注重采取非强制手段,即更多采用民主和参与方式,强调与公众的协商行为和重视公众的参与度。这种非强制手段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如美国就是靠教育的财政投入来控制各州教育法规的执行的。
此外,从人力资本理论来看,对教育的投资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是为未来的一种投资行为。发展基础教育,造就高素质的人才是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经费的重要指标就是看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德国前教育部长勒曼1987年访华时曾说:“谁在教育投资上节约了,谁就输掉未来。”发达国家都很注重教育投资。就美国而言,“目前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总投入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9%,各州的教育经费投入比10年前也有明显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通常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1995年,德国、英国、韩国等国公共教育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8%、5.4%、3.6%。
大国的崛起是一项长远的战略,中国的伟大复兴一定要从教育抓起,大力提高国民的素质,这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战略。我国用30年走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教育发展之路。不过,发达国家普及教育之后的理念变革及制度创新,却不是轻易能够赶超的。国家发展大计需要人才的支撑,需要全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中华民族伟大负心的历史重任必须面对这一艰难战役,所以相关政策法律制度必须跟上脚步。中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时。
[1]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Z].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3]教育部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4]唐宇元.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5]温家宝.教育大计,教师为本[N].新华社,2009-9.
刘蓓(1983-),女,法学硕士,长春工业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助教,主要从事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