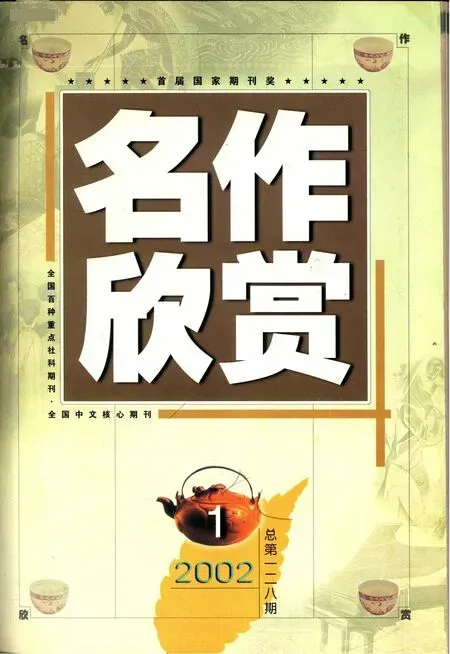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我读着》:“我写出,我看到”
2010-08-15/陈超
/陈 超
作 者:陈超,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多多,朦胧诗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行礼:诗38首》《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多多诗选》等,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对于许多诗人来说,写诗要有对日常生活“硬事实”和已成的情感经验的“仿真性”。诗人要做的工作是对这些“可靠”的材料进行提炼、组织,谁干得出色,谁就赢了。近年来现代诗的流行写法就是如此。这也带来了现代诗准确、恳切的意蕴和语调。我想将这种写作概括为“我看到,我写出”。
相对于这种流行写法,在当下诗坛遭到背弃或抵制的是“我写出,我看到”的写作。诗人凭借丰盈的想象力和神奇的语言天赋,写出什么才出现(看到)什么。这路写法之所以遭到背弃或抵制,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这路写法较容易蒙事,使众多骨子里没啥名堂的“嗜诗症”患者,凭一点点怪癖和把玩语言的技巧来瞒天过海。读者一旦识破,就会产生抵制心理,并广泛迁怒于所有这类诗人;其二,优异的超现实主义诗歌,需要真正的才能——如果不说“天才”的话。这种才能对诗人而言就是原创力,对读者而言就是敏识能力。而具备这种真正才能的人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都永远是极少数。
多多是属于“我写出,我看到”这条文脉上的杰出诗人,甚至是当代实验诗这路写法的源头。他从不追摹日常生活事实,而是不断地发明一种“语言现实”。即“我”写出什么,才出现什么。
这首诗基本的“情理线索”是追忆父亲(也可以说是“父辈”),逝去的一代人在分裂而屈辱的岁月里,“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以及那些粗糙而鲜润,颓废又健康,哀愁却又有秘密欣喜的细枝末节。但其基本“措辞线索”或曰中心语象则是“马”。父亲与马是处于同一变化中又彼此打开、彼此发现的互指关系。诗人从领带、裤线神奇地转到“蹄子”,然后一路写开,而不只是象征主义式的以马来隐喻父亲。这正是多多诗歌的既诡异而又精审之处,中国诗坛很少有人能像多多那样,做到将诡异和精审完美地同时呈现出来。
这首诗,随时面临着将要发生的“语言事件”。它是和书写动作同步出现的崭新叙述,或者说语言与感觉同步发生。从开始的“十一月的麦地”到结尾的“伦敦雾中”,像一条历尽沧桑的溜索两端的扣结,坚实而完整地抻起了这首诗的时空喻指;而在弯曲柔韧的溜索中间,有多少心灵的细节,可能的语象撞击速度,感觉的迂回升沉。还有,在溜索之下又有多少逝水的温暖召唤和凶险的漩涡!
《我读着》——“我读着”。我一直以为,对于多多来说,每一首诗至少都有两个主旨,一个主旨是诗歌情境固有的,另一个则是关于写作本身的。也可以说,“写作的可能性”(或曰语言的可能边界)本身就是多多诗歌的“主题”之一。因此,诗人说“我读着”本人发明的语言事实,而不是“我回忆”本真的经历,它们是“我”刚刚从词语中一步步读出来的,随写而生,随生即盛,“我”也是自己书写物的读者。另一方面,对读者而言,诗人吁求我们与他一道“读”,即仿照这首诗的写法去读它。阅读也变成一种特殊类型的“写作”,我们在阅读中将这首诗“再写一遍”。
因此,我们其实不必对多多的诗歌意蕴进行固定的“解读”、“阐释”(它更适于智性的象征主义诗歌),而是直接感受即可。对他的诗,知者(感者)自知,不知者永远不知,社会历史式的解读帮不了后者的忙,只会伤害一首杰作。那么朝向这些语词和“音粒”的欢乐吧——“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一边溜着冰,一边拉着小提琴/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对这样的句子,没说的,我狂读享受,并对诗人记恩。
我读着
/多多
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父亲
我读着他的头发
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
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
一边溜着冰,一边拉着小提琴
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
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
我读到我父亲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马群
一棵小树上挂着他的外衣
还有他的袜子,还有隐现的马群中
那些苍白的屁股,像剥去肉的
牡蛎壳内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
我读到我父亲头油的气味
他身上的烟草味
还有他的结核,照亮了一匹马的左肺
我读到一个男孩子的疑问
从一片金色的玉米地里升起
我读到在我懂事的年龄
晾晒谷粒的红房屋顶下开始下雨
种麦季节的犁下拖着四条死马的腿
马皮像撑开的伞,还有散于四处的马牙
我读到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
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
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
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
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
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
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