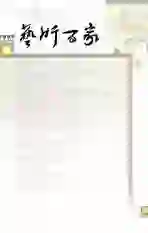企盼清官与张扬人的自由
2010-05-10李建明曹必文
李建明 曹必文
摘要:本文对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涉及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的戏剧进行了比较。莎士比亚更关注大人物的命运,西方人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而关汉卿描写的主体一般是小人物,小人物力量极其单薄,面对权贵的欺凌,往往求告无门,只能靠外力——鬼魂或清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追求大团圆结局。中国人过分讲究忠奸、好坏对立,又使得关汉卿笔下的坏人往往是恶的化身,看不到丰满的性格,这与西方对个人命运顽强探索和反抗、努力挖掘人性的深度是不同的。莎士比亚对于善于恶,更多的时候并不借助于法律来解决,而是充分表现人的本质。在他看来,悲剧的原因根源于人自身,人的自由意志往往陷入到罪恶之中。他思考人的救赎,寻求人的终极关怀,而不是把恶人绳之以法就万事大吉。莎士比亚从不把清官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他的作品中没有清官文学。
关键词:关汉卿;莎士比亚;善与恶;鬼魂或清官;戏曲艺术;戏剧艺术;比较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9)07-0095-05
清官文学自宋元以来,代代相传。西方有反映法律或冤冤相报的文学作品,但却没有清官文学这品种。关汉卿对于一代文学的元曲,莎士比亚之于欧洲文艺复兴,都是标志一个时代的文化巨人。两人在身世和成就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这里,仅就他们善恶斗争的案情剧进行比较。关汉卿写有《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窦娥冤》等公案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奥赛罗》等戏有惩奸除恶的内容,《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戏有公爵出面判决,也可看成宽泛的公案文学。本文试图对中西方两位作家的案情剧进行比较,希望揭示西方何以没有清官文学的秘密所在。
一、草民的冤屈与人的权益
钟嗣成在《录鬼簿》中记关汉卿杂剧存目有60多种,现存杂剧十八部,关汉卿的悲剧作品主要有《窦娥冤》、《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等。这些悲剧都以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为主角,写出了小人物的无奈与悲哀。也体现清官解民倒悬、刚正不阿的品格。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围绕安东尼奥为帮助朋友巴萨尼奥的婚事而向高利贷者举债,夏洛克对安东尼奥一直怀恨在心,听说他要借钱,想乘机报复。他不要利息,却要安东尼奥在借据上写下:如到期不还,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抵偿,偿还期到,突然传来安东尼奥海上航船悉数沉没的消息,安东尼奥面临以肉抵债的厄运。该剧的重点是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西娅和侍女女扮男装,以法官身份在法庭上就“还债割肉”的官司与夏洛克较量。主题是慷慨无私的友谊、真诚美好的爱情以及善良仁爱的美德同嫉妒、仇恨、残酷之间的冲突。这里,且谈谈本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鲍西娅如何利用法律手段巧妙地战胜夏洛克,并保卫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贪婪、冷酷的夏洛克,在第四幕中盼到了他日夜都想报复安东尼奥的机会,在法庭上,公爵用情来打动他,希望他对安东尼奥动恻隐之心,而夏洛克复仇心切,面对最高长官的劝说,他坚决不答应,并威胁道:“要是殿下不准许我的请求,那就是蔑视宪章,我要到京城里去上告,要求撤销贵邦的特权。”当鲍西娅以法官的身份来劝夏洛克慈悲为怀无效时,巴萨尼奥请求法官“运用权利,把法律稍微变通一下,犯一次小小的错误,干一件大大的功德,别让这个残忍的恶魔逞他杀人的兽欲。”鲍西娅回答道:“那可不行,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力变更既成的法律,要是开了这一个恶例,以后谁都可以借口有例可援,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了。这是不行的。”私情、权利都不可以变通法律,“威尼斯的法庭是执法无私的,只好把那商人宣判定罪了。”“根据法律,这犹太人有权要求从这商人的胸口割下一磅肉来。”鲍西娅在法庭上肯定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而莎士比亚在这里也向人们表现了法治的弊病,夏洛克这样的坏人同样可以利用法律致安东尼奥于死地。这是莎士比亚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让鲍西娅利用对法律的解释惩罚了夏洛克。正当夏洛克准备割人肉泄愤时,鲍西娅说:“且慢,还有别的话哩。这约上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只是写明着‘一磅肉;所以你可以照约拿一磅肉去,可是在割肉的时候,要是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当夏洛克表示不打官司时,鲍西娅紧追不放:“等一等,犹太人,法律上还有一点牵涉你。威尼斯的法律规定凡是一个异邦人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明确有实据者,他的财产的半数应当归受害的一方所有,其余的半数没人公库,犯罪者的生命悉听公爵处置,他人不得过问。”夏洛克人财两空,法律对他似乎又过于残忍。所以,莎士比亚提出了一个公道与慈悲相结合的主张,把希望寄托于人们的道德良心之上。鲍西娅在法庭上对夏洛克说:“慈悲……是一种属于上帝的德性,执法的人倘能把慈悲调剂着公道,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这是莎士比亚的声音。
鲍西娅并没有乞求清官——公爵——借用他的权利去压服对方,而是利用人人通过学习都能掌握的法律,才在一磅肉的诉讼中取胜。这与鲍西娅生长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关。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成功的一个方面,就是人们懂得的自身价值和意义,并且用法律提供制度保障,鲍西娅的胜利是法治精神的胜利。
而生活在十三世纪末的窦娥则没有这种幸运。窦娥生活的元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吏治最黑暗的时期,剧中的桃杌见到告状的就下跪,“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审判程序按“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方式办理,“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成为普遍现象。这时窦娥们要想申冤洗雪,只能倚仗清官。
清官为草民洗冤也有条件。即如窦娥而言,死后冤魂不散,几次托梦给已当上提刑肃政廉访使的父亲告状。窦天章不顾失女之痛,先是对女儿一顿训斥:“你是我亲生女儿,老夫将你治不的,怎治他人?我当初将你嫁与他人家,要你三从四德……”他首先查实女儿是否遵从了三从四德,窦天章从女儿的三桩誓愿一一应验,也就是在“天”、“神”作旁证,封建伦理道德作准绳的情况下,窦天章才给女儿伸冤,杀了张驴儿,惩戒了桃杌。
显然草民的冤屈得昭雪的前提是他们的行为必须符合封建伦理道德,他们必须是封建王朝匍匐在地的顺民。《蝴蝶梦》中,王氏兄弟三人为父报仇将葛彪打死,此时必须有一人来抵命,王母与三兄弟争相顶罪,最后王母留下三子抵命,而三子却正是王婆婆的亲骨肉。王婆婆的出发点是怕“教人道后尧婆两头三面”,“教人道桑新妇不分良善”。王氏之所以让亲子顶罪,更多的是出于宗法制度下家庭伦理对一个妇女的要求。正式这种继母的贤德,让包公感动,才使用调包计救了三子一命。
由此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清官为草民昭雪的更多的是利用手中的权利,而不是法律的尊严,在《威尼斯商人》中,公爵作为威尼斯的最高长官,却无权干涉或影响法律诉讼公正进行,他更无权变更明文规定的法律。而中国的包公们则是以智慧的化身,采取巧妙手段惩恶除奸。鲁斋郎罪大恶极,但按
照常规的律令手段,无法将他绳之以法,于是在戏中包公采用了改名换姓的方法,用“鱼齐即”的名字巧取皇帝的亲批,待朝廷将其判斩的文书批下来后,再将“鱼齐即”添字加点改为“鲁斋郎”,从而智斩了这个权豪势要。善良百姓在遭遇不幸走投无路时,就把自己的生存希望凝聚在清官们身上,盼望有清官出现,为民做主,清官形象是民众的强烈诉求。窦娥在沉冤伸雪时还恳求父亲“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现实生活冤案遍布人间,“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生活在黑暗现实的百姓,渴求的是清正廉明的清官。问题是中国的清官是人治的产物,他是在凭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法律在行事,这样的清官梦,是很容易破灭的。元好问在《薛明府去思口号》:“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清官梦只是民众和作者本身的一种寄托和安慰,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无论朝代更迭,“清官”情结便始终凝聚在人们心中,挥不去,剪不断。而一旦草民的冤屈得以昭雪,马上换来的是草民们的歌功颂德,进而对于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皇权制度也一同被歌颂。《蝴蝶梦》中,当包待制救了石和,王婆与三儿石和拜谢,三呼万岁,“一齐的望阙疾参拜。愿的圣明君千万载,更胜如枯树花开。”祝愿皇权制度千载万代永不变。这就不仅是个人悲剧,而且是民族悲剧。正是这些温顺善良,屈从依附的民众,使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
而在《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感谢的不是公爵,而是法官鲍西娅,这是法律的尊严,是法律在维护社会正义和人道。只有在没有法理的古代中国,无数个没有人身权利保障的弱者和小人物,才会盼清官来伸张正义,澄清人间是非。
二、权豪势要与魔鬼化身
莎士比亚对于善于恶,更多的时候也不借助于法律来解决,而是充分表现人的本质。这从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的身上可以体会出来。关汉卿和莎士比亚作品中都出现了一些反面人物,关汉卿剧本中表现为权豪势要,揭露权豪势要的罪恶,是关汉卿杂剧现实性的表现之一;而莎士比亚中的恶人则表现了强烈的自由意志。
《望江亭》中的杨衙内自报家门:“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普天无处不闻名;则我是权豪势宦杨衙内。”“花花太岁”指凶横浮浪、肆意女色的纨绔子弟。古人以木星为凶煞,取名为“太岁”,“浪子丧门”,指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流氓恶棍。古人称岁之凶神为“丧门”,死丧哭泣之事。杨衙内贪谭记儿“颜色”,“一心要他做个小夫人,”占为己有。为此,他对已娶谭记儿为夫人的白士中怀恨在心,便妄奏皇上,欲置白士中于死地。
莎士比亚在喜剧中,曾憧憬过“爱征服一切”的理想蓝图,不过,他也看到了早期人文主义解放所致的个人主义膨胀、无尽的贪欲所带来的罪恶。
莎士比亚剧作中深刻反映了一些魔鬼的化身,这就是几个著名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奸诈、淫邪的克劳犹斯,为逞一己私利,害死无偿善良的苔丝狄蒙娜的伊阿古,陷害父兄、夺取继承权的爱德蒙,谋杀国王的麦克白。
与中国权豪势要所表现的无赖本色相比,这些人更加多一点狡诈和阴险,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
伊阿古是《奥塞罗》中的重要人物。他居心险恶,却以一幅忠诚老实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奥塞罗就轻信了伊阿古的谗言,甚至把他当作知己,称他为“忠诚而正直的人。”伊阿古利用奥塞罗头脑简单的特点,向他的心里不断注入邪恶的毒液,牵着他的鼻子引进自己布下的一个又一个的圈套,并以一个手帕证实苔丝德蒙娜的不贞,促使奥塞罗在愤怒和嫉妒中掐死了妻子。伊阿古不仅是一个奸贼,而且是一个贪图利禄的哲学家。在伊阿古看来,人的价值不在于人本身,而在于人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高官显宦才是衡量人的伟大的重要性的尺度。他不相信真诚的友谊和爱情,认为世上存在的只是贪心和淫欲,他认为奥塞罗和苔丝德蒙娜之间那种出自内心深处的爱情,只是“一阵淫欲的冲动”和“一番意志的放纵”。他生活中遵循的唯一信条就是一切为了自己,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伊阿古与奥塞罗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处世待人的两种不同态度的冲突。在实施报复奥塞罗的阴谋中,伊阿古以他的伪善、狡诈和阴险,不仅仅摧残奥塞罗的肉体,还摧垮他的精神。这种十恶不赦的罪人比起权豪势要手段更为阴险毒辣。
中国的权豪势要要依靠权势横行霸道,表现了流氓成性无赖至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皇帝的庇护,有至高无上象征皇权的势剑金牌和文书(御旨)。据《马可波罗行纪》第八0章载:大汗对那些在远征和作战中建立了功勋的人,都给予提拔和晋升,“此外赐给美丽银器及美丽甲胄,加给牌符。”牌符勒文于其上曰:“长生天地力里,大汗福荫里,不从命者罪至死。”“凡持此种牌符者,皆有特权在其封地内为其所应为诸事。”“有时给海青符于此诸大藩主。持有此符者,权势如大汗亲临。持此符之人欲遣使至某地,得取其地之良马及他物,惟意所欲。”杨衙内的金牌正是这种牌符,皇帝就是他的后台老板。杨衙内为了满足淫欲而不惜杀人,这是元代现实的写照,比如阿合马,“其所厌恶之人而彼欲除之者,不问事之曲直,辄进谗言于大汗曰:‘某人对陛下不敬,罪应处死。大汗则答之日:‘汝意所乐,为之可也。于是阿合马立杀其人。其权力由是无限,大汗宠眷亦无限,无人敢与之言。”
《鲁斋郎》中的鲁斋郎更是集流氓、恶棍、权势于一身。他好色,“强赖人钱财,莽夺人妻室”。他“随朝数载,谢圣恩可怜,除受今职。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鸟戎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就是这样一个“本分的人”,见到李四妻子长得美,便借修壶为名,赏了李四及其妻子三杯酒,然后挑衅地对李四说:“兀那李四,这三盅酒是肯酒,我的十两银子与你作盘缠,你的浑家,我要带往郑州去也,你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他见到张珪的妻子,又顿生淫念,逼张珪送妻与他,并把玩腻了的李四之妻伪称自己的妹子而转让给他。为了满足兽欲,丧尽廉耻,令人切齿。这是元代社会写真,元代南方的“甲主”可以随意凌辱“甲人”的妻女,又如《元史·奸臣传》中的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已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仅被迫献出妻女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对此,在元代做官多年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有记载,“凡有美妇而为彼所欲者,无一人得免。妇未婚,则娶以为妻。已婚,则强之从己。”鲁斋郎身上,就能看到阿合马的影子。关剧塑造的权豪势要就是对元蒙统治下的以强凌弱,夺占人家妻女的特权阶层的艺术概括,他们倚仗皇权,有恃无恐,随心所欲,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坏事,用不着躲躲闪闪,这是一群人渣,比不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坏人。莎士比亚笔下的是野心家,其意
志和能力让人佩服。
再深入地比较一下,中国人权豪势要多少带点脸谱化味道,而西方的坏人则性格复杂,表现出人性的深度。
在关汉卿保存下来的剧本中,出现恶棍形象的有《窦娥冤》的张驴儿、《望江亭》中的杨衙内,《蝴蝶梦》中的葛彪,《救风尘》中骗娶宋引章而后对其朝打暮骂的周舍,《鲁斋郎》中的鲁斋郎。这些坏人虽不是千人一面,但无一不是凶恶的无赖,代表着元蒙时代特权阶层的滋生的黑暗势力。《鲁斋郎》和《望江亭》中的杨衙内的上场诗大同小异,他们的好色兼无恶不作是一个德性,一个腔调。这与中国戏曲多表现人物的类型化有关系。
西方的一些反面人物的性格复杂,有时还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夏洛克的报复是阴险的,但是安东尼奥“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辱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夏洛克心里郁积着因种族、宗教偏见带来的愤懑,他的行为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当他听说他的女儿杰西卡拿一个指环买了一只猴子,他对杜伯尔说:“该死该死!杜伯尔,你提起这件事,真叫我心里难过,那是我的绿玉指环,是我的妻子利娅在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送给我的,即使人家把一大群猴子来向我交换,我也不愿把它给人。”唯利是图的夏洛克在心底也藏着对亡妻的一片深情。
爱德蒙在《李尔王》中陷害哥哥,出卖父亲,和高纳里尔勾结谋害她的丈夫,挑起高纳里尔和里根姐妹之间的杀戮,可以说是该剧中最阴险的人物,但是这样一个坏人在起初也让人同情。老葛罗斯特当着肯特伯爵的面,也当着自己的儿子爱德蒙谈他,对这个私生子毫无爱意,“这个畜生不等我的召唤,就自己莽莽撞撞地来到这世上。”在父亲离开后,爱德蒙有这样一段独自:“为什么我要受世人的排挤,让世人的歧视剥夺我的应享的权利……为什么他们要给我加上庶出、贱种、私生子的恶名?”
爱德蒙的报复是由世人尤其是家人对他贱视引起的,他的反抗有争取平等权利的合理要求。他也知道,合理的争取是不起作用的,他采取的是邪恶手段:“不管什么手段只要使得上,对我来说,就是正当。”克劳狄斯既有专制君主的残暴,又有资产阶级纵欲无度的兽性,就是这样一个篡权者,也在密室中祈祷,他在用真诚的利刃剖析自己的良心,为自己的罪恶行为忏悔,在生命中汹涌着贪欲暂时得以平息。
正是由于西方注重描写人性的深度,所以反面人物也显得高大丰满,而不是如中国的无赖相。莎士比亚塑造反面人物中,麦克自堪称“黑色的巨人”。
麦克白不是克劳狄斯,伊阿古那样天生的坏蛋,他是作为一个觊觎王位的英雄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他是一个拥有强大而深刻的灵魂的坏蛋。莎士比亚细致地揭示了一个英雄是怎样从善良变为嗜恶的。麦克白原是一个有巨大才华的苏格兰贵族,他不仅平定过国内叛乱,还击败过挪威的入侵,可是,他潜隐的野心,在女巫的挑唆和妻子的怂恿下,开始极度膨胀,根据“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之巩固”的经验,先弑君,随后铲除异己,成为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然而麦克白终于没有变成彻底的恶棍,他尚未泯灭的良性仍然顽强地抵抗,善与恶的搏斗在内心交织并扼杀了他的睡眠,谋杀了国王邓肯,他面对自己血淋淋的双手,完全惊呆了:“这是什么手!嘿,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么?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他眼前不断出现死去的邓肯和班柯的形象,使他觉得每一个人都窥透了他内心的罪恶的秘密。这种恐惧使他不停地杀人,直到他自己被杀。在这个滑向深渊的痛苦过程中他感到生命的无意义:“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他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他所经受的极度痛苦的良心谴责,说明他的良知和人性没有完全被罪恶吞噬,因而他的沉沦会引起人们一定的同情。而他在义军讨伐之下,仍保持困兽犹斗的勇气,再一次提醒我们他曾经有过巨人的形象,因而令人生出惋惜之情。
这样,莎士比亚笔下的罪人,都表现了人的自由意志。在他们身上,这种自由意志体现为对物的占有权利。克劳狄斯、伊阿古、爱德蒙和麦克白夫妇等人的罪恶,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同时毫不退缩地为这种选择负责。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向现在的秩序进击,走向疯狂,不惜走上犯罪道路,成了罪行累累的恶人,为恶的结果是吞噬自身以及它所能触到一切人物。显然,这种人的毁灭,绝不是靠清官来解决的。而中国的权豪势要,虽然肆无忌惮,只不过是有后台的无赖,是缺乏自由意志、彻头彻尾的坏蛋。这种人的克星只能是摧折豪强的清官。
三、伦理规范与终极关怀
中西戏剧的冲突双方都表现出恶人终究要灭亡的命运。这两种结尾有可比性,但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西方的圆形运动带有螺旋上升的意思,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和解,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而中国戏剧大团圆不是急剧斗争之后获得的更高层次的和解,基本上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可以看成是一种圆形的回复。
前面已经说过,关汉卿戏曲都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里的小人物为悲剧主体,写尽了小人物的无奈与悲哀。《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但在九儒十丐的元代,读书人生活没有着落,一贫如洗,借了别人的羊羔利无力偿还,不得不将女儿抵给债权人蔡婆婆当童养媳。等到侥幸博得一官半职,与女儿已是阴阳两隔。至于女儿,更是个悲苦的弱女子,有冤无处诉。《鲁斋郎》里,被鲁斋郎抢去妻子的李四是个银匠,张畦虽在郑州做文案都孔目,但迫于鲁斋郎的淫威,竟然上演“夫主婚,妻招婿”的活剧,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蝴蝶梦》中王老汉一家都是安分守己的小人物,他们既没有自觉的行动意识,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与邪恶力量抗衡,表现出的是被动承受。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里强权和小民之间力量悬殊,弱者与强权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在关汉卿剧中,戏剧冲突不激烈。《鲁斋郎》中的张珪虽然背地里骂鲁斋郎“全失了人伦天地心,依仗着恶党凶徒势”,却还是亲自送妻子上门,甚至鲁斋郎问他:“张珪,你敢有些烦恼,心中舍不的么?”他忍痛答道:“张珪不敢烦恼。则是家中一双女儿无人看管。”像张珪这样的小人物连表达痛苦的胆量都没有,还谈何反抗。由于人物没有能够形成具有超越性的自由意志,所以不能说凭自己的努力把冲突一步一步推向质变的临界点,其大团圆结局只能靠外力——清官、鬼魂来完成,弱小与邪恶不是在斗争中改变关系,只是事物的相互代替,并非矛盾冲突在更高层次上的和解。比如《窦娥冤》的鬼魂复仇,窦天章在审问张驴儿时,张驴儿抵赖,这时窦天章说:“我
那屈死的儿呀,这一节是紧要公案,你不自来折辩,怎得一个明白,你如今冤魂却在哪里?”窦娥冤魂马上和张驴儿对簿公堂,她以鬼的身份行使着人的使命,与哈姆雷特和父亲的鬼魂不同。《蝴蝶梦》中关汉卿为包公设计的“蝴蝶梦兆”情节,有助于表现善恶相报不爽的劝世意义,使观众的心理得到安慰。
这种鬼魂梦兆情节在莎士比亚剧里也有,但是重视人物意志的西方尽量避免外在力量的介入。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情节的‘疏解应当出自情节本身,而不是像《美狄亚》,或像《伊里亚特》中的启航那样,靠救难神的帮助”。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救难神”就是古希腊人在剧情无法继续下去时用来解除困难的外在力量。西方人虽然也借助这一手法,但他们限制使用,使自觉的行动成为戏剧的主体。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也有被害者的鬼魂出现,但只是通过麦克白的语言来表现;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和父亲的鬼魂见了面,父亲向他道出了真情,哈姆雷特意识到自己有为父亲复仇的义务,接下去莎翁就展示哈姆雷特的行动,这出戏的开始出现了老王的鬼魂是一个很强的悬念,莎士比亚在第一幕结束就把这个悬念解开,目的就是要开门见山展开戏剧冲突,并紧紧围绕着揭示人物的命运、性格和思想来设置情节,作者让观众的视线都集中在哈姆雷特身上。很明显,鬼魂在《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中只是一种穿线性功能,而鬼魂在关剧中是一个行动角色。中国人在不触动现实的情况下将希望寄托于来生,或者借助清官演绎着“善必胜恶”的浪漫情怀。
关汉卿这种大团圆结局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养成了顺从、依赖、保守的民族心理。《老子》第40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在他看来物极必反是事物变易的规律,事物的运动发展总要返回原来的状态,只有顺从自然规律才会恒久。传统的农业生产的经验性使得守成多于创造,并使长辈、族长、皇帝的绝对权威逐渐形成。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农民对于宇宙万物变化产生了循环思想,并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概括。“风水轮流转”“时来运转”是国人对于世事的通俗表达,这必然导致中国人安于现状,对和谐、宁静的诉求超过对变革斗争的追求。“三纲五常”是家园同构、孝忠统一的伦理规范。因此,关剧中主人公多是善良,被动应战的承受型抗恶者,一个缺乏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主人公,不会也不敢为了个人欲望和信念而与对手殊死“抗争”乃至横尸舞台,只好以“大团圆”收场。
而西方文化属海洋文化,海洋民族崇尚的是知识、智慧,具有大海一样汹涌澎湃的性格,比较重视斗争,喜欢冒险,哪怕会给自己带来灾难。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对自己充满信心,从不回避任何困难和灾难,有胆量与命运抗争,哈姆雷特通过鬼魂而得知父亲被谋杀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为父报仇的使命。奥塞罗和李尔王都偏执于自己的性格、主张和意志。就是如伊阿古、麦克白那样的恶人也具有自由意志。他们是悲剧冲突的挑起者,他们尽管失败,但拥有个体生命的尊严,让人景仰。
如果再深入地进行比较,还可发现中西方结局一个是以表达伦理规范为目的,一个则是以体现人的终极关怀为宗旨。
中国的悲剧价值和意义在于用伦理来感化观众,很少感到西方悲剧中那种恐惧之情。中国的戏曲人物体现善恶有报的特点。
关汉卿在作品中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他提出的要求贤人政治是平民最朴素的愿望,同时又是符合圣贤愿望的,他在《窦娥冤》中关注的焦点是道德,他揭露的是张驴儿父子和赛卢医的无法无德,抨击的是昏官酷吏的缺德凶暴,并以在这种环境中突出窦娥作为节妇孝妇的道德力量为旨归。用道德判断代替人性、历史的判断,使关汉卿对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观念的宣扬异常热衷。如《哭存孝》本取材于《五代史·义儿传》,为了达到宣扬忠义目的,关汉卿不惜改造历史,突出李存孝的“忠心仁人”。由于李存信,康君立在李克用醉后进谗,李克用下令车裂了李存孝。《蝴蝶梦》是包公断案的清官戏,但关汉卿却将主题更改为颂扬王婆的贤德,包拯载结尾中声明要“扶立当今圣明主,欲播清风千万古”,在断语中声称“国家重义夫节妇,更爱那孝子顺孙”。所以,王婆一家不但母子团聚,儿子还当了官。传统悲剧总是习惯趋向对善的追求,追求大团圆之趋,很少出现西方麦克白、奥塞罗那样由于自身弱点而造成的悲剧。
西方的悲剧的本质在于模仿一个严肃的不幸事件,悲剧的价值不在于悲剧的不幸本身,而在于人物行为含有崇高的非凡的严肃性。因此西方悲剧常常表现为对形而上的探索,悲剧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着重体现自我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哈姆雷特著名独自“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个更高贵?”哈姆雷特是王子,是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的王子,人的尊严,新人巨人的尊严,“重整乾坤的责任”,都使他强化着不落凡俗的高贵。哈姆雷特的对手是克劳狄斯及其一帮爪牙帮凶。“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恩格斯《致拉萨尔》),使这位单枪匹马的复仇者注定要失败。虽然如此,但他在思想上思索了、探索了。
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罪恶无所不在。克劳狄斯、伊阿古、麦克白夫妇放纵私欲,毁灭了他人,也毁灭了自己。就是悲剧人物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甚至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人,也在追求他们的理想过程中,陷入到罪恶中。莎士比亚认为,人具有自由意志,正是自由意志导致人的罪恶,正因为人的本质有罪恶,所以认识有限性的存在。因为认识有限性的存在,所以需要救赎。如何获救,基督教把获救的希望寄托于上帝,莎士比亚受基督教的影响,但有区别,“莎士比亚戏剧所展示的,是人学体系中的罪恶于救赎,即罪恶源于人,而救赎也依赖于人。”在《威尼斯商人》里,他希望通过慈悲和爱来解决纷争。
综上所述,我对关汉卿与莎士比亚涉及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的戏剧,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莎士比亚更关注的大人物的命运,而关汉卿描写的主体一般是小人物,由于中西方社会结构不同,中国是一个高度专制的帝国权力组织,缺乏西方中世纪的中间组织,没有享有自治权利的城镇,没有分散的贵族权力,更没有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小人物力量极其单薄,任何权贵飞来的横祸,都会使他们陷入苦难深渊,变成任人蹂躏的奴隶,法律不会维护他们的权益,他们求告无门,只能靠外力——鬼魂或清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追求大团圆结局。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宗法社会,由此导致了讲忠孝节义讲名分的戏剧观。而过分讲究忠奸、好坏对立,又使得中国人笔下的坏人往往是恶的化身,看不到丰满的性格,这与西方对个人命运顽强探索和反抗、努力挖掘人性的深度是不同的。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悲剧的原因根源于人自身,人的自由意志往往陷入到罪恶之中。面对无处不在的罪恶、人是有限性的存在,他在关怀人的救赎,寻求人的终极关怀,而不是把恶人绳之以法就万事大吉,如中国古人追求的大团圆。这几方面的因素,使得莎士比亚不把清官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西方没有清官文学,应该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