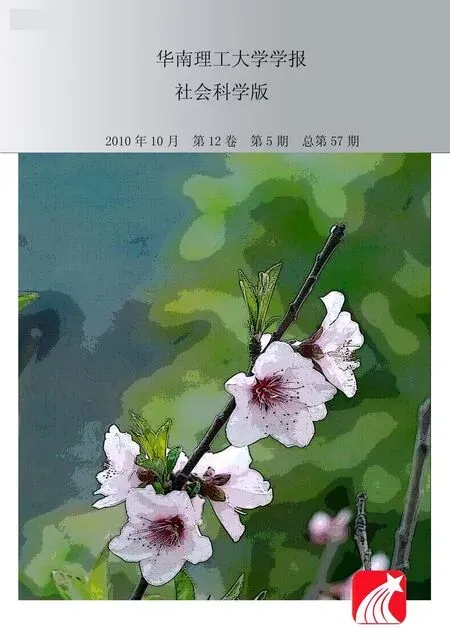追忆·困扰·突围
——从《四婵娟》看明末清初文人的婚姻理想
2010-04-11傅湘龙
傅湘龙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洪昇依据有关的历史文献, 截取谢道韫、 卫茂漪、 李清照、 管仲姬等四位著名才女人生经历中最为绚丽的生活片断加以叙写, 构成以“咏絮擅诗才”、 “簪花传笔阵”、 “斗茗话幽情”、 “画竹留清韵”为叙事重心的单折短剧系列。表面上看, 《四婵娟》意在敷演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 重温古代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另一方面, 无论是卫茂漪、 李清照、 管仲姬婚后浪漫温馨的文艺活动, 还是谢道韫所展示的确保未来婚姻质量的综合素质, 显然蕴含着洪氏对于文人婚姻家庭的价值选择。明末清初, 通俗文学作家反复叙写日新月异的家庭灾难和欲罢不能的绝望心态, 由此形成近乎痴人说梦却得到广泛认同的“才子佳人情结”。将《四婵娟》置入这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并与其他作家的深切感受和调整思路进行比较, 不难窥见当时知识阶层为摆脱婚姻困境所选择的“突围”方向。
一
在《四婵娟》第三折, 洪昇借助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夫妻唱和, 概述“多半是参商”的“古来夫妇”前赴后继地谱写大同小异的人生悲剧, 抒发“虽则是唤一双, 问谁能两愿偿?大古来姻缘簿里甚荒唐”①[1]768以下注释未予标明的, 均引自《洪昇集》之《四婵娟》文本。的深沉喟叹, 并通过对若干个案的逐一评述提出衡量婚姻质量的价值标准: 1、 “须是终身厮守谐老百年的, 方才算个美满。”弄玉和箫史将艺术化的夫妻生活带入永恒世界, 树立了“为闺房生色”的神仙伴侣典范;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所合非正”的私奔行为虽然颇遭非议, 但“旷代才子”得配“绝世佳人”的婚姻组合终究令人羡慕无比; 此外, 孟光的“举案”、 张敞的“画眉”亦堪称“韵绝千古”之举。2、 “若恩爱虽深, 或享年不永, 或中道分离, 到底算不得个第一等。”“并肩人不离半晌”的沈东美、 “玩贤妻眼皮供养”的高柔、 “极尽温存之致”的荀奉倩, 在异常亲昵的夫妻关系中营造甜蜜而短暂的恩爱, 却无法消解曲终人散的悲凉结局留下的永久伤痛。3、 “起先不无间阻, 毕竟终成美满, 别成夫妻一种奇缘。”倩女、 玉箫、 贾云华等痴心女子不顾一切追求如意郎君, 在“历尽千魔障”乃至付出生命代价之后得偿所愿。4、 “当日个燕失双飞雁失行, 到头来月再团圆花再芳。”刘无双、 乐昌公主、 绣龟侯氏、 织锦苏娘因各种变故夫妻离散, 劫后重逢“越显得锦前程风月广”。5、 “才子偏不得遇佳人, 有佳人又偏不得遇才子”, 甚至“佳人配了才子也不能美满恩爱”。在林林总总“不成夫妻”的错配姻缘中, 或为冯敬通、 刘孝标之类遭遇“顽妻板障”、 “劣妇乖张”的可怜男子, 或为步飞烟、 朱淑真那样“命随花葬”、 “诗断人肠”的不幸女性, 亦不乏与“含痛而亡”或饮恨终身的霍小玉、 崔莺莺命运相似的薄命红颜。在上述五种类型的婚姻中, 前四类皆是以“恩爱”作为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唯一区别在于是否保持“谐老百年”的时间长度和波澜不惊的平稳状态, 因而在具体操作中极易出现彼此混淆的情况。赵明诚与李清照“情缘两得, 才貌并佳”, 凭借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兼而有之的婚后生活“做人世夫妻榜样”当之无愧, 但将之誉为“就在美满之中, 也算是第一等”则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甚相符。在洪昇心目中, 构成可持续发展的恩爱和谐的“美满夫妻”, 既要求男性们克服“轻狂薄幸”习性心无旁骛地“怜香惜玉”, 更取决于女性包括容貌、 才情、 性格、 气质在内的自身条件。正由于此, 洪昇从众多的古代佳人中精心挑选适应文人婚姻生活需要的四位知识女性, 并依据自我的审美向度对相关的历史文献做出主观取舍, 向世人推出亦实亦虚的“婵娟”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 洪昇“把古来佳人才子尽评论”时列举的美满夫妻与历史文献(包括笔记小说)记载基本对应, 但并未将既往“美满”、 “恩爱”婚姻范例中的女性纳入“婵娟”的范畴。这种“另辟蹊径”的具体操作, 无疑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思考: 一方面, 只有在容貌、 才学、 品行、 性格诸方面彼此认同, 才能轻松愉快地进行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 从而始终保持恩爱和谐的夫妻关系。“年三十”且“肥丑而黑”的孟光, 不仅外在条件与“佳人”标准相去甚远, 亦且从未显露诗词歌赋或琴棋书画方面的艺术修养, 除了采用“举案齐眉”的方式苦心孤诣地维系来之不易的婚姻, 不可能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制造任何浪漫的刺激。张敞或许将妻子视为天姿国色的绝代“佳人”, 但深情款款地为之“画眉”毕竟只是在特定时间内颇有夸张之嫌的个人行为, 不具备永无止境地持续操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才子”与“佳人”的婚姻并非纯粹两情相悦的个人行为, 理所当然地肩负着“做人世夫妻榜样”的社会责任, 因而必须自觉遵循传统的审美价值标准。卓文君的容貌与才情固然符合“佳人”要求, 为维持生计甘愿放弃女性矜持“当垆卖酒”亦殊属不易, 但身为寡妇不立志守节却夤夜私奔难免招致非议。卷入女色阴谋之中的西施堪称“佳人”之翘楚, 然而“二十年深宫肮脏”的人生经历无论如何会在注重处子贞洁的文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或浓或淡的一抹阴影, 况且完成政治使命后与范蠡五湖泛舟的美满结局也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概而言之, 由于女性自身条件的欠缺和表达方式的单一, 孟光、 张敞们的婚姻呈现出生活化的内在特质, 在向往“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文人群体中很难产生共鸣。卓文君、 西施容貌艳丽且能营造浪漫温馨的婚姻生活, 但违背常规的私相结合与吴宫擅宠的晦暗历史注定其只能在“另类佳人”中独占鳌头, 而与符合“正宗佳人”所有要求的“婵娟”绝然无缘。
为了凸显谢道韫、 卫茂漪、 李清照、 管仲姬完美无缺的“佳人”特质, 洪昇煞费苦心地对历史文献进行了为己所用的“技术处理”。首先, 用合乎逻辑的想像虚构填充语焉不详的文献记载, 竭力渲染“四婵娟”不让须眉的艺术才华和温柔贤淑的性格气质, 从不同的角度将其界定为旷世难逢的理想婚姻伴侣典范: “又聪明, 又标致”的谢道韫, “虽是个女子, 却只耽情笔墨, 每日刺绣余功, 常在叔父膝前谈论今古”, 其咏柳絮诗“不即不离, 若远若近, 传神写意, 俱在个中”, 使“斌斌文采”自视甚高的兄长谢琏甘拜下风。卫茂漪“独精书法, 簪在妙楷, 擅绝古今”, 无论是要言不烦地评点恭敬向学的弟子们的临帖功课, 还是汪洋恣肆地向“傲骨嶙峋”的书法名家王羲之传授“书家三昧” 不亚于一代宗师的精湛技艺和洒脱气度足以征服所有清高自负的“才子”。李清照不仅词学造诣令人自愧不如, 更善于设计“烹茶检书”之类的娱乐休闲, 其“女才子”的审美价值在新奇别致的婚姻生活中得到完整体现。“德性幽闲, 才情蕴藉”的管仲姬不同凡俗, 在“秋光正好, 山水撩人”的重阳佳节“徐徐弄彩毫, 款款揎罗袖”, 画出“袅袅婷婷、 娟娟冉冉、 疏疏瘦瘦、 瑟瑟更翛翛”的万竿翠竹, 又即兴抒发“人生极贵是王侯, 浮利浮名不自由, 争得似, 一扁舟, 弄月吟风归去休”[5]809的恬退情怀, 鼓励“只为尘清苦逗留”的丈夫义无反顾地做出“急流勇退”的最终抉择。其次, 对于历史文献中与既定目标相悖的有关记载, 只是含糊其辞地插入文本中极不显眼的位置, 甚至为避免产生疑惑而索性不予涉及, 从男性视角对“婵娟”们的婚姻做出有失客观公允的审美评价。谢道韫嫁与王羲之次子凝之为妻, 因丈夫颇显平庸而“意大不悦” 以极度失望作为起点的婚姻自然不可能达到“美满”的终极效应。在该剧的结尾, 谢安希望侄女“更当留心翰墨”以便“做个好媳妇”, 却忽略其“痴郎骏马偏多舛”的怨怅与无奈。换言之, 女性的“容貌端庄”、 “才华妙丽”, 只是让丈夫最大限度地享受“美满”, 基本上与婚姻质量和女性对自身婚姻的感觉脱离关系。卫茂漪长期独守空房, “在家无事, 于含香馆中设下绛纱, 传授书法”, 过着平静有序而异常充实的生活, 既没有两地相思引发的无法排遣的深深幽怨, 更不存在因寂寞难耐而“红杏出墙”的潜在危险, 从根本上解除了丈夫的“后顾之忧”。
二
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 人心激荡的时代氛围影响下, 与经济活动紧密联系的知识阶层婚姻生活受到经济转型带来的强烈冲击。面对日益窘迫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丈夫拈花惹草的滥情态度, 不堪忍受的妻子直接而放肆地展示出自我的强悍性格, 从而使原本被想象为整日卿卿我我的夫妻关系, 迅速演变成弥漫腥风血雨的人间地狱。“肆其横暴”的“娘子军”接二连三推出杖责鞭打、 罚跪戒眠、 揪耳拶指、 顶灯骑头、 针扎烟熏等花式百出的名目对家中畏妻如虎的“弱夫”予以声色俱厉的家法惩治, 极力把“吹残绮阁之春”的悍戾气与“淹断蓝桥之月”的酸醋劲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死要面子、 不想“家丑外扬”的知识者尽管绞尽脑汁想要脱离这种“朝打暮骂”的无底深渊却因“苦疗妒之无方”而弄得焦头烂额, 不得不落到包羞忍辱, 关在门内做小伏低的悲惨地步。
“菩萨般的相公”陈季常自从娶了一个“夜叉般的娘子”后就全然没有了平日结交知心挈友时诸多的惊人才思与慷慨气魄。不仅对柳氏的撚酸发怒完全束手无策, 而且反把友人苏轼贴心贴肺的仗义之言和对柳氏苦口婆心的劝诫视为“颠言诳语”, 斥责他多管闲事, 不免流露出要以自己逆来顺受式的绝对服从来“消灾去障”的颇显单纯的心理渴望。(《狮吼记》)
号称“天不怕, 地不怕”的狄希陈惟独怕了自己的媳妇, 尽管以“时时如临深渊, 刻刻如履薄冰”的如逢大敌的应战心态慎之又慎, 仍屡次遭逢“从天而降”的飞来横祸。有如“鬼见阎王”般的心理恐惧和精神焦虑在他心头久久挥之不去。(《醒世姻缘传》)
“惧内, 天下之通病也。”一般的平凡士子尚且抛开不论, 就是“戴纱帽”的县令以至土地老爷为了避免当家奶奶大发醋意, 在审理女犯之前总是先派手下查看其是否躲在屏风后面秘密审听。为了避免或缓和日益升级的家庭内战, 百般无奈的县令老爷只好把自己的身份与体面统统丢到脑后, 直接在公堂之上向医僧求取疗妒的秘方。(《歌代啸》)
从借助棍棒之力到“脂粉之气不势而威”, 知识阶层的文人在骄蛮妻子的“阃威”之下不仅丧失了传统的“夫为妻纲”的男性家庭优势, 亦且遭受“白日折磨, 夜间挝打, 备极丑行”的人格屈辱, 鬼哭狼嚎、 抱头鼠窜以至于“茫茫然如鸟雀之被鸇殴者”不知凡几。易怒的江城对丈夫高藩动辄就是诟骂指抓或摘耳针刺, 甚至以“绣剪剪腹间肉”, 因而总“以爱故, 悉含忍之”的高生常常在“词舌嘲啁, 常常聒于耳”的心理压迫与棍棒交加的狼狈不堪中丑态百出。(《聊斋志异·江城》)年过四十而膝下无子的大名诸生杨万石怕极了肆意横行、 把家中闹腾得鸡犬不宁的妻子尹氏, 平时与小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语。” 杨万石遭逢了父亲衣食不保、 小妾崩注堕胎、 弟弟投井殒身、 侄儿憔悴嬴弱的种种不堪, 虽积聚起满腔的忿懑不平, 声泪俱下地拜倒在深为其打抱不平的侠义狐仙马介甫面前“伏首贴耳而泣”, 却仍不敢存有休妻去妇的念头。(《聊斋志异·马介甫》)。
“罚跪、 戒眠、 捧灯、 戴水, 以至于扑臀”等妒妇经常采用的制夫之条早已把家中所谓的“铮铮铁汉”驯化成了唯命是从的“低眉金刚”, 更有摄于妻子“鞭扑不加, 囹圄不设, 宽仁大度”的不怒之威而“自遣其妾而归化”的软弱丈夫。即使是敢于承担起救苦救难重任的“家族救助者”在那种“锁门绝食、 迁怒于人”的悍妇面前, 也不免“避祸难前, 坐视其死而莫之救”, 惟有抒发爱莫能助的喟然叹息。
举人穆子大遭受妻子淳于氏荼毒, 陷入水深火热的艰难困境; 学中朋友义愤填膺地连续两次实施声势浩大的“剿妒”之举, 但不是因自己献媚取宠功亏一篑, 就是被工于心计的“悍妇”诱敌深入, 在仰面受粪的尴尬情势下放弃男性的尊严。行妒与疗妒在同一空间和时间里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拉锯大战。“大小妻室共有二十多房”、 在“疗妒”问题上饶有心得因而得以大享齐人之福的费隐公堂而皇之以“妒总管”的名号自居, 终日登坛说法, 传授“弥酸止醋之方”; 而在与“妒总管”两次交锋中大获全胜的淳于氏一时得志, 盛名在外, 竟也有不少愿拜为门生的妒妇来“求她广行教化”。尽管穆子大在费隐公的精心安排下以瞒天过海的假死妙计反客为主, 诱骗淳于氏进到失节改嫁的道德惩罚中从而及时挽回了这段濒于崩溃的婚姻。然而我们终不免怀疑这种再度重来的修复型婚姻还能剩下几分郎情妾意的幸福与温馨可言。(《连城壁·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
顾影自怜、 几乎已经望眼欲穿的石尤氏因为介之推的不辞而别、 又且19年来音信全无而独守深山, 早已把心中深沉的爱恋转成为刻骨的仇恨。当护驾归来的介之推提出要与她再续情缘时, 在“茕茕孑立、 形影相吊”的艰难等待过程中饱受煎熬的石尤出于宁可死相守、 也不愿生别离的怨憎之心毅然选择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命终结方式, 投身于熊熊山火中与介之推同归于尽。(《豆棚闲话·介之推火封妒妇》)
《狮吼记》、 《歌代啸》、 《醒世姻缘传》、 《豆棚闲话》、 《连城壁》这些戏曲与小说文本中所反映出的知识阶层文人普遍在家庭中遭受的长期而残酷的生理摧残和心理折磨, 可以说正是当时混乱不堪的文人婚姻生活的真实投射。徐渭的结发妻子潘氏不仅容貌美丽, 而且人品极佳, 因此深得他的欢心。但是在潘氏因病早逝后, 他与续娶的胡氏、 张氏等三个女子相处都不甚和谐。嘉靖四十五年冬日, 狂疾复发的徐渭“为琐事与妻张氏争吵, 铲雪时, 一说用钉耙, 一说用瓦器掷张氏, 以至谋杀”[6]335, 最后还因此事下狱。虽然我们不能绝对确认徐渭当时的出手动机,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 徐渭在中年复发的几次癫狂之症与他后来三次不甚顺利的婚姻经历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至少可以认为他的这种心里病变基本上没有在家中得到应有的有效治疗, 病情不免加速恶化最后酿成“手刃亲妻”的家庭惨剧。
传统意义上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在明末清初时期出现质的变化, 丈夫日渐气矮, 妻子趁而势高。对于丈夫来说, 凶残、 暴虐的妻子已经如同“附骨之疽”和“脖项上瘿袋”、 “去了愈要伤命, 留着大是苦人”; 但是“悍妇不难以武胜, 而难于德胜”, 如果现在将悍妒妻子休去, 也难保下一个不再是个“母夜叉”、 “胭脂虎”。怪不得蒲松龄在书中借异史氏之口对世俗社会中苦不堪言的文人婚姻生活大发感叹: “每见天下贤妇十之一, 悍妇十之九, 亦以见人世之能修善业者少也。观自在愿力宏大, 何不将盂中水洒大千世界耶?”[7]863动辄得咎、 时刻面临生命危险的知识阶层的文人在如此种种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家庭关系中背负着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 迫切地向往能找到一个温柔贤淑的满意妻房。
三
鉴于现实生活中极其恶劣的夫妻状况, 艰于呼吸的知识阶层满怀希望地投入到以描写爱情、 婚姻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创作当中, 并且呈现出多向度的自我调整方式, 或是脱出现实来凭空虚拟, 或是适应时代而力趋合俗, 孜孜不倦地寻找梦寐以求的理想婚姻形式及其实现途径, 以求得到自己内心情感归属的些许满足。
其一、 自述“一自外入, 室人交遍谪”的天花藏主人和其他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大多对目前所处的婚姻现状置有微词, 不免想入非非, 虚拟出一大批风华绝世的少年佳人才子以尽量满足自己对理想夫妻生活的渴求。此类小说以男女两方门当户对的家世背景、 极为匹配的外在容貌以及难分伯仲的文学才华为前提条件成功谱写出天才少女与青年才俊喜结良缘的“传奇神话”。才子和佳人渐趋明显的幼龄化趋势也可以说是年龄优势大有愈演愈烈之风, 最终是在《平山冷燕》这部小说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十岁即以《白燕诗》名动京师的“弘文才女”山黛、 十二岁便在与假名士宋信比试时轻松胜出的冷绛雪双双与燕百颔和平如衡这两位十几岁就考中案首、 最后果然不负众望一举夺魁的饱学才子成就了令人艳羡的美满姻缘, 并且成为被世人津津乐道的风月美谈。
在具体的叙事操作上, 青年男女在婚前的恋爱过程被高度强化和明显拉长, 而对进入婚姻状态后的夫贵妻荣、 多子多福等后续情况只作了简略交代。由于这些在子女择偶标准以及婚姻缔结问题上达成一致认识的开明家长给予了儿女们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 才子和佳人均得以在婚前通过游学访美、 考诗定亲等公开形式成功实现了必要的心理交流和彼此关注良久的容貌期待, 与此同时男女双方的情感发生、 发展也在与拨乱小人的斗争和波折中曲折前进。一方面, 才子以“若非淑女, 小弟可以无求; 若果淑女, 那有淑女而生妒心”[8]152的“淑女准则”来试图消解心仪女性的悍妒心性; 另一方面才华横溢的绝色佳人更是不甘示弱地展现出绝不争风吃醋的豁达襟怀: “贤妹所虑, 在世情中固自不差, 只是我爹爹不是世情中人, 爱愚姐自爱贤妹; 况又受姑娘之托, 断不分别彼此, 叫愚姐作妒妇也。”[8]203这些少年得志、 意气风发的“科场英雄”轻松摆脱了“河东狮”禁夫纳妾之苦, 坐拥双美甚至众美的风流艳想几乎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心理满足。凭借上述种种情节铺垫作为充要条件, 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得出他们婚后必然获得和睦、 幸福的情感生活的结论显然是顺理成章了。
其二、 以世俗大众的心理接受倾向为价值目标的鸳湖烟水散人在小说细节叙述与人物塑造上增加了更多的时代因素, 表现出应时应景的创作风格。《女才子书首卷》中作者娓娓道出的女子在容、 韵、 技、 事、 居、 候、 饰、 助、 撰、 趣等十个方面的近乎完美的女性审美标准无疑显示了才子佳人小说作品与生俱来的理想色彩。然而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是, 书中所叙写的佳人从出身背景、 外在容貌、 娱乐休闲等外在标准到才情技艺、 性格品性等内在尺度, 都呈现出一种由主观理想向客观现实回归的生活化倾向。这些女子不仅在体态容貌上与作者最初理想中的“完美情人标准”相去甚远, 而且在家世背景上, 固然不乏有少数几个“裔出簪婴”或出自“富户之女”的大家闺秀, 但更多的是下层生活中身份卑微的小家碧玉, 较之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文本中色艺俱佳的“高雅型佳人”明显更具有世俗社会中现实女性的生活特点, 具体表现为作者对她们“醉倚郎肩、 兰汤昼沐、 枕边娇笑、 花阴小遗、 眼色偷传、 拈弹打莺、 微含醋意”的世俗生活情趣以及“护兰、 煎茶、 焚香、 裁剪、 调和五味”等日常生活能力所进行的着意强调。这种呈整体下降趋势的女性出身背景不仅直接限制了女性在艺术修养水平上无法达到作者理想状态中无所不能的高度, 而且使得某些女子在婚前自觉突破“男女大防”而在她们本应勉力恪守的“男女授受不亲”的基本行为操守上自我约束能力大大减弱。此外, 同样是普遍来自于社会下层生活的所谓才子, 就算只是考较诗、 词等方面的才学造诣, 也在这批学问已经大打折扣的女子面前技输一筹, 打上了世俗生活的深刻烙印。所有这一切, 无不流露出作者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对女性由理想佳人向生活女性的世俗化回归的痕迹。
此外, 冒辟疆、 侯方域、 毛奇龄等念念不忘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幸福经历的失意文人, 写作了《影梅庵憶语》、 《李姬传》以及《曼殊别志书传》等回忆性记实传记散文。茫然若失的痴情男子在字里行间尽情抒发了对翩然而去的知己红颜刻骨铭心的思念以及天人永隔、 物在人亡的失意怅惘。
相形之下, 洪昇与妻子黄兰次足可列为明清时期文人夫妻的幸福典范之一。出生于书香门第、 世宦之家的洪昇因为家学渊源的关系具备了极好的文学修养, 在诗词、 绘画、 音律以及骈文等方面无不精擅。而精晓音律, 雅好词曲的兰次与洪昇是嫡亲的表兄妹关系, 两人在孩提时代就建立了两小无猜的友谊, 结婚之后更是志趣相投、 相敬如宾。尽管洪昇屡试不第而且中途遭逢了“家难”和“《长生殿》之祸” 在他们清贫而坎坷的一生中, 黄兰次始终作为洪昇忠实的生活伴侣以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心从精神上给了洪昇最大的支持和安慰。
步入晚年的洪昇有感于社会的“妻权”氛围、 旁人的悲惨经历、 自身的幸福体会, 再加之在过往戏曲创作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 以不主故常的独特审美眼光对与谢、 卫、 李、 管四位古代才女相关的大量历史资料进行了兼权熟计的取舍与观照, 充分展示了她们各自生活历程中最为畅快得意或者是最为幸福温馨的一段, 向世人推出一组展现女子高超的文艺才华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知识阶层的理想夫妻生活的杂剧系列, 并且独辟蹊径从男性(包括丈夫和亲友)的全新视角对这四位杰出女性自身具备的文学才华以及艺术修养在稳定各自婚姻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做出了重新审视与独家评判。在洪昇笔下, 四位才女已经完全脱出了羁缚在历史文献中的几多不幸, 成为“有名有实”的幸福女性。无论是谢道韫卷帘赏雪、 饮宴赋诗的秀外慧中; 卫茂漪设绛帐于含香馆、 以师道自居、 传《笔阵》秘诀、 授书法源流的落落大方; 还是李清照与赵明诚斗茗检书、 兰汤换妆、 花下纳凉的夫唱妇随以及管仲姬与赵孟頫盟鸥狎鹭、 泛舟游湖、 题画和诗的柔情蜜意都足以引起人们对于现实婚姻的强烈向往与无限憧憬。这种优雅和睦、 互敬互爱的理想夫妻关系在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文人家庭关系大调整的时代风貌中无疑与传统雅文化系统中文人的婚姻追求最为接近, 确实堪称最契合中上层文人情感理想的婚姻模式。
综上所述, 天花藏主人和烟水散人这些下层文人面对弥漫着愁云惨雾的文人家庭混乱局面的残酷现实所选择的趋于理想虚幻或者是现实通俗的“突围”方式不免从多个方面折射出了他们急于解决男性举步维艰的家庭窘境的迫切心理和精神寄托; 而以洪昇为典型代表的中上层文人从历史典籍中提炼人物、 情节并作出主观取舍的操作手法则可以称之为知识阶层文人对于如何维持和睦、 稳定的理想夫妻生活的最佳诠释方式。
参考文献:
[1] 刘辉校笺. 洪昇集 [M].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2] 徐震堮. 世说新语校笺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4.
[3] 张彦远. 法书要录 [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
[4] 赵明诚撰 金文明校证. 金石录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5] 唐圭璋编. 全金元词 [M]. 北京: 中华书局1979.
[6] 丁家侗. 东方畸人徐文长传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 张友鹤辑校.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荑秋散人编次. 玉娇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9] 章培恒. 洪昇年谱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