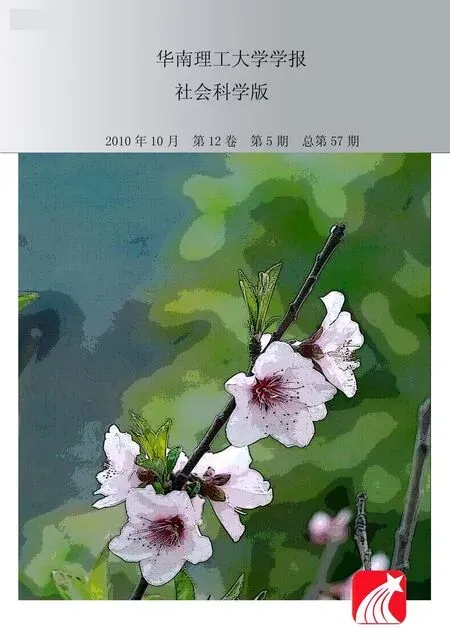引入美国市场份额规则的思考
2010-04-11史尊魁
史尊魁
( 武汉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美国的侵权法将“市场份额规则”归入到“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内容中予以论述。据此, 国内主流学者认为“市场份额责任实际上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推定, 如果被告能够证明自己的产品同原告的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那么被告就破坏了产品责任构成要件中的一环, 被告也就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1]笔者认为,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美国市场份额原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追偿理论(a theory of recovery), 当原告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加害人的时候, 原告可以要求生产具有替代性产品的厂商对其损失承担市场份额责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慧星教授为首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篇》并没有规定“市场份额规则”, 但由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篇》第1958条, 关于产品责任的分担中则规定了“数人生产的同类产品因缺陷造成损害, 不能确定致害产品的生产者的, 应当按照产品在市场份额中的比例承担民事责任。”
目前为止, 学界对“市场份额规则”的研究比较少。学者们大多在论述“共同危险行为制度”时, 附带提到“美国市场份额规则”。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 并没有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共同危险行为”制度, 但是美国市场份额规则中存在的加害人不清事实以及举证责任倒置方面的特点, 与大陆法系“共同危险行为制度”在制度构成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因此国内学者基本上认同“市场份额规则隶属于广义上的共同危险行为制度”。[2]最近, 随着大规模侵权事故的发生, 特别是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人们对食品、 药品安全的不断反思, 学界开始对“美国市场份额规则”予以关注。虽然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没有采用“市场份额规则”, 但对该规则进行深入的研究却有其必要。
一、 美国市场份额规则简介
(一) Sindell v Abbott Laboratories 案
Sindell 的判决由加州最高法院在1980年做出。Sindell 是一位年轻的妇女, 诉称由于其母亲在怀她的时候服用了DES药剂, 导致原告患上了生殖系统癌症。在20世纪70年代末, DES被公认为是一种有效安全的保胎药, 医生一般都会建议可能流产或早产的孕妇使用DES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据统计, 在1947年至1971年之间, 大约有500万至1000万美国妇女在怀孕期间服用过DES。但在1971年, 研究人员发现, 在怀孕过程中使用DES的妇女所生育的女性后代可能在少年或青年时期患上腺癌。因此, 美国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随即发出药品公告, 警告医生应当停止给怀孕妇女使用DES。此后不久, 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一部分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过DES的女孩在成长过程中患上了腺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因DES而导致的病例逐年增加, 其中一些受害者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 希望通过司法途径获得赔偿。Sindell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当时的背景下形成了“DES女儿们”(DES daughters)的集团诉讼, Sindell 是集团诉讼中的一个受害人。[注]David M.Schultz, Market Share Liability in DES Cases: The Unwarranted Erosion of Causation in Fact, 40 De Paul L. Rev.771,771(1991)该案中, 原告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了DES, 从而导致原告在成年后患上了癌症。但是, 从原告母亲服用DES到原告发病, 前后历时20多年。在确定谁是真正的被害人时, 原告自己也无法进行举证。案件的事实表明, 所有生产DES的被告在主观上都存在过失, 但是要求证明到底是哪一家被告造成了原告的损害, 难度非常大。当时, 有近200多家的企业生产DES, 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原告提起诉讼时已经因破产等原因退出了市场, 另外有些企业受到管辖权的限制。因此, 原告在200多家企业中选择了占DES市场份额最大的五个厂家作为被告予以起诉。
(二)不宜适用“联营责任”、 “连带责任”
“DES”案出现后, 法院基于“遵守先例”的考虑, 首先考虑能否适用其他规则, 特别是连带责任规则和联营责任规则。
首先, 无法适用连带责任。Sindell 并没有将200多家制造商都告到法庭上, 而是选取了占DES市场份额最大的五家厂商, 这与适用传统连带责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Summer v.Tice”案不同, 法官在该案中之所以适用连带责任是基于两点考虑: 首先, 全部有过错的人都成为了被告; 其次, 任何被告的单一行为都足以导致原告的损害。
在无法适用连带责任后, 法院考虑适用联营责任规则。所谓的“联营责任原则”是在Hall vs E.I.Du Pont de Nemours & Co.案中确立的。该案中, 多个儿童分别在不同的瓶盖爆炸事件中受到伤害, 为了维护这些儿童的权益, 美国瓶盖产业的六大生产商都被起诉。有证据表明这些生产商在瓶盖的生产和设计方面存在合作关系, 共同遵守产业内部的安全标准, 共同把某些安全生产方面的职责委托给某一行业协会。由于本案中被告的数量有限, 并且被告之间的行为彼此存在关联, 法院裁定, 如果原告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有瑕疵的瓶盖是由某一被告生产, 那么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就被转移给所有被告承担。由于Sindell案中, 涉及的被告制造商更多, 而且各被告之间也不存在共同授权行为, 因此Sindell案中法院判定“联营责任”原则在该案中不适用。[3]115
(三)法官的政策性因素考虑
在英美法中, 社会政策是法官进行判案的重要考量因素。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在没有轻视逻辑推理在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作用的条件下得出结论说, 在审判过程中, 对社会政策的考虑颇为重要。法官试图解释社会意识, 并试图在法律中使之得以实现, 但在这样做的时候, 他有时实际上也是在帮助形成和修改那种他所被要求解释的意识。[4]149我国侵权法学者张新宝教授认为, 法律理论中的法律政策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所欲实现的目的, 它既指单个部门法的目的, 也指特定法域内制度所要实现的整体目的。[5]401现代侵权法的法律政策在于通过公平合理地确立行为人责任, 来实现社会生活中个人自由、 个人安宁和社会效用的平衡。[6]45“法律”与“法律政策”二者的关系, 类似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在法学中的讨论。当形式正义无法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从而导致实质意义上的不公正时, 法官在决策时宜加入“法律政策”的考量。
在Sindell案中, 法官考虑的政策因素包括: 首先, 该案中原告是无辜的, 但被告具有主观的过错; 其次, 该案的社会大背景是大规模产品侵权, 社会政策本身偏向于无辜的原告; 第三, 相对于个人而言, 企业在承担责任上具有更大的优势, 他们可以通过购买保险等方式分散风险; 第四, 按照法律经济学的观点, 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方面, 被告将更有动力进行产品风险警示。因此, 基于以上四方面考虑, 法官确立了市场份额规则。
(四) DES案的争议焦点
1、 适用市场份额规则的前提是物质侵害必须满足“可替代性”要求(fungibility requirement)
DES案中, 法院创设了适用市场份额原则的前提条件: “可替代性”要求, 对造成损害的产品要在化学性质上具有一致性。其他产品侵权案件中的受害者就没有像DES中受害者那么幸运了, 理由是其他产品不具有“可替代性”。因此, 市场份额规则在美国被闲置了大约有20年。在DES案件中, 市场份额规则运用相当成功, 但是后来的其他产品侵权案件中, 却遭到了惨败。
直至2004年, Allen Rostron 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市场份额规则中“一致性要求”(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分析的文章, 认为“一致性”包括三个方面: 1, 产品在功能上是可以相互取代的; 2, 产品的物理性质相同; 3, 产品导致了同一的风险后果。可以看到, Allen Rostron 教授对“同一性”作了扩大解释, 如此, 法院就可以扩大适用市场份额规则。很快, 威斯康辛州高级法院在Thomas v. Mallet一案中, 立即适用了Allen Rostron 教授的分析方法, 对受到铅涂料影响的孩子们适用了市场份额规则。 该判决出来后, 立即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讨论。有学者直接质疑这一判决的准确性, 依据是: 铅涂料并没有对受害者强加一种相同的风险, 因为涂料中有的铅含量重, 有的铅含量轻。此外, 铅涂料行业有100多年的历史, 在实务操作中, 不可能由法院准确地定位出各自的市场份额, 法院也没有能力找出到底哪些生产商进入、 退出或者又重新进入了市场。
“可替代性”是适用“市场份额规则”的第一道屏障, 从目前美国司法界、 学术界的动向分析, 对该规则的适用持谨慎态度的法官、 学者居多, 提倡扩大适用的学者则占少数。
2、 突破传统侵权法举证责任的争论
市场份额责任的确立是对于程序法上的“优势证据规则”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的一个例外。因为根据“优势证据规则”, 原告至少要举证有51%的可能是被告造成了原告的伤害, 而在Sindell 案中, 原告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举证责任的。因此, 法官选择了突破传统侵权法上事实因果关系的举证, 将举证责任转向被告方。
3、 无辜被告 VS 无辜受害人的利益平衡
美国市场份额规则的最大难点在于法院认为并没有相关的数据来证明市场份额责任。Sindell一案中, 法院整整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调查五大DES生产商的市场份额, 花费了大量社会行政成本。
同时, 美国很多侵权法学者认为, 对市场份额规则的运用, 将会对今后产品充足供应产生消极性影响, 打击生产商对新药的开发激情。在DES案件中, 法院面临着两难的局面: 一方面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该案对药品行业产生的消极影响。此外, 不可避免的是, 适用市场份额规则, 会导致某些受害人搭便车的情形。
二、 我国立法引入市场份额规则的必要性分析
(一)顺应社会变迁下的侵权法挑战
十九世纪以来, 整个私法伴随着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而实现转变。“我们可以把一般性的演进趋势归结为: 由市民—自由的到社会的法治国; 假使我们把一般性的演进理解为, 社会以维持法的独立性与尊重私人权利的方式, 实现对其成员之社会的、 经济的与伦理的生存所负责的话。这个转变的三个最本质要素为: 藉由私权的社会功能将之相对化、 此种权限在社会伦理上的拘束以及, 背离十九世纪古典私法体系的形式主义。”[7]517现代社会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中, 这样的变化需要不断有新的法律规则来解决新的问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 社会不公平现象使欧洲面临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国家的角色、 功能急速膨胀, 以各种社会、 经济立法来减少社会不公平, 抵制社会主义的发展。私法自治被大幅修正, 私法体系原来建立的概念、 价值、 方法均为之动摇。[8]33工业化时代下出现的大规模侵权行为(mass tort), 特别是重大的产品质量侵权, 正是对传统侵权法的巨大挑战。时代变迁的背景下, 在立法中引入市场份额规则, 是立法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回应。
(二)强化对私法中的“弱者”保护
星野英一教授在《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一书中指出“根据这些, 可以说已经将人作为自由行动的立法者、 平等的法律人格即权利能力抽象地加以把握的时代, 转变为坦率地承认人在各方面的不平等及其结果所产生的某种人享有富者的自由而另一种人遭受穷人、 弱者的不自由, 根据社会的经济地位以及职业的差异把握更加具体的人, 对弱者加以保护的时代。”[9]185私法中的人, 已不再是“智而强者”、 而是“弱而愚者”。
人本身具有一种价值, 即人不能作为其他人达到目的的手段, 人具有“尊严”。从这一立论中可以推导出: 每个人都有权要求其他任何人尊重他的人格、 不侵害他的生存(生命、 身体、 健康)和他的私人领域; 相应地, 每个人对其他任何人也都必须承担这种尊重他人人格及不法侵害他人权利的义务。[10]47在此大前提下, 重新审视法律追求的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制度的任务, 不仅仅是保护个体的权利状态, 而且还要保护法律共同体成员为达到共同目的而进行合作的组织。[11]16因此 , 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受害人予以倾斜保护。
(三)践行“有损害必有救济”的传统侵权法理念
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交换正义”和“矫正正义”。交换正义意味着, 如果一个人夺走了他人的资源, 就得从取得该资源的人那里将资源取回来, 以补偿失去该资源的人, 从而恢复平衡。因此, 在非自愿交易中, 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 “法官要努力通过惩罚来恢复平等”, 剥夺一方当事人的“所得”, 恢复另一方当事人的“所失”。[12]293矫正正义认为, 在因个人行为所造成的不幸事件中, 公平观念要求应该对损失负责的人对其侵害行为造成的可赔偿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适当的说, 损失归因于某人的应负责行为, 即由于你受到的损失是我的行为结果, 因此矫正正义要求我对你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13]248
亚里士多德认为, 当一个人实施了不公正行为, 而另一个人承受了该行为时以及当一个人造成了损害而另一个人承受了该损害时, 法律只关注其不同的危害(已经造成), 而且法律会平等地对待他们每个人。因为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现象, 因此法官要设法将这种不平等状态恢复到平等状态。[13]191市场份额规则中, 生产商之所以要承担市场责任份额, 是因为生产商对DES的错误选择导致了受害人的不幸, 对原告而言的不幸, 在生产商那里却成了“利益所得”, 因此, 被告必须为其利益所得付出代价。
三、 我国引入市场份额规则的制度完善
(一)现有研究关于“市场份额规则”的适用条件
美国《侵权法重述》中规定“在某些涉及通用类有毒物质的案件中, 原告无法在一群生产者中区分谁制造了对特定原告造成伤害的特定产品, 此种情形下(尤其是在涉及DES时), 法院无须原告指出哪一家生产者造成了伤害, 只要求原告列出每一家生产者的市场份额, 根据生产者各自的市场份额进行赔偿。[14]328《产品责任法(第三次)重述》第11节之C, 对市场份额责任进行了论述: “法院在判断是否采用按比例分配责任的原则时, 通常应当考虑如下因素: (1)产品的通常特性; (2)损害的潜伏期; (3)原告在经过彻底调查之后仍然不能确定被告的身份; (4)瑕疵产品与原告所受损害之间因果联系的清晰程度; (5)缺乏造成损害或对损害有重大影响的医疗环境因素; (6)是否有足够的市场份额数据作为合理分配责任的依据……”[15]116-117但是, 在实践中, 美国侵权法学界目前对“市场份额规则”整体上是持有比较谨慎的看法, 很少法官会大胆适用“市场份额规则”, 因为市场份额规则中举证责任的倒置冲破了传统侵权法的理念, 对市场份额责任的适用代表了与传统侵权法的隔离, 许多法官、 学者建议“市场份额规则”应由立法者通过制定法的形式解决。
如果不通过立法形式解决, 法院要在DES案的基础上适用市场份额规则, 有学者认为, 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 必须是同一种产品导致了同一的风险, 或以同一种方式导致了同一的风险; 其次, 受害者必须是不可能追溯到特定的产品生产商, 即无法确知谁是真正的加害人; 第三, 作为法院, 必须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准确地判定各被告的市场份额。综之,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 对市场份额规则的运用还是非常谨慎的, 主要是基于生产商和消费者二者权益的考量, 既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又不能沉重打击到生产商的信心。
(二)对《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篇》中关于“市场份额规则”的评论
纵观《侵权行为责任法》的条文, 并没有将美国市场份额规则引入我国立法。唯一可供分析的是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篇》第1958条, 关于产品责任的分担中规定了“数人生产的同类产品因缺陷造成损害, 不能确定致害产品的生产者的, 应当按照产品在市场份额中的比例承担民事责任。”从立法理由看, 主要是借鉴了美国的市场份额规则。但是, 该条的规定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 市场份额规则的实质是因果关系的推定, 在归责原则上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在举证责任上,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但是, 该条并没有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的倒置”。
其次, 该条文并没有明文规定被告的免责事由。根据现行《产品质量法》的立法精神, 对生产者是适用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 对销售者是适用过错责任(fault liability)。在美国, 作为产品生产商的被告只有证明自己的产品(1)没有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予以销售; (2)没有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予以销售; (3)没有生产导致损害的产品类型。被告证明到以上三个事由中的一个, 才能“免责”。而根据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篇》第1956条“产品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 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 (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 显然, 这三个免责条件不适宜运用到市场份额规则中。
第三, 该条虽然规定了由生产商按照其产品在市场份额中所占的比例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没有涉及到销售商与生产商的关系。这将在司法实践中引发困扰。
(三)本文观点
在我国, 学界有观点认为“适用市场份额规则, 可供法院考量的因素包括: 第一, 产品是否具有通用性, 即该产品是否具有相同的规格和性能, 并经过生产企业的大批量生产, 从而使原告无法查明造成其损害的被告; 第二, 损害的潜伏是否具有长期性, 即该产品所导致的损害是否经过了较长的时期后才显现。正是因为这种长期性, 使得原告因记忆模糊或证据缺失而无法查明具体的被告; 第三, 该缺陷产品与原告所受损害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具有明确性, 只有在现实中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受害人同样损害或者在实质上促成类似损害结果发生的产品及环境等因素, 才能够适用市场份额规则。如果存在其他因素, 则原告所受到的损害与被告侵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将受到破坏; 第四, 法院和当事人能否查明并充分利用‘市场份额’的数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即此类市场份额数据存在并且能够查明, 法院才能在适用市场份额规则时享有可靠的参考依据”[16]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分析, 引入市场份额规则是现实需要, 符合侵权法的时代精神。然而, 《侵权行为责任法》中没有引入市场份额规则, 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现有的配套立法以及学术研究尚未成熟, 相关制度亟需改善, 表现在: 首先, 立法理念的确立; 其次, 实体方面的制度改善; 第三, 程序方面的制度改善。
1、 立法理念
在立法理念方面, 在我国引入市场份额规则, 一方面要考虑无辜被害人与无辜加害人之间的利益衡量, 以及相关行业的利益; 另一方面, 要充分考虑到司法实践的复杂性以及法官判断“产品市场份额”的能力问题。
2、 实体方面
在实体制度完善方面, 需要考虑三方面制度安排: 第一, 市场份额规则的构成要件; 其次, 市场份额规则的适用范围; 第三, 影响市场份额规则的具体因素。
第一, 在制度构成方面, 本文认为, 构成“市场份额责任”的要件是: (1)各生产商各自存在过错, 即主观上是过失的状态。(2)生产商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尽管原告不能指出谁是真正的加害人, 但只要被告生产的产品具有同一性, 并造成了同一的损害, 由于产品本身固有的潜伏性, 导致被害人无法针对被告的行为进行举证。立法基于弱者的倾斜保护, 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的转移。在司法实践中, 遇到的难题是: 生产商如何才能证明到被害人的损害结果不是由其生产的产品造成的, 即被告到底要证明到何种程度才能免责?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3)存在损害的事实。(4)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加害人。原告无法举证谁是真正的加害人是适用市场份额规则的前提条件, 如果可以证明加害人是谁, 那就应该适用一般侵权的规定。(5)有足够的“市场份额”数据作为法院合理分配责任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适用市场份额规则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法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精力去准确判断出各个被告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这并非轻而易举, 因为我们面对的市场并不是完美市场(pure market), 而是一个混合市场(hybrid market)。 在美国DES案件中, 法院的调查整整持续了9个月之久, 因此对法院而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各个DES生产商的市场份额。但是, 其他产品侵权中, 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也是导致美国将市场份额规则搁置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 调查各生产商的市场份额需由行政部门予以协助, 从而增加了行政上的成本。
在Hymowitz 诉 Eli Lilly and Co.案中, 纽约上诉法院在该案中认为, 为了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以及保证市场份额责任原则在各个案件中适用的一致性, 市场份额的计算应当以全国性的市场作为计算的基础。按照这种计算市场份额的方法, 就可以根据各个被告的过失程度来分配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 而各个被告的过失程度又是以其对公众所造成的损害危险的大小来确定的。[3]116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司法条件分析, 以全国性市场作为计算基础的条件尚不成熟, 一方面, 数据容易受到准确性、 权威性的质疑; 另一方面, 全国性市场与地区性市场数据相差甚远, 对受害人而言, 地区性市场数据更能准确反映到被告的过失程度。
其次, 市场份额规则的适用范围。本文认为, 在目前应将市场份额规则限定于产品责任领域, 这与《产品责任法》保护受害人理念相一致。在产品责任领域, 生产商相对于受害人而言, 处于举证、 赔付的双重优先地位, 而在其他领域, 如网络侵权, 加害人与受害人并无明显的差别, 不宜适用市场份额规则。
第三, 具体影响市场份额规则的要素: (1)产品的可替代性。正是因为各生产商之间的产品具有可替代性因素, 才能导致损害的同一性。否则, 原告就无法将所有生产商视为被告请求赔偿。(2)产品的潜伏期。产品的潜伏期决定了受害人的损害一时无法凸现, 这就使得受害人丧失了举证谁是真正加害人的优势。在此情形下, 适用市场份额规则才具有正当性。
3 、 程序方面
从实践分析, 市场份额规则往往涉及到众多受害人, 如我国“三鹿三聚氰胺”事件中受害人众多。然而,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 若在市场份额规则中适用将遭到制度性障碍, 即“首先, 诉讼标的的同一种类, 限制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的作用; 其次, 裁判效力的有限扩张性, 减弱了代表人诉讼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的适用空间; 第三, 代表人诉讼制度程序设计及人民法院自身的角色定位, 影响了它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的作用。”[17]
因此, 建议在程序保障方面有所改进, 引入诸如集团诉讼、 示范诉讼等机制更好地保障受害人利益。
尽管市场份额规则能为受害人提供法律上的救济途径, 但是这一规则的适用成本比较高, 因此, 除了依靠法院适用“市场份额规则”外, 政府可以考虑创设一个国家基金, 或者通过对各大生产商征税, 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 (侵权行为编)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235.
[2] 杨立新. 侵权行为法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3] [美]Vincent R. Johnson. 美国侵权法 [M]. 赵秀文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4] [美]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M]. 邓正来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5] 张新宝.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6] 张小义. 侵权责任理论中的因果关系研究——以法律政策为视角 [D].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06.
[7] [德]弗朗茨 维亚克尔. 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下) [M]. 陈爱娥, 黄建辉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8] 苏永钦. 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9] 星野英一. 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王闯译 [M]//. 梁慧星. 民商法论丛(第8卷)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10]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 [M].王晓晔等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11] [德]迪特尔 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 [M]. 邵建东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12] [美]James Gordley. 私法的基础——财产、 侵权、 合同和不当得利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13] [美]格瑞尔德 J波斯特马. 哲学与侵权行为法 [M].陈敏, 云建芳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4] 美国法律研究院. 侵权法重述—纲要 [M]. 许传玺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15] Restatement Third, of products Liability, 11, Comment [m]//. [美] Vincent R. Johnson. 美国侵权法. 赵秀文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6] 马新彦, 孙大伟. 我国未来侵权法市场份额规则的立法证成——以美国侵权法研究为路径而展开 [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1): 93-101.
[17] 刘璐.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赔偿民事诉讼程序之保障 [J]. 法学, 2008(11): 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