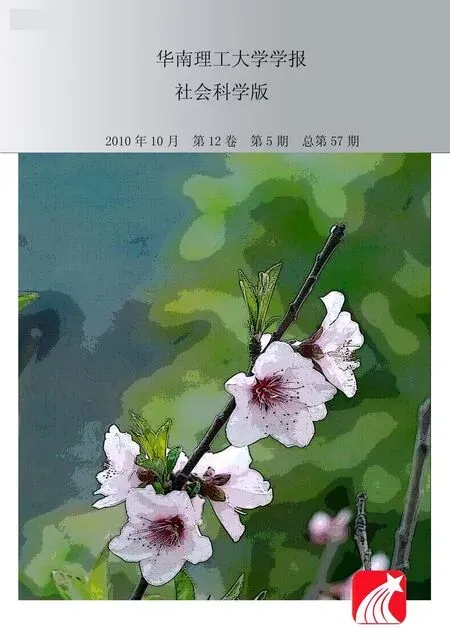试论我国刑法变更对生效裁判的影响
2010-04-11廖梅
廖 梅
(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根据我国刑法溯及力的立法规定, 新法颁布时尚未审判或尚未审判完毕的案件是刑法溯及力适用的对象, 从维护法律权威性和社会秩序稳定性角度出发, 根据旧法做出的生效裁判不得随意变更, 即新法的变更原则上不应当影响根据旧法所做出的生效裁判。但是, 刑法由于其惩罚手段的特殊性, 其修改会影响行为人诸如自由、 生命等重大法益, 同时从现实情况来看, 目前刑法变更频繁, 在轻刑化刑事政策的作用下, 刑法规定不仅重视入罪、 加重刑罚, 而且开始做出罪、 减轻刑罚的尝试, 刑法修正案(七)关于绑架罪较轻量刑幅度的增加即为明证。[1]在此情况下, 我国目前刑法溯及力关于生效判决的适用问题在立法和理论上就存在探讨的余地。
一、 各国或地区关于本问题的立法规定
大体来说, 对于刑法溯及力所适用的范围, 世界上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刑法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类型:
第一种立法类型规定, 刑法溯及力的立法规定适用于已有生效裁判的刑事案件。如西班牙刑法第24条规定: “即使法律规定时已被明确判决, 而被判决者正在服刑, 但只要对于犯罪及过失罪之犯人有利, 刑法具有溯及力。”《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条规定: “规定行为不构成犯罪, 减轻刑罚或者以其他方式改善犯罪人状况的刑事法律, 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即适用于在该法律生效以前实施犯罪的人, 其中包括正在服刑的人或已经服刑完毕但有前科的人。……如果犯罪人因为犯罪行为正在服刑, 而新的刑事法律对该行为规定了较轻的刑罚, 则应在新刑事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减轻刑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较轻的新法对于判决已经确定的案件有效, 可以发生免罪免刑或者减轻刑罚的效果。一些保护公民权利的国际公约也一般倾向于将溯及力原则适用于判决已经确定的案件, 例如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5条第1款规定, 如果在犯罪之后依法规定了应处罚较轻的刑罚, 犯罪者应当减刑。这一规定隐含了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后法不仅适用于判决尚未确定的案件, 而且适用于判决已经确定的案件。
第二种立法类型规定, 原则上刑法溯及力的规定仅仅适用于未经审理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案件, 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刑法溯及力的规定可以对已经生效判决的执行发生效力。如法国刑法典第112—4条规定: “新法的即行适用不影响依旧法完成之法律行为的有效性。但是, 已受刑罚宣判之行为, 依判决后之法律不再具有刑事犯罪性质时, 刑罚停止执行。”如在我国的台湾地区, “在刑法裁判已经确定以后, 遇有法律的变更, 而新法不以其行为为犯罪, 或以其行为为不罚时, 该变更之新法固不影响已确定之裁判, 若确定之裁判尚未执行, 或执行尚未完毕者, 应免其刑之执行”, 意大利刑法第2条第2款规定: “行为后法律变更为不处罚者, 其行为不为罪; 其已判决者, 终止其刑之执行及效力。”韩国刑法第1条第3款规定: “裁判确定后由于法律变更, 致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时, 免除其刑之执行。”这种立法规定正如有台湾学者所言, “但所谓免其刑之执行, 仅生免除执行之效果, 其有罪之裁判, 仍然存在, 故在法定期内再犯罪而合于刑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者, 仍须以累犯论处”。[2]87
第三种立法类型明确规定刑法溯及力的规定仅仅适用于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案件, 对于判决已经生效或者判决正在执行的案件, 没有适用刑法溯及力规定的余地。如我国刑法第12条在第1款规定了刑法溯及力的规定适用于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案件后, 在该条第2款明确规定: “本法施行以前, 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 继续有效。”根据该条规定, 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不适用于判决已经生效的案件。
二、 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争议观点及其评析
关于我国刑法溯及力对生效判决的效力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与目前立法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 对于刑法溯及力与已生效判决的效力问题, 既要维护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也要考虑已有诉讼秩序的稳定性, 因此, 新法施行以后, 原则上都应认为原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尤其是在定性上, 不管刑罚是否执行完毕, 原判罪名不得改变, 不得以新法定罪量刑为轻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当然理由, 更不得以新法规定为据撤销原判的定罪, 从而保持判决的稳定性。但是在新法改为无罪的情况下, 应适当兼顾行为人的利益和体现新法的评判价值, 应认可新法的溯及力, 免除余刑的执行, 即允许在具体执行上作变通处理, 通过减刑、 假释以达到免除余刑执行的实际效果。[3]17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从刑法的公正性和人道化着眼, 应认为新法认为无罪并且刑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 应当予以释放, 不再执行, 对于罪重变为罪轻的案件, 只要还在原判刑罚的执行过程中, 就应当允许依照新法予以改判。[4]134
笔者认为, 我国目前刑法关于刑法溯及力与生效判决之间关系的规定显然存在不足之处。新法体现社会治理新的需求, 新法不再认为是犯罪或者罪刑较轻, 原判刑罚如果仍然不加改变, 则与新法的治理方法相悖, 而且浪费不必要的司法开支。上述两种观点都提出了改进建议, 其实质是对上述第一、 第二种立法模式的选择。第一种观点实质是采取上述第二种立法模式。该观点在刑法溯及力与已生效判决之间的关系上, 认识到二者之间存在维护诉讼稳定性、 权威性与保障行为人权益之间的价值冲突, 在这一点上抓住了二者矛盾的实质。但是其在这种价值冲突中采取所谓折衷的立场, 认为应当兼顾维护诉讼稳定性、 权威性与保障行为人权益。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妥:
首先, 刑法溯及力原则是与罪刑法定原则密切相联的一个原则, 甚至可以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人权保障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核和理论基础之一,[5]98, 由于刑罚惩罚手段的严厉性, 刑罚判决的变更会对行为人的重大法益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 在刑法溯及力与已生效判决的关系上, 在面临维护诉讼稳定性、 权威性与保障行为人权益之间的价值冲突选择时, 应当首选行为人权益的保护。而上述第一种观点中的折衷、 平衡方法, 其实质是对诉讼稳定性、 权威性的维护, 只是对行为人权益保护略有兼顾, 不能彻底保护行为人的权益, 显然与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规定溯及力制度的初衷相悖。
其次, 如果将刑法溯及力对已生效判决的效力仅仅限制在第一种观点范围内, 则会出现无法逾越的立法和司法困境。在立法上, 既然承认新法认为无罪的案件应当停止余刑的执行, 也就是承认了新法对已生效判决的效力, 则否认新法对其他生效判决的效力就难以自圆其说。并且, 如果部分的承认刑法溯及力对生效判决的效力, 即在新法认为无罪的已决案件中, 停止余刑的执行, 那么如何进行司法操作、 也就是说这种行刑状态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按照上述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所言, 通过减刑、 假释的方法予以变更刑罚的执行, 则明显不妥。因为减刑是我国刑法中的成熟行刑制度, 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 新法变更导致的原判刑罚不再执行显然不是减刑的范畴, 而假释的效果是“有条件的释放”, 符合一定条件才算刑的消灭, 否则还要收监执行余刑, 将新法变更导致的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归入假释违背保护行为人权益的初衷。因此, 不彻底承认刑法溯及力对已经生效判决的效力, 认为仅仅发生免除余刑的法律效果, 在实践中不能达到预想的理想效果。
第三, 上述第一种观点部分肯定刑法溯及力对生效裁判的效力, 不符合国际公约的精神。如前所述, 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5条第1款已经肯定了刑法溯及力对生效裁判的效力, 1998年我国已经加入了该国际公约, 在这种背景下, 部分肯定的观点难以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接轨。
因此, 笔者认为, 从维护行为人权益出发, 为彻底贯彻刑法溯及力“从旧兼从轻”原则, 应采取上述第二种观点, 也就是借鉴第一种立法模式, 即认为刑法溯及力的立法规定适用于已有生效裁判的刑事案件。具体来讲,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 对于已有生效判决的刑事案件, 犯罪人正在刑罚效果范围内, 新法认为无罪或刑罚减轻的, 应当依法改判; 第二, 对于已有生效判决的刑事案件, 犯罪人已经服刑完毕, 新刑法认为无罪的, 则原犯罪人可以申请法院依法定程序予以无罪确定, 以消灭前科, 复归社会。这里, 之所以认为对于新法认为无罪、 而原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当事人仍然可以通过溯及力的规定申请确认无罪, 是因为前科的存在对行为人复归社会将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是在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已受刑事处罚者有报告前科义务的背景下, 这样的规定尤显必要。
三、 我国关于本问题的司法实践考察及其建言
事实上, 我国司法实践已经认识到新的刑罚依据对已生效裁判案件当事人的影响, 并通过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新的刑罚依据对已生效裁判案件的效力。例如,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的“涉枪涉爆”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5月1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非法制造、 买卖、 运输枪支、 弹药、 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对于非法制造、 买卖、 运输枪支、 弹药、 爆炸物等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虽然对于打击该类案件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客观上导致刑罚处罚面过大或者过重。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9月17日又颁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关于审理非法制造、 买卖、 运输枪支、 弹药、 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该《通知》规定, 对于《解释》施行前, 行为人因生产、 生活所需非法制造、 买卖、 运输枪支、 弹药、 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 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不作为犯罪处理; 行为人确因生产、 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 买卖、 运输枪支、 弹药、 爆炸物, 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 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人民法院经审理并已经依照《解释》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 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诉, 经审查认为生效裁判不符合《通知》关于不作为犯罪处理以及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规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 并依照《通知》规定的精神予以改判。
根据上述《通知》的规定, 《通知》中对于确因生产、 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 买卖、 运输枪支、 弹药、 爆炸物且没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的, 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处罚或者处罚较《解释》轻。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通知》的规定, 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 这无疑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承认刑法溯及力对已生效裁判效力的一个实例。
笔者认为, 这种范例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起到较好的实际效果, 切实保障案件中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这种方式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 用刑法司法解释的方法突破刑法溯及力的已有规定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根据我国宪法, 刑法司法解释只能就刑法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释, 不能超越刑事立法的权限[6]8。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虽然起到了保障人权的作用, 但是这种不当的方式从长远来看对法治有害的。在我国司法解释的历史中, 也曾出现利用司法解释确定刑法溯及力对已生效裁判效力的问题, 如1987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猎杀大熊猫, 倒卖、 走私大熊猫皮的犯罪分子的通知》规定: “对近期已判处的这类案件, 凡属犯罪情节严重, 量刑畸轻, 社会反映强烈的, 人民法院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该司法解释是利用审判监督程序对行为人适用从新兼从重原则的典型。当然, 随着社会法治的发展, 这种情况已经基本上杜绝。但是这种用刑法司法解释的方法突破刑法溯及力已有规定的做法确不宜提倡, 甚至是危险的, 建议国家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此问题进行直接规定。
其次, 从上述司法实践来看, 新的刑罚依据适用于已生效判决的途径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 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 基于“原判决、 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原因予以重审。笔者认为这种做法虽解一时之需, 但亦经不起推敲。理由是, 已有生效判决的案件在
出现新法后需要改判的原因确实是法律发生了变化, 而依旧法作出该生效判决时适用法律是没有错误的, 如果依据该条款对案件发动重申, 将会使此类案件与审判时人为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混淆; 其次, 按照目前已有司法解释的规定, 此类案件按照基于“原判决、 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原因予以重审也不会发生适用新法的效果, 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9月25日发布的《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 应适用行为时的法律。根据该规定, 此类案件也不能适用新法, 如果按照上述《通知》适用新法, 则会出现司法解释的冲突。
因此, 笔者建议, 可考虑在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中直接规定新法发生变更为发起重审的根据, 并对其适用法律的“从旧兼从轻”原则进行提示性规定。
参考文献:
[1] 周道鸾. 从《刑法修正案(七)》看立法导向 [N]. 法制日报, 2009-04-01(8).
[2] 高仰止. 刑法总则之理论舆实用 [M]. 中国台北: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 1986: 87.
[3] 张晓薇 牛振宇. 刑法既判力与刑法溯及力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 (8): 171-175.
[4] 刘仁文. 关于刑法溯及力的两个问题 [J]. 现代法学, 2007, (4): 133-136.
[5] 马克昌. 当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 [M]. 北京: 人民检察出版社, 2004: 98.
[6] 马克昌. 刑法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