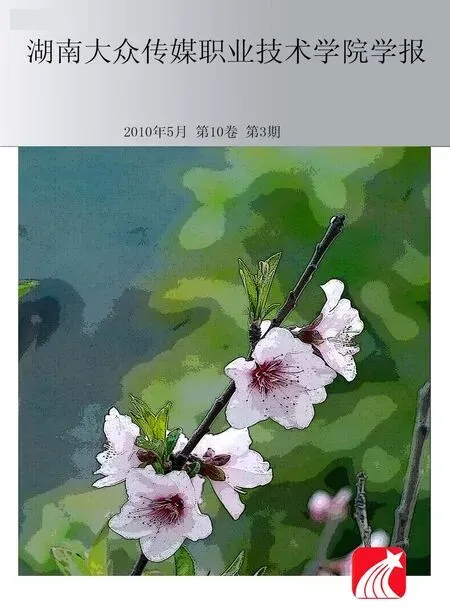1949年前我国广播法规的 “平衡”理念分析
2010-04-11肖燕雄
肖燕雄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权利(力)平衡论被我国一些行政法学家认为是行政法规的理论基础,其主要观点有:第一,平衡是指矛盾双方在力量相抵后保持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第二,既然是相抵,则必然是一种制约,即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相互制约,通过制约从而实现一种动态平衡,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公平。第三,平衡论认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行政权力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1]
传媒法属于行政法规。在传媒法中,权利(力)平衡方涉及政府、媒体创办者与经营者、媒体消费者(受众)、广告商。本文以平衡理论为分析工具,针对我国现代主要的广播法规,逐一考察其中不同行政主体、行政相对方或相对人所享有或被赋予的权利(力)状况,并试作简单的纵向比较。
一、北洋政府的无线电及无线广播管理法规
我国的广播事业开始于无线电通信技术伴随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而传入我国之时,故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因素。
据有关史料记载,我国使用无线电报始于清朝末年。1905年(光绪十一年)秋,北洋大臣袁世凯购置无线电收发报机,分别安装在北京、天津、保定和北洋海军的舰艇上,用于沟通军事情报。由于无线电通信技术一开始是用于军事的,所以政府对其的管理十分严厉。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涉及无线电的法令《电信条例》,它规定:无线电器材属军事用品,非经陆军部特别许可不得自由输入我国;未经中国政府有关当局批准,也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私自设立无线电台,擅自收发无线电报。
《电信条例》对无线电器材的这一属性划分体现出政府一种谨慎的防御心理。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对思想的钳制是很严厉的,当意识到信息有了自由流通的渠道时,他们习惯性运用的手段就是“堵”。至于对这一新技术的建设性研究和管理则排在次要位置,甚至在最初并未纳入他们的思考范围。也就是说,当时的统治者本能地用一种防御性的法规来阻止尚未本土化的新技术的发展。
无线电广播出现后,北洋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从无线电报到无线电广播是科学技术的又一次飞跃,他们对新出现的现代传播媒介的管理相沿以习,把广播电台与用于通信联络的无线电台等同看待。1923年1月23日晚8时,奥斯邦电台正式播音,它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无线广播电台。可是该电台刚刚问世就被北洋政府交通部下令取缔,理由是它违反了《电信条例》。1923年4月该电台停止播音。奥斯邦电台之后,美国开洛公司(Kellogg Co.)上海分公司创办的开洛广播电台也受到了相同的待遇,由此加强并巩固了《电信条例》诞生以来政府一以贯之的管理原则。
奥斯邦电台出现后,人们把广播叫做“空中传音”。神奇的“空中传音”引发了上海租界里中外听众的“无线电热”,收音机的人均拥有量迅速上升。无线电这一新技术因其信息传递的快捷性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尤其对于一个传播相对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的地区而言更是如此。而且,早期的广播节目多为新闻和娱乐节目,这对于丰富民众生活、开拓人们视野有很大的帮助,它毕竟不同于那种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另外,外商经营广播电台的目的多数是为了推销无线电器材,对于他们而言这是赚钱的好机会,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广播媒介的兴盛更多地是经济行为而非政治行为的结果。如果说《电信条例》颁布时因为与之相伴的是外敌入侵,所以确实需要将无线电主权摆在首位的话,那么此时新技术本身已经展现出它的一些优势与特征,表明它也可以是中性的。但是,面对新技术的恐惧感和面对外来信息惯有的抵抗心理,使得北洋政府当局在新兴媒体面前不可能与时俱进。
在外商办广播的影响下,中国政府和民营企业也开始涉足广播领域,而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也伴随着这种实践一步步成熟、完善起来。交通部从屡次查禁广播电台的经历中逐步认识到,播送新闻和音乐的广播电台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无线电台,收音机也不同于无线电收发报机,所以他们开始筹备新的法令。筹备的举措之一就是开展讨论。当时关于制定无线电广播法令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广播电台究竟是官办还是商办,收音机是自由出售还是委托专卖,是征收广播(收听)费还是征收各种执照费等几个问题上。讨论的结果是,1924年8月北洋政府交通部颁发了《关于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的暂行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无线电广播的法令。
《暂行规则》的一些条款仍然是依照《电信条例》而制定的,但基本精神已有所改变。它规定装用接收机必须由交通部核准,领取执照;还规定了什么区域、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收听什么节目以及执照费等内容,中国公民、华侨、外国人都在允许收听之列。由此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对待无线电广播的态度已经由无条件取缔改为有条件限制,建立广播电台和出售、安装收音机再也不是违法之事,因为有条件允许装用接收机自然是默许了广播电台的存在。另外,该规则还明文规定允许外国人安装收音机,对外商设立广播电台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可见政府的态度已经由全“堵”改变为有条件地“放”,这显然是对实际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的适时之举。
北洋政府交通部在拟定关于无线电广播法令的同时甚至之前,就开始酝酿筹建官办广播电台,因为他们清楚,在允许收听的情况下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但是由于当时各派军阀割据,建台之事一再受阻。只有奉系军阀于1923年在哈尔滨建立了我国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并建立了东北无线电监督处来管理广播事业。此外,1926年颁发的《无线电广播条例》、《专设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和《运销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这三个无线电广播法规,比两年前交通部公布的《暂行规则》已稍趋完备和严苛,它明确规定任何人或任何机关不得在东三省内私运、私售或私设任何无线电机器并经营广播无线电事业。不同于《暂行规则》的默许态度,广播国有国营色彩十分明显。当然,这一法规只在一定范围内付诸实施。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播管理法规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军阀混战结束,国民党政权在全国建立了相对统一的统治。为了宣传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十分重视对无线电广播的控制。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的建设委员会设立无线电管理处。8月1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开播。12月,建设委员会公布《中华民国广播无线电台条例》,后又公布《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规则》。但是,一直以来无线电事业都是交通部的管辖范围,建设委员会的此番举动使两者发生冲突。后来,国民党三届二次会议决定无线电事业归由交通部管理。1930年,交通部公布《装设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规则》。这些法规与北洋政府的法规比起来要完备许多,具体体现在:
其一,在广播电台的创办管理和内容管理上,国民党政府对于无线电广播的认识较北洋政府深刻了很多。《中华民国广播无线电台条例》对广播电台的所有权和节目内容两个最基本的方面都作了规定,管理上初显系统性。在所有权方面,该条例第三条规定:“广播电台得由中华民国政府机关公众或私人团体或私人设立,但事前须经国民政府建设委员无线电管理处之特许,违者由当地负责机关制止其设立”,交通部公布的有关法令也允许公私团体和个人经营广播电台。在节目内容方面,该条例规定:“广播电台不得广播一切违背党义、危害治安、有伤风化之一切事项,违者送交法庭讯办”,“政府如有紧急事件须即广播者,私家广播电台应为尽先广播,不得拒绝,但得酌量收费。”这表明政府允许民营电台的存在;节目内容方面的限制,除了强制性宣传和不得违背党义外,其多数是在情在理的,也与西方国家商业电台“必须传送”公益信息的原则相符。1929年,交通部无线电报话管理处拟定的《广播无线电台机器装备使用暂行章程》规定:“广播无线电台播音节目之传单或刊登新闻纸上之公告,应先期汇呈交通部或交通部无线电报话管理处。”这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政府在电台所有权放开的基础上,在内容管理上的控制愈趋加强,即采取了严厉的新闻预防手段——事前检查制度。
其二,允许商业电台存在,制定保障商业活动的条款。《中华民国广播无线电台条例》将广播无线电台分为“经费完全自给”和“以营业为目的”两种,前者不再向听户征收收听费,收执照费四十元;后者须向本地领有收音机执照的听户征收收听费,收执照费一百元。并且规定广播电台可以播出商业广告,收取广告费,但不得逾每日广播时间十分之一。为保障电台经费,早期的上海电台由听众组织播音会,交纳会费资助电台,电台则按播音会要求播送节目。开洛电台曾由外国听众组织的中国播音会(CBA)和中国听众组织的中国播音协会(BAC)两个听众组织出资点播节目,以维持电台的开支。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亚美电台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后来由于广播电台和收音机的增多,不交会费同样可以收听节目,统一收费点播节目的做法行不通了,听众组织即自行解体,代之而起的是电台以出卖播音时间为客商做广告的经营方法。此后,中小资本家认为办广播有利可图,纷纷购机设台,替客商做广告以盈得利润。而且,广播电台还可以按照无线电品营业规则,兼营租售收音机件之商业。这些都是广播法规先进理念的直接体现,有其可称道之处。因为商业电台业主是广播事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利益主体,其商业活动应是结构性合法活动,他们的利益必须受到法律的保障。
由于政策法规的允许,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一批民营广播电台,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一地。民营台大致有教育性广播电台、宗教性广播电台和商业性广播电台三种。它们的内容多为科学、宗教和娱乐性节目,而距离政治较远。尤其是商业电台,它们多依靠广告收入维持。因此,为了吸引听众,广播节目内容也愈加强调娱乐倾向,娱乐节目播出时间要占全天播音时间的85%以上,其中评弹占到第一位,其次为中西音乐、申曲(沪剧前身)、滑稽戏、故事等,甚至经常播出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污秽俚俗的滩簧、滑稽之类的节目,而其原来的使命——传递新闻已经成了附属品。当然,其中政府对意识形态节目的严厉管制也是出现这种现象的诱因之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实际上将矛头指向共产党,宣传上的控制变得更为严厉,试图把广播电台都变成自己的喉舌。
这首先体现在对外商台的限制上。1932年11月,交通部公布《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它规定:“凡中华民国之公民,完全华商之公司,经在民国政府立案之学校、团体或其他合法之组织,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广播电台,但须呈交交通部领得许可证后始得装置。其非完全华商之公司及非完全华人国籍之团体,须经在国民政府注册领有注册证书者,始得请领许可证在中国境内设立广播电台。”而其实际的做法是,逐步取缔当时外商所办的广播电台,多以收购、“收归部办”的方式实现其目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列强各国对在华利益愈加关注。在此背景下,国民党政府考虑得更多的是外商办台引发的政治性问题,认为他们“在平时固仅以牟利,非常时期则阴为间谍,不仅妨碍我国播音领空之主权而已”,若不从速“先行收回或撤销国境内外人所设之电台,恐将接踵设台,以巨大电力扰乱我中央电台与公营民营电台之播音,并以之作不利我之宣传,势将无法制止或干涉。”1937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广播教育实施办法》,明文规定:“绝对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广播电台”。拿《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广播教育实施办法》与几年前的《中华民国广播无线电台条例》对照,南京政府在对待商业电台的问题上体现了内外有别的政策。
其次,通过加强对节目内容的管制来限制民营台等非官办电台的发展。1936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简称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广处、宣传部、交通部、教育部、内政部等国民党党政机关部门组成,由陈果夫任主任委员,是国民党管理全国广播事业的决策机构。10月,交通部公布了该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这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开始以法律形式着重从广播节目的内容上控制广播电台。1937年,继上述《办法》之后,交通部又公布了《民营广播电台违背<指导播送节目办法>之处分简则》和《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这些法令明确规定:广播电台每天的播音节目从种类、播送时间到标题、担任人员姓名都应预先呈交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审阅;各广播电台播音节目的时间内必须按交通部的规定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无转播设备者届时停播。另外,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教育节目材料标准》还就新闻类节目规定:“国内外重要新闻均根据中央社稿或采用当地报纸上的‘中央社电’或收录中央电台之广播新闻”,要求重要新闻高度一致化。1928年《中华民国广播无线电台条例》中的“必须传送”原则到这时演变为《教育节目材料标准》中严苛的新闻统制政策,从一种信息必须得以广播而变为只能广播一种信息。这样一来,节目审查的主要对象实际上就是娱乐节目。虽然法令明文规定禁止播送违反善良风俗、宣传迷信、词句猥亵的故事、歌曲、唱词,但实际上在审查中,一些充满低级趣味的娱乐稿件,如《四大美人》、《月下幽情》等都得到许可,而制止得最为严重的反而是《救亡进行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反对内战、奋起抗日的歌曲,这与此时国民党政府为了钳制公众舆论,镇压进步的、革命的新闻出版活动而实施的严苛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与8年前的《广播无线电台机器装备使用暂行章程》比较,《民营广播电台违背<指导播送节目办法>之处分简则》和《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完善并发展了南京政府的广播内容事先检查制度,可谓深文周纳,详尽赅备。自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成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民营广播电台被撤销9座,暂停播音4座,受警告处分3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方利益集团进入一种紧张的对抗状态,各方的价值取向都单一地体现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上。在国统区,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加强战时广播的宣传力度,抗御日本侵略者的广播宣传,另一方面积极反共,利用法规和一些非法手段试图干扰、破坏、取缔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掌握了广播事业的领导权,进行奴化宣传;在解放区,共产党积极建设自己的广播事业,进行抗日宣传。战时广播管理呈现为一片混乱状态。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政府先是积极接收日伪广播电台,接着,1946年交通部公布《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将广播电台分为三类:交通部所办的国营广播电台,其他政府机关所办的公营广播电台和中华民国公民或正式立案完全华人组织设置之公司、厂商、学校、团体所设的民营广播电台,而外籍机关人民、非完全华人组织设置的公司、厂商、学校、团体一律不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广播电台。此规则虽然允许民间办广播电台,但是却从电台的设置、分布、数量、发射功率以及广播内容等多方面加以种种限制。比如,国民党官办电台1个台可以使用3个频率,而民营台20多家却只能使用15个频率,只能轮换播音。于是,民营台在此打击下变得一蹶不振。但也有在夹缝中求生存者。从1946年8月起,上海市电信局陆续批准23座民营电台播音,同年10月11日,上海市民营广播电台同业公会成立,除此之外的民营电台均在被取缔之列。即使是这样,国民政府上海市电信局、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局三方仍然多次采取联合行动查封“非法电台”。1948年10月,国民政府国防部以“戡乱”宣传需要为名,准许上海16座“军营”电台播音,将“非法电台”合法化。除了“建台”方面的限制外,国民党政府还在“收听”方面加以限制。1948年,交通部修正公布《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规则》,设立十分繁琐的登记程序,并且多次下令禁止收听解放区的广播。
由此可以看出,自1927年的《中华民国广播无线电台条例》开始,国民党政府就试图限制官办电台之外的声音,直至绝对禁止外台和严格限制民营台,管制愈演愈烈。具体而言,在所有权上,外商电台在1937年后被明文禁止,而民营电台一直是被允许的,这多少体现出国民党政府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媒体运营色彩;在节目内容上,管制一直很严苛,对于非官办电台而言,几乎只有娱乐性的内容是被允许的,因为他们多数为商业性质的电台,广告收入直接关乎他们的存亡,所以低俗煽情的内容成为主打,而在政治上他们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甚至主打的娱乐性内容也常常成为官方管制政治内容的突破口。至于对那些政治上对立的声音(如中国共产党电台)更是不惜以非法手段(如任意而为的新闻检查)消灭之,其对广播的管制与对报纸的管制并无二致。[2]
综观上述两段时期的广播事业,其社会历史环境的最大特点是不稳定。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国共分裂、抗日救亡、内战爆发,各种力量此起彼伏,政治整体始终都在未形成或未稳固之中。依照一方的威权统治而订立的规则虽然得以颁行一段时间,但威权不够或未达之处,必然受到其他方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各方的各自为政上。这种挑战不是一个整体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利益冲突或转让的表现,而是各个不同整体间的斗争。此时,政治上非整体状态必然表现为行政法规中行政权力的撕裂和行政主体针对相对方的霸权状态(战时传播政策就是其典型)。博登海默认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结合体,这里的正义和秩序都是对一个整体而言的。[3]在一定范围内,如果还存在多个利益整体,并且彼此无法共同商讨,那么必然不能形成超越各方的价值追求,法律的秩序就无法诞生,就不能保证一部整体法的出现,即权利(力)的平衡无法实现。
具体而言,在上述广播法规中,平衡理念的弱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府在广播中的权力过于强大,宣传压倒一切,媒体内容处在党国的绝对控制之下,新闻检查手段用到极致;第二,没有法律条款明示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即使一直允许民营广播存在,它也始终处于弱势;第三,作为传播的一方,甚至是主要的一方,广播消费者(听众)的权益保障内容付诸阙如。但是,还不至于说其缺失平衡理念,虽然这种理念是在若有若无间。如毕竟基本上给予民营商业台的存在空间(虽然有时是“字面上”的),承认商业台依靠广告赢利的合理性。现在回过头去研究1949年前的广播法规时,一则必须设身处地地体察其非“整体”状态下的失衡性,二则要深加苛责这种失衡特性。因为,上文分析的非“平衡”状态法规并不是全部处于战争时期,特别不全是在八年抗战时期,而战时新闻制度是可以作为例外存在的。
我国现代广播法规中的平衡观念未能很好形成,除了上文所分析的“整体”撕裂问题外,还因为:其一,广播媒体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手段,其技术力量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加之统治者的旧有传播观念的阻滞,法律制定者未充分掂量不同主体的权利要求;其二,虽然政府与电台的民营方似乎达成统一追求,但是后者因为商业利益的驱动而在内容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位表现,使得法规制定者浓墨重彩地限制节目内容有了“正当”的口实,而一如上文所述,真正限制的却又不主要是纯娱乐节目。于此可见,法律的完善还需要一个多方成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罗豪才,沈岿. 平衡论: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再谈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J]. 中外法学,1996(4);罗豪才,甘雯. 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J]. 中国法学,1996(4).
[2] 肖燕雄. 我国近现代新闻法规的变迁[J]. 二十一世纪,1998(6).
[3] 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27-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