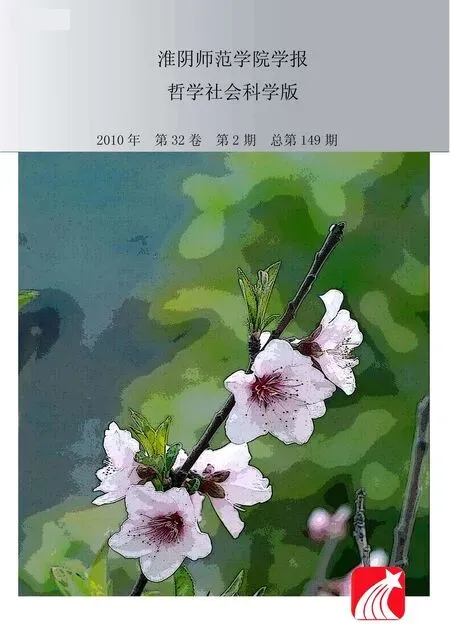论汉代游仙诗的来源、艺术形态及其影响
2010-04-11张树国
张树国
(杭州师范大学 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36)
【文艺学】
论汉代游仙诗的来源、艺术形态及其影响
张树国
(杭州师范大学 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36)
游仙观念来源于原始巫教和道家学派,在信仰、仪式与方技三个方面规定了游仙诗艺在汉代的发展方向和艺术形态特征。汉武帝时代的郊祀活动通过对神灵的献祭祈求游仙长生,祭神乐舞发展为游仙乐舞,在《郊祀歌》中得到完美的展现;同时游仙诗也是两汉时代世俗宴享仪式上的艺术消费品。汉代游仙诗艺具有仪式性、表演性和在场性特点,是从《楚辞·远游》到魏晋游仙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对魏晋文人同类题材作品的创作具有重大影响,成为古典浪漫主义的重要范型。
游仙诗;仪式形态;文本形态;游仙乐舞
游仙诗作为浪漫主义“范型”在古典诗歌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浪漫主义诗人如屈原、曹植、嵇康、阮籍、郭璞、李白、李贺等都有游仙诗创作,曹道衡先生认为郭璞的《游仙诗》是“我国古典浪漫主义诗歌从屈原到李白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环节”[1]。《离骚》可说是最早的游仙诗,而对文人游仙诗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作品是《楚辞·远游》。汉至魏晋六朝的游仙诗作品有260余篇,作者60余人,学界主要关注点在魏晋文人精神生活与游仙诗创作的关系,但游仙诗创作观念、结构模式很大程度上受汉代巫术、宗教仪式及世俗娱乐生活的影响,这一方面则罕为学者所重视。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巫术、宗教仪式对游仙文学艺术结构生成的影响[2]。原始巫术观念、神仙信仰和通神方术构成了游仙诗的“原型”,至少在三个层面规定了游仙文学发展的方向:(一)信仰。游仙信仰在原始萨满教中就已出现,在战国时代楚、齐、秦等国“造神”运动中得到了重要发展,具体体现为魂灵崇拜、山海崇拜、药崇拜观念等,体现为“昆仑神话”体系与“蓬莱仙话”体系的合流。(二)仪式。游仙诗体现在郊庙祭仪中,通过献祭供养神灵,以求得到仙药而长生成仙,乐舞可以说是对天地神灵最高级的献祭;同时在世俗宴享仪式中也多有“求仙药”的描写,决定了游仙诗的结构特征。(三)方技。老庄道与黄老道认为凭借导引来“制炼形魄”、“却谷食气”实现长寿乃至飞升的愿望,成为神仙修炼的理论指南;在文学中的典型代表为《楚辞·远游》。
上述三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古文人游仙诗的风貌。这些文人的“白日梦”虽然梦境千差万别,但希望“蝉蜕弃俗累”的心理一直支配着人们的游仙活动;为求得“仙药”,他们隐居深山采药炼丹;而游仙诗中几乎千篇一律的“乘蹻”意象即乘龙、虎、鹿、凤凰等来飞升远游,无疑来自于巫师陟神的法术。从源流上来说,游仙文学与原始巫术、道教关系紧密,结合了老庄道家、黄老道家及魏晋玄学思想,共同体现了本土宗教强烈的生命取向和对超验世界的追求和向往。而以原始宗教为思想基础的游仙文学也形成了一个有别于现实主义诗歌表现技法的独特传统,即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呈现为三种艺术形态:一是仪式形态,本文称之为“游仙乐舞”,以诗、乐、舞综合体为代表特征,如《楚辞·九歌》、汉《郊祀歌》等;二是世俗形态,以汉乐府歌辞为代表;三是借鉴神话意象和原始思维表现游仙主题的文人创作形态,从《离骚》、《远游》到阮籍、嵇康、郭璞的文人诗等。在这三种形态中,以多神崇拜为中心的原始宗教祭仪凝练为诗歌创作的意象结构,演变为歌乐舞综合艺术的表演形态;神话的时空观转化为对诗境的自觉开辟,成为隐士类型心灵境界的展现。
一、游仙观念来源于神话与方术
原始崇拜观念包括魂魄观念、山海崇拜、神药崇拜等,对游仙观念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在神话典籍《山海经》中有相对系统的记载。同时老庄道、稷下黄老道以及燕齐方仙道对游仙观念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
巫觋思想是战国神仙思想的源头,巫觋与神仙家或方士实际上异名同谓。如神仙名录中有“羡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羨门、高誓。”《集解》引韦昭注“羨门”为“古仙人”,“羨门”实即通古斯语“删蛮”即巫师的音译,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中记载:“国人号为删蛮者,女真语巫妪也。”比较标准的翻译是“萨满”,英译shaman,意思是“因兴奋而狂舞的人”。神仙家关于“羽化登仙”的老生常谈实际上来源于《山海经·海外南经》“羽民国”的传说,“其为人头长,身生羽”。《海内经》:“有人焉鸟首,名曰鸟民。”在《尚书·禹贡》中记载“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岛”字经文原作“鸟”,《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都作“鸟夷”;《大戴礼记·五帝德》云:“鸟夷羽民。”“鸟夷”是中国沿海原住民,羽民为鸟夷之一类,此地以鸟为图腾,可参看石兴邦先生的著名长文[3]。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南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了“羽人”玉佩,在江西新干发掘的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个集人、兽、鸟于一身的羽人形象,具有很强的神话色彩[4]。可见早在商代就有羽人崇拜的信仰。直到汉代,对羽化仙人的描绘仍是汉画像石艺术中的重要题材。
《楚辞·远游》云:“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这一“不死旧乡”据顾颉刚研究,指的是昆仑和蓬莱,“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是上古时代两大重要神话系统[5]。《山海经》中记载“昆仑神话”最为系统,楚地文献如《庄子》、《楚辞》记载昆仑神话多与《山海经》互证。顾颉刚认为:“《山海经》一类的书必然为当时的作家们所见到或熟读。”“昆仑”在楚系神话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蓬莱”则是战国时代燕齐方士的发明。从地理方位上来说,前者在西方,后者在东方。顾颉刚曾对“两大神话系统”做了有趣的对比:西方人说人可成神,如黄帝、西王母、禹、羿、帝江等住在昆仑山上;东方人说人可成仙,如宋毋忌、正伯侨、羡门高等住在蓬莱仙岛上;西方人说神之所以长生久视,是由于“食玉膏,饮神泉”,还有不死树、不死药;东方人说仙之所以能永生,是由于“餐六气,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霞”。“昆仑”与“蓬莱”来自于不同地域,两者的异同也就是“神话”与“仙话”的异同。“蓬莱仙话”实际上来源于海市蜃楼,这在《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及《封禅书》中有记载。战国是神仙之风煽扬很盛的时代,《史记·封禅书》云:“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怪迂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并提到燕国方士如宋毋忌、正伯侨、充尚(《汉书·郊祀志》作“元尚”,托名刘向的《列仙传》中作“元俗”,《史记会注考证》引沈涛曰:“当作元谷,谷与尚相近,传写遂误以为尚。”)、羡门(子)高、最后(《史记会注考证》引王念孙说,“当为聚穀”,宋玉《高唐赋》“有方之士,羡门、高溪、上成、郁林、公乐、聚穀”可证)等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所谓“形解销化”,裴骃《史记集解》:“服虔曰:尸解也。张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变化也。”[6]修炼的目的是使人“蝉蜕”,变而为仙,将灵魂从躯体里解放出去。战国时代,上自贵族下至平民多有致力于修炼以期羽化成仙者,如齐宣王、燕昭王等人,直到后来的秦始皇、汉武帝。
原始宗教中的魂、魄观念对早期仙论有很大影响。殷周时代的死后信仰主要体现在“宾帝”与“配天”观念上。按照这种说法,先公先王死后,虽然肉体埋于地下,而灵魂则上天成为天帝的“宾客”或辅佐,卜辞中常见“宾于帝”之类的文字,金文中也常见“皇考严才(在)上,翼在下”之类的语句,《诗经·大雅·文王》中说:“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子产对魂、魄的说明:“人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据此可知,古人献祭的目的在于供养神灵,使其魂魄精强,福佑后人。据余英时先生研究,子产这一关于魂魄的解释,可能来源于月亮的“生魄”、“死魄”之说。《汉书·律历志》:“魄,月质也。”人的生死与月魄的生死密切相关,魂、魄在先秦属于二元论的灵魂观。[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乐祁说:“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但后来,“魄”指形体,“魂”指灵魂,《礼记·郊特牲》:“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先秦古籍说到“魂魄”时,往往作为偏义复词使用,偏重于“魂”义。古人比较相信“灵魂不灭”的说法,在出土的仰韶文化期的陶棺顶端往往凿有小孔,以备灵魂出入。《礼记·檀弓下》记载季札葬子后,说:“骨肉复归于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礼记》中多处记载专门用来招魂的“复”礼,《楚辞·招魂》就是“复”礼的文学表现。可以说早期“方仙道”是在形魄与灵魂二元论的认识基础上,提出“形解销化”之说的,其形象表述来自上古的“蝉蜕”观念。
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多刻有蝉纹图像。据马承源先生研究,蝉纹约开始于殷墟中期,盛行于殷末周初,主要饰在鼎和爵的“流”上,少数的觚以及个别的小器盘也饰有蝉纹。古说蝉居高饮露,清洁可贵,但蝉纹还有深刻的象征义,即死而复生。蝉又名复育,《论衡·无形篇》:“蛴螬化为复育,复育转而为蝉。”汉代玉琀多作蝉形[8]。米尔恰·伊利亚德认为,蝉的幼虫是从地里面钻出来的,因此它是幽暗的象征。蝉是复活的标志,因此放置于死者口中。在饕餮面具即象征光明与生命的黑暗魔鬼的口中,往往刻有特殊的蝉的图案[9]。郭璞《尔雅图赞》云:“虫之精洁,可贵惟蝉。潜蜕弃秽,饮露恒鲜。万物皆化,人胡不然。”这一“蝉蜕”意象可以说是神仙家最好的“自然范本”。在《史记·屈原列传》及班固《离骚序》中,保存了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对屈原之死的一段精彩议论:“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蝉蜕”、“浮游”实际上即方仙道所谓“尸解”、“形解”之说,指肉体虽坏而精神解脱。《抱朴子·论仙》引《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尸解仙”在仙班中位列“下士”,同时还要经过生死的转换,在死的“彼岸”而不是生的“此岸”达到永生之境。刘安以神仙家思想来阐释屈原,所以多有发明。此后诸如曹植《游仙诗》“排雾凌紫虚,蝉蜕同松乔”、嵇康《游仙诗》“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等,也应用了这一意象。
道家思想及战国导引术对游仙观念的影响很深。被称为“游仙诗之祖”的《楚辞·远游》,其思想来源主要为《管子》中的《内业》、《白心》、《心术》(上下)四篇黄老道文章以及《淮南子》中的《原道训》、《俶真训》及《精神训》。《老子》强调“致虚极,守静笃”、“专气致柔”,“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讲的是古代气功养生原理,并由人体自身的呼吸推及宇宙自然之理,此说为张家山汉简《引书》所引用,强调“吸天地之精气”,以避免“多病易死”,“精气”为稷下黄老道家的核心概念①。《内业》中云:“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陈鼓应先生解释为:“天地万物都有精气,万物赖它获得生命。”但将“鬼神”解释为“天地精神”则恐不然。古代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易·系辞》中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如果没有鬼神之类的观念,那么祭祀的动机及仪式也就难以理解了。《庄子》书中也多有“真人”、“神人”等的描述,如《逍遥游》中的列御寇“御风而行”、“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吸风饮露”,乘六龙而游于四海之外,《大宗师》“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等等,这些思想都为神仙家所吸收。按照黄老道及神仙家的说法,若体内积聚了足够多的精气,就可以白昼飞升,远游天地四方。古代气功在文献中有吐纳、导引、食气、行气、调息、胎息等说法,马王堆帛书中有《却谷食气篇》,为先秦古佚书,里面记载的导引术又见于《抱朴子》、《赤松子》、《黄庭经》等古籍。《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神仙十家,二百五卷,以黄帝、宓戏、泰一、神农为名,其书多亡。“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可见战国秦汉以来,人们在长生药方和导引方面做了许多尝试。桓谭《仙赋》云:“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傍,仙道既成,神灵攸迎。”[10]《后汉书·逸民列传》记矫慎“少好黄老”,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吴苍致书称“吾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遁”,可见黄老思想在当时很有影响。《文选》卷十八记载汉马融之《长笛赋·序》云“有雒客舍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注云“《魏武帝集》有《气出》、《精列》二曲”,为魏晋乐所奏,“气”、“精”为道术之士惯用语,此二曲属于游仙诗。
论及原始崇拜对游仙观念的影响,不能不提到《山海经》,这部古书可说是上古巫文化的总汇。西汉刘歆《上山海经表》认为此书是传说中伯益所作,《论衡·别通》曰:“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但此书有许多时代错误。《山海经》之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禹本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隋书·经籍志》言:“萧和得秦图书,又得《山海经》,相传为夏禹所记。”《山海经》一书虽然只有三万一千多字,但包罗万象,涉及远古历史地理、天象、宗教、巫术、神话等众多方面,可以说是上古巫文化的百科全书。同时《山海经》作为远古口传社会的遗产,其古史价值已经得到人们的重视,如王国维对卜辞殷先公王亥的考证,引《山海经》以证成其说[11]。胡厚宣引《山海经》来论证卜辞中的四方和四方风名[12],即以充满神话色彩的《五藏山经》而论,谭其骧认为也是“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13]。《山海经》本来是巫师的口传而题以夏禹、伯益的,鲁迅认为“盖古之巫书”(《中国小说史略》),“巫以记神事”(《汉文学史纲要》)。《山海经》中记载的巫术宗教习俗给予游仙诗以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山海崇拜与不死药崇拜。晋代郭璞鉴“首创传训”,对《山海经》进行注释,并作《山海经图赞》二卷。正是由于郭璞对古代神秘文化的喜欢,“激活”了这部古书,从而使其《游仙诗》创作别开生面,被钟嵘《诗品》誉为“中兴第一”,代表了游仙诗创作的顶峰。
二、汉代献祭仪式中的游仙诗
“游仙诗”往往寄附于巫术宗教性质的“献祭”仪式中。这些祭仪的主持者是帝王们,祭仪具有为帝王独占的特性。按照人类学者的观点,献祭的种类分为礼物献祭、食物献祭和契约献祭,即古人所说的“珪币牺牲”之类,献祭的目的在于奉养神明[14]。原始宗教中的祭神乐舞是对神灵最高的献祭,可以说是游仙乐舞的远源。《周礼·大司乐》中记载周代保存六代大舞,如舞黄帝《云门》以祀天神,舞唐尧《咸池》以祭地示,舞虞舜《大韶》以祀四望,舞夏禹《大夏》以祭山川,舞商汤《大濩》以享先妣,舞武王、周公《大武》以享先祖等。除《大濩》、《大武》为歌颂武功的宗庙乐之外,其他均属祭祀自然神的乐舞。《楚辞·九歌》可以说是仪式形态游仙诗的代表作,《东皇太一》首句“穆将愉兮上皇”,点明这是祭祀“上皇”即后世所谓“帝祖”的乐舞,结句“君欣欣兮乐康”之“君”即主持祭仪的国君。此外,如“驾飞龙兮北征”(《湘君》)、“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大司命》)等都具备游仙诗的特色。
《九歌》在汉武帝时代郊祀活动中还在上演着,汉《郊祀歌·天地》云:“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武帝时代的郊祀仪式将祭神乐舞发展为游仙乐舞,《郊祀歌》十九章是仪式上的唱辞。《宋书·乐志》卷一云:“汉武帝虽颇造新歌,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这一“郑声”、“新歌”据陈本礼《汉诗统笺》所说:“武帝爱读《离骚》,曾命淮南王作章句,故《郊祀》诸歌皆仿佛其意,第喜奇异,好神仙,夸祥瑞,究非《清庙》、《维天》之比。”[15]在《郊祀歌》十九章中,《日出入》、《天马》、《天门》、《华晔晔》、《五神》诸诗,都是武帝“好神仙”的游仙诗。如《日出入》,据朱乾《乐府正义》记载:“武帝惑于方士之言,入海求仙,希图不死,一时文士,揣摩世主而为之辞。”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观是邪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来下!
《汉志》引晋灼曰:“日月无穷,而人命有终,世长而寿短。”应劭曰:“訾黄一名乘黄,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之而仙。武帝意欲得之,曰:何不来邪?”“乘黄”见于《山海经·海外西经》“白民之国有乘黄,乘之寿二千岁”。后来征伐大宛得汗血马,而作《天马》之歌,其中“天马徕”重复六次,梦想借助这一“龙之媒”来“游阊阖,观玉台”,与以歌功颂德为主的仪式化宗庙祭歌不同,这些游仙诗作体现了浓重的生命意识。
游仙乐舞成为宗庙颂歌和世俗娱乐的固定题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华丽喜庆的视觉印象。古代奏舞必于高台之上,以产生飘飘欲仙、凌云欲飞的舞蹈效果。在甘泉(今陕西淳化)祭至尊神太一的“泰畤”建有“紫坛”,是祭祀乐舞或者说游仙乐舞汇演的场所。《九歌·湘夫人》“荪壁兮紫坛”,《汉郊祀歌·天地八》“爰熙紫坛,思求厥路”,值得注意的是,“紫坛”乐舞表演的主体为“女乐”,《汉书·郊祀志》记载成帝时匡衡上书:“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于古”,而传统祭天地宗庙的“雅舞”一般由“良家子”充任②。《汉书》中多次记载汉武帝游幸甘泉之事。除甘泉紫坛外,武帝时代的建章宫也有仙境设计,《封禅书》记载“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仙龟鱼之属”。张衡《西京赋》对汉建章宫“渐台”的描绘:“渐台立于中央,赫昈昈以弘敞。清渊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与方丈,夹蓬莱而骈罗……美往昔之松乔,要羡门乎天路。”此外,汉代还修建了许多登临望远的“观”,《史记·封禅书》记齐人公孙卿之说“仙人好楼居”,于是在长安作“飞廉桂观”,在甘泉作延寿观。《艺文类聚》卷六十三记载,汉代宫殿名称如长安临仙观、仙人观、平乐观、天梯观、瑶台观等都与仙有关。这种求仙的热情到汉成帝时仍未减弱,桓谭《仙赋》云:“余少时为中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郊,先置华阴集灵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端门南向山署曰望仙门,窃有乐高妙之至,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西京杂记》记成帝“设云帐、云幄、云幕于甘泉紫殿,世谓之三云殿”。赵飞燕曾在其上表演《归风送远之曲》。
《练时日》为《郊祀歌》十九章的首章,为迎神乐章。当神灵来到以后,表演祭神歌舞的童男女的舞姿为“众嫭并,绰奇丽,颜如荼,兆逐靡。被华文,厕雾縠,曳阿锡,佩珠玉。侠嘉夜,芷兰芳,澹容与,献嘉觞”。意思是说,供神女乐面目姣好,衣着华丽,颜色如荼般柔美,穿着轻细如云雾一般的薄纱,伴随着清脆珠玉之音,表演着降神的舞蹈,即《郊祀歌·天地》“千童罗舞”的场面。西汉淮南王雅爱求仙,据张衡《舞赋》云:“昔客有观舞于淮南者,美而赋之曰:美人兴而将舞,乃修容而改袭,服罗縠之杂错,申绸缪以自饰。”《乐府诗集》五十四《舞曲歌辞》中有《拂舞歌辞·淮南王篇》,应劭《风俗通》、崔豹《古今注》均以为淮南王刘安、小山之徒所作,清朱乾《乐府正义》卷五认为“此诗大概是哀淮南王之愚以取祸”③。“拂舞”为汉代杂舞,用于宴飨④,配诗写淮南王求仙,修筑“百尺高楼与天连”,在上面“扬声悲歌音绝天”、“繁舞寄声无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游仙乐舞一直是宫廷舞蹈中的保留节目,如唐代的仙女乐舞最为著名的《霓裳羽衣舞》,相传为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几山而作。在相传为华夏正声的《法曲》基础上,吸收了道乐和佛教乐《婆罗门曲》而成为游仙乐舞的典范⑤。由此可见,原来“以舞降神”的巫术仪式演变为艺术表演形式。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任何宗教仪式都是一种“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s)”[16]。可以说,古人奏舞与其说是出于宗教目的,不如说是娱乐性的演出。由巫祭仪式、降神乐舞发展到富有视觉冲击力的游仙乐舞,都是在尽情展现人类永恒的梦境,同时也赋予游仙艺术以华丽高雅的内涵和形式,标志着游仙文学由娱神到娱人、由巫术宗教功利性到审美性的演变过程。
三、汉代世俗宴乐场合中的游仙诗
汉代游仙文学除体现在郊祀活动中外,更多地应用于世俗宴乐场合。汉代祭祀乐为太乐或太予乐所管辖,而世俗乐章则归乐府。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17]东汉还有黄门鼓吹,《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九月戊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李贤注引《汉官仪》云:“黄门鼓吹有四十五人。”《汉书·艺文志》记有“黄门倡车忠等歌诗”。“黄门”为官署之名,“当时名倡,皆集黄门”。晋崔豹《古今注》云:“汉乐府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唐六典》卷十四云:“后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人。”《通典》卷二五:“汉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属少府。”汉代游仙诗的表演唱往往由“黄门倡”来承担。
在西京长安、东汉洛阳都建有“平乐观”,为作乐之处与观兵之所,皇帝往往驾临。平乐观,亦作“平乐馆”、“平乐苑”,汉高祖时始建,武帝增修于长安上林苑。《汉书·武帝纪》:“(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觝于上林平乐观。”东方朔有《平乐观赋猎》之文。张衡《西京赋》有“大驾幸于平乐”句,薛综注:“平乐馆,大作乐处也。”东汉定都洛阳,汉明帝取长安飞帘(廉)、铜马移洛阳西门外,置平乐观。张衡《东京赋》:“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东汉平乐观同时还是耀兵之所,如《后汉书·孝灵帝纪》:“帝自称无上将军,耀兵于平乐观”等。李尤《平乐观赋》记该观本为观兵耀武之所,而在“万国肃清”的和平年代,又是乐舞百戏的表演场所,其中就有“有仙驾雀,其形蚴虬”这种“扮仙”的节目。当时可能属于“散乐”,郑玄注《周礼·春官·旄人》云:“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唐书·乐志》云:“散乐者,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凑。”可见其来自民间,为倡优表演的一种民间乐舞。“平乐观”中有“总会仙倡”(《西京赋》),“扮仙戏弄”(傅玄《正都赋》),乐府游仙诗很可能是这些娱乐节目中的唱辞。比较典型的如《清调曲·董逃行》,古说为董卓之事,⑥可能是后汉游童所唱的《董逃歌》借用了乐府游仙诗之《董桃行》(《宋书·乐志》),《董桃行》来源于托名班固所作的《汉武帝内传》,又见《宋书·乐志》:“王母觞帝,索桃七枚,以四啗帝,自食其三,因命董双成吹云和之笙侑觞。”歌辞结尾多言“陛下”,如求得“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这种难得的“仙药”后,“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陛下长生老寿”、“陛下长与天相保守”。《相和歌辞·王子乔》中有“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圣朝应太平”以及“圣主享万年”之说,在演唱这些游仙诗时,皇帝可能“在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倡优代言的“套语”,这在歌舞戏中实属常见。说参任半塘对梁武帝所作游仙乐舞《上云乐》的解说[18]。据朱晓海先生研究,乐府游仙诗的演出规模可分为三类:一是编织于百戏之中的一个节目,扮演、特技效果为重,歌舞部分为辅;一则规模较小,以演唱为主,仙人引导,驾鹿遨游,奉药覆命等表演为辅;一为独角演唱,别无布景、道具及其他人物,但会借用手势、移位、改变声口,加强演唱效果,也表现演唱者的技巧,见存游仙诗绝大多数似乎属于后一种⑦。当时贵族之家也普遍使用倡乐,如《相和歌辞·鸡鸣》:“黄金为君门,碧玉轩兰堂。上有双樽酒,坐使邯郸倡。”《盐铁论·散不足》:“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而小坐而责办歌舞俳优,连笑伎戏”;仲长统《昌言》:“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优伎乐,列乎深堂。”这种娱乐形式在两汉时代很普遍。
两汉乐府中的游仙诗作,如《相和歌辞》中有《清调曲·董逃行》、《吟叹曲·王子乔》、《平调曲·长歌行》,《瑟调曲》中有《善哉行》、《陇西行》,《大曲》中有《西门行》,《舞曲歌辞》中有《淮南王》等。此外曹操古题乐府中除《气出倡》、《精列》外,《陌上桑》、《秋胡行》等为借用乐府旧题而作的游仙诗,也“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些游仙诗作拥有大致相同的结构程式,为躲避“来日大难”(这些“大难”包括死、病或人世迫厄)——驾着六龙(或者天马、白鹿等)——游历名山(如昆仑山、太华山、泰山、蓬莱山)——见到仙人王子乔(或西王母、赤松子、安期生等)——仙人给我药(灵芝、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类)一丸或一箱——使我延年寿命长,好比是一首诗作的无限复制。这一情节结构体现着原始崇拜对游仙诗的深刻影响,比较典型的如《平调曲·长歌行》: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紫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下面试对两汉乐府游仙诗的原型进行分析。
首先,游仙诗的“游历名山”意象体现了山川崇拜的原始信仰,比较典型的仙山有昆仑、华山、嵩山和蓬莱。《山海经·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又如《大荒西经》有轩辕台,《北经》有共工台。《吕氏春秋·音初篇》“有娀氏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竹书纪年》说商纣“筑南单之台”,《大雅》中有“灵台”,《史记·孝武本纪》记录汉武帝作“柏梁台”“通天台”“神明台”“渐台”等,这些台的原始功用主要是“享神”、“觞帝”。《楚辞》中的《离骚》、《远游》都有通过昆仑山到达“天门”来见诸神的记载,昆仑山是楚巫陟天的重要凭借。战国以后泰山、蓬莱山、太华山逐渐取代其地位,《白虎通·封禅》中说:“王者易姓而起,必升于泰山何?报告之义也。”《书钞》引《通义》云:“泰山,五岳之长,群神之主,故独封泰山,告太平于天,报群神功也。”相传在泰山封禅者自黄帝以来共七十二家。同时泰山又是鬼丛集之所。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泰山治鬼”条说:“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左氏》、《国语》未有封禅之文,是三代以上无仙论也。《史记》《汉书》未有考鬼之说,是元、成以上无鬼论也。”陈槃《泰山主死亦主生说》引《太山镜铭》云:“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醴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兮直上天,受长命,寿万年,宜官秩,保子孙。”[19]除了泰山之外,崧高山是仙人王子乔成仙“宾帝”之所在。《逸周书·太子晋》:“然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此“太子晋”即王子乔,《列仙传》称其“好吹笙作凤鸣,道士浮丘公接上崧高山。”赤松子与王子乔合称为“松乔”,《列仙传》记其游于昆仑山西王母所。西岳华山据郭璞《华山赞》曰:“华岳灵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浆。”《平调曲·长歌行》:“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紫幢。”蓬莱山作为海上仙境当在战国之世,《史记·封禅书》中说:“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蓬莱仙山实际上是由于海上经常出现的海市蜃楼景观。《史记·封禅书》记秦皇、汉武派人向仙人安期生求药,但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其次,“驾六龙”即乘“蹻”游仙的意象来源于巫师“陟神”的法术。“蹻”是巫师与神仙家赖以“登帝”的媒介,一般以龙、鹿最为普遍。《山海经》中如南方祝融、东方句芒、西方蓐收皆“乘两龙”。1987年曾在河南濮阳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墓中壮年男性周围有三组用蚌壳铺成的龙虎鹿三种图案,张光直认为是原始道教中的龙虎鹿三蹻,“从考古学和美术史的资料来看,仰韶到魏晋这5 000年间一直不断有巫蹻的符号存在”[20]。《抱朴子》内十五:“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有三法,一曰龙蹻,二曰虎蹻,三曰鹿卢蹻。”《相和歌·吟叹曲·王子乔》:“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宋书·乐志》记魏武帝辞《驾六龙》,又名《气出唱》,为汉代旧曲,言驾六龙,东到泰山、蓬莱山,“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至天之门,来赐神之药”。曹植《升天行》:“乘蹻追术士,远之蓬莱山”,等等,可以说“乘蹻”意象是典型的巫术和游仙母题。
再次,乘“蹻”寻仙目的是求讨神药,“求药”、“采药”意象在游仙文学中比较常见,体现了上古以来的药崇拜观念。《山海经》就记载了大量的“不死药”,《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璞注说“群巫上下此山采药也”。郭璞《中山经图赞·帝台浆》:“帝台之水,饮蠲心病。灵府是涤,和神养性。”《海外南经图赞·不死国》:“有人爰处,员丘之上。赤泉驻年,神木养命。禀此遐龄,悠悠无竟。”《海内西经图赞·甘水圣木》:“醴泉睿木,养龄尽性。增气之和,去神之冥。”饮用帝台浆或赤泉、醴泉,食神木或圣木的果实,不仅可以疗病,同时可以涤荡心灵,祛除昏惑冥顽,使人精神和融通畅,逍遥自得,从而达到颐养天性、超凡入圣的境界。在两汉时期,采药成了隐士们的生活来源,同时也是隐士文学的典型意象。《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了几位采药隐士,如台佟采药武安山中,韩康采药终南山,庞德采药鹿门山等。魏晋时代也产生了大量采药诗,如嵇康《游仙诗》云:“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俗累,结友家板桐。”郭璞《游仙诗》:“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登岳采五芝,涉涧将六草。散发荡玄溜,终年不华皓。”
据托名汉刘向的《列仙传》记载神仙73人,具体成仙之途有三:一为用药,自然植物类:如松子、桂芝、菊花、地肤、菖蒲等;矿物质类:饵术、煮石髓(石钟乳)、五石脂等。以这两种方法成仙者如渥绻、涓子、彭祖、文宾等;二是通过养性交接之术成仙者,如容成公、女丸等人;三是以艺术成仙者,如务光好琴、王子乔善吹笙做凤凰鸣、萧史弄玉善吹萧引凤等,这是诸成仙之途中较为高雅的一种。在诸多仙人中,西王母、赤松子、王子乔和安期生最受神仙家的青睐。西王母在民间信仰中信众最多,西汉哀帝建平四年的“行西王母筹”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⑧。王子乔知名度最高,也最投合文人游仙的心理。先师禇斌杰先生曾吟诵唐人高骈的炼丹诗:“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以求仙之苦比喻学问无捷径可走。而《淮南子·齐俗训》则云:“王乔、赤松子,吹呴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守真。”松、乔亦擅长导引之术。晋葛洪《神仙传》卷一记“彭祖”之语:“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太阶;或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彭祖”仙话流传久远,据说活了700岁。彭祖原为古国之名,为“祝融八姓”(《国语·郑语》)之一,在今江苏徐州一带,历夏至周,国祚七百(一说为“八百”)。因为口头传说的模糊性,至迟在战国,演变成了“彭祖寿七百”这样一个长寿的仙翁。《庄子·刻意》云:“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上博简》中有《彭祖》一篇,记载彭祖与耉老两人关于养生的对话,是现存发现年代最早的彭祖书[21]。张家山汉简《引书》云:“春产、夏长、秋收、冬臧(藏),此彭祖之道也。”[22]讲述四季养生之道及用导引术治疗疾病之法等。
乐府游仙诗应属于古代祥瑞文化的一部分,总的基调是喜庆吉祥与悲哀怅惘的二重奏,这和汉代审美风尚有关。《淮南子·氾论训》云:“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根心者也。”悲、丽是对歌、舞的不同审美标准,汉乐主悲,游仙诗作也不例外。《礼记·乐记》云“丝声哀,竹声滥”,《吴越春秋》云“金石之清音,丝竹之凄唳,以之为美”。据王运熙先生说,这种特点的形成与使用乐器分不开,“雅乐乐器主要用金石,故声音庄重;清乐则用丝竹”[23]。实际上汉代无论雅俗,皆用丝竹,编钟一般只有两件,不能演奏旋律,在乐队中起和声作用[24]。“相和歌”为“丝竹相和,执节者歌”,萧涤非认为《相和歌》中的平、清、瑟三调皆用筝,《风俗通》说:“筝,秦声也。”认为汉之相和三调与秦声有密切关系[25]。刘熙《释名·释乐器》云:“筝施弦高急,筝筝然也。”在汉代为独奏乐器,如《陌上桑》,据崔豹《古今注》记载,原本为筝曲,曹操借用此古题来写游仙诗。据侯瑾《筝赋》,无论是在清商乐,还是雅曲、郑卫之声中都可鼓筝。《宋书·乐志》记有《汉旧筝笛录》,除独奏外,也是相和歌的主要伴奏乐器。另如“箫”为悲音,亦用于丧乐,《汉书·周勃传》记其先时“常以吹箫给丧事”,师古注:“吹箫以乐丧宾,若乐人也。”王褒《洞箫赋》云“故知音者乐而悲之”。《瑟调曲》使用“瑟”这种弹弦乐器,《风俗通义》引用《黄帝书》“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可见瑟也属于“悲音”,与乐器特点相符合,内容亦有悲的成分。《相和歌·平调曲》“长歌行”中记“仙人骑白鹿”送给主人神药一箱,使其“延年寿命长”,但结尾“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魏武帝《气出倡》、《吟叹曲·王子乔》古辞性质与此相同。这些以悲为主的音乐、诗篇反映游仙之事,应属于《乐记》中所说“声哀而不庄”之类,《文心雕龙·乐府》说“魏之三祖”乐府“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评价非常准确。
四、汉代游仙诗艺的价值意义及其影响
汉代游仙诗展示了求仙的两个途径:一种是希望通过献祭供养神灵而获取神的赐予,得到仙药来成仙;另一种是在乐舞之类的世俗娱乐中直接向神灵求药,带有很强的民间色彩。游仙歌诗成了宴会上的一种吉祥语,仪式性、在场性、表演性、娱乐性是上述两种形态的主要特征。而对魏晋文人游仙诗产生直接影响的作品则是《楚辞·远游》,被称为“游仙诗之祖”,其游仙途径是在早期黄老道和战国方仙道的影响下,力图通过自己修炼而成仙。相传秦始皇曾令博士作《仙真人诗》,已佚失,所以也谈不上影响。相对来说,两汉游仙文学在整个游仙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楚辞·远游》到魏晋文人游仙诗之间,经过两汉将近400年的时间,游仙文学的传统一方面经过太乐、乐府中的表演唱而得到很好的延续,同时通过文人的赋、诵、歌、赞以及民间信仰层面的传说而得到发展。学界往往对两汉时代的游仙文学不够重视。
《楚辞·远游》从一开始就给游仙诗创作定下了悲凉的调子,“悲世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关于其作者和时代,学术界存在着很大争议。刘永济认为:“《远游》篇中所具之思想,已非纯粹道家,而与秦汉方士飞升之意同。”[26]诗篇杂引王乔、赤松及秦始皇时方士韩众。游国恩先生《楚辞概论》认为非屈原所作,出自西汉人伪托[27]。《远游》诗句与屈原《离骚》、司马相如《大人赋》有许多相同之处,胡小石《远游疏证》云:“廖平尝有《远游》篇与司马相如《大人赋》如出一手、大同小异之说,今细校此篇,十之四五皆合《离骚》文句而成,其余或采之《九歌》、《天问》、《九章》、《大人赋》、《七谏》、《哀时命》、《山海经》及老、庄、淮南之书。又其辞旨恢诡,多涉神仙,疑伪托于汉武之世。”[28]而在《远游》之后,代表游仙诗创作高峰的则是魏晋文人的作品。《文选》中“游仙”类只收录了西晋何劭(敬宗)、郭璞的七首游仙诗,而《艺文类聚》卷七十八“仙道”类收录游仙诗比较广泛,从三国魏到南陈22家作品,有曹丕、曹植、何劭、张华、成公绥、郭璞、庾信、阴铿诸人之作,此外还收录了赋、颂、赞、碑、铭、书、论等关于游仙题材的作品,保存了许多神仙家的“仙话”。这些“仙话”分别来自《史记·封禅书》、《晋中兴书》、《庄子》、《淮南子》、《列仙传》、《汉武内传》、《汉武故事》、《搜神记》、《神异经》、《十洲记》、《风俗通》、《异苑》等书,体现了战国秦汉以来的民间信仰,多为游仙诗人所取材,可以作为仙家的“本事诗”来读。从《楚辞·远游》到郭璞的文人作品通常赋予传统游仙诗体以更为深刻、更为现实的内涵,突出表现在“远游”意象的发明与使用上,给文人游仙诗作涂抹了一层悲壮色彩。曹植《游仙》《五游》《升天行》《仙人》为极意模仿《远游》之作,“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五游》)即来源于“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阮籍《咏怀》“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于是准备“远游崑岳旁”。这些文人的“白日梦”,一方面以传统游仙题材作为创作的内在动因,远古巫觋思维与神仙家言以及郊祀仪式成为“诗的宗教”;另一方面有感于世路迫厄,故寄慨周天,将世路险嚱与仙界自由、人生短促与仙界永恒相对照,滓秽尘网,锱铢缨绂,正如钟嵘《诗品》评价郭璞的诗,与其说“列仙之趣”,不如说“坎壈咏怀”。这些文人游仙诗具有更深沉的内涵,与仪式表演没有太大关系,怀千年之往事,发思古之幽情。与咏史、怀古一样,成为自抒怀抱、别有寄托之作。
(二)游仙诗突出地体现了古典浪漫主义的生命本质,在游仙的“白日梦”中掩藏着生命无解的悲哀,哀叹时光流逝和生命短暂是游仙诗的常见主题。
游仙图在楚帛画《人物御龙图》及《人物龙凤图》中体现为灵魂升天的情景,而在两汉墓葬石刻画像中体现得最多,题材难免千篇一律。“仙人”诸如西王母、东王公、王子乔、赤松子等“出场”次数最多。但仙人能否在生命的此岸中“修”到?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更多的是“人生如朝露”、“奄若风吹烛”的感叹。《后汉书·五行志》注云:“《风俗通》曰: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傀)儡”为丧家之戏。同书《周举传》记顺帝阳嘉六年三月上巳日,权贵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之上,“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薤露》为丧家之乐,诗词云:“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还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晋陶潜《搜神后记》卷一(又见《艺文类聚》卷七十六“仙道”)中记载“丁令威”故事:“辽东城门有华表柱,忽有一白鹤集柱头。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庾信《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道士封君达,仙人丁令威。煮丹于此地,居然未肯归。”学仙成了破解人生困局的不二法门。《古诗·驱车上东门》所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即便如此,学仙的热情在中古时代仍旧高烧不退,曹丕《折杨柳行》(见《宋书·乐志》),为魏晋乐所奏,其诗“三解”云:“彭祖寿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李善注郭璞《游仙诗》“虽欲腾丹谿,云螭非我驾”,引曹丕《典论》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然而惑者,望乘风云,冀与螭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谿。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逝者莫反,潜者莫形,足以觉也。”正是因为了解了生命的本质,从而对神仙之道充满了怀疑。曹植的《飞龙篇》、《升天行》、《五游咏》、《远游篇》、《仙人篇》、《驱车篇》、《平陵东》、《桂之树行》、《苦思篇》等,将游仙诗作写得很华丽,开辟了魏晋文人游仙诗的传统。
(三)游仙诗提供了观察社会人生的一个重要视角,为隐士文学解决仕隐、出处、进退问题提供了很高尚的精神“出口”,进而从天空观察大地,从无限审视有限,由自然关注社会,神性成了丈量人生的尺度。
两汉乐府诗的习惯模式是“飞升”以后向神仙讨取仙药,使“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满足人们好生恶死的本能需要。相比之下,魏晋游仙诗人要达观得多,境界也显得广阔。在诗人的想象中,当飞升、远游后,随之而来的是视角的转换,空间的感觉消失了,而仙界的时间也如同静止了一般。如郭璞的《游仙诗》“四渎流如泪,五岳罗若垤”,晋庾阐《游仙诗》“三山罗如粟,巨壑不容刀”,梁简文帝《仙客诗》“高翔五岳小,低望九河微”,李贺《梦天》“遥看齐州九点烟,一杯海水空中洒”,等等。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记载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见仙女,在山中住了半年,回家后,人间已历六世。这个故事流传非常久远,唐人李商隐、曹唐等人都应用过这一典故,词牌中有《阮郎归》、《宴桃源》、《醉桃源》、《碧桃春》,等等。在仙家看来,衰老是因为时间的流逝造成的,而时空观的改变则使人们超越了有限的束缚而达到无限,这一视角的转换体现了游仙诗人追求精神自由的情怀。
(四)仙人生活情趣是文人隐士的赋予,同时也成了自由人生的范式。
游仙诗不乏对仙界与仙人的想象,如《相和歌辞·瑟调曲·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玉台》“伏趺”作“道隅”);《艳歌》描写天上诸仙的宴会,想象力极为丰富:“今日乐上乐,相从步云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葛洪《抱朴子·对俗》写仙人生活,“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如何超越老、病、死的宿命和充满忧患的社会,游仙诗刻意营造的仙界是对精神疲惫的抚慰,是对心灵的净化。《抱朴子·论仙》云:“若夫仙人,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仙经》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29],通过“熊经鸟申”之类的导引之术锻炼身体,预防疾病。司马承祯《天隐子·神仙》云:“人生时禀得灵气,精明通悟,学无滞塞,则谓之神;宅神于内,遗照于外,自然异于俗人,则谓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于修我灵气,勿为世俗所论折;遂我自然,勿为邪见所凝滞,则成功矣。”神仙家表述修炼之道有时虽过于玄虚,对于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来说,自有其积极意义在。而尤其重要的是,游仙诗使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如此贴近生命的主题,从而成为精神自由的象征和对存在有限性的超越。
注 释: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1页。
②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卢植《礼注》:“汉大乐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取适(嫡)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三十、颜色和、身体修冶者以为舞人。”
③ [清]朱乾《乐府正义》卷五,乾隆五十四年刊秬香堂藏版。浙江省图书馆藏。
④ 《乐府诗集》卷五十二云:“自汉以后,乐舞寝盛,有雅舞,有杂舞。雅舞用之郊庙、朝飨,杂舞用之宴会。”“杂舞”包括《公莫》、《巴渝》、《槃舞》、《鼙舞》、《拂舞》、《白纻》之类是也。
⑤ 据《杨太真外传》引刘梦得诗:“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驿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舞》。”而据《唐会要》卷三十三记载,天宝十三载改诸调名,改《婆罗门曲》为《霓裳羽衣曲》。王灼《碧鸡漫志》引唐郑嵎《津阳门诗注》,说是道士叶法善引明皇游月宫,听到仙乐,用笛子记下了半段,恰西凉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于是将其作后半,而制成《霓裳羽衣曲》。白居易《新乐府·法曲》云“法曲法曲舞霓裳”、“乃知法曲本华风”,认为《法曲》为华夏正声。《法曲》源于东晋、南梁佛教“法乐”,其音清而近雅,相延至唐,《霓裳羽衣曲》是在《法曲》之上吸收道教乐和佛教乐《婆罗门曲》而创作的。白居易《霓裳羽衣歌》云“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全唐诗》收集了王建、刘言史、鲍溶、张祜、杜牧、李商隐、薛能、温庭筠、曹唐等人咏霓裳舞的诗,可见自天宝以来,该舞一直为宫中的保留节目。
⑥ 晋崔豹《古今注》曰:“《董逃歌》,后汉游童所作也。终有董卓之乱,卒以逃亡,后人喜之为歌章,乐府奏之以为儆戒焉。”《后汉书·五行传》曰:“按董谓董卓也,言虽拔扈,终归逃窜,至于灭族也。”《风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禁绝之。”杨孚《董卓传》曰:“卓改‘董逃’为董安。”《诗纪》云:“一作灵帝中平中《京都歌》。”见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汉诗”卷八。
⑦ 朱晓海《魏晋游仙、咏史、玄言诗探源》,载赵敏俐、佐藤利行主编《中国中古文学研究——汉唐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⑧ 《汉书·哀帝纪》云:“(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汉书·五行志》云:“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汉书·天文志》亦有记载。
[1] 曹道衡.郭璞和游仙诗[J].社会科学战线,1983(1).
[2] 吴贤哲.汉代神学思潮与汉乐府郊庙、游仙诗[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6);张宏.汉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J].北京大学学报,1996(4);张树国.论巫文化对游仙文学艺术结构生成的影响[J].广州大学学报,2004(9).
[3] 石兴邦.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M]//中国原始文化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4] 彭林.四羊方尊与长江流域的商代文明[M]//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07.
[5] 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J].中华文史论丛,1978(2).
[6]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69.
[7] 余英时.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M]//燕园论学集——汤用彤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84.
[8]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M]//商周青铜器纹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0.
[9] 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M].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70.
[10]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338.
[11]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M]//观堂集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4:409.
[12] 胡厚宣.甲骨文中的四方和四方风名[J].复旦学报,1956(1).
[13] 谭其骧.《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提要[M]//山海经新探.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4] 昂利·于贝尔,马赛尔·莫斯.献祭的性质与功能[M].杨渝东,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173.
[15] [清]陈本礼.汉诗统笺(又名《汉乐府三歌笺注》)[M].嘉庆庚午(十五年,1810):裛露轩藏版.浙江省图书馆藏.
[16]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83.
[17]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M]//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1422.
[18] 任半塘.唐戏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9.
[19] 陈槃.泰山主死亦主生说[M]//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1867.
[20] 张光直.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M]//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96.
[21]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2] 张家山汉墓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71.
[23] 王运熙.清乐考略[M]//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72.
[24] 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53.
[25]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0.
[26] 刘永济.屈赋通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225.
[27] 游国恩.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8:147.
[28] 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93.
[29]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彚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1.
“网络与人文研究”征稿启事
本栏目选题范围包括网络与哲学政治问题、网络与社会经济问题、网络与道德法律问题、网络与语言文学问题等,要求论题新颖独到,理论性强,论述透辟,避免通篇一般叙述。来稿字数请控制在8000字以内,行文格式符合《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排规范,请打印并附寄磁盘文件(或发送电子邮件,E-mail:zhchao053@163.com)。
本刊编辑部
I207.22
A
1007-8444(2010)02-0225-11
2009-10-20
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ZW021);200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6JA75011-44024)。
张树国(1965-),男,辽宁阜新人,文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刘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