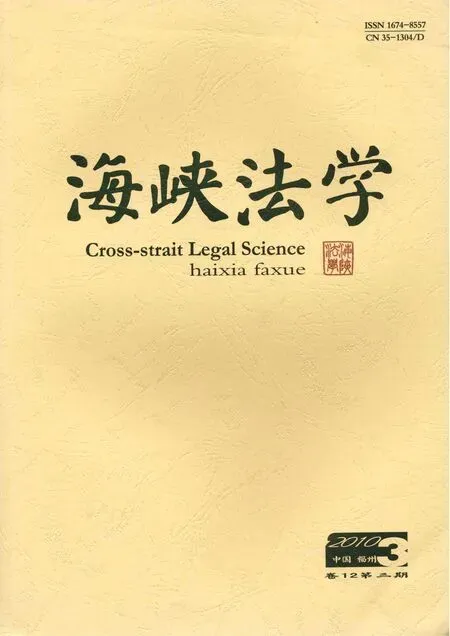论“商法公法化”之逻辑思辨
2010-04-10艾围利
艾围利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论“商法公法化”之逻辑思辨
艾围利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商法公法化”这一命题存在以下逻辑错误:第一,将“公法”概念偷换为“强制性法律规范”或“严格责任”等;第二,商法属于私法是定性分析,但论证“商法公法化”又改采定量分析;第三,部门法划分方法不周延导致商法与经济法界限不清。“商法公法化”所反应的真实本质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只是国家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并不都体现为公法,涉私强制性法律规范亦体现为国家对商事关系的干涉但属于私法。国家对商事关系的干预主要体现为涉私强制性规范,商法公法化趋势并不明显,无法获得证实。
公法;私法;商法公法化;涉私强制性规范
随着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结合,不少学者认为现今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倾向,并进行了大量的论证。而“私法公法化”又以“商法公法化”为主要表现形式,但是这一命题在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则少有人论及,本文试图从逻辑上对“商法公法化”这一命题进行一番探讨,以期厘清“商法公法化”之真正面目。
一、“商法公法化”——事实还是判断?
部分学者认为“商法公法化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客观事实”。[1]但多数学者将“商法公法化”作为了一个被证明的对象,并提出了各种证据予以证明。这实际上是将“商法公法化”作为一个待证明的命题来看待的,本人也持这种观点,“商法公法化”只是学者的一种判断而非事实,否则就无需进行论证了。
当前比较通行观点认为,所谓“商法公法化”,是指商法“虽以私法规定为中心,但为保障其私法规定之实现,颇多属于公法性质的条款,几与行政法、刑法等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却已形成‘商事法之公法化’”或者是指在商法领域“公法规范注入私法领域的现象”。[2]为了论证“商法公法化”学者提出了以下论据予以论证:商法价值理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商事立法中强制性规范的增多、商行为后果承担上的严格责任主义以及现代商法在传统私法责任制度外发展出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法律调整机制。[3]这些论点的内涵是否准确?论据是否足以支撑论点?本人将在下文中予以论证。
二、“商法公法化”之逻辑前提
(一)逻辑前提之一: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商法公法化”的逻辑前提之一就是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如果没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则无所谓“商法公法化”了。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在《学说汇纂》中最早对公法、私法给出了定义: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罗马国家的稳定”;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并且乌尔比安随着定义举例说:“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4]现代学者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主要有四种学说:(1)利益说:以公益为目的者为公法;以私益为目的者为私法。(2)从属规范说:规范上下隶属关系者为公法;规范平等关系者为私法。(3)主体说: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或双方为国家机关者,为公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均为私人者,为私法。(4)特别规范说(新主体说):国家或机关以公权力主体地位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者,该适用的法律为公法;该法律对任何人皆可适用者,则为私法。[5]这四种划分标准各有所长,台湾地区学者越来越重视第四种学说,而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也是第四种学说。新主体说实际上是一种综合评价标准,能扬长避短,因此,本文采第四种划分标准,即根据法律关系的主体及身份来区分,适用于国家或机构以公权力载体身份参加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为公法,适用于任何人皆可参加的法律关系(包括国家或机关以非公权载体身份参加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为私法。
需要探讨的是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否等同于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划分,换言之,是否公法即为强制性规范,私法即为任意性规范。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不得通过当事人的约定排除该项规范适用的法律规范;[6]也有学者认为强制性规范是法律规定行为人应当为或者不能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7]而所谓任意性规范,是指适用与否由当事人自行选择的规范;[8]有学者亦认为任意性规范是指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做出约定而无需遵守的规范。[9]由此可见,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同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划分标准并不相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及其身份,而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划分标准为法律关系主体选择适用该法律规范之自由度,两者相去甚远。正是基于此才有涉私强制性规范与涉公强制性规范的划分,[10]也就是说虽然公法以强制性规范为主,私法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但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私法上也存在强制性规范。不过一般认为强制性规范体现了国家的干预,而公法亦调整作为公权载体之国家机关参加的法律关系,因此,如何区分涉私强制性规范与公法规范显得尤其重要。强制性规范中国家机关的干预,指的是立法机关对该强制性规范之适用主体在选择适用该强制性规范的自由度上的干预,一般要求该强制性规范调整之法律关系主体必须适用或不得适用该强制性规范,但立法机关本身并不是该强制性规范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而在公法规范所适用的法律关系中国家机关本身即为该法律关系主体。根据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两者虽均涉及国家机关,但涉私强制性规范所涉及国家机关并非该涉私强制性规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因此涉私强制性规范为私法而非公法。商法上绝大多数强制性规范皆为涉私强制性规范,属私法而非公法。有学者甚至认为商法上的“强制主义”或许称“条件主义”更贴切,[11]如公司类型法定、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公司合并、分立时所需之股东会决议等往往只是商事主体行为之条件要求,法律关系主体仍为私法主体,而非作为公权载体之国家机关。由此看来,以商法上强制性规范增多作为论据来论证“商法公法化”趋势是不合论证逻辑的。
另外需要研究的是严格责任是否属于公法规范。严格来说严格责任属于英美法上的概念,它相当于大陆法上的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但以严格责任证明“商法公法化”的学者认为,严格责任包括无过错责任和连带责任,其理论出处则语焉不详。无过错责任是指在责任的追究上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的归责方式。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存在连带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债务人在债务完全清偿之前,都负有完全清偿义务的责任承担方式。无过错责任和连带责任较之过错责任和独立个人责任来说确实要严格一些,但却无法和公法规范划上等号。我国法理学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分为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12]法律责任属于法律后果,是违反法律规定或违约后产生的消极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而法律责任的归责,是指国家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根据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判断、认定、归结和执行法律责任的活动。由此可见,法律责任在本质上体现了国家强制力是法律得以实施的保障。任何法律责任,不只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是如此也相同,其最终归结均需国家暴力机关的保障,“法律的实施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那么法律在许多方面变得毫无意义,违反法律的行为得不到惩罚,法律所体现的意志也得不到贯彻和保障”,[13]因此,法律责任本身不是判断公私法的基准。而公私法以行为主体及其身份作为划分标准则正说明了,某条法律规范到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其判断基准是该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部分,而非法律后果部分。概言之,法律责任对行为模式具有依附性,是违反第一性义务之后的纠正性措施,法律责任的公私法属性亦依附于行为模式,因此,法律规范的公私法属性应该以其行为模式部分为判断基准。而刑事赔偿责任的出现更是对以上论述的佐证,赔偿责任也可以成为刑事责任的一种。[14]这样看来,将严格责任的出现视为商法上公法规范的增多也是不合适的。
(二)逻辑前提之二:商法属于私法
“商法公法化”的另外一个逻辑前提是商法属于私法,若商法本身即为公法,则无所谓“商法公法化”了。商法属于私法,这似乎已成为了法学界的公理,但对于这一公理仍有必要弄清其真面目。首先,部门法的划分标准与公私法的划分标准是否一致,商法是否为私法内部的进一步划分。学界通行的做法是以调整对象为基本标准,以调整方法为辅助标准来划分部门法,显然这一标准和公私法划分标准并不一致,部门法划分采取以法律关系客体为主兼顾其他的综合性标准,而公私法划分采取以法律关系主体为主兼顾其他的综合性标准。以民法为例,一般认为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从语义结构可以看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中的中心词为“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为定语修饰词。由此可见,民法这一部门法是以调整对象——“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主要标准兼顾其他标准而从整个法律体系中划分出来的,“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是辅助性标准。而民法属于私法则正好相反,基于“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这一体现主体及身份关系的标准来划分。实际上,商法并非是在私法内部进行进一步划分的结果。从部门法理论历史发展的路径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从渊源上看,部门法理论源于苏联,该理论的引入是我国在建国初期全盘照搬前苏联法学理论结果之一”,“并逐步将其演化为法学理论研究中一个占据基础性地位的研究范式”,[15]而在苏联是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的。依据该理论,部门法的划分是在废除公私法划分的基础上对整个法律体系进行的重新划分,这就可能导致商法并非完全包括于私法中,而是横跨公私法。而对商事立法进行历史实证研究就会发现的确如此,《法国商法典》、《德国商法典》、《日本商法典》等均包含大量的公法规范。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商法不是对私法的进一步划分,商法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横跨公私法的,商法中包含了大量的公法规范。而之所以说商法属于私法,是因为部门法的划分和公私法的划分得到了某种暗合,使得商法主要由私法规范组成。根据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原理,主要部分为私法规范的商法在性质上被定性为私法。综上所述,从哲学上定性分析,包含了大量公法规范的商法属于私法,但以商法上存在公法规范来论述“商法公法化”趋势也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某些公法规范是商法立法之初就存在的,并非后来才出现的。
三、“商法公法化”之逻辑分析
(一)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
学者在论述“商法公法化”这一命题时,较多采取以下几方面论据:商法中公法规范的增加;商法中强制性规范的增加;商法中严格责任适用的增加。
由此可见学者们在论述“商法公法化”时采取的是定量分析的方法,即商法中公法因素的增加。换言之,“商法公法化”不是一种定性的分析,“商法公法化”所要论述的不是商法中公法规范从无到有,或者商法已经属于公法。但是对“商法公法化”现象采取定量分析方法本身存在逻辑缺陷。
一方面,商法属于私法采取的是哲学上的定性分析得出,而在论证“商法公法化”时又改为定量分析,前后标准不一。如此一来则在思维上产生混乱,造成“商法公法化”趋势的错觉,整个思维过程如下:商法(主体私法规范+部分公法规范)通过定性分析变成为商法(私法规范),定性分析之后的商法(私法规范)通过定量分析变成为(主体私法规范+部分公法规范)。实则前后的商法并无变化仍然是主体为私法规范,包含部分公法规范,但却造成了商法由不包含公法规范到商法上出现公法规范的错觉,由此产生“商法公法化”的论断。
另一方面,既然“商法公法化”采取的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则数据的统计应该是必须的,只有前后数据的比较才能得出公法规范增加的结论,但学者们至今似乎并无一人进行过系统的数据统计。不进行系统数据统计的另外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可能公法规范数量增加的同时整个商法规范的数量也在增加,而且整个商法规范数量的增幅可能高于公法规范数量的增幅,由此一来商法中的公法规范数量虽然增加了,但公法规范在商法上的地位可能反而弱化了。然而与认为存在“商法公法化”学者愿望背道而驰的是,商法中所谓的公法规范数量反而有减少的趋势,“公司设立从许可主义、严格准则主义改为准则主义,商人登记从设权效力改为宣誓效力,法定资本制改为授权资本制,一人公司的承认、最低注册资本要求的缓和等等,无一不是在强化商事主体的营业自由。”[16]
同时对商法进行定量分析还必须选择好基准点,即前后的比较点,而其中以形式意义的商法规范还是实质意义的商法规范作为基准点尤其重要。形式意义的商法是以商法为名称制定的法典;实质意义商法则是从规范总和上把握的法律制度。[17]实质意义的商法是形式意义商法加上其他单行法、部门法中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但是经过简单的逻辑分析就会发现,“实质意义的商法”提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实质意义的商法一方面把其他单行法或部门法中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划归商法的范畴,但同时又未将形式意义的商法中属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规范剔除出去,由此一来形式意义商法中属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规范在形式意义上为商法规范,在实质意义上又成为其他部门法规范。以形式意义商法中的行政法规为例,一方面在形式部门法上,其属于形式意义的商法规范,但另一方面实质部门法上,其又属于行政法律规范。但若将实质意义的商法理解为剔除了形式意义的商法中其他部门法规范之商法与其他部门法中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则根本不会存在“商法公法化”的论断,因为即便商法上出现再多的公法规范其仍不属于商法,不存在“商法公法化”的问题。因此,在探讨“商法公法化”的基准点时,只能以形式意义的商法为准。若然如此,则独立于商法之外的与商法有密切联系的单行公法规范不得作为论证“商法公法化”的论据,据此作为论证“商法公法化”最得力证据但以单行行政法规形式出现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商事登记法规不得用于论证“商法公法化”。
综上所述,对商法进行定量分析方法本身存在诸多逻辑错误,由此导致“商法公法化”的论断只是体现了人们的感官反应,并未揭示事物的本质。
(二)“公法化商法”还是“公法性经济法”?
在探讨“商法公法化”时还必须弄清楚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因为两者虽然都调整经济关系,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公私有别。商法调整商事关系,即商人之间或与商人在商业上所为之法律行为而在他们相互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属于私法范畴。经济法调整国家在协调本国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属于公法范畴。但人类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本身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并无绝对的分界线,只是法学界在划分商法和经济法这两大部门法时,根据各自的调整范围人为的将经济关系割裂开来。这就导致部分经济关系到底由经济法调整还是由商法调整产生分歧。以证券、保险监管为例,初学法律者会发现在商法课程中会涉及证券、保险监管,在经济法课程中也会涉及证券、保险监管。从我国当前的法律体制来看,证券、保险监管体现的是国家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督、规制,从部门法划分上看明显应该属于经济法的范畴,但如上所言,经济活动本身的一体性导致商法将与其调整的经济关系有密切联系却原本不属于其调整的某些经济关系也概括进行了规范。商事登记制度也是如此,其体现的是国家工商登记机关的市场调控,具体表现在企业设立登记之市场准入和工商登记机关年检制度上。因此在论述“商法公法化”时,必须区分到底是商法上应有的公法规范还是由于人为的误解将部分经济法不当划归商法而形成的公法规范,即区分“公法化商法”和“公法性经济法”。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商法上用来证明“商法公法化”的部分公法规范,实际上属于经济法,只是由于部门法划分标准的模糊性或者说由于在部门法划分上没有彻底的遵循划分标准,导致错误的将部分原本属于经济法的内容划归商法。毋庸置疑,我们不应该以错误划归商法的经济法规范用来证明“商法公法化”。
四、“商法公法化”之逻辑缺陷及其修正
(一)“商法公法化”之逻辑缺陷总结
通过以上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商法公法化”这一命题存在以下逻辑缺陷:
1.偷换概念。将“公法”概念偷换成“强制性法律规范”或“严格责任”。因此以商法上“强制性法律规范”或“严格责任”增多来论证所谓“商法公法化”。
2.标准混乱。对同一事物采取不同划分标准来分别论述,在商法为私法上采定性分析,在“商法公法化”上改采定量分析。在实质意义的商法界定中,将其他部门法中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纳入商法范畴,但却不将商法上属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规范剔除。
3.外延不周延。商法和经济法调整范围界定不清,外延上重合,将本应属于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当做商法看待。
(二)“商法公法化”之本质——商法规范与“国家”或“国家机关”关系研究
将商法上用于证明“商法公法化”的强制性法律规范、严格责任、本应属于经济法而错划归商法的商事登记制度和证券、保险监管等排除出“商法上公法规范”的范围之后,用于证明商法公法化的证据就只剩下商法价值理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以及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增加。而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不光是商法的价值取向,民法亦同,因此,不足以证明商法公法化。唯一证据就只剩下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增加,但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真的有在增加吗?仅以我国 2005年修改之前和修改之后的《公司法》做比较可以发现,旧公司法涉及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条款包括第206条——214条、216条——228条,共计 22条,而新公司法涉及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条款包括第199条——216条,共计18条;而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条文数在旧公司法和新公司法条文数中所占比例分别为9.61%和8.29%。数据显示,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条款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在公司法中的比例均呈现下降的趋势。
通过对“商法公法化”进行逻辑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商法公法化”只是一个虚构的景象,但透过这一虚构的景象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商法公法化”所要反应的真实本质,即国家公权力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只是国家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并不都体现为公法,在此我们可以将商事法律规范与国家或国家机关的关系进行总结。
1.商法上的任意性规范。虽然作为“法”的组成部分,商法上的任意性规范“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意志,从形式上说是国家意志”,但在具体的法律适用层面任意性规范并不体现国家的干预。相反,商法上的任意性规范反应了商事主体的经营自由或营业自由,反应了商法是私法的属性,因此是商法的主要组成部分。
2.商法上的公法规范。这种商法规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一方为商事主体,另一方为国家机关,体现的是国家直接参与商事法律关系,对私人商事关系进行干预,主要是指行政责任规范和刑事责任规范。
3.商法上体现国家干预私人商事关系的非公法规范。这种商法规范体现了国家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但国家或国家机关并非该商法规范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不属于公法规范。这类商法规范主要包括两种:
(1)涉私强制性规范,即法律关系主体仅包括私人的强制性商法规范。这类商法规范主要体现了国家立法机关对适用该商法规范的商事主体在选择适用该商法规范的自由度上的干预。在立法之时就已事先设定好,该商法规范调整之法律关系主体必需选择适用该商法规范或者不得选择适用该规范,否则法律行为无效。
(2)连带责任和严格责任。这类商法规范是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技术来对本该由私人自由决定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干预,其实际上是加重了责任人承担责任的难度或削弱了责任人证明其无需承担责任的证明难度,对相对人给予更好的保护。
如果将国家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那么商法上的公法规范反应了国家的直接干预,而商法上涉私强制性规范和连带责任、严格责任则体现了国家的间接干预。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私人商事关系的干预应该尽量选择后者。
[1] 杨少南.从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角度看商法的公法化[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13.
[2] 张国键.商事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0:20.
[3] 于海梅.浅析商法的公法化趋向[J].潍坊学院学报,2008(3):114-115.
[4]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9.
[5] 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2-14.
[6] 王轶.民法典的规范配置——以对我国合同法规范配置的反思为中心[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79.
[7] 李龙.法理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3.
[8] 沈宗灵,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38.
[9] 王建平.民法法典化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60.
[10] 裘实.强制性规范的界定与民事行为效力的判定[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5):45.
[11] 樊涛,王延川.商法总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88.
[12]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71.
[13] 公丕祥.法理学[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8.
[14] 刘东根.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功能的融合[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9(6):34.
[15] 张璐.部门法研究范式对环境法的误读[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3):23.
[16] 杨少南.从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角度看商法的公法化[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17.
[17] 王保树.商法总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3-14.
D913.99
A
1674-8557(2010)03-0080-07
2010-05-25
艾围利(1981-),男,湖北天门人,武汉大学法学院2009级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王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