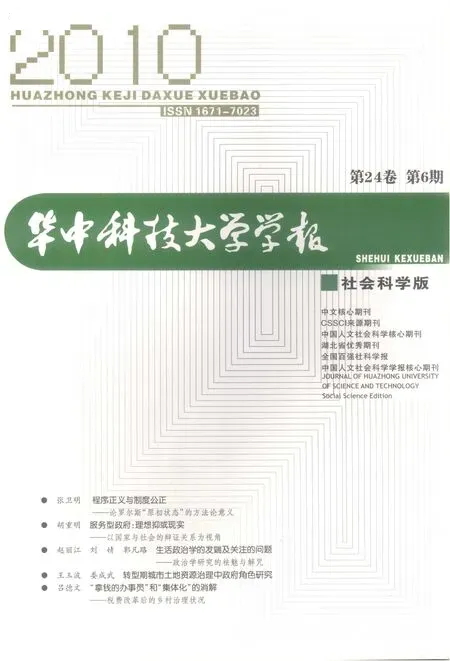是单向塑造还是双向规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诠释合法形态探究
2010-04-08肖士英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肖士英,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是单向塑造还是双向规约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诠释合法形态探究
肖士英,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大众关于人类解放实践的感性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该实践的理性认识,构成了关于该实践内在关联的“双重解释”:前者孕生、支撑后者,后者基于向前者学习而生成,又通过教化等途径向前者渗透,批判地塑造、提升前者,从而共同为大众解放实践提供精神支援系统。这双重解释间如此相向规约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完整内涵,是由“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塑造”这样的双维取向前后衔接、循环互动所构成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双重解释;单向教化;双向规约
一、问题的提出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43可见,对“历史过程”和“思想进程”而言,前者对后者具有基础地位,后者则反映并统一于前者。不过,前者对后者的基础地位并不具有先验性;后者对前者的统一性也并不能直接实现,而都只能经由群众创造和认识历史的活动间接地获得和完成。毕竟,“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031,851。“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103所以,前者的主体主要是群众,后者的主体则既包括理论精英,也包括群众。只不过群众主要通过感性认识,理论精英主要通过理性认识来构成后者。可见,群众既是前者、也是后者的主体,群众通过实践和认识既在塑造、也在诠释着前者。理论精英的使命则主要在于通过诠释前者来构成后者。群众对前者的诠释,无疑是理论精英关于前者诠释的基础,构成了理论精英关于前者诠释的“前见”。当然,理论精英关于前者的诠释反过来也规导着群众关于前者的诠释。这样,大众和理论精英各自关于前者的诠释,就构成了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的“双重诠释”[3]35。它们相互间既具有独立性,又以大众的“诠释”孕生理论精英的“诠释”为原始起点、以后者反过来规导前者为回馈形态,展开无限深化的循环互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下文或简称“大众化”)而言,它尽管只能生成和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的相互关系之中,但“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塑造和诠释历史过程的姿态而具体、历史地存在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只能生成和存在于这二者塑造和诠释历史过程的互动关系之中,其内涵也只能生成于由这二者所构成的“双重诠释”相向规约过程中。
然而,学界迄今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诠释,约束大众关于该过程的诠释这样的单向视角、并未着眼于“双重诠释”相向规约这样的综合视角来解读“大众化”内涵,从而使得“大众化”仅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单向塑造大众的过程,其结果使得关于该概念内涵的理解走向片面化、庸俗化。学界对该概念内涵的这种解读,具体表现为如下观点。第一,传播教化论:宣教马克思主义,使其“被广大群众掌握”[4]。该观点合理性在于着眼于理论精英对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化,来理解“大众化”内涵,其局限性在于未能着眼于大众孕生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二,结合、适应群众实践需要论:“指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以“形成适应”大众需要的马克思主义[5]。该观点把“大众化”理解成理论精英通过使马克思主义“适应大众需要”而塑造大众的单向过程,忽视了着眼于大众能动塑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三,规导大众精神世界论:使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世界观紧密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大众精神世界的坐标和实践的指南”[6]。该观点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精神世界的过程来揭示“大众化”,未着眼于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四,升华大众经验论:“用大众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的新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7]该观点着眼于用马克思主义“升华”“大众实践经验”来理解“大众化”,忽视了大众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固有能动孕育和塑造功能。
上述观点都把“大众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的单向塑造过程,由于单向塑造的本质就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由一般理论转换成大众内在精神力量,所以,单向塑造确实是构成“大众化”的必要内涵。不过,既有研究忽视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历史和逻辑在先地位,始终也在历史地约束着马克思主义,从而“马克思主义”对“大众”的约束并不能离开大众对它的约束独立存在这一事实,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解具有如下缺陷。其一,既把其主体构成简单化了,也使其主体地位陷于错位。“大众化”发生于“马克思主义”与“大众”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必然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和大众这样的双重主体。而群众史观决定了前者只是“大众化”的次属主体,后者则是其首属主体,从而对次属主体具有历史的、逻辑的在先地位和主导功能。其二,将双维取向一维化了。“大众化”主体的双重构成,决定了“大众化”过程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这一取向,也具有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这一取向。然而,既有研究忽视了后一取向,从而使所揭示的“大众化”内涵具有残缺性。其三,既把其空间属性狭隘化了,也遮蔽了其时间属性。既有研究对大众化内在取向的片面理解,必然把本由双维取向构成的空间属性狭隘化,遮蔽由其固有双维取向互动构成的“大众化”渐次展开、深化的历史过程,从而必然使其完整时空属性破碎化。其四,把本质简单化为理论精英向大众施舍解放秘诀的过程,扭曲了马克思主义与大众间的历史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对大众解放实践尽管具有能动作用,但也具有依赖性、受动性。大众化内在地具有理论精英与大众相向教化、相向学习这样的双重本质。既有研究只看其一忽视其二,把问题片面化了。其五,把其主题庸俗化为由理论精英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存量,向大众意识和行为等量传导的单一过程,忽视了大众基于自己实践形成关于解放规律的感性认识,即大众探索和形成自己朴素的马克思主义、用自己的智慧间接塑造新的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增量这一同样重要的主题。其结果则是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阻遏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
诸多缺陷根源是一致的,即未能立足于群众史观来理解问题。因此,有必要依托群众史观重新诠释“大众化”的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既有诠释的依据及其合理性评价
对人的活动而言,“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做什么或我们应该做什么,而只在于在我们所意愿和所做的背后发生了什么”[8]1。对“大众化”内涵而言,人们用来诠释它的“依据”及其对诠释它的活动的约束,显然就是诠释它的活动“背后发生了”的“什么”。这种诠释活动“背后发生了”的“什么”的合法性,决定着对它“所意愿和所做的”诠释的合法性。因此,考察关于它的既有诠释的依据及其合法性状况,无疑是弄清既有诠释症结的前提,也是深化关于它的认识的切入点。
既有研究把“大众化”内涵诠释为“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的过程。这种诠释显然贯穿着这样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性认识,是由理论精英创立和发展的;其内容是用专业概念通过严密逻辑系统来表达的。受社会分工约束,大众知识修养、理论思维能力与理论精英相比所存在的差距,决定了大众并不能直接创立、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支撑大众解放功能的有效发挥、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掌握和运用,就都需要理论精英向大众宣教马克思主义,使其由外在于大众的理论形态,向内化于大众灵魂和行为、并有效支撑大众解放的现实精神力量转变。实现了这种转变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已内化于大众灵魂与行为之中并规定着它们,成为大众自己的内在精神力量,那么,马克思主义实现如此转变的过程及结果,在既有研究看来,就是“大众化”的过程及其结果。
这种逻辑中的诠释要成立,前提条件在于它认同“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和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这一认识论原则。否则,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就没有根据。上述逻辑中的诠释既然把“大众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的过程,可见它是建立在上述认识论原则基础上的,从而该认识论原则就是支撑它的基本依据。该依据尽管有一定合理性,但理性认识毕竟来源于感性认识,因而其合理性并不是充分的。马克思曾指出:“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这“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罢了”[9]541。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和实践的这种依赖性,决定了它必然为它们所塑造。而这种实践和感性认识既然主要是大众解放实践和大众关于该实践的感性认识,那么,这种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成发展的基础;这种感性认识也就因其构成了关于大众解放实践的科学理性认识生成的基础,而具有原始、朴素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以此为基础生成的关于大众解放实践的科学理性认识,则呈现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可见,感性与理性认识都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环节,它们基于大众解放实践而相互作用,并随实践发展,通过前后相继的互动,驱动内隐于和依存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向前演进。这表明,大众关于解放实践的感性认识塑造理论精英的理性认识的过程,即它塑造作为科学理性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该过程必然使马克思主义打上大众感性认识内在要求的印记,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众自己所孕育、塑造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该过程就有理由被看作是“大众化”的过程。
三、诠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合法依据
探究诠释“大众化”内涵的基本依据必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
“大众”作为“普通行动者是有思想的人,他们的观念构成性地进入他们所做的事情中”[3]65。因此,“社会科学家建构其理论并试图检验这些理论所依据的数据主要取决于普通行动者所做的前期‘工作’”[3]113。可见,大众解放实践和认识,始终在塑造和诠释着世界的意义系统,从而使得“社会科学涉及的是一个预先解释的世界……与其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得不根据日常行动的普通概念来演绎,还不如说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能够首先掌握这些普通概念,也就是说,他或她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洞悉想要分析或解释的生活形式的特征”[3]276。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精英而言,要有效解释和规导大众解放实践及其认识,首先必须“洞悉想要分析或解释的”大众解放实践和认识这样的“预先解释的世界”,即首先要向大众实践和学习。
当然,“正如社会科学家采用日常词汇……并且在特殊意义上使用它们一样,普通行动者往往会接受社会科学家们的概念和理论,而且将它们具体化为自己行为的理性化过程中的构成因素”[3]276。这是因为,大众实践和认识具有自发性、朴素性,也需要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可见,“在社会成员使用的概念和社会学观察者使用或者被他们当作新词创造的概念之间,必然存在一种互补关系”[3]268。这表明,在大众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解释与理论精英对该事业的解释之间,存在着一种“双重解释学:不仅关系到参与和领会包含在普通人进行社会生活生产过程的意义框架,而且关系到在专业性概念设计的新意义框架内对此进行的重构”[3]35。所以,“不能回避行动者的解释和观察者的解释之间的关系问题”[3]113。这就要求理论精英必须把这两种“意义框架”“协调”起来[3]112。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精英必须向大众营造的关于解放事业的初始解释和朴素意义框架学习,并对其“进行重构”,使其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提升;另一方面,大众这种初始解释和朴素意义框架也需要向马克思主义学习,接受其规导。
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它作为科学理性认识,并非先验、自足的,而是基于大众关于自身解放实践的感性认识逐渐发育、升华而成的。马克思就曾批评过青年黑格尔派割裂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做法:“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1]191因此,必须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同大众感性认识基础统一起来。
不过,尽管“社会生产因为社会成员具有积极建构能力而得以形成,但是,它必须利用一些资源,并依赖于社会成员不知道的或他们只是朦胧意识到的一些条件”[3]274。而这样的“一些条件”只能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来揭示。同理,大众“不知道的或他们只是朦胧意识到的一些”解放“条件”,只能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批判地“重构”大众相应感性认识来揭示。可见,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关于解放实践的感性认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前者基于后者而生成,受后者约束,同时又反作用于后者,对后者具有批判、提升和超越的张力,并驱动和引导后者发展。二者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后者是前者由以构成的朴素性层面和历史性环节,因而也间接地内在于后者之中;前者则由于必须由后者来孕生,从而也潜在地内在于后者之中,并反过来规导后者。这二者通过这种关系前后相继、循环互动,既实现其各自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又相互支撑、相互驱动,促成对方存续发展。
“大众”与“马克思主义”上述关系,是以大众解放实践为基础历史地生成的,并为该实践历史地中介着,同时又反过来规定着该实践。这样,这二者的关系也就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大众实践”这三方间的关系。相应地,诠释“大众化”内涵的依据,就只能存在于这三方关系中。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性认识,间接内蕴着大众关于解放实践的感性认识;“大众”的这种实践及其感性认识,也需要理性认识的规导;而对“大众实践”而言,它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各自内在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所约束和塑造。“马克思主义”、“大众”、“大众实践”这三者各自的上述构成和上述特性,决定了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规约和化简为“大众实践”、“关于实践的感性认识”与“关于实践的科学理性认识”这三者的关系。相应地,承上可知,诠释“大众化”内涵的依据,也就只能存在于这三者关系之中。
显然,这三者的关系是实践与认识不同层面间,以及认识内部不同层面间的相互关系。该相互关系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服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与认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相应地,只能生成于这三者相互关系中的“大众化”,其内涵也就必然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与认识相互关系基本原理所塑造和约束。不难看出,上述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依次表现为实践与感性认识的关系、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理性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这样三个环节。它们前后相继,依次向下一个环节渗透、转化,共同驱动着上述三者向其新形态演进。这决定了上述三者依循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相互关系原理,通过前后相继的三个互动环节所形成的矛盾统一体,就构成了诠释“大众化”内涵的依据。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基本取向的双维性
实践与感性认识的互动,只是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提供了实践和感性认识基础,尚未直接生成马克思主义,所以,该互动环节并不直接存在“大众化”问题。
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互动环节看,该互动首先表现为大众关于解放实践感性认识孕生、塑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为大众自己创生、呈现为属于大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此而言,该过程自然就是“大众化”的过程。由于该过程始终以大众实践和认识塑造马克思主义为取向,因而该过程可称为以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大众化”过程。
随着感性认识孕生理性认识过程相对完成,在该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认识,反过来规导大众感性认识的过程随之展开。受社会分工约束,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感性认识的规导,需要理论精英向大众宣教它来实现。马克思主义这种由原来作为悬浮于大众感性认识之上、外在于大众心智的抽象理论,通过理论精英宣教,转变为大众感性认识内在规导力量的过程,显然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大众所掌握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那么,该过程就是“大众化”过程。由于该过程以追求马克思主义育化大众灵魂、规导大众感性认识为内在取向,所以,由该过程所生成的大众化形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为取向的“大众化”形态。至此,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互动环节所规定的大众化形态,就完全呈现出来了。
从马克思主义通过约束大众感性认识,而与大众实践互动这一环节看,该互动首先呈现为马克思主义通过为大众掌握运用,而作用于大众实践、接受其检验,并随其发展而发展的过程。显然,该过程是马克思主义融入大众实践、成为被其检验和塑造、打上了大众力量印记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大众创生、塑造与其实践要求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可见,该过程就是“大众化”的过程。由于该过程追求以大众实践塑造马克思主义,因而,由此所生成的大众化,即以大众实践塑造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大众化”。
随着上一作用过程的完成,继之而起的过程表现为:经由大众实践检验得以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反过来指导该实践,向大众实践内在规导力量和大众解放成果转化,从而成为大众自己享有、受益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因此,该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由于该过程追求以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实践,由此生成的大众化形态,可称为以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实践为取向的大众化形态。至此,理性认识与大众实践互动环节所规定的大众化形态,就完全呈现出来了。
如前所述,约束“大众化”内涵的前述三个参量的互动,只具有由上述三个互动环节依次展开所构成的可能的形式。由于大众实践及其认识是无限展开的,所以,前述三个参量的互动在完成了由上述三个环节依次所构成的互动历程之后,必然会随着大众实践和认识的无限展开,一方面不断启动更高层面的互动,另一方面,它们间的互动又只能在上述可能的形式中重复进行。这决定了前述三个约束参量间的互动,在依次经历了上述可能形式之后,必然随着大众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重新以这种可能的形式持续不断展开,从而使前述三个参量间的互动,呈现出周期性无限循环演进的态势。
与此相对应,由上述三个约束参量间周期性循环互动所规定的“大众化”,也会随之以周期性循环形式无限展开。不过,尽管这种周期性无限循环互动会不断为“大众化”注入新内容,但由于这种互动不会有新的约束参量生成和介入,从而不会改变约束参量的既有格局和既有互动模式。如前述,由于由上述三个约束参量的互动所规定的“大众化”内涵的基本取向,是由三个约束参量的互动模式决定的,所以,上述三个约束参量间这种周期性循环互动无论怎样无限演进,生成于其中的“大众化”的具体内容尽管会随之无限演进,但其内在基本取向在不同的循环周期中,则必然是稳定、连续、一致的,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决定了上述三个约束参量间的无限循环互动的一个周期,就生成了“大众化”的完整内涵。因此,可着眼于三个约束参量一个完整互动周期不同互动环节,来把握“大众化”的完整内涵。
如前述,一个互动周期第一互动环节,与“大众化”内涵并不直接相关。对于一个互动周期第二互动环节而言,如前述,它首先生成了以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大众化”形态,继而生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为取向的“大众化”形态。这两种形态前后相继,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离开对方而孤立存在。对于一个互动周期第三互动环节而言,如前述,它首先生成了以大众实践塑造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大众化”形态,继而生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实践为取向的“大众化”形态。这两种形态,前后相继,同样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离开对方而孤立存在。
这表明,一个互动周期孕生的“大众化”形态依次分别表现为:以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为取向、以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为取向、以大众解放实践塑造马克思主义为取向、以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解放实践为取向等“大众化”形态。显然,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以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为取向。其中第二种和第四种本质上也是一致的,即都以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为取向。显然,这是两类不同取向的“大众化”形态,不能相互替代、相互归约。可见,“大众化”内涵具有两种不同维度的内在取向,而不是既有研究主张的仅具有以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为内容的这样一维取向。
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不同取向的互动与整合
对于“大众化”内涵所具有的“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取向和“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取向这二者而言,其关系并非凝固、静止的,而是处于互动演进之中的;同时也不是简单并列、外在对峙性的,而是以不同方式相互支撑、相互约束,从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存在着。具体来说,首先,前者对后者具有历史和逻辑在先地位,是后者得以生成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后者基于前者而生成,并随着前者演化而演化。其次,后者反过来转化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策驱前者进入新境界;由此进入新境界的前者,又会构成新的后者生成的基础。二者在这种互为基础关系中相互驱动,在无限循环中朝前演进。这表明,随着大众化过程的展开,前者对后者所具有的单向基础地位,就相应地转换为二者互为基础、相互依赖、双向规约关系。再次,二者的相向基础地位是异质性的:前者对后者的基础地位主要是实践性、世俗性的,后者对前者的基础地位主要是理论性、超俗性的。这种异质的地位关系,构成了二者共契、互补关系的基础。最后,二者始终处于以前者生成为起点,以后者继起生成并作用于前者为一个互动周期的终点,而相向孕育、规约、转化的无限循环互动中,既使二者结合为一个整体,又使二者关系得以无限深化、上升。
可见,“大众化”既是由两个不同向度的内容构成的整体,也是由两个不同向度的内容,以大众解放实践为基础,相互依赖、双向规约,所构成的周期性循环的无限上升的历史过程,因而是特定内容所构成的整体与特定历史过程的统一体。就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它是大众实践和认识孕育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通过塑造大众、转化为大众追求解放的精神力量,而有效实现大众解放的过程统一体;就其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言,它一开始表现为大众实践和认识孕生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继而表现为理论精英对大众宣教上一过程所生成的马克思主义,使其为大众所掌握的过程;接着表现为大众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经由实践运用和检验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最后被上一过程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大众所认同,从而得以有效规导大众实践,转化为大众解放现实成果的过程。该过程完结后,“大众化”一个周期尽管随之得以完成,但其本身并未随之终结。在上一周期最后一个互动环节中依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实现了一定程度解放的大众,运用在此过程中所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其新的解放实践,生成关于该实践新的感性认识,从而孕育新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大众化”也就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并在新周期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大众新的解放。这种新周期的完成,又会为更新周期所接续。这样的过程永无终止,“大众化”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得以无限展开、深化。
综上可知,“大众化”内涵由多环节构成。其一,其主体表现为大众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精英这双重主体,而非仅有后者一重主体。前者使命在于基于其实践,创生马克思主义由以生成的感性认识资源,间接孕生、塑造马克思主义;同时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其内化到自己灵魂中,使其成为大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后者使命在于向大众学习,把大众关于解放实践的智、情、意批判性改铸、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理性认识,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向大众宣教由此生成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使其内化为大众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其二,其内在取向并非仅有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这一维取向,而是也具有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这另一维取向,从而具有由这二者构成的综合取向。其三,其时空属性既表现为由上述二维取向构成的完整空间结构,也表现为由上述二维取向,通过相向规约构成的周期性无限循环上升的历史过程,因而是一个时空统一体。其四,其本质是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两个过程的统一体,而非仅具有后一过程这一重本质。其五,其主题是大众基于自己实践形成关于解放规律的感性认识即大众自己揭示的朴素马克思主义、从而用自己的智慧间接孕生打上自己意志印记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与理论精英把其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向大众传导、使其内化为大众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两个主题的统一体,而非仅有后一主题。
显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作为上述诸环节的统一体,其每一环节都是由两方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既有研究则只看到了各环节的一个方面,遮蔽了另一方面。其结果,不但使“大众化”内涵处于残缺状态,而且把其庸俗化为理论精英向大众施舍理论的过程,最终扭曲了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的真实关系。
六、结语
如何诠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是受历史观约束的。认为其内涵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这样的一维取向,那就意味着既认定“历史是由学者”这样的理论精英“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9]540,也认定群众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1]109。因此,理论精英必须用其掌握的“隐秘思想”来教化大众;大众则只能被动接受这种塑造。这种诠释显然是与群众史观完全对立的。认为该概念内涵具有大众塑造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塑造大众这样相向规约的双维取向,那就意味着认定“普通行动者是有思想的人,他们的观念构成性地进入他们所做的事情中”[3]65。“社会科学家建构其理论并试图检验这些理论所依据的数据主要取决于普通行动者所做的前期‘工作’。”[3]113因此,群众具有能动塑造者的机能,理论精英要生成和发展科学理性认识,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当然,受社会分工所带来的认知局限性约束,群众也须接受理论精英所把握的科学理性认识的教化。显然,支撑这种诠释的历史观,正是群众史观。可见,要确当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前提在于具有可靠的历史观。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毛泽东选集 ·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3]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4]王国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探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 3期。
[5]陈方刘,田辉:《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云南社会科学》2008第 2期。
[6]曾令辉,丁莉:《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及其价值》,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8第 2期。
[7]左伟清,刘尚明:《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第 1期。
[8](德 )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 》,夏镇平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One-way Shape,or Two-way Statute:Legal Form Inquiry ofMarxist Popularization
X IAO Shi-ying
(Econom 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Shanxi No rmal 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The public perceptions of human liberation practice andMarxis m rational knowledge about it,constitute“double interpretation”of the inner rela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practice:the former gives birth to and supports the latter,the latter,which is generated by learning from the for mer,penetrates through channels as education and critically shaping,enhancing the for mer.Thus they provide a spiritual system support for the public liberation practice.This double interpretation deter mines thatMarxist popularization is a utility by the linking and interaction in two-dimensioned way of“the public shapingMarxis m”and“Marxis m creation”.
Marxist popularization;double interpretation;one-way enlightenment,two-way statute
肖士英 (1962-),男,陕西蓝田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9XJA720001)
2010-07-02
A81
A
1671-7023(2010)06-0036-07
责任编辑 蔡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