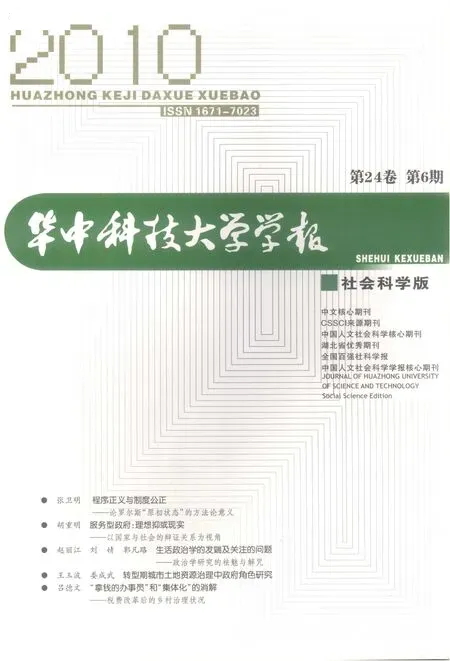语言与真理:试论罗蒂对哈贝马斯启蒙计划的批判
2010-04-08郑维伟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天津300191
郑维伟,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天津 300191
语言与真理:试论罗蒂对哈贝马斯启蒙计划的批判
郑维伟,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天津 300191
后现代哲学家对理性主义提出批判性的质疑,进而从政治上拒斥自由主义。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发掘理性主义传统中的交往理性来证成自由主义。罗蒂则认为自由主义无需形而上学证成,自由主义需要的是从历史叙事中揭示自由民主社会相对其它共同体的优越性。语言观和真理观构成了理解罗蒂与哈贝马斯分歧的枢纽。
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真理;证成;语言
哈贝马斯和罗蒂是当今世界颇具影响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也彼此视为朋友和有价值的对话者。两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相同,即在后现代状况下如何证成自由主义。不过,两人对于证成方式则南辕北辙:哈贝马斯延续了启蒙运动以来用理性主义来证成自由主义的传统,虽然他对理性作了重新诠释,罗蒂则希望抛开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相关性,诉诸于具体历史场景和政治文化来叙述自由主义的优越性。“背弃理论,转向叙述”[1]8构成了罗蒂证成自由主义的基本方式。无论罗蒂还是哈贝马斯都抛弃了传统语言观,前者青睐语境主义而后者独钟语用主义,两人也抛弃了传统符合论真理观,前者认同于种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而后者尚依赖于普遍有效性诉求。语言观和真理观构成了理解罗蒂与哈贝马斯分歧的枢纽。
一、启蒙运动的两张面孔: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
罗蒂认为,启蒙运动有两张面孔,即启蒙自由主义和启蒙理性主义。前者的目标就是要在人间创建天堂,创造没有等级、阶级抑或残酷的世界;后者则旨在寻求一种全新的、整全的世界观,用自然 (Nature)和理性 (Reason)来取代上帝[2]19。
哲学家对这两张面孔的不同诠释,导致其政治和哲学批判的分歧。近代哲人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作为自由秩序的基础。唯有承认所有人都具有共通的理性能力,个人才会照料自己,独立判断,成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守护者,才会抵抗任何以为他人着想的名义而从事侵害他人自由的勾当。诚如麦金泰尔所言,在启蒙时代“理性取代了权威和传统。理性证成诉诸于任何理性的人都不否认的原则,从而独立于所有那些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3]6。而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密尔尽管对人类的易错性 (fallibility)高度警惕,他还是相信自由辩论是易出错的人类接近真理的唯一道路,因为在自由辩论中人们都诉诸理性,普遍的理性引导我们达致真理而拒斥谬误[4]23。
对启蒙的理性计划的批判,几乎与启蒙运动相伴而生。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更是甚嚣尘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声称,理性的辩证法本身摧毁了自 18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理性”和“人性”等观念,起初作为批判力量的理性异化为统治阶级宰制的工具。而理性主义瓦解导致古典自由主义丧失了赖以证立自身的哲学基础,致使自由社会在道德上破产[5]4。利奥塔、福柯等激进左派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同时,也质疑政治自由主义。他们认为,自由秩序已经变成规训和压制现代人的力量,因此必须从政治和哲学两方面对之进行彻底地批判[6]165。
哈贝马斯视现代性为一尚未完成的事业,他认为启蒙话语内部的交往理性足以证成自由主义,由此构建出“一个比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元叙事更加普遍、更加抽象的解放叙事。”[6]164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只看到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走向了反面,而没有发掘启蒙理性主义内部的自我修复能力,即以交往理性来证成政治自由主义[7]345-379。近代以来,以主体理性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已经走到尽头,必须被以交往理性为中心的理解范式所取代[7]352。主体理性把人置于存在者的中心,人成了决定一切存在者的主体。而交往理性则诉诸于视角系统构成的,并且在语法上表现为人称代词系统的人际交往的训练来学会视角的转换,即“一旦用语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获得了优势……自我就处于一种人际关系当中,从而使他能够从他者的视角出发与作为互动者的自我建立联系。”[7]348简言之,交往理性就是一种把对方当成一个你 (you)而不是当成一个他 /她 (he/she)的努力,于此你才可能努力理解并试图进入对方。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内在于语言。这是他最深刻的洞见,即从语言这种人类最独特又普遍的行为中,构筑出他的理性理论[8]301。为了证成这一说法,哈贝马斯诉诸于奥斯汀语言行动理论的三种说法,即以言表意行动、以言行事行动以及以言取效行动,并把交往行动界定为所有参与者“无保留的追求他们的以言行事之目的的那类交往行动”[9]295。这样,交往行动的参与者就必须“悬置观察者和直接以成功为取向的行动者所持的客观化态度,而采取将与第二个人就世界上某物达成理解的说话者的施为性态度。”由此,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如何证成交往理性与以言行事的语言行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诉诸于先验论证,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预设一些有效宣称 (validity claims),这种行动才有可能。换言之,交往行动者“必须承担一些虚拟形式的语用学前提”,被置于一种“弱的先验力量的“必须”之下。所谓有效宣称是指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以及主观的真诚性。当说话者用言语行动向对方说话时,他就想要达到交往的目的,“保证必要时将用恰当的理由来兑现所提出的主张。”[10]22,6,23当听者明白并接受了这句话,即接受了说者的有效宣称。如果他不接受这句话,则说者就会提出理由来支持自己的有效宣称,以期说服听者,于是双方进入辩理阶段。如果听完说者的理由,听者接受了,说者就重新回到了他的有效宣称。但如果听者提出理由来说明说者的有效宣称不成立,则说者会再提出理由来支持自己。这个过程可以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双方同意为止。
罗蒂赞同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立场,但不同意其继续拘泥于以理性主义话语来证成自由主义的语言游戏,而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反讽的自由主义,即把自由主义同理性主义撇开,否认以理性主义来证成自由主义①罗蒂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有独创性的,他认为虽然义务论或契约论能证成自由主义,但这并非必然的证成方法。这一方法,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的提出也是很有启发性的。参见萧高彦:《爱国心与共同体政治认同之构成》(陈秀容、江宜桦主编:《政治社群》,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1995年版第 279页)。。在他看来,启蒙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缠绕在一起纯属巧合,即好比把耶稣和基督联系在一起一样。耶稣是指那位兄弟之爱的传播者,而基督指那位神,他将在末日审判中对罪者处以永恒的折磨[2]27。这一论述,可以看作是在后哲学时代捍卫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尝试,亦即捍卫古典自由主义的方式必须超越启蒙理性主义的语言游戏。因此,罗蒂既赞成福柯等人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又不满意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来证成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注定左右为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蒂与哈贝马斯之争,不关乎启蒙自由主义的可能性,而只关乎自由主义的证成方式[11]1-12。罗蒂本人也把这种分歧视为“纯粹哲学上”或者“技术上”的差异[12]57。
二、语言的自然化和历史化
在罗蒂看来,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从而把理性社会化 (socialize)和语言学化 (linguistify),这绝对正确。但罗蒂认为,应该更进一步把理性自然化 (naturalize),可哈贝马斯在此却止步不前[13]2-3。他之所以不愿意向前推进的原因在于,(1)从哲学上来说,他认为理性是规范性,而规范是不能够自然化的[13]5;(2)从政治上来说,哈贝马斯是为了避免相对主义的指责,为了证明自由民主政体比极权政体更“理性”,所以必须保持理性的规范性以体现启蒙运动的普遍性,证立政治自由主义[6]165。对哈贝马斯在政治上的良苦用心,罗蒂是赞赏的。
如上文所示,哈贝马斯诉诸交往理性的优先性来证成沟通行动的普遍有效性,进而证成在理想的言说境况中审议民主的可能性,达到捍卫自由主义,实现公共领域现代复归的目的。由此可见,批判哈贝马斯的关键在于彻底质疑交往理性的优先性和沟通行动的普遍有效性,但罗蒂却以迂回侧击的方式来批判哈贝马斯的论述,因为正面应战的结果是陷入对方设定的语言游戏,而“让他选择武器和战场。”[1]67
罗蒂的论证策略是从根本上质疑哈贝马斯的语言观,如果其语言观错误,那么以以言行事的言语行动来证成交往理性的做法也就难以成立了。如果说哈贝马斯是沿着语用学的路向来理解语言,而罗蒂就是沿着语境主义的路向来理解语言。前者预设了语言共同体的成员运用语言表达式的同一性,而后者则试图表明语言表达式本身就是偶然的,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是不可通约的。所以,就对语言的理解而言,两人的争论是语境主义与语用学之间的争论。
实际上,罗蒂对语言的论述,是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的,即实用主义自然化的路径和历史社会学的路径。语言是我们应付世界的工具。作为世内存在者,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与世界照面,与之打交道。语言开启了世界,使世界成为我的世界。世界无言,只有人类言说。惟有当我们用一个程式语言设计了自己之后,世界才能引发或促使 (cause)我们持有信念[1]15。世界无法为我们说什么语言提供建议,世界与此在因语言而共在。所以语言与世界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彼此维持的关系,而不是再现的关系。“失落的世界”没有任何本质或基础有待我们去发现,只有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世内存在者,用语言来描画和构造世界。
在世内存在,人类可以选择不同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但是被抛的命运却无可逃离。被抛的命运规定了人类语言的偶然性。设若我们被抛入柏拉图时代,我们会逐渐熟悉描述希腊世界的语汇,会对奴隶制、奥林匹斯诸神、东方野蛮人等描述心安理得。设若我们被抛入近代启蒙世界,我们会逐渐熟悉科学修辞,对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经验与理性等等二元论习以为常,安然栖居于伽利略、牛顿等科学语汇描述的世界。语言与世界之间相互维持、彼此生成的生存论态势,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的开显以及我们描述世界的工具——语言——的偶然性。
从历史社会学 (historico-sociological study)的路径来论述语言,主要体现在他对黑格尔和法国大革命的阐释[14]73。在某种意义上,罗蒂关于语言的讨论都围绕着黑格尔的[15]213-214。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家是在其时代中把握思想的,所有理念都具有历史性。罗蒂认为,黑格尔的这一说法打开了这样的可能性,即把所谓永恒的哲学问题视为特定的社会实践和语汇的表达更为妥帖。这种可能性意味着,当一套语汇耗尽了它描述世界的功能时,新的语汇便会取而代之。罗蒂写道:“黑格尔所描述的精神逐渐自我意识到其内在本质的过程,恰好可以描述欧洲语言实践以越来越快的速率改变的过程。”[1]16-17法国大革命以令人震撼的方式提醒人们,社会关系的全部语汇,几乎可在一夜之间被取代。自由、平等、博爱的语汇赋予人类描述、应付世界以新的工具,把人类带入新语言游戏,而阶级、等级以及神学的语汇则退隐到幕后。不同的语言创造出不同的人类和世界,而不是上帝或理性造就了人类和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被发现的!”新的语汇之所以能够取代旧的语汇,并非因其更接近于世界的本质,而在于它碰巧更方便我们对世界的描述。
上述论断,对于思考政治自由主义和启蒙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罗蒂认为语言与工具之间的类比并不是很恰当,因为我们设计一个新工具能够事先知道它对我们有什么用,而新语言的创造只有在回顾的时候才有用,因为那些制作新语言工具的人无法知道历史演进的实际状况,无法描述他们的目标。只有我们这些后来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才能够了解新的语言工具对于社会历史的意义。所以,启蒙理性话语工具的发明者,无法知晓启蒙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彼时自由主义还没有在社会实践中现实化。这样,由启蒙理性主义来证成政治自由主义就是可疑的了。
然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说新的语言工具的发明者无法确证启蒙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证成关系,那么我们后来者是否有可能确证呢?显然,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都认为后人可以发现并确证两者之间的关系。可罗蒂认为,只有当新语言形式处于危机中、新的隐喻本义化时,这种新的话语形式才成形,而“一个成熟的文化偏颇不公地和其他文化相较,自我辩解的表白,其所使用的语词不太可能是当时促使这文化诞生所使用的语词。”[1]83以后见之明“发现”启蒙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将理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便显得南辕北辙、牵强附会了。质言之,理性主义话语本身是后见之明的产物,与自由主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人类自由成长的历史,并非以真理为基础,而是通过某种后见之明或回溯而得 (hindsight or retrospection)。”[16]232
证成自由主义无须形而上学基础,也不必诉诸中立化的程序原则①C.Mcmahon认为,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均持有这种观点(参见 C.Mcmahon,Why There IsNo Issue Between Habermas and Rawls,i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9,No.3(Mar.,2002),pp.111-129),不过,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罗蒂承认最初他也是这么认为,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尤其当罗尔斯表明自己的哲学立场之后:“证成某一正义观念的不在于其符合某种先于我们并给予我们的秩序,而在于其与我们对自己、对我们的期望的更深刻理解相一致,在于我们认识到,只要既定的历史和传统包含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这种正义观念对于我们就是最合理的。”(Rawls,“Kantian Constuctivism inMoral Theory”,Journalof Philosophy88(1980),p.519)罗蒂认为,罗尔斯的立场表明,他是要诉诸于历史社会描述的方式来说明特定的正义观念,而不是从哲学上来证成之 (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and tru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84-185)。,而在于“把它和其他关于社会组织的尝试——过去的,以及乌托邦主义者所设想的——加以历史的比较。”[1]79罗蒂这一观念来自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有的语汇都是人类所创造的,都是人类创作诗歌、乌托邦社会、科学理论等作品所使用的工具。因而,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人类语汇创造的产物。随着一套语汇转到另一套语汇,从一个核心隐喻转到另一个核心隐喻,人类用以描述自由主义社会的语汇也随之改变。自由社会被做成之前,不可能对其进行无预设的批判反省,其形成也不可能不用特定的语言或者独立于历史脉络之外。因此,我们不可能找到中立的“理性”概念来判断自由社会的演进是否合乎理性,而证成自由社会的充分理据“只诉诸大家熟悉的、共同接受的前提,而且是随心所欲的。”[1]80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诉诸于历史的比较,如果与过去的生活相比,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人类享有了更多的自由、减少了残酷,如此就足以说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在理想的自由主义政治中,罗蒂认为,文化英雄创造新的语汇和隐喻,能使我们逐渐摆脱启蒙运动的语汇。在新语言游戏中,理性的位置殊可怀疑,指责诉诸于历史而不是理性来证成自由主义为文化相对主义[17]39和非理性主义便显得苍白无力。
罗蒂称文化英雄创造的文化为“诗化的文化”,即“不再坚持要我们在描画的墙背后再寻找真正的墙,在纯粹由文化建构出来的试金石之外再寻找真理的真正试金石。正由于诗化的文化肯定所有的试金石都是文化的建构,所以它会把它的目标放在创造更多不同的、多彩多姿的文化建构上。”[1]80它的目标在于创造更多的文化建构,对我们所熟悉的自由主义社会进行再描述,而不是为之寻找哲学的基础。而哈贝马斯之所以执迷于交往理性以证成自由主义,是因为他患上了典型的德意志怀乡症,即“典型的关于现时代自我意识的德国故事 (始于黑格尔、经由马克思、韦伯和尼采)聚焦于这些人物身上:他们痴迷于由于我们抛弃我们祖先的宗教而失去的世界”[6]171。换言之,哈贝马斯的德意志怀乡症乃是一种对过去的向往,期望延续以往德国哲学家以其理性哲学来证成自由主义的梦想。哈贝马斯所缺乏的正是历史叙述和乌托邦想象,所以在罗蒂看来,他是一位干瘪的、缺乏想象力的哲学家[18]24-29。
三、真理与证成 (justification)
罗蒂从正面对哈贝马斯以真理来保障沟通行动的普遍有效性,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在他看来,哈贝马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就是混淆了真理与证成之间的关系。罗蒂认为,尽管“真”的用法种种,但我们在语言实践中根本无法祛除其警戒性使用(cautionary use)。一个信念可以被证成,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信念就是真的。譬如“你的信念 S已完全得以证成,但也许并不为真”这种说法,在这里“真”只是提醒我们:证成是相对于用来作为 S的根据的那些信念的,所以并不好于它们,而且证成性并不能保证,只要我们把 S作为“行动准则”就万事大吉了[19]128。真理的警戒性使用,只是对人类的有限性的一种提醒 (reminder),对人类的易错性的一种承认 (confession)[20]52。
人注定挣扎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生和死界定此在在世的命运。我们永远都无法超越自身的限制,永远都无法知晓所有可能的境况。罗蒂认为,真理的无条件性与证成的有条件性之间的分野是站不住脚的,毋宁在时间性的视域中,真理与证成之间的分野是过去和未来的可证成(justifiability)之间的分野[13]4-5。换言之,证成性只有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才有意义,在特定的历史情境或语言游戏中,一个命题只有占据恰当的位置才能为当时的观众所接受为真。舍此之外,对于真理,人类不能要求过多。而哈贝马斯以真理的无条件性 (unconditional)证成沟通行动的普遍有效性,意味着“一朝证成,永远证成”(once justified,always justified),“一朝为真,永远为真”(once truth,always truth)[21]57。
在此,罗蒂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即真理与证成是可以分离的。西蒙·汤普森根据他的说法,把命题区分为四种。首先,根据我们此时此地的经验,可以区分出两种命题,即 (1)命题可以被证成且为真;(2)命题不能被证成或为真。例如,如果我当下说“地球是圆的”、“奴隶制是罪恶的”,显然根据我们此时此地的经验,这两个命题都可以被证成,也都为真。如果有人问你为何确信“地球是圆的”,我可以诉诸于当前最有用的科学证据;如果有人说你为何确信“奴隶制是罪恶的”,我可以诉诸于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尊严。如果我当下说“地球是平的”、“奴隶制是可行的”,显然根据我们当下的证明标准,这两个命题既不能得到证成,也不能为真。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真理和证成之间的区分从实践上说并没有意义。其次,如果我们从此时此地的经验来衡量彼时彼地的经验的话,又可以区分出两种命题,即 (3)命题可以被证成,但不为真;(4)命题不能被证成,但为真。比如,如果 14世纪的欧洲人说“地球是平的”,或公元前 4世纪的雅典人说“奴隶制是可行的”,那么依照他们当时的经验上述说法都可以被证成,但我们现在均知道它们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当时的判断标准是不充分的。相反,如果公元前 4世纪的雅典人说“奴隶制是罪恶的”、14世纪的欧洲人说“地球是圆的”,显然这两个命题不能为当时的标准所证成,但我们现在都知晓它们为真。在这两种情景下,真理与证成是可以分离的[22]41-43。
显然,汤普森的区分预设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罗蒂认可了种族中心主义。这种种族中心主义是自由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条件[23]。换言之,上述四种命题的区分实际上都预设此时此地的标准的正确性。可是,我们如何面对同时代其他的共同体的证成标准呢?罗蒂认为,种族中心主义只是说明了我们的共同体的证成标准的稳定性,而面对其他的共同体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来消除疑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话必然达成最终的共识,如果对话能够达到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了解之同情,那么这样的对话才是可欲的。哈贝马斯诉诸于不同共同体之外的超越性的、批判性的标准来寻求克服不同共同体各自的偏好,以期最终达成共识。或者说,哈贝马斯认为真理与证成是不可分的,真理就是探寻之终了所证成的标准,如此则不同的共同体才能达成共识①哈贝马斯对于真理的看法经历了转变,最初他把真理作为理想的可辩护性,到后来他实际上在真理与证成之间的关系上才有所松动,出现了所谓的“实用主义转向”。但我认为,哈贝马斯关于真理的见解在结构上并没有根本的转折,因为他一直没有放弃超越语境的普遍真理的诉求。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沈清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0-54页)。。显然,这种对话是不可欲的,因为我们无法找到这样的理想性的情景和标准,除非我们借助于上帝之眼。罗蒂借助于种族中心主义将人们的目光转向具体的程序和制度,他说:“我们不能学到通过思考理性的本质、人的本质或社会的本质而作为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的平衡木的这些制度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会通过观察当这些制度都被弃置一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来认识到这些制度的重要性。”[6]190
至于哈贝马斯认为真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是哲学的核心问题,而这一紧张要为从理论上证成民主政治的诸多困难负责。在他看来,通过区分话语的策略性使用(strategic use of discourse)与朝向达致理解的言语行动 (use of language oriented to reaching understanding)就可以成功地化解两者之间的张力。可是罗蒂认为,话语的战略性使用和非战略性使用之间分野,实际上相当于其中我们都在乎说服其他人的情形与我们希望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的情形之间的区别,相当于古希腊时期的知识与意见之间的分野。但在具体的历史视野中,有效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张力依然如故,哈贝马斯所期望的超越时刻也遥遥无期,而徒增柏拉图主义残余的嫌疑[13]8。
罗蒂赞赏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悬置道德本体来证成道德判断普遍有效性的努力,他所质疑的是一旦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这种努力就变成了花拳绣腿,徒有观赏的价值而没有现实可行性。譬如,我们尝试说服一个偏执狂 (bigot)来承认普遍的有效宣称,他可能会同意,但他会说这些普遍宣称正是其所为。如果你接着说他的做法在别人看来有显著的矛盾,他会说这些如是看待他的人都疯了。即使最终他认同了我们所认为的普遍有效性宣称,他也可能会抱怨自己以前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而不会对其没有反思自己的前见而心存遗憾。其实,罗蒂的这一指责并非有力。因为,哈贝马斯多次申言,交往行动只有在理想的言说境况中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讲,交往理性是有效性宣称得以成立的论证程序,从而排除了一切宗教和形而上学假设。民主政治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审议与决策的理想程序。在诸神之争的情况下,民主政治证成自身不能诉诸于任何一位“神”,只能将其正当性根据置放在程序本身[10]297-298。而罗蒂所预设的偏执狂并非社会人的常态,忽略了对理想程序的尊重,而有诡辩之嫌。
实际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漠视许多前见在有效性宣称中的作用,以及社会习俗对沟通行动的制约。我们的社会实践根本无法超越社会习俗,正是这些社会习俗塑造了我们的身份认同,除非新来者进入我们的语言游戏,认同我们的社会习俗而成为“我们 (we)”,否则沟通行动根本难以达成。人是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偶然存在,成为“我们”并非意味着新来者要凭借交往行动,而只是说他碰巧发现我们的语言游戏和社会习俗能够更好地描述自我和世界,仅此而已[13]6-8。此外,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否能够走出他所反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哲学范式,也是令人怀疑的[24]233。也在这个意义上,罗蒂指责哈贝马斯普遍有效性诉求实际上是在为自由主义寻找哲学基础,“这其实是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的后果;而启蒙运动科学主义本身,又要求人类计划必须由非人的权威背书的宗教需求之残余。”[1]78在后哲学时代,启蒙运动的政治修辞已经比较没有用,自由主义需要的是重新描述,而重新描述必须借助于乌托邦的想象和新的隐喻与语言游戏的证成。
在罗蒂看来,证成须向外转而非向内转,须朝向证成的社会环境,而不是诸内部表象间的关系。例如,我说,“今天芝加哥下雨了。”“你怎么知道。”“我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好吧,我将带把雨伞。”在此,我的信念是这样的命题,即引用我的对话者接受并视之为支撑我的信念的其他命题而证成。如果他们不接受它,那么我可以继续援引其他的命题直到我们达成共识。因此,证成只是能够为信念赋予好的理由(good reason)的问题。至于好理由的标准本身则建立在认识的共同体的同意[25]44。一旦我们把证成诉诸于谈话和社会实践,则证成就是整体论的(holistic),而认识论传统的证成则是还原论的。据这一前提,则知识就不是心灵之镜内部表象的准确再现问题,而是对信念的社会性证明;哲学问题也不再是人与非人的对象之间的对照,内部空间和外部世界的联结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从而哲学问题转换成为人的问题。参照社会使我们能说的东西来说明合理性与认识的权威性,罗蒂称之为“认识论的行为主义”(epistemologicalbehavioris m)[26]174-175。传统认识论的诉诸于后设基础来确保认识的确定性,可是后设诉求的起点本身是成问题的,倘如进一步追问则必然跌入虚无的深渊;而认识论行为主义则停留在社会意见的范围,满足于意见的效用,从而避免了面对虚无的恐惧,而满怀知识进步的社会希望。所以,在罗蒂看来,哈贝马斯试图发掘启蒙理性传统中的交往理性来证明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依然拘泥于近代认识论传统。
四、小结
罗蒂与哈贝马斯之间的论辩,为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时代,重新审视哲学与政治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展现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复杂性及其自我修复能力。
就哲学风格而言,这一争论是古希腊苏格拉底式寻求真理的追问与诡辩家自足于意见世界嬉戏调侃之间论争的现代回响。罗蒂否认第一哲学追求的可能性,他安然栖居在柏拉图的洞穴内,宁愿观赏墙壁上走动的影子①理查德·沃林曾把罗蒂称之为古代雅典时期的智者,他认为罗蒂如同智者一样在宣扬糟糕的信仰、浅薄的自我陶醉的时代哲学等。笔者认为,沃林的说法过于简单,他没有认识到罗蒂实际上并不是否定哲学,而是在尝试一种可能性,即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为哲学划定疆界。沃林还是局限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认为私人化了哲学就等于完全抛弃了哲学。因此,笔者把罗蒂比喻为古代雅典智者与沃林迥然不同,智者的生活方式在价值上并不低于哲学家,如果说哲学家生活在深渊,而智者则满足于生活在表面。表面更接近生活世界。参见 RichardWolin,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ch.7.;而哈贝马斯则焦虑地寻找走出洞穴的途径,并期望把洞穴中的民众解救到理想国的乐土。
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实用主义传统内部的张力:罗蒂崇杜威、詹姆斯而黜皮尔斯,几乎没有提及米德[27]61,而哈贝马斯则几乎没有提到詹姆斯[28]49,而对皮尔斯、米德推重备至。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在其《交往行动理论》的发展中,哈贝马斯事实上一直赋予实用主义——尤其是皮尔士版本的实用主义——以核心的意义。”[28]37
就自由主义社会的证成而言,哈贝马斯发掘启蒙运动内部的反话语来重新为自由社会奠基;而罗蒂的历史情境主义诉诸于历史的描述和乌托邦的想象。反讽的是,两人同为自由主义社会辩护而在哲学观点上则针锋相对:哈贝马斯是基础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罗蒂则是反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可能更有助于描述罗蒂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关联。哈贝马斯就像卡通片《猫和老鼠》里的“汤姆”,非常笨拙地在贫乏的矿场发掘,而罗蒂则像聪明的“杰瑞”,不停的寻找新矿场。杰瑞的乐趣就在于对汤姆的挑衅。没有汤姆,杰瑞的生活也没有乐趣。历史主义的兴起,如果舍弃了普遍主义的帷幕,也会索然无味。
不过,罗蒂对启蒙自由主义的特殊辩护远非完美无缺。在笔者看来,用历史主义来取代普遍主义,实在是犯下了非此即彼的错误。如果我们承认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让普遍主义成为哲学证明的替罪羊,这是不公正的。相反,只有普遍主义才能与现实的既得利益者拉开距离,从而具有批判力量。普遍主义的理论不只是具有证明的作用,而且具有自我批判的功能。为了彻底的撇清哲学对政治的证成作用,罗蒂矫枉过正地忽视了理论的自我批判功能。正如麦卡锡所说,以偶然性来替代必然性,以反讽主义来替代普遍主义,这就好像是在倒洗澡水时连同孩童一起倒掉一样[29]370。
另外,罗蒂的历史主义完全使哲学概念政治化了,从而堕落成为“最为庸俗的党派偏见。”[30]160比如,他把启蒙计划简单地区分为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这是不确切的。启蒙的要义在于确保个人公开运用理性的能力,说自由主义是启蒙的政治计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忘记了社会主义同样是启蒙运动的政治计划[31]5,107-108。在某种程度,社会主义恰恰是在自由主义止步不前的地方,继续推进了启蒙的事业。
(本文于 2009年 5月 25-27日提交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举办的“哲学:东西之际——华人青年学术会议”,在此对会议主办方以及拙文评论人香港大学哲学系孙金峰博士谨致谢意)
[1]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2]Richard Rorty.The Continuity Between the Enlightenm ent and“Postmodernism”,in Keith MichaelBaker and Peter Hanns Reill(eds.),W hat’s Left of Enlightenm ent?A Postm odern Question,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Alasdair MacIntyre.W hose Justice?W hose Rationality?Notre Dam e, IN: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88.
[4]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5]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6]Richard Rorty.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年版。
[8]石元康:《两种民主与两种理性》,载许纪霖主编:《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9]Ju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 unicative Action,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London:Heinemann,c1984-c1987,Vol.1.
[10]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11]Chantal Mouffe,Deconstruction,Pragmat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em ocracy,in ChantalMouffe(ed.),D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6.
[12]Eduardo Mendieta(ed.),Take Care of Freedom and Truth W ill Take Care of Itself:Interviews w ith Richard Ror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3]Richard Rorty,Universality and Truth,in Robert B.Brandom(ed.),Richard Rorty and his Critics,Blackwell PublishersLtd,2000.
[14]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 atism,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82.
[15]Richard Donovan,Rorty’s Pragm atism and theLinguistic Turn,in Robert Hollinger&David Depew(eds.),Pragm atism:From Progressivism to Postnodernism,Connecticut&London:Praeger,1995.
[16]Michael Peters,Achieving Am erica:Postm odernism and Rorty’s Critique of the CulturalLeft,in TheView of Education/Pedagogy/Cultural Studies,Vol.22.No.3.
[17]Jürgen Habermas,Richard Rorty’s Pragm atic Turn,in RobertB.Brandom(ed.),Richard Rorty and his Critics,Blackwell PublishersLtd,2000.
[18]Józef Niznik and John T.Sanders(eds.),Debating The State of Philosophy:Haber m as,Rorty,and Kolakowski,London: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1996.
[19]Rihc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and Tru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0]Rihcard Rorty,Response to Sim on Thom pson,in Matthew Festenstein&Simon Thompson(eds.),Richard Rorty:Critical D ialogues,Polity Press,2001.
[21]Richard Rorty,Response to Jurgen Haber mas,in Robert B.Brandom (ed.),Richard Rortyandhis Critics,Blackwell PublishersLtd,2000.
[22]Simon Thompson,Rorty on Truth,Justification and Justice, in Matthew Festenstein & Simon Thompson(eds.),RichardRorty:Critical D ialogues, Polity Press,2001.
[23]PetersM.A and Marshall.J.D(1999),Rorty,W ittgenstein and Postm odernism:Neopragm at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thnos,in W ittgenstein,Philosophy,Postmodernis m,Pedagogy,Westport.CT&London.Bergin&Garvey.
[24]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8年版。
[25]Gary Gutting,Rorty’s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in Charles Guignon&DavidsR.Hiley(ed.),Richard Ror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6]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 irror of N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27]Leszek Koczanowicz,“The Choice of Tradition and the Tradition of Choice:Habermas’s and Rorty’s Interpretation of Pragmatis m”,Philosophy&Social Criticis m,1999,Vol.25,No.1.
[28]童世骏:《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7年版。
[29]ThomasMcCarthy,“Private Irony and Public Decency:Richard Rorty’s New Pragmatis m”,Critical Inquiry,Vol.16,No.2,W inter,1990.
[30]George Bragues,“Richard Rorty,Postmodern Case for LiberalDemocracy:A Critique”,in Humanitas,No.1-2.,2006.
[31](美)斯蒂芬·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殷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Language and Truth:A Critique to Habermas′s Enlightenment Project by Richard Rorty
ZHENGWei-w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Tianjin Academy of Governance,Tianjin300191,China)
Many post-modern philosophers critically questioned rationalism and refused liberalism in politics.Haber mas tried to justify liberalism by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n the tradition of rationalism.While Rorty believed that liberalism cannot be justified bymeta-physics.What the liberalism need was the explanation that could show the superior of liberal democracy to other commonwealth in historical narration.The concept of language and truth is the key in understanding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m.
rationalism;liberalism;truth;justification;language
郑维伟 (1979-),男,山东郯城人,法学博士,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天津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07BZZ022)
2010-08-03
C93
A
1671-7023(2010)06-0007-08
责任编辑 蔡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