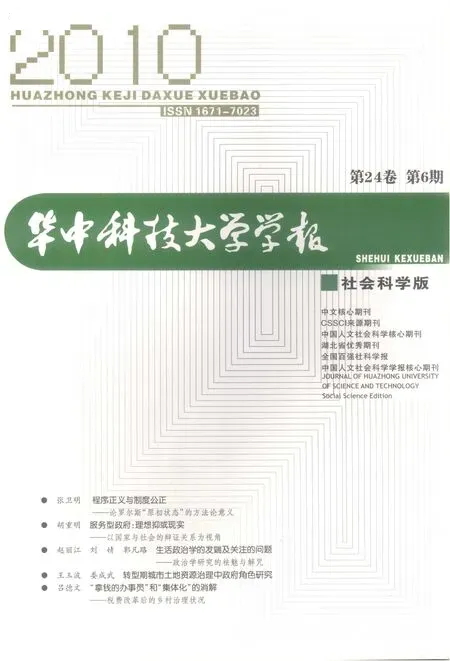程序正义与制度公正——论罗尔斯“原初状态”的方法论意义
2010-04-08张卫明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张卫明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程序正义与制度公正
——论罗尔斯“原初状态”的方法论意义
张卫明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原初状态”假设是罗尔斯发展正义理论的方法论出发点。他以古典契约论方法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无知之幕”装置,对将要选择两个正义原则的主体进行知识限制和具体特性设计,使“原初状态”在形式上完全成为一种纯粹的正义程序。这一独特的方法论构建思路对于我们如何确保制度是公正的,以及制度如何运行才是公正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程序正义;制度公正
罗尔斯是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家,他的理论旨趣是社会正义,其发展正义理论的方法论原点是“原初状态”。他认为,在“原初状态”假设中,只要保证这一假设能够达到纯粹程序的正义性,其推理结果不管如何,都是正义的。这就是说,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是在公平的“原初状态”程序下的合理推理;进而,在这两个正义原则指导下的社会必将是良序的社会。罗尔斯这一方法论思路,对于我们处理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公正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作为纯粹正义程序的“原初状态”
择出两个正义原则 (平等自由的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首要任务,也是他构建良序社会的出发点。为保证原初状态中人们所选原则的正义性,他认为,关键的步骤就是要首先排除原初状态中各种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对主体选择活动的影响,消除各种可能的“交易优势”,使主体在进入选择状态时处于公平的地位;其次是保证选择主体在选择过程中具有同等的“自我”特性,使他们不存在身份等级差异。这一正义程序的设计,罗尔斯是通过他独特的方法——“无知之幕”来完成的。
1.公平的主体知识限制
罗尔斯认为,“无知之幕”的无知,不是选择各方处于弱智意义上的无知,而是有意识地排除某些信息,奠定初始的平等境地,为我们所希望的公平原则的出场提供便利。
罗尔斯假定各方都不知道某些事实。首先,对他的自然天赋和社会出身一无所知:无人知道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的阶级出身,也不知道他天生的理智和力量等。其次,对个人价值观念和性格气质一无所知:没有人知道他的善或好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的特殊性,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心理特征,如是否喜欢冒险,气质是悲观还是乐观,等等。最后,各方对他们所处的特定社会和所属世代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这一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或者它能达到的文明或文化水平,以及他们属于什么时代。这一状态就是使各方不知道将使他们陷入对立的偶然因素的状态。
然而,这样的状态并不是使一切文明重来的状态。在“无知之幕”下,人们仍然具有关于社会和社会合作的一般知识。首先,各方知道他们的社会处于正义的环境,社会合作必要且可能;其次,各方知道与社会合作有关的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如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原则,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人的心理学法则。概括地说,“各方被假定知道所有影响正义原则选择的一般事实 ”[1]132。
2.公平的主体特性设计
在“无知之幕”下,主体自我特性及主体间关系的设定直接关乎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目标。他认为,“所有人在选择原则的过程中都有同等的自由权利,每个人都能参加提议,并说明接受它们的理由。显然,这些条件的目的就是要体现平等——体现作为道德主体、有一种他们自己的善观念和正义感能力的理性的人类存在物之间的平等”[1]16-17。这就是说,契约各方是平等、自由和理性的。
各方是自由的。如果没有自由的条件,各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那就根本不存在订立契约的行为。强调自由,就是保证缔结契约是一个自愿的过程,由此也才能保证所立契约的公平性。罗尔斯认为,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义务和责任的基础之上的自由。它包含着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要求,而责任和义务的承担是出于主体的道德认同。因此,这种自由既是自律的自由,又是取向性要求的自由。
各方是平等的。罗尔斯理解的平等是,“他们都被看作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以从事终身的社会合作,并作为平等的公民参与社会生活”[1]33。很明显,他强调的平等是一种构成平等基础的参与的平等,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资格要求的平等。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具有了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并参与社会合作,他与其他人在权利上就是平等的。
各方是理性的。罗尔斯认为,“理性的”是指“人们乐于提出这样的原则,即这些原则必须表达出能为所有人都视为公平的合作条款的东西,或者当这些原则是由别人提出的时候,他们也乐于加以承认。人们也明白,他们应该承诺履行这些原则,即使由于环境的迫使而不得不以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代价,如果别人被预期能够同样承诺履行它们的话”[1]12。而在合作体系中,我们应将“理性的”作“合理性”理解,即“按照经济理论的标准,解释为采取最有效的达到既定目标的手段”[1]11。
由于“无知之幕”的覆盖,选择者只知道他们必须保护自己的自由,扩大他们的机会,增加达到其目的的手段。但是自由平等和理性的主体无法知道以及如何推进他们的特殊利益。这样,理性的参与主体必须蕴含某种特征。所以,罗尔斯假设:(1)“理性各方相互冷淡,不受嫉妒之累,否则,嫉妒倾向于使每个人的状况更坏,在此意义上它使集体不利”[1]143。(2)理性人在选择正义原则时要考虑“契约承诺的强度”[1]144。各方在订立契约时,必须非常谨慎。他们不会签订一个他们明知不可能维持或维持起来将有很大困难的契约。“这样,在评价各种正义观时,处于原初状态的人们就要假定他们采用的正义观将被严格地服从,他们契约的结论将按这一基础推出”[1]144。
二、对于制度公正的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将原初状态当作纯粹程序正义装置,其目的就是:(1)将参与选择的主体控制在同一个起点,从而使人们必然选择两个正义原则;(2)两个正义原则一旦择出,社会基本结构必须在它的指导之下运转。
沿着罗尔斯的思路,我们对制度的公正问题可以进行这样类似的思考:(1)采取何种措施或步骤可以控制制度在运作之前有一个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起点,从而保证制度设计的公正?(2)制度设计一旦完成,制度如何运作才能确保其公正性质?
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厘清制度公正这一范畴的真实含义,否则我们将会无的放矢。
(一)什么是制度公正
对制度自身的公正问题的探讨涉及关于“制度”涵义的理解。有人认为“制度是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权利和义务的集合”[2]50-51,有人认为“是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形式或群体活动形式”[3]282,也有人认为“是规则化的行为模式”[4]49,或“是规范化、定型化了的正式行为方式与交往关系结构”[5]27,以及“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1]50等等。
我们认为,制度应是两方面的统一,即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正式规范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通过某种权威机构来维系的社会活动模式。如此理解的制度,一是其对象和范围只限于公共生活领域,二是其目的指向是社会或者共同体的一定目标或者“善”,这就使某种权威机构有其存在的必要,三是制度作为组织社会共同生活的方式或者社会技术,其实用性和效力更被人们所重视。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并非所有的制度都是伦理制度,也并非所有制度都自然而然地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于是,公正性成为制度的不同于实用性和效力要求之外的另一种理性要求。
这种理性要求是指制度在其建立时是否具有公正的根据以及是否被赋予了公正的属性。具体说来,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制度建立的有关正义观基础,二是这种正义观基础的合理性。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它是指同一制度可以具有不同的正义观基础。在这里,制度是纯形式的东西,而其性质和内容则依据其正义观基础的不同而具有根本的区别,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无政府主义的“正义即互助”、“正义即无统治”的正义观,主张建立无政府的制度。功利主义的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正义观,要求建立一种能够带来最大限度的幸福的制度。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到以诺齐克、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激进派所持的正义观,则认为管事最少 (或者有限)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正义的政府。
同样是国家制度,在阶级社会里它是剥削制度、专制制度。剥削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6]414。社会主义制度,它则是一种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制度,“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制度。这些都表明,制度的设计和建立不能离开一定的正义观基础。
(二)如何确保制度的公正设计
考察何种制度才是真正公正的这一问题,其深层之处则是对支撑制度的正义观的合理性的追问,这是制度本身公正性的根本方面,也是对上述第二个方面的回答。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保证制度设计本身的公正呢?
1.保障人权
制度的安排在于“规范体系”的设计,即为社会公共权力的运作设定合理的法律程序。“正当程序建立在政府不得专横、任性地行事的原则之上。它意味着政府只能按法律确立的方式和法律为保护个人权利对政府施加的限制进行活动”[7]15。这样,它一方面防止社会公共权力的恣意扩张及非法专横行使;另一方面又为社会公共权力的合理、正当行使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它才能体现制度的目的性意义,即以人为目的: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以程序为核心的制度化保障,它既能为公民的人权平等提供保护,又能体现公民的自由意志和尊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保障人权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体现制度的工具性与合目的性要求。
2.追求法治
法治理想的张扬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尽管人们对法治的内涵和意义的理解颇多争议。但是,“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物”[8]73。它强调目的性法律推理和论证方法形成公共决策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法治首先表现为规则的形式合理性,即强调秩序、普遍性、稳定性与逻辑一致性,并且将所有的人都视为无差别的、中立性的“客体”。
3.崇尚民主
法治化的制度或纯粹性的程序可以是非人道的、压制性的,并不必然带来正义和“好结果效能”。在本质上,现代意义的制度不是使主体客体化的流水线,不再仅仅处于纯粹形式主义和仪式性特征阶段;相反,它是参与者角色互动、意见对话与整合的场所,处于开放性、角色参与性、对话性和论证性阶段。它兼具主体性、契约共识性和民主性。参与性、透明性、话语论证性、主体间性构成当代制度的基本范畴。“制度理性受沟通伦理指引……法律规范只有在论证话语中得到相关者的合作与赞同才能获得有效性”[9]160。实际上,现代制度既吸纳了民主和人权的价值 (主体性),又吸纳了法治的价值(形式性和工具性),既是一个统合了民主和法治价值的独立范畴,也是一种兼备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实践理性、反思理性。
4.兼顾秩序与自由
人可以生活在无自由、有秩序的社会中,却难以生活在有自由无秩序的社会之中。在霍布斯、洛克、卢梭到康德这些古典契约论的“自然状态”假设理论中,思想家们无一不具有需要一个能够协调自由人之间的自由关系,形成制度性秩序的强烈愿望,以便通过制度达到以自由来限制自由的目的,使个人自由的行使不会损害他人和社会自由,从而实现对自由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充分表明了在人类社会中,秩序对自由的优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自由的永恒追求,这不但是个人的内在价值诉求,也是社会制度的最高价值目标。由此,正义的制度应当是秩序与自由的兼顾,是制度内人类社会必要的秩序和最大限度自由的实现。
5.保证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都是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效率是制度发展和制度文明的重要尺度,一个没有效率的制度,其存在价值及合理性将遭到怀疑。公平就是制度安排和设置是正直合理而没有偏私,能以同一标准对待相同的人或事,体现为主体平等、机会平等、权利与义务平等等方面。离开效率的所谓公正的制度是不可取的,它会使社会停滞不前;脱离公平原则,片面追求效率的制度安排也不能持久,它会导致社会发展不平衡,不能实现可持续全面发展,
(三)制度如何运作才是公正的
一定社会或者共同体建立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制度在社会中的意义,追求社会的正义。因此,制度建立后的一个必然的环节就是制度的执行和运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度本身只是一套正式的规范体系和社会活动模式。它虽然表明一定社会或者共同体因此而具有处理社会问题的社会能力,但它却只是社会或者共同体所期望的观念性的可能力量,它要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能力,就必须付诸实践。
制度运作和执行的实践过程不单是制度自身的被动运作,而是主客体的互动过程。它既包括“客体”——制度自身的公正运作一面,又包含主体道德自觉的发挥。只有这样的双向吸引、动态的公正制度的运作才有可能真正具有生命力,不断向理想的价值目标趋近。
1.制度的被动运作
制度基于一定的正义观而建立,其性质和内容由此而规定。制度的运行正是为了实现制度得以建立的正义观基础。在实现这种正义观时,制度运行只需按照由这种正义观所确定的规范、规则、社会活动模式而行事,却不顾这种正义观及其相应的规范、规则、社会活动模式的对与错及优与劣,它具有明显的“照章而行”的特征,而且,制度的自我运行不容许人们对这种正义观及其相应的规范、规则、社会活动模式有丝毫的怀疑和批判,更不容许人们有违背它们的行为,它具有对个人而言的他律性和强制性特征。
制度运行的这些特征,意味着制度的实现必有一定的权威机构来保障。在此,我们需面临制度运行的层层递进的正义思考。第一,权威机构的存在是不是公正的?我们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不公正,还是新老自由主义者有保留地承认它的公正性,或专制主义者、权威主义者则认为它是完全公正的;不管国家或政府只应拥有极其有限的权力和职责,还是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的权力和职责,我们都不做过多的讨论。我们认为,只要满足一条——“主权在民”,即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权威就具有道德合理性和正当性;第二,当权威机构被承认有必要存在之后,制度运行又面临着第二个公正性问题,即权威机构使制度如何运行来实现这种公正及其相应的规范、规则和社会活动模式?
首先,制度通过限制恣意实现社会正义。
“权力易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化”[10]1。制度的裁判者也具有一定的制度权力,因而也不可逃脱权力易腐化的本质规律,即容易导致恣意。由于对立于制度的是恣意,因而分化和独立才是制度的灵魂。由于分化的组织和角色各自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要求独立地实现其价值,于是明确相互之间的活动范围和权限就成为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通过对恣意的限制保证了制度的运行不受外部环境的干扰,从而实现制度公正和社会正义的统一。
其次,制度通过优化选择实现社会正义
制度限制恣意的同时,并不排斥自由选择,相反,它使选择更合乎理性。现代制度中的职业主义原则、制度公开性和纠错机制,制度根据证据资料进行自由对话的条件和氛围,以及通过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和实际结果的拘束力这两种因素对制度参加者参与动机的调动,使得选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自由的,合乎理性的,同时又是有序的。因此公正合理程序的设计使法变得更合法化,使人的选择更合理化,从而真正实现社会正义的自由价值。
再次,制度通过确立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正义
在动态的意义上,“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法律程序就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11]1-20。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办事就是要依制度、程序办事,而确立法律程序的权威就是确立法律的权威。制度通过实现和保障人的理性来健全民主和推进法治的秩序化。公平合理的制度会增加法律的权威基础,而法律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它是维护社会安定和秩序的基本手段。因此公正合理的制度使得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确立应有的权威,从而实现社会正义的秩序价值。
2.主体的道德自觉
制度是人的本质的观念化和物化,是人的社会需要的产物,是个体需要蕴藏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化形态,因此,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离开人而独立自存。制度是参与者角色互动、意见对话与整合的场所,它本身就包含着个体守制精神这一内在机理。如果制度的创制、实施和遵从等诸方面的公正理念不能转化为个体内在的价值准则和价值目标,即不能达到主体的道德自觉,制度的公正性运行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我们必须将制度公正与道德自觉关联起来考察。
道德自觉是指社会主体有效地发挥主导性和能动性,自觉遵循普遍的规范体系,使主体的行为与规范体系保持协调,并促使其优化的认识和实践过程。现实的公正制度创制后,并不必然导致人们对它的服从,所以,道德自觉的能动性居于关键地位。
首先,公民意识是基础。对公正制度的道德自觉,既不能依赖神的启示,又不能依赖外界的强力,而应置于类似于康德和罗尔斯的道德人的理性之上。通过道德自觉,守制者必然会表现出对制度公正的体认和对自身感性的局限性的认识和控制。当制度本身是公正的时候,亦即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时,对它的遵循自然能给主体的实践以正确的导引,实现主体的目的。主体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人存在,同时更是社会性的存在,即作为公民,并将他人也作为这种主体人来认知时,才能真正达到对守制的道德自觉。所以,这种公民意识的具备和体认是关乎制度公正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对公民权利的要求,也就无法产生对制度的需求,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导致对制度公正的认同。
其次,守制意识是核心。道德自觉与人的受动性本质密切相关。所以,在守制上,道德自觉有两种表现:一是在对制度公正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心甘情愿”,它表现为“不仅应当如此,而且还乐于如此”,我们称之为道德自觉的高级形态。另一种是出于对不遵从制度的恶劣后果的畏惧而“不得不如此”,我们称之为道德自觉的低级形态。对道德自觉的效应评价主要依赖于这种自觉所作用的客体制度是否公正。如果制度是公正的,这种自觉就体现出价值合理性,同时,道德自觉也会是一种主动积极的反应。反之,当制度是不公正的,即不具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时,或当制度安排表现为凝固化时,往往会导致道德个体的循规蹈矩和道德群体的平和有序,甚至道德自觉的虚伪和道德自觉的丧失。
最后,制度安排与时俱进是关键。人类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制度公正具体内涵的动态取向。与之相适应,守制的道德自觉必然会建立在对制度公正新的理性体悟基础之上。低级形态的道德自觉只会增加制度公正的老化,而积极意义的高级形态的道德自觉不但能展示自我的主动介入精神,而且能在主体制度的理想预设与道德期望中促进公正制度的良性发展。由此,在不断趋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人类终极价值合理性的征途中,道德自觉必须深深扎根于时代的现实背景。看不清时代发展的方向或落后于时代,高级形态的道德自觉就会退化为低级形态,导致制度安排的凝固化或甚至导致制度正义的缺失,其结果将使现有制度安排崩溃和沦丧为虚无;同时,也应避免守制的道德自觉过分张扬,超越当下时代境域,一味追求纯粹理论预设,这样就会导致制度公正性超出现实价值合理性界限而等同于现实乌托邦。
[1](美)约翰 ·罗尔斯:《正义论 》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2](美)丹尼尔·W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陈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美)乔治 ·赫伯特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 》,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年版。
[4](阿根廷)基尔摩·奥唐奈:《论委任制民主》,载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5]高兆明:《制度公正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7](美)伦斯特洛姆编:《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8](英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王明毅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9]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10](匈牙利)安乐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陈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1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Procedural Justice and Institution Fa irness——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Rawls′Original Position
ZHANGWei-Ming
(School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410083,China)
“The original position”hypothesis is the methodo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Rawls to develop the theory of justice.Rawls proposed“veil of ignorance”,based on the approach of the classical contract theory,restrained the knowledge on two subjects of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designed its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which made“the original position”in the form of a pure procedural justice completely.This unique constructive thinking is significantlymeaningful for us to explore problems as how to guarantee the institution justice,and how to function is fair for institutions.
original position;veil of ignorance;procedural justice;Fairness of institution
张卫明 (1969-),男,湖南湘阴人,中南大学博士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伦理学。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基金课题 (09B054);中南大学博士后基金课题资助项目
2010-07-10
B82-051
A
1671-7023(2010)06-0001-06
责任编辑 吴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