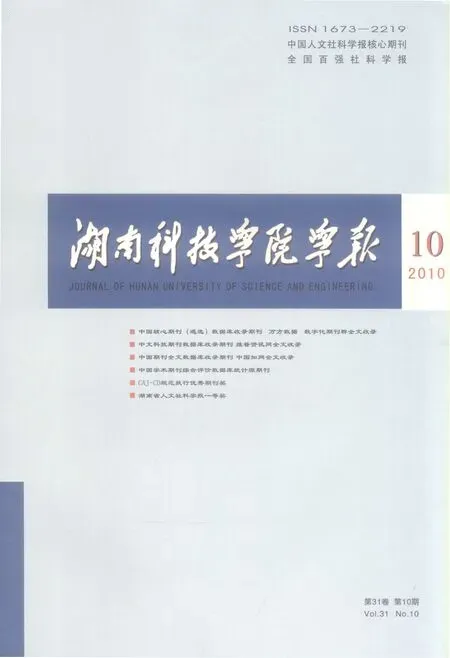先秦军事法律思想中的人道规则探析
2010-04-07黄孝禹
黄孝禹
(西安政治学院 军事法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8)
先秦军事法律思想中的人道规则探析
黄孝禹
(西安政治学院 军事法学系,陕西 西安 710068)
先秦时期是一个中国社会由分裂向统一过渡的动荡时期,出现了思想上百家争鸣和军事上列国纵横的局面。先秦军事法律思想中,又以儒家和兵家主张重民、爱兵,以“仁”治理人民和军队为代表。但是在这一神权向王权过渡的时期,这些看似人道思想的规则又存在其目的性和片面性。因此,虽然先秦时期的军事法律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人道思想与人道规则,但终究未能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先秦;王权;人道思想;人道主义
先秦时期是中国军事法律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为以后军事法律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在由分裂向统一过渡的这一动荡时期,出现了思想上百家争鸣和军事上列国纵横的局面。诸子百家对军事法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初步形成了传统的军事法律思想体系。儒家主张德治、礼治,其中心思想是“仁”,是爱民,那么运用到军事法律思想中便是对人的关怀,具体来说是在战争中对兵与民的关怀。而同时期的兵家则与儒家有很多共通之处,虽然强调军队的纪律性,重视严格的军事法律,但是也同样包含着“仁”的理念。那么,这个所谓的“仁”究竟是什么?与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又有何异同呢?
一 先秦时期军事法律思想中的人道规则
先秦时期军事法律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为主流思想的兵家、儒家和法家对待军事法律思想的态度又各有不同,法家一味地强调军队纪律的严明性,注重军事法律的权威,并反对以仁治军。与之恰恰相反,儒家作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不但在其军事法律思想中贯穿着以“礼”待民,以“仁”治军的理念,还提出禁暴除害的战争法思想。而以上这些儒家思想正体现了战争中对兵与民的关怀,可以称之为人道。
那么儒家的人道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其代表人物出于重民、爱民的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谴责各国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而实施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残暴行为,对遭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发出“善战服上刑”的呐喊。但是儒家的反对战争并不是针对所有的战事,他们反对的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的兼并战争,对于救民罚罪的正义战争,他们则是大加赞赏的。
这一时期儒家另一极具人道情怀的战争法思想则更具有前瞻性。他们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敌方军队,而不是灭失敌军士兵的肉体;在于摧毁敌国的政权,而不是奴役敌国的人民。“故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故如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不杀降者等规则的出现,已经具备了战争法人道规则的一些基本特征。
另一先秦时期的主流军事法律思想是兵家思想,尽管它与法家思想有着诸多的共通之处,但是其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他们对于战争的目的与性质、作战指挥的谋略、军事法律等问题都有系统、独到的观点。
兵家注重战争的性质、军队的宗旨和军事法律的取向,是与他们以礼治军、强调德爱的观点相联系的。西周时期的礼,是一个比较杂乱的概念。兵家在使用“礼”这一概念时,一般是指与军事法律相对应、相补充的军队中的道德、教育、习惯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经常与“仁”所通用。
兵家的“礼”注重民心,认为人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是战争胜利的条件,提出“仁之所在,天下归之”的命题,强调通过“仁”来联络人民,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建立强大的军队,是难能可贵的。兵家之所以将关心民众疾苦与治理军队联系起来,是因为军队来自人民。如果民众热爱国家,忠于君主,遵守法律,军队也就能够具有服从军事统帅、遵守军事 法律的习惯和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作风。
兵家的“仁”还表现在关心士卒的疾苦,爱护士卒,将帅要与士卒同甘共苦上。其作为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思想,能够认识到士兵在军事、战争中的巨大力量,从而提出关心爱护士卒,而不是一味地出发士卒,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二 先秦时期军事法律思想由神权向王权的过渡
在法律思想史上,最早出现了神权法的观念。同样,在军事法律思想领域,最早也存在着一个军事神权法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但它是法律思想、军事法律思想的最早形态。军事神权法观念从远古时期逐渐形成,到西周时开始发生动摇。
周朝是以小邦灭掉了大邑商,周王朝统治者为了解决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如商灭夏一样希望通过宗教作为自己政权合理化、永恒化的论证。但是西周统治者的这种宗教化的法律观念遇到了挑战。商朝统治者曾经宣称自己是代替上天讨伐夏桀的,但后来自己的子孙却受到别人的讨伐。这种现实使得人们对这种所谓的神权产生了怀疑,军事神权法的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在这样一个历史冲击下,周王朝统治者只能在继续宣扬军事神权法的同时,强调一个“德”字,放出只有有“德”者才能顺承天命的观点。而其自身对所谓的神权的怀疑也使得所实施的政策更加偏重于个人的王权的巩固。在这里,王权成了独立的变项,而神权则是从属的变项。这样就出现了神权王权化的基本模式,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王权政治”的基础。
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王朝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同时,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
既然有兼并与争霸,就意味着连年的战事。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政治家们、军事家们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这也正如前所述,在分裂向统一过渡的这一动荡时期,出现了军事法律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兵家代表人物孙子认为关系战争胜负的因素主要是五个方面,即道、天、地、将、法。法家、儒家和兵家是先秦的主流学派。法家主张以严刑酷法取天下,鼓吹赤裸裸的暴力原则,不仅是非人道,而且是反人道。儒家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以爱为出发点,与兵家形成两种不同形态的人道思想。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思想,都摆脱不了战争胜利所需的“道”与“法”。这里的道与法可以“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那就只有通过军事法制建设了。实际上,上述兵家与儒家关于人道规则的军事法律思想也正是出于此目的。
三 先秦时期军事法律思想中的“人道”与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
作为一种思潮或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最迟适用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它是以个人为着眼点的观点,主张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尊重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当作人看待,而不是把人看作人的工具。其最初形式是人文主义。在反封建中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法国第一步宪法的序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宣传书。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超阶级、超时代的抽象人性论,其追求的社会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他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逐渐失去进步的历史意义。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相应出现了公开抛弃人道主义旗帜的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法西斯主义集团所推行的种种灭绝人性的政策,集中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反人道的本质。但是,在世界上有一大批正直的公众,仍然信奉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并从这个原则出发抨击资本主义世界种种反人道的罪恶,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道主义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流派,如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实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往往自命要褒扬人的价值,提高人的地位,以现代眼光研究人的状况、特点、前途和利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大都把爱当作实现人道的杠杆。弗洛姆认为,人的苦难是由于缺乏爱引起的。缺少爱虽不能引起生理意义上的死亡,但却是促使人走向坟墓的根源。然而,生命的意义深深扎根在人的身上,作为生物的本能,它表现在肉体和精神中。这是对生命的渴望,也是爱的基础。马尔库塞设想在一种无压抑的文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充分爱欲化,人的自由和幸福能在此获得充分的实现。施密特认为,借助爱就能实现人道化。因为,爱是幸福的状态,而获得这种状态又依赖于对某人或某物的爱。而且,爱改善人的状况,提供人生的意义,使人充分发展。
一般而言,战争以杀戮为手段,去实现一般政治中所无法实现的政治目的。似乎从战争的本质上来看,它应当与人道主义不沾边。事实上,战争是与人类社会共生的,自从有了社会。也就有了战争。战争的历史如此悠久,战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如此密切,于是人类在其自身发展史中早就形成了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战争的文化。战争的残酷和暴烈是由战争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但战争过既然为社会之物,人类之物,人类社会必然要求他比较地、尽可能地人性一些。人类这样的与其行为本身的势能呈反向性质的要求,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普遍并非匪夷所思。
中西战争史上,人们对老弱病残人群的保护,对财产掠夺的限定,不斩信使、不杀降者的规定,都是人类战争史上呈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内容。至于近现代,则出现了战争法、国际法庭,人类借以规范国家间、民族间的战争行为。换言之,战争是有文化、讲规则的,战争文化中包含着深刻的人性,这是现代战争人道主义特点的床基。
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考,它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规则。先秦时期的人道思想和人道规则,就是这样的东西。它并不随着那个产生它的时代的结束而消逝,却有着永久的价值和永恒的魅力。
那么为什么先秦时期儒家和兵家都未能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近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作为西方一种历史久远的思潮和理论,亦有它发展、丰富的过程,它最初的含义指的是公元前100多年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所指的一种具有对人的精神关怀,旨在促使个体的人的才能得到最大发展的教育制度。到了14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则以人文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综其要义是:歌颂人的伟大,突出人的地位,反对抬高神、贬低人,肯定人性存在,提出理性、意志自由、追求享乐等为人之本性,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反对宗教桎梏和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尘世享乐、反对禁欲主义和把幸福寄托于来世天国。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人道主义的主要内涵则表现为:将自爱、自保和趋乐避苦的身体感受的生物性和理性当作人的本性,认为人们应享受生来就有的自由平等权利,反对君权神授和等级特权制度,提倡博爱,主张为了人民自己的利益,应当爱他人,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和追求的人道目标。总之,西方近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最基本点在于:弘扬人的个性,追求人的自由,主张人的平等。
把先秦时期儒家、兵家思想置于近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的视域之内,其共同的缺失之处是对个体价值的忽视,其理论根源是对人性的片面化的预设。儒家重民、爱兵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积极意义。他们注意到了人民、士卒对于战争的意义,对兵家爱兵的观点进一步做了论证。这对减轻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核给士兵造成的牺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儒家重民、爱兵的目的绝不是真实地反映人民和士兵的愿望,代表人民和士兵的利益,他们重民、爱兵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民、士卒心甘情愿地为奴隶主贵族效命,为王权效命。而兵家的名言“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则更是建立在“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的愚兵政策之上。因此,先秦时期军事法律思想中虽蕴含着人道思想与人道规则,但是终究无法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
[1]周健.中国军事法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余子明.中国军事法律思想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5.
[3]张彩凤.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4]武装冲突法研究所.尊重国际人道法[Z].西安:西安政治学院科研部,2006.
(责任编校:燕廉奚)
E29
A
1673-2219(2010)10-0128-03
2010-05-30
黄孝禹(1985-),男,河南信阳人,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军事法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武装冲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