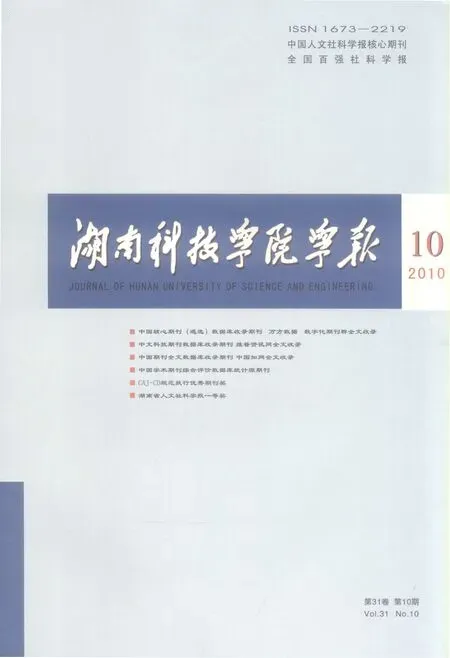才子佳人小说在康乾时期的叙事演变
2010-11-20周华南
周华南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湖南 长沙 410002)
才子佳人小说在康乾时期的叙事演变
周华南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湖南 长沙 410002)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操作在康乾时期出现了新变:其一,在小说人物身份、地位、境况及性情的设定上,开始从完美回归现实;其二,叙事重心进行了调整,即缩短定情过程而放大历经磨难情节,呈现出与世情小说合流的态势。
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情欲
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在产生伊始,就以弘扬情的纯净与坚贞为创作主旨,奠定了爱情喜剧的固定模式。在贯穿有清一代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此类小说虽未经历脱胎换骨的蜕变,却 也顺应时代文化的变迁在叙事模式、情爱意识等各方面进行了自觉调整,呈现出不同风貌。康乾时期,世情世态叙事成分的加重直接导致了才子佳人小说叙事的演变。细致解读这一现象,有助于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此类小说的发展流变进行动态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提供的资料,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总数达到50部左右,其中《两交婚》、《玉支玑》等作品的叙事与《玉娇梨》等早期同类小说一脉相承,故视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而《终须梦》、《五凤吟》、《幻中真》等20余部、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作品因将叙事重心逐渐转向沉重的现实生活,在叙事上发生了明显改变,是本文主要研究对象。[1]
一
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操作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对小说人物身份、地位、境况及性情的重新设定上。
传统的“才子”与“佳人”必出自名门,对爱情忠贞不二且才胆识样样具备,是渐臻“完美”的典型。而康乾时才子佳人小说的男女主人公逐渐走下“完美”的神坛,开始向有情有欲有缺点的平常人过渡,回归现实状态。《跂云楼》中的柳毅发迹前的经历可谓惨不忍睹,不仅衣食无着,而且青年丧妻,教书不成,只能以卖草鞋为生。《终须梦》里的康梦鹤更是诸多才子中命运最苦的一个。传统的才子们只需有才便社会地位、娇妻美妾手到擒来,日常生计也绝不至于发愁,每日只需吟风弄月,追逐佳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吹捧赞誉之声,最重要的是他们“视功名如同拾芥”,不考则已,一考必轻轻巧巧地高中。康梦鹤的形象可说是对这种一帆风顺、不识人间烟火“才子”形象的颠覆,他幼年即在战乱中背井离乡,少年丧父,青年时入衙作吏却因不肯同流合污而被打,开铺占卜又因过于迂腐而遭人奚落,谋个塾师之职又得罪小人而被辞;更可气的是屡赴科考屡次不第,最重要一次竟因沿途算命挣盘缠而贻误考期;好容易得个佳人为妻,却与儿子中途暴卒。究其不幸的原因,绝非小人拨乱那么简单,而更多地与其所处社会地位、身世际遇、官场黑暗及社会群体对真正有才之士的藐视有关。此外,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们虽也秉性风流,定情之后却能矢志不渝地忠于爱情,显示出超越世俗的高雅情爱观。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的情爱意识则更多地趋向于世俗社会,并不同程度地掺入了欲的成分。《五凤吟》中的祝琪生爱欲两分明,心系邹雪娥、平婉如两位大家闺秀,却将素梅、绛玉、轻烟三个婢女作为泄欲对象,行事之初均是强逼,带有明显的玩弄意味。而“从小气质,与凡夫不同”的赵青心“常愿读尽天下第一种奇书,占尽天下第一种科甲,娶尽天下第一种美人”[2],毫无顾忌地坦露自己与市民阶级一般无二、充斥着强烈功利色彩的性情志愿。(《绣屏缘》)
至于佳人,《玉娇梨》中的苏友白将有才、有色、有情作为评判的三大标准。《平山冷燕》中的平如衡偏激地认定:“女子眉目秀媚,固云美矣。若无才情发其精神,便不过是花耳,柳耳……”[3]到了《两交婚》中甚至出现了“妇若无才,已非淑女”[4]的观点。在这种以才为美的审美关照下,山黛、冷绛雪(《平山冷燕》)、辛古钗、甘梦(《两交婚》)、柳蓝玉、赵红瑞(《画图缘》)等才女横空出世,将女性的文才夸张到极限。鉴于此类书中所充斥的大量的佳人诗作,鲁迅先生所以作出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5]的结论。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显然弱化了佳人这种不切实际的“诗人”气质,在大多数佳人出场时,作者竭力渲染其貌美,对“才情”的展示不是略过不提就是寥寥数语带过,使其仅仅作为“色”的点缀出现。才子们也不再大张旗鼓地将“才”作为选择佳人的首要条件,《空空幻》中的花春更直截了当地宣称:“就是青楼少妇,若果有拔萃的姿容,小生亦甘与之配。”除了诗才,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还必须具备“识”的素质,即权谋机变。《好逑传》中的水冰心、《玉支玑》中的管彤秀、《两交婚》中的辛古钗、甘梦、黎青等“知穷通,辨贞奸”,“机巧横生,智计百出”,不仅具备高明的政治眼光与处世谋略,而且对人性的善恶、社会生活的复杂以及人际关系的敏感都达到了洞若观火的地步。以此才识周旋于世,不仅游刃有余,永远处于有惊无险的不败之地,而且轻而易举地将小人权贵玩弄于鼓掌之间,相形之下,众才子在人情世故、识人应对方面亦有如弱智,不能抵之万一。康乾时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则脱去了“神化”外衣,还原成软弱无依、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地位的弱势群体。同是叔父为谋己家产而逼婚,冯闺英自认“我母子二人到底女流见识,哪里当得他的暗算”,故除了乖乖应允且与母亲“相对涕泣”外,毫无他计可施(《醒风流奇传》)。《春秋配》中的姜秋莲与张秋联、《梦中缘》中的金翠娟与水兰英、《赛花铃》中的方素云、《醒名花》中的梅杏芳、《山水情》中的邬素琼、《飞花咏》中的端容姑不仅命运多舛,如逐水扬花般任人摆布设计,而且面对家庭的变故和生活的考验,只知一味哭天喊地,寻死觅活,把处于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脆弱无助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才子佳人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见钟情,拨乱离散,及第团圆。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一见钟情”只是爱情发生的形式之一,而男女主人公的离散也绝非仅由“小人拨乱”一种原因造成,二者远远不能概括才子佳人小说在演变过程中的种种变式,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莫若用“风流遇合,历经磨难,及第团圆”来概括更为科学。
作为“事专男女”的才子佳人小说,以大量的篇幅铺排男女主人公的风流遇合过程显然是理所当然,但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康乾时期此类小说在叙事重心上已进行了明显的调整。

注:前四书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限于篇幅,兹未全录。
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以言情为中心,不惜花费大量笔墨精心打造一个个多姿多彩、引人入胜的风流遇合故事,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不再有耐心细腻刻画男女主人公从未识——相知——定情所经历的种种风光旖旎的浪漫过程及缠绵心态。一方面是佳人人数的增多,如《空空幻》《梅魂幻》就达到12位,另一方面却是才子佳人遇合过程占全书比例的缩小,二者兼顾的唯一方法则是简化定情过程。于是《幻中真》在第1回就让才子吉扶云与佳人易素娥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从见面到成亲的全过程,随后以9回的篇幅详述这对佳偶长达16年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即便《五凤吟》中的祝琪生肩负与5位佳人谈情说爱的重任,作者也仅用5回就干净利落地结束其在温柔乡中左右逢源的得意与享受,转而堕入因奸人迫害而造成的劳燕分飞、九死一生的悲惨遭遇。为缩短定情过程,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反复渲染的“一见钟情”“因诗相慕”被置换成“自幼定亲”甚至“并无交集”,如此即可省却在爱情产生伊始所必须交代的种种试探、交流、吸引、传情细节,直接进入婚姻甚至欲的主题。如《终须梦》中的康梦鹤与蔡平娘自幼定亲,因此即使蔡父悔婚,平娘亦能义无返顾地毅然与康结为连理;《醒名花》中的佳人梅杏芳慎守闺礼,却因丫鬟佛奴的误传诗柬而被久欲谋其产的兄长梅富春诬以失节,从此命运与素未谋面亦无甚好感的才子湛翌王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其次,从爱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平山冷燕》、《玉娇梨》等通过“诗词酬和”“诗文比试”“考诗选婿”环节不厌其烦地炫耀男女主人公的诗才,让双方在高密度的诗来词往中暗生情愫以致心心相印,既缔造了令人心动神摇的绚烂佳话,又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训,将“情”牢牢地控制在“理”的范围内。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出现了“情”“欲”并行不悖的现象,一方面才子继续与有身份地位且守贞知礼的“大家闺秀”中规中矩地交往,另一方面又急不可耐地与婢私通、与尼滥交甚至通过狎妓、养小官来发泄自己的欲望。除了前文提到过的《五凤吟》,《赛花铃》中红文畹追求佳人方素云未果,不仅勾搭婢女凌宵先成鱼水之欢,主动与小官何馥结后庭之好,而且事后马上将二人抛诸脑后,仍对方氏一往情深直至奉旨成亲。
对定情过程的简化与变异必将导致小说雅文化品格的下降,而对“历经磨难”这一情节的显微放大又使小说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内容,更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的悲剧性。就磨难原因而言,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几乎清一色起于“小人妒才”,张轨如妒苏有白之诗才,用计调换诗文几乎令白红玉与才貌相当的佳偶失之交臂(《玉娇梨》);假名士宋信与冷绛雪比试诗才受辱,恼羞成怒之下调唆窦知府将其送往京城为婢(《平山冷燕》)。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磨难原因不仅复杂得多,而且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或为金钱利益之争,如《幻中真》里吉扶云与易素娥16年的离散起于易之堂兄易任、易佑对其家产的谋夺;或与政治斗争相关,才子梅傲雪(《醒风流奇传》)、梅璧(《二度梅全传》)被权奸逼得亡命天涯,皆因二人之父与其政见不和而导致的忠奸斗争;或生逢战乱及其它无法避免的灾难,如康梦鹤幼时家乡遭海寇抢掠,不得已逃往他乡,以致与未婚妻天各一方(《终须梦》)。其次,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小人所干大都是调换诗文、冒名顶替等绝不会对男女主人公造成多少人身伤害的勾当,权贵逼婚不成或将佳人之父调往危险之地、或令才子孤身平寇,却绝对达不到加害目的,反给当事人提供了立功升官的机会。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则以乡绅恶霸、当朝权奸居多,不仅陷害手段残忍,破坏力也惊人。他们不是通过扳盗栽赃、诬陷杀人等手段将才子下在狱中屈打成招,就是纠集地痞流氓强抢佳人,逼其自杀保贞。男女主人公在经历家破人亡的痛苦后不得不飘零江湖、东躲西藏,多年后方得重聚。第三,磨难性质的变化。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小人权贵虽不时挑起事端,却不会令读者感到焦虑或愤懑,相反,在他们自欺欺人的愚蠢举动中常常蕴涵着喜剧因素。因才胆识远远高出对方,才子佳人们永远对小人们保持着一种心理优势,后者的拨乱虽制造了一些波折、烦恼与麻烦,但决不会影响前者的人生轨迹、前程际遇。简言之,二者之间是美与丑的斗争,是一种审美的对立。康乾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丧失了这份从容与轻松,虽然大部分作品勉强维持了大团圆的结局,但小人权贵们制造的磨难往往把才子佳人们逼得走投无路,惨不堪言甚至不惜以死抗争。可以说,此二者之间是善与恶、忠与奸的对立,是生与死的较量。
综上所述,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虽未挣脱传统的情节俗套,但在具体的叙事操作上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呈现出与“描摹世态,现其炎凉”[5]的世情小说相合流的态势。
[1]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Z].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2]苏庵主人.绣屏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4]天花藏主人.两交婚[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On the Narrative Evolution in the Genius and Beauty Novels during the Kang Qian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ZHOU Hua-n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Changsha Hunan 410002,China)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arrative evolution in the Genius and Beauty Novels during the Kang Qian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First,there are the change from the perfect back to reality in the fictional identity,position, situation and nature of the set.Another is that the narrative focus was adjusted,which shorten the process tokens of love and extended the suffering plot.
the genius and beauty novels; the Narrative ;Ardour
I206
A
1673-2219(2010)10-0074-03
2010-05-16
周华南(1975-),女,湖南湘潭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王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