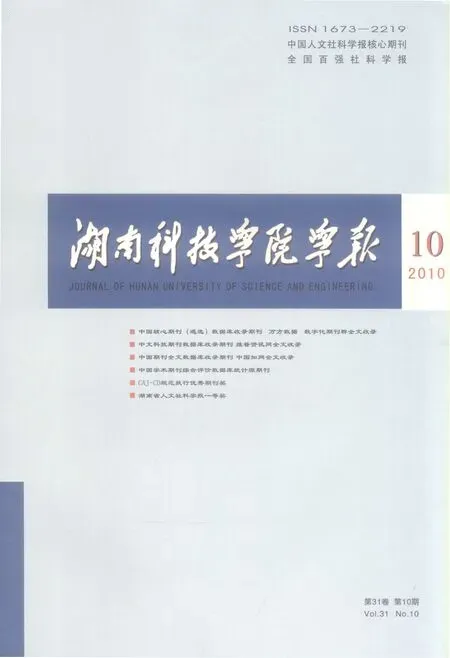姜夔之诗学理论
2010-04-07晏萍利
晏萍利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姜夔之诗学理论
晏萍利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姜夔除以词名世外,其诗又在南宋诗坛上独树一帜。在《白石道人诗说》中他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诗学主张,要求独创,重视学习,提出诗歌有四种高妙。其中精思、自悟是他比较独特的诗学观点,承继前代江西诗派的同时又促成了诗学理论的转变,成为贯通江西诗学与严羽《沧浪诗话》的桥梁。
姜夔;诗歌;诗学理论
姜夔(1155—1221),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人。他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除以词名世外,其诗又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在《白石道人诗说》(以下简称《诗说》)中他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诗学主张,要求独创,重视学习,其中精思、自悟是他比较独特的诗学观点,承继前代江西诗派的同时又促成了诗学理论的转变,为宋代诗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正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的:“在江西诗派以后,在《沧浪诗话》以前,可以看出诗论转变之关键的,应当推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了。”[1]P308
一 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
对于姜夔的诗歌创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运思精密,而风格高秀,诚有拨于宋人之外者,傲视诸家,有以也。”他的学诗经历,主要学黄庭坚,初从江西派入手,后又转学晚唐陆龟蒙,这就使他的诗歌风格兼有江西派的清劲明朗和晚唐诗歌的蕴藉绵渺。虽然他在后来学有所成时宣称“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2]P1。但这种“悟”是“学”到一定境界时的一种质的提升,创作由此进入了相对自由的状态,不是初学者所能达到的;学是初学者入门的工具和凭借,就像姜夔所叙他自己学诗经历了三个阶段,刚开始“泛阅众作”,在“病其驳”之后“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2]P1,始“大悟学即病”,这三个阶段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由博学到学有专攻,再到对所学进行批判,形成自己的诗学思想。“大悟学即病”是他意识到江西诗派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这种借鉴因循的诗歌创作方法,刚开始也许有利于那些诗才不高、学养不够的初学者,但长此以往,一味自限门径、视前人诗法不可逾越的思维定势会成为牵制他们的一条无形锁链。因此他和前辈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诗人在诗学思想上得到了契合,盛赞独创精神,要求推陈出新,走有自我风格的创作途径。
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二)》中提出诗歌创作要有创新精神:
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彼惟有见乎诗也,故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及其无见乎诗也,故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如泥,如水在器,其苏子所谓不能不为者乎?
姜夔的这段话乍看下文辞比较简单,但却蕴含着很深的道理。彼“有见乎诗”的“求与古人合”或“求与古人异”的诗歌创作方法,吻合江西派所谓“夺胎”、“换骨”之说,这种创作让作品难以规避“古人”的影子,因而缺乏个性,切中了江西诗派的创作弊病。要走出古人的窠臼,还不若“其无见乎诗”的高妙,有意求与古人合,断能相合,虽不求与古人异,必能异,达到“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自然兴会式的领悟,这样的创作方式走向了江西诗学的另一端,于当时诗坛风气来说是反拨,是一种创新。假如诗歌的发展总被古人拖后腿,那也是诗歌发展的悲剧。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以下简称《自叙》)中总结自己的创作说:“余之诗,余之诗耳,穷居而野处,用是陶写寂寞则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钓能诗声,不惟不可,亦不敢。”他认为自己的诗是抒写自己情性的,“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诗说》),若对前人亦步亦趋那今人就沦为了古人的影子,没有了诗人的“灵魂”乃至时代的特色。姜夔要求的是自成一家,而当时的社会评判风气是崇尚模仿,诗人以善模仿来钓取诗名,对于有很强个人意识的姜夔来说“不可”,这是“俗”,他要求“不俗”,具体到诗歌创作上,他认为“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此外,姜夔结合自身创作实践,在《诗说》中树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标准:“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他明确以气象浑厚、体面宏大、血脉贯通、韵度飘逸的风格特征反对江西诗派过于雕刻、注重字句的习气, 生涩瘦硬、奇崛拗峭的风格,对于打破江西诗派的藩篱,这种主张可以说是慧眼独具,也赢得了后世严羽的共鸣,严羽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3]P7,此外严羽重盛唐、尚妙悟、反雕镂的诗学观念又和姜夔多有关联。《诗说》可以说有贯通江西诗学与《沧浪诗话》的诗学意义。
二 益 学
如上所说,姜夔虽然大言“学即病”,但这主要针对江西诗派因循模拟的不良风气说的,在姜夔那个时代,诗歌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唐诗这座壮伟的高峰,江西诗派也已经走过了它的光辉岁月,沿着梅欧苏黄的巨人脚印,追寻着中兴四大家远去的背影,前人已经给姜夔那个时代留下了丰厚的财富。姜夔深刻地认识到初学者走入诗歌的殿堂还是要通过学习,他说:“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姜夔阐明了其作诗话的目的:“《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能诗而后能尽我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一是艺术创作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精通者总结艺术经验,不仅可使自己的创作不断精进,而且可以给初学者指示门径,从而壮大诗人群体;二是通过《诗说》抛砖引玉,让“能诗者”尽其之说,加快诗学理论的建构。
《诗说》的这两个创作目的,从最表层看,他多谈作诗之技巧方法,把指导后学放到了首位。《诗说》全文共30条,其中诗歌创作论占了很大的比例,主要涉及到诗的辨体、立意、布局、措辞、说理等多方面,另外也包含了诗歌的审美取向,诗源和诗评。许印芳在《诗法萃编》中说:“语语精致,中有旨意深微者,初学猝难领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积学有年,细绎其言,始能解悟。”此语一语中的。另外,姜夔又说 “沉着痛快,天也。自然学到,其为天一也”,把天才和后天学成者的成功置于同等的地位,无疑给了才性不足的诗人以安慰和鼓励。
而益学的目的在于学习前人的基础上突破前人的束缚,作诗最主要的是体现不同个体的情感内蕴,不是恪守已有的体制。姜夔在《自叙》中说:“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下逮黄初,迄于今人,异韫故所出亦异。或者弗省,遂艳其各有体也。”他崇尚《诗经》三百篇的自然天成,从汉代至宋,很多诗人因自身禀赋天性不同而写出了有个性的诗篇,但是也有很多末流的作者不懂世易时移的道理艳羡诗歌固定不变的体制,因而偏离了诗歌创作的正道。
所以,姜夔所说的学,只是诗歌创作中的一个台阶,学习前人的优秀成果和成熟的诗歌创作技法,在诗歌创作中检验提升,若有窒碍则又回归到学,同时又不能死守成法和固有体制,以形成自身独特的创作风格、体现自身独有的情感内蕴为创作的旨归。这就是是姜夔给后学指示的门径。
三 精 思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在要求“益学”的同时姜夔论诗主张“精思”。《诗说》认为:“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奚为?”只有通过“精思”,即创作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诗歌创作才能“工”,才能“造乎自得”,具有“一家之风味”;否则,诗歌平淡无奇,即使量再多,但出不了精品,也是无益。可见,姜夔一方面强调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他又有求精求好的重质意识,重视诗歌的审美效果,非常可贵。
对于“思”,有“覃思、垂思、抒思之类”[4]P500,比如葛立方说“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扼,有物败之则失之矣”[4]P500,这涉及到创作灵感问题,而姜夔的“精思”则是创作主体的自身心理状态及在情绪、态度、情感、意志“共同作用下的心理过程,涵盖内容远胜于葛立方的“诗思”。“精思”一词,较早见于唐代皎然的《诗式序》:“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这里的“精思”具有名词性质,它作用于万物“万象不能藏其巧”,是一般人不能及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带有一种神秘性的色彩,而姜夔的“精思”的指向则是求诗的“工”,以及达到诗的“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相对有了可行性。另外《诗式》又反复强调“苦思”,也只是单方面的立足于创作主体本身精神肉体的体味,对作品本身没有审美上的要求。和姜夔的“精思”有类似诗学价值的如《河岳英灵集》中殷璠评价刘眘虚的诗“思苦语奇”,殷璠也注意到了创作中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以及作品为之呈现出的美学风貌,这种美学风貌蕴含着创作者自身的意志情感。然它能涵盖的面还是不及姜夔的“精思”广泛:精思的指向,不仅是作品整体风格,还包括了诗歌创作技巧、结构布局、措辞说理和审美等方方面面
姜夔精思的落脚点,包括了创作论、审美论和诗学批评这些方面。以创作论为例,他认为措辞、用事、说理、写景须做到:
难说处一语而尽, 易说处莫便放过; 僻事实用, 熟事虚用; 说理要简切, 说事要圆活, 说景要微妙。
在意与辞的关系上, 姜夔提出了意格决定论: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 格出于意,先得意也。
意格欲高, 句法欲响, 只求工于句字, 亦末矣。故始于意格, 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远, 句调欲清、欲古、欲和, 是为作者。
另外,姜夔论说了谋篇布局和他的审美思考:
作大篇,尤当布置。首位匀停,腰腹肥满。多见人前面有余,后面不足; 前面极工,后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 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
即讲究文章结构要安排的详略得当,不能虎头蛇尾,讲究意蕴和法度,做到波澜起伏,开阖变化,获得“出入变化,不可纪极”的表现力。这也是对诗歌整体审美效果的思考。
姜夔以上的诗歌创作论,明确表现出姜夔的“精思”中有“法度”意识,另外要有求新求奇的独创意识,这正是对江西诗学精神的继承。而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是履行了他的要求,他《送项平甫悴池阳》诗说:“如切切秋虫语,自谓平生用心苦。”正是他苦心孤诣、用心良苦的写照。
四 自 悟
除在创作技法上殚精竭虑外,姜夔又在《诗说》中提出四种“高妙”之境,这是“精思”所趋,同时也超越了“精思”的涵盖:
碍而实通, 曰理高妙;出自意外, 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姜夔所谓“理高妙”,是指诗在理法上要因难见巧,自至理高妙的境界;所谓“意高妙”,是指诗的立意要超出一般,求新求怪,达到出人意表的境界;所谓“想高妙”,是指需要精思,把幽深细微的外物写得透沏清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所谓“自然高妙”,是指诗的风格不尚险求怪,文采不求华美,如出水芙蓉,达到妙不可言的那种的艺术境地。要达到这四种妙境,姜夔提出了:“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他意识到要凭借文字达到妙境,前三种妙可以在学习前人、精于思考的基础上酝酿悟入,然第四种妙恰是通过“悟”这种灵感迸发的方式获得,笔补造化,有如参禅,姜夔最为属意。
“悟”即借助于禅宗的“悟入”方式来领会“诗法”,在遍参诸方的基础上以期一朝顿悟,江西诗派的黄庭坚、韩驹、吴可和吕本中的诗论都已提出。
学诗当如学参禅,为戊切边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韩驹《赠赵伯鱼》
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吴可《学诗诗》)
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吴可《藏海诗话》)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功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吕本中《童蒙训》)
韩驹和吴可追求的是一种既学步前人又不墨守陈规,既有法而又不拘成法的超脱,但因为江西诗派自黄庭坚以来过分执着于诗法和句法,江西诗派的创作一直未臻“不烦绳削而自合”的佳境。至吕本中也求悟入,他推重谢朓“流转圆美如弹丸”的佳妙,希望求新求变,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自成一家。
再看姜夔,他所要达到的“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创作主体需要在自身艺术修养到达一定境地后而得,难免刻意,本质上没有跳出吕本中他们的圈子。至于“自然高妙”,则是摒弃了所有理性因素、人为修饰,得益于瞬间的兴感神会,纯粹是一派任心而发,浑然天成的气象。对于这种气象,陈伯海先生认为“(姜夔)将悟的对象由文字、意象提升并导入诗歌内在的意境与韵味,便直通向了宋末所倡导的‘妙悟’说”[5]P254。因而超越了吕本中等前辈的诗学思想。严羽认为“妙悟”乃诗歌创作的本色当行,同时又标举“兴趣”,赞叹“妙悟”和“兴趣”并举的诗歌 “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3]P26,和姜夔所倡的“自然高妙”相吻合,可说是美的极致。然姜夔“无见乎诗”的审美态度及灵感迸发式的诗歌创作方法又不同于严羽所倡导的熟读、涵咏前人好诗以立识开悟,两者和而不同。
综上所述,姜夔的诗歌创作态度一方面承继了江西诗派的诗学精神,同时他又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不应以古人为依傍,诗人的创作虽说未完全脱离江西诗派崇古思想的笼罩,但他毕竟以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了自己的诗歌创作方向,强调“益学”和“精思”,他的四种高妙之说在诗话史上独树一帜,因此可以说超越了江西诗论,成为从江西诗学到严羽《沧浪诗话》接力的关键一棒,应该受到后人的重视和研究。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2]孙玄常.白石道人诗集笺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3]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葛立方.韵语阳秋[A].[清]何文焕.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5]陈伯海.中国诗歌之现代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I206
A
1673-2219(2010)10-0071-03
2010-06-13
晏萍利(1980-),女,江苏常熟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王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