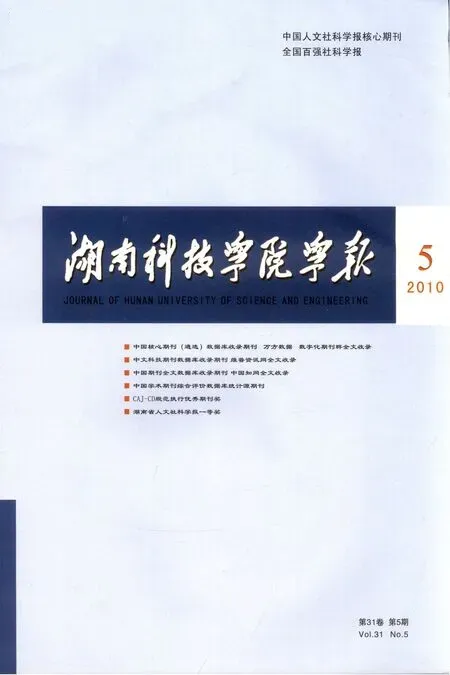解读《诗经》中的女性意识
2010-04-07刘海燕
刘海燕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甘肃 成县 742500)
解读《诗经》中的女性意识
刘海燕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甘肃 成县 742500)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女性是其中一道夺目的风景线。《诗经》中的女性具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呈现,在这些多姿多彩的女性生活呈现中,清晰可见丰富而独特的女性意识,文中论述了女性的觉醒意识,反抗意识和忧患意识。
《诗经》;觉醒;反抗;忧患
千百年来,人们对《诗经》的解读异彩纷呈。作为女性参与创作的文本,《诗经》中的女性意识非常浓郁。女性和女性意识,是“五四”时期随着人的解放大潮才出现的现代词语。近年来女性意识这个主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关于女性意识的探讨非常热烈,对女性意识的理 解也不尽相同,女性学家陈志红说:“所谓女性意识,一方面源于女性特有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在体验与感受外部世界时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角度,这实际上是一种性别意识,这时它更多地属于自然属性的范畴;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决定着女性意识发展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的历史内容。”[1]
一 女性的觉醒意识
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集中体现在对女性压抑的精神扩张和对爱情自由、婚姻幸福的大胆追求和讴歌上。我们知道,西周时期已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确立了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因而女子在社会地位与婚姻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没有自主权,没有为自己争取自由的权力。长此以往,她们自觉不自觉都接受了那些不平等的道德规范,全部的精神都受制于丈夫了,不幸的婚姻产生了怨妇和弃妇,这些遇人不淑的女子,在《诗经》中比比皆是。她们大多含悲忍泪,默默地承受,屈辱地生活。
然而《诗经》中的某些女性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她们在爱情婚姻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若遭背弃,她们就奋起控诉男子的薄情寡义,捍卫自己的尊严,为自己讨回公道。尤其是弃妇诗,在闺怨之余大多透露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卫风·氓》为代表的弃妇诗固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诗中弃妇的哀伤里含有其无限的悔恨,她既恨“二三其德”的丈夫,同时也恨自己的轻率,并且在“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慨叹里,充分认识到了男女在爱情上的不平等。这种“把男女放在同样是人的地位上来思考自己的悲剧,充分显示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2]P79
《郑风·褰裳》表现了一位少女对所爱男子的戏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这位女子主动挑衅,可谓狂野不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她的女性个性。她虽然深爱这个男子,但毫无哀告乞求之意。这一点表达了女子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不依附于男子,而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愿望。显然,在爱情面前,她要求与男子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利,决不任人摆布。这种意识,表现在封建社会地位极低的一个女性身上,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有力挑战。
《诗经》中主体意识觉醒的女性不再是一味地幻想、祈求,而是清醒地认识了她身边的社会:即使遭弃、即使受到群小的侮辱仍然不甘屈服!《邶风·柏舟》中的女子便是这样一位觉醒者,“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女子倍受摧折凌侮,含垢忍辱,暗中擦泪,捶胸顿足之外,难得的是还有一颗高飞的心!这些蕴含蓬勃生命力的女性,当她们失去平等、自由时,倾泄而出的是满腔的怨愤,随之而出的还有对刚确立的礼教制度的否定和蔑视!然而,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女性都处在低于男性的地位,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意识难以产生具有时代意义的大规模觉醒,只能是零星的、片面的觉醒。
二 女性的反抗意识
女性的反抗意识,是指女性在面对男权的压迫和损害时,表现出的自我意识和对压迫者的控诉与反抗。《诗经》中的反叛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的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抗婚姻不自由,二是抨击吃人的礼教。
《鄘风·柏舟》:“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诗经译注》云:“这是一位少女追求婚姻自由,向‘父母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之命’公开违抗的诗。”[3]P24这个女子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她希望嫁给意中人,却遭到母亲的反对,面对高堂严命,她既没有放弃主张,俯首听从,也没有左右为难,束手无策,而是执著坚持,勇敢抗争,大声疾呼道:“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既喊出了她对阻碍爱情幸福势力的满腔愤怒,对封建礼教的指责与反抗,又表白了对爱情的真挚与专一,其刚烈的个性表现出了追求爱情自主与婚姻自由的渴望。在《诗经》时代,“违犯礼教的规定而自行结合的行为被斥为‘淫奔’,社会不承认这样的婚姻。”[4]在清楚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女子仍坚持这样做,足见其反抗的坚定,而坚定的信念源于她对命运负责的反抗意识。
《召南·行露》反映的就是对仗势逼婚者的坚定反抗,表现了女子的坚强意志和反抗强暴的战斗精神。开始时“厌邑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只是怕遇人不淑,如同露水沾湿衣服一般。“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亦不女从!”这话语中包含着悲剧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强者,她依然坚强不屈,机智地捍卫自我的人格与爱情的尊严。她不愿意受金钱、虚名的诱惑,这就使得她不同于时代的平庸女子,她不顾权势的威逼,这更是她勇敢的表现,她用自我的行动愤怒地捍卫着作为女性的尊严。其间更多的是悠悠的怨,是对男子强行逼婚的怨,是对男权至上的怨,是对一夫多妻制的怨,是对男人的喜新厌旧的怨,是对女性地位卑微的怨,她的怨代表着所有时代女性的心声。这是《诗经》中第一首反抗妻妾制度的诗歌,这个勇敢的女性成了后世女性抗拒逼婚的榜样。也许有了它的照明指引,才有了后来梁祝用生命来抗婚捍卫爱情尊严的悲美。
而《大车》中的女主人公则冲破了道德的限制,要求同爱人逃往远方,这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这样的勇敢里表现着面对强大势力的坚强与决心,这样的勇敢里更多的是女性对爱人那悠悠的痴情,没有了这份痴情,也绝没有离经叛道的反抗。《郑风·将仲子》中,一个女子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她不得不含泪告别爱人,但是在她的心里涌动的仍然是对礼的抗争和反叛,礼无法从心里抹杀她对“仲”的思念。
中国历来不乏反抗这种礼教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冲击着压制在他们身上的非人礼教。《诗经》中塑造了这样一批富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反抗是她们关注个人命运与生活的开始,是女性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健康向上的心理体现。
三 女性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女性意识,除对自身情感的关照和对礼教制度的对抗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那就是女性作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然有对自己国家所产生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秦风·小戎》这首诗,通过女主人公回忆丈夫出征时的壮观场面,进而联想到丈夫给她留下的美好印象,希望他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早日凯旋。尽管诗中也有温情脉脉的情思,也有婉约缠绵的寄语,但流露出更多的是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
《载驰》更是这样一首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勇于打破礼教桎梏的作品。“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毛诗序(小序)云:“《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不得,故赋是诗。”可以看出,无论是《诗序》还是后世注家均认为这是中国第一位女性诗人许穆夫人所作,诗的主题是赞颂女主人公弃习俗之小礼顾国难之大礼的远见卓识。许穆夫人一听到卫国沦陷,没有顾及女性无三年之丧不许出境之礼,匆匆回国吊问卫候。长路漫漫,炽情悠悠,然卫大夫迎她于潜,不体恤其忧国之情,却苛责她有失礼之举。面对非难、面对国乱和一个个没有主见急救国难的国人,她不能马上回到许国,又无法抑止浓烈悠远的情思。于是她想登山化情和采摘贝母疗情的方法,这一行为倒使她由化情到泄情,倾诉了女性的思虑和主张,为什么她受扰于许而又不见谅于卫呢?她由通过郊行去移情,“芃芃其麦”又加剧了亡国之痛和救国之念,刚毅的勇气,果敢的行为,卓尔不群的政治预见使她鄙视那些怯懦的大夫君子,“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全诗充斥了作者对故国危亡的爱国、忧国之思以及对许大夫轻视自己意见并阻止自己救卫的愤怒之情,诗者真实的心灵世界在强大的男权统治下本色流露,呈一种外放张扬之征,而在情感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个性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可触可感。这时女性考虑的不再是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了,而是自己国家的兴亡,这是女性忧患意识的具体表现。
思妇诗中的女性尽管深恋自己的丈夫,但在个人,家庭和国家中能以国家为重,将思亲与忧国很好地结合起来。《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作品中以全知叙事视角,展示了思妇和被思人物的两个声音:一个是在外被思人的声音,这个声音中透露出国家有事,子民自当奋不顾身急赴国难,不敢偷闲、休息;一个是思妇的声音,表现出家人的思念与劝慰,既勉励亲人有所作为,又以“归哉归哉”三章复沓咏唱,表达出深切的呼唤,传达了思念之情。
无论是《小雅·采绿》中心不在焉,无心装扮的妇女(“终朝采绿,不盈一匆。予发曲局,薄言归沐。”);《周南·卷耳》中无心劳作,借酒浇愁的贵妇(“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还是《小雅·杕杜》中求卜问盆,优思劳瘁的女子(“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在对丈夫的殷殷思念之情中,都包含着她们一种深深的忧国忧民之情。可以看出,《诗经》女性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忧患意识,是女性天然具有的,男性的高压,赋予了它凄凉色彩。
[1]陈志红.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思考[J].文艺理论家,1987,(2).
[2]陈鋆宝.试论《诗经》中的弃妇诗及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11).
[3]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康正果.风骚与艳情[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责任编校:王晚霞)
book=28,ebook=98
I206
A
1673-2219(2010)05-0028-02
2010-03-19
刘海燕(1976-),女,甘肃西和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语、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