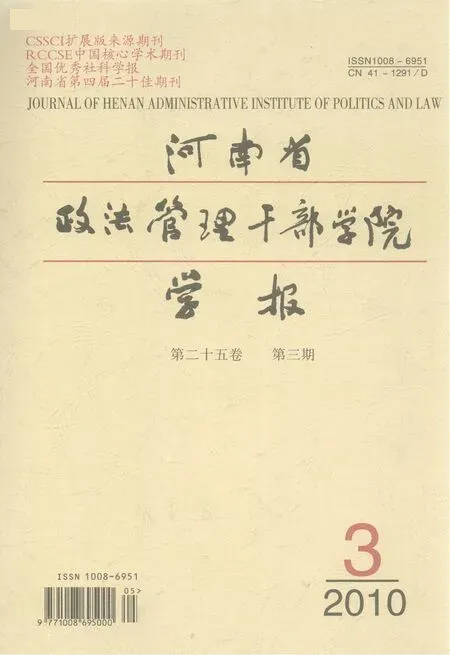法律的人性关怀与刑罚轻缓化
2010-04-07李希慧龙腾云
李希慧 龙腾云
(1、2.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法律的人性关怀与刑罚轻缓化
李希慧1龙腾云2
(1、2.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人性就是人类基于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所产生的内在需要。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这与资产阶级倡导的唯心主义私欲观、利己主义是不同的。实现人性的手段可以做价值判断,人性本身却没有善恶之分;人性不能得到满足是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尽量满足人性而不是压制人性;人性满足得越充分,发生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人们对刑罚的敏感度也越高;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方面的人性需求,在当今我国还需进一步满足,以便为刑罚轻缓化创造良好的氛围。
人性;需要;刑罚;轻缓化
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限制死刑并最终废除死刑”也已成为我国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加速刑罚轻缓化的进程无疑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要使某一个事物减少或者消失,不可避免地要分析这个事物产生的原因。笔者以为,刑罚产生的机理可以这样理解:任何人都有欲求,人们的欲求通过合法的方式得不到满足,探索欲和冒险欲便驱使行为人突破禁忌、采用犯罪的方式去争取;为了控制非法满足欲望的方式,维护社会的稳定,刑罚便应运而生了。人类的这种欲望恰恰就是人性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①从先秦而至现在,儒道两家对于“人性”和“人欲”的概念,大体都是“同出而异名”地在应用了。详见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 179页。。刑罚实际上是采用“堵”的方式来控制人性的“洪水”,但“疏导”的方式也许会更有效——也就是在人类犯罪前就尽可能满足人性。因此,可以这样推断,制度的人性关怀有利于刑罚的轻缓化,人性的充分满足也会加速刑罚消亡的进程。
一、人性无善恶
(一)人性概念的界定
人性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和话题。哲学上,人性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各种特性或属性的总和与概括。……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1]。也就是说,人性从人的本质角度来理解,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有人进一步认为,人的本质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个人和他人的关系,还应该包括每一位单体所具有的个性。这种观点认为“人性是指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为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而表现出来的本质属性。它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是建立在人类各种需要基础之上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对立体”[2]。
还有人认为,“人性的实质就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更好地适应人文社会生活表现出来的能力、行为和心理素质”[3],“人性的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但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一曰追求性,二曰竞争性,三曰合作性,四曰文适性”[4]。
陈兴良教授认为,“人性,又称为人的本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在理论上,人性是一个魅力
我们认为,不论学者们怎样表述人性,实际上都离不开“需要”这个基本的要素,正是基于需要,人类才表现出他的本质属性。这种需要可能是自然的、可能是社会的、可能是物质上的、可能是精神上的。就人的自然属性而言,与动物的本质无异,比如对食物的需要、对性的需要等。就人的社会属性而言,它是人作为有尊严的社会成员的一种需要,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动物是不具备的,比如对权力的需要、对财富的需要、对平等的需要等。这种需要是后天形成的,与人类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人类需要的复杂性,在本质上与动物区别开来,因为动物除了自然的需要外,别无他求。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说:“个人有许多需要”,“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7]。“人的需要不纯粹是生物性的因素,而是历史因素,它不仅为人的肉体组织所引起,也为生产活动等历史条件所决定”[8]。因此,我们认为:人性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是人类基于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所产生的内在需要。这种需要与资产阶级倡导的唯心主义私欲观、利己主义、利益至上原则是不同的,这种需要也是由一定的客观物质和社会条件决定的。本文也正是从唯物论的“人性需要”层面来论证人性的满足与刑罚发展的关系的。
(二)人性没有善恶之分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的先哲们都建立了各种人性学说。比如,我国古代孟子建立了性善论,荀子倡导性恶论,韩非子提出了人性自私论,意大利哲学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倡导“人性邪恶自私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性是“唯利是图”的。先哲们谈论“人性”的善恶自私、唯利是图,与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人性,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哲学主要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界定人性,比如人性的善恶之争,西方哲学对人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性与经验的争论上。孟子、荀子以及西方哲人们讨论的人性之善恶,是对满足人性手段的一种评价,而非对人性本身的评价。人性善恶论都是将“人性”与“人性的评价”混为一谈。如果将人性理解为“内在需要”,无论是人的自然属性,还是人的社会属性,本身都没有善恶之分,人性是无法也不必做出价值判断的。
比如,近代经验主义思想家洛克把人的心灵看做一张白纸,没有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理性,人通过对外界的感觉和内在的反省得到的观念,写在这张纯洁的白纸上。因此,人性本质上是中性的,是无法做价值判断的。英国的休谟也认为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他认为一切道德都是人为的而并非人类天性,善恶的观念只有在人类的社会中才存在,并认为人性满足的过程才有善恶之分,也即通过人与外界的交流才能判断出是非善恶。他将判断善恶的标准归结为人获得快乐的方式,而不在于是否快乐本身。他指出,“一个行动、一种情绪、一个品格是善良的或者恶劣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们一看见它就发生一种特殊的快乐或不快。因此,只要说明快乐或不快的理由,我们就充分地说明了恶与德。……我们并非因为一个品格令人愉快,才推断那个品格是善良的;而是在感觉到它在某种特殊方式下令人愉快时,我们实际上就感到它是善良的”[9]。也就是说,休谟认为判断善恶的对象是人性实现的过程、方式或者载体,而不是人性本身。所有人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边沁也认为,“一个行为是善是恶,只要考虑它的结果如何而定。其所以是善,是因为它能够引起愉快或排除痛苦;其所以是恶,是因为它能够引起痛苦或排除愉快”[10]。也就是说,善恶仅仅是对行为结果的评价,而不是对行为产生的内在需要进行评价。例如,基于人的生理需要而欲与其他社会成员发生性关系,如对方同意且在隐蔽处为之,则双方获得快乐并且众人没有痛苦,那么该手段是善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如果对方不同意而为之,则手段是恶性的。无论手段是善是恶,引起手段行为的性欲没有善恶之分,是绝对纯洁的。再比如,基于权力欲,行为人在既有规则体系下获得权力,自己的权力欲得到满足是快乐的,多数人认可他获得权力,那么多数人是快乐的,因此综合评价行为是善的或者至少是中性的;在规则体系之外获得权力,得权者独乐而众人不悦,综合评价行为是恶性的。无论获得权力的手段是善是恶,但权力欲本身没有任何善恶之分。
因此,人性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所有人性在道义上都应该得到满足而不是被压抑,国家和社会需要甄别的仅仅是满足人性的手段。
二、人性得不到满足是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
人类实施犯罪行为,有着多种复杂的原因,其中有的是个人的心理、生理原因,有的是社会原因,还有的是环境原因,有时是一种原因起作用,也有时是多种原因起作用。但是,无论哪种原因,我们认为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终极的原因,即人性得不到满足①当然,人性能否真正得到满足尚需探讨,它直接关系到事实上的犯罪能否消亡,但人性能否满足的疑问不应该成为压制人性的理由。本文认为刑罚有消亡的时刻,由此可以推导出:需要给予严厉处罚的当今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也会消亡。至于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事实上的犯罪是否会消亡,尚需进一步讨论。。
人性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中建立了“需要体系”,将其概括为三类:自然需要、社会学需要和精神需要[11]。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1)生理需要。这是最基本、最强烈的需要,如对食物、饮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气的需要,这是对生存的需求。(2)安全需要。要求生活有保障而无危险,如对生活秩序与稳定的需要。(3)归属需要。与他人亲近,建立友情,相互依赖,在自己的团体里求得一席之地,有所依归。(4)尊重需要。……(5)认知需要。即对知识和理解的欲求,或者按照通俗的说法就是好奇心。……(6)审美需要。即人们对美的需要,如对对称、秩序、和谐等的需要。……(7)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人的成长、发展、利用潜力的需要。马斯洛把这种需要描述为一种想要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样子,实现人的全部潜力的欲求。”[12]上述各种欲求或者需要是人性的基础,这种欲求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满足,就会滋生各种犯罪。正如圣经所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叔本华也认为人的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所以人只能忍受。马克思曾对资本家的逐利性做过十分形象的说明,从某一方面印证了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将会导致严重的恶果,他在《资本论》中写道,“……有 50%的利润,它(指资本,笔者注)就积极地大胆了;利润达到100%,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利润达到 300%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资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着绞首的危险了”[13]。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犯罪现象:行为人之所以实施政治方面的犯罪,是因为人们的权力欲无法在合法形式下获得满足;行为人之所以实施经济方面的犯罪,是为了获得财富以满足自己的利益欲望;军事战争方面的犯罪就是集团或者利益团体固有利益得不到满足,不得不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抗争的活动;文化方面的犯罪,是行为人欲获得先进文化而不达或者自己所持的文化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造成的恶果;生态方面的犯罪,是行为人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破坏自然界的行为……总之,一切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都是行为人的人性不能通过正常的方式获得满足。
三、规章制度应该最大限度满足人性而不是压制人性
(一)顺应人性的制度能够减少犯罪的发生
矛盾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是虚幻的,所以我们应该正视矛盾,而不是逃避矛盾,更不应该人为制造矛盾。尽管人性得不到满足是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将人性扼杀在摇篮中。假如我们遏制了所有人性要素,那么人也就不能称之为人。正是因为人性本身无善恶,所以我们在面对人性得不到满足这一矛盾时,应该尽量满足人性,而不是压制人性。反观我们的刑罚,不是为人性的宣泄寻找出口,而是极力抑制并设立了一堵更高的墙,从这个意义上说,刑罚也在制造犯罪。“法律向人宣布:‘你要是犯罪,你就得完蛋。’而它却使人处于非犯罪不可的境地。”[14]因此,国家的规章制度应该尊重人性,顺应人性,使法律防患于未然而不是止患于已然,使得人们不是不敢犯罪而是没有必要去犯罪。
压制人性的法律将会引起更多的不法,压制人性的刑法将会引起更多的犯罪,顺应人性的刑法终将会使刑罚消亡。因为人性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刻,将是刑罚自己消亡的时刻。鉴于此,国家的各项制度应该提早为人性的宣泄找到一个合理的出口,这样做有利于减少犯罪的发生。比如,成熟的民主制度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权力欲和平等欲,当这种人性得到更好满足的时候,阶级方面的犯罪、政治方面的犯罪将会减少甚至消失;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分配的公平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财富欲、平等欲,当人们的财富欲、平等欲得到很好满足的时候,经济犯罪和生态犯罪将大大减少;经济全球化消灭疆土界限,逐渐消灭国家主权和军事存在,那么走私类犯罪、国家间犯罪、军事犯罪等跨疆域犯罪将不复存在。因此,从理论上说,人性得到满足的程度越大,犯罪率将越低。
(二)人们对刑罚的敏感度与人性满足的程度成正比
同样的一种刑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感受是不同的。“人的想象,自然而然适合于所在国的习俗;八天监禁,或轻微罚款,对于一个生长在温和国家的欧洲人,其刺激的程度,不下于割去一条手臂对于一个亚洲人的威吓……一个法国人受了某种惩罚,声名扫地,懊丧欲绝;同样的惩罚,施之于土耳其,恐怕连一刻钟的睡眠都不会使他失去。”[15]也就是说,在温和、崇尚自由的国家里,自由是多么的重要,监禁八天堪比失掉一条手臂,但是在一个把犯罪人不当人看的社会中,失掉一个手臂也算不得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刑罚的轻重,取决于人性满足的程度。人性满足得越充分,人们对刑罚的敏感度越高,刑罚就可以越轻;人性越被压制,人们对刑罚的敏感度就越低,刑罚就不得不更重。
以崇尚自由的人性为例,一个国家能够给予公民的自由越多,刑罚就可以越轻。恰如孟德斯鸠所言,“刑罚的增减和人民距离自由的远近成正比例”[16]。人们对刑罚的感受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法律越制造尊重人性、尊重自由的氛围,人们就越能感受到监禁刑的威力。“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总是顺应着它周围的事物,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生机勃勃的欲望力量使得轮刑在经历了百年残酷之后,其威慑力量只相当于从前的监禁。”[17]
再以追求平等的人性为例,比如说政治越民主,针对政治犯罪的刑罚就可以越轻。孟德斯鸠认为,“严峻的刑罚比较适宜于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政体,而不适宜于以荣誉和品德为动力的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在政治宽和的国家,爱国、知耻、畏惧责难,都是约束的力量,能够防止许多犯罪。对恶劣行为最大的惩罚就是被认定为有罪。因此,民事上的法律可以比较容易纠正这种行为,不需要许多大的强力。”[18]“如果一个国家,刑罚并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话,那就是由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罚。”[19]孟德斯鸠很好阐述了民主对于减轻适用刑罚的重要作用。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专制社会中,废除死刑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讲,是一种梦幻般的神话,然而在当今中国,人权观念、民主观念已经深入民心,废除死刑的总趋势也已不可逆转。如今,世界上已经有 100多个国家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了死刑。死刑的废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性得到较好满足、人们对刑罚灵敏度增强的必然结果。这也能够充分解释如下现象:为什么有的国家民众对于取消死刑能够接受,有的国家民众对取消死刑觉得不可思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各个国家对人性的尊重程度不同,因此形成的社会氛围不同。一个专制的、等级的、不自由的、没有把犯罪人当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对待的国家,取消死刑比登天还难;相反,一个民主的、平等的、自由的、把犯罪人当成一个正常人看待的国家,取消死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当今我国刑罚轻缓化所需满足的基本人性诉求
所谓刑罚轻缓化是相对于刑罚的严厉、残酷而言的,是刑罚进化过程中向着轻缓方向发展的一种趋势。刑罚轻缓化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思想,也就是国家尽量控制刑罚的范围和严厉程度,以尽可能小的刑罚或者非刑罚获取最大程度的社会稳定。但是,刑罚能否轻缓化是由人性满足程度决定的,如果人性被过度地压制,过轻的刑罚将不足以威慑和抑制犯罪,很容易导致社会混乱。当今我国在民主、自由、平等方面较过去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与刑罚轻缓化特别是废除死刑所需满足的程度,还有一定差距。实际上,人性的内容十分复杂,刑罚轻缓化所需满足的人性诉求也十分广泛,加之文章篇幅有限,本文不一一列举。考虑到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的重要性,我们仅从这三方面做一粗略归纳。
(一)民主
民主与专制相对,专制强调对人的束缚,是遏制人性的,民主是宽容的,尽量满足权力欲和平等欲的。民主能够让竞争与平等的欲求得到较好的回应,大大增加了政治的稳定性,有力地减少了犯罪尤其是政治方面犯罪的发生。例如,历史上推翻昏庸君主统治的武装暴动等犯罪,在当代民主社会已经被柔和的民主选举取代;民主、竞争、平等参与的人性诉求得到了较好满足,在一定意义上消灭了武装暴动或者军事起义。
(二)自由
自由主要包括人身自由、财产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等;自由的实质是国家、社会赋予公民多少权利的问题。
1.人身自由方面。
人有没有处分自己身体的自由呢?从刑法的角度和尊重人性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处分自己身体的自由应该获得尊重。比如自杀、通奸、淫乱、吸毒等等,都不应该入罪。
再以迁徙自由为例。人类自古就有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的习惯,应该说,选择适宜的生活环境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人类却以种种理由抑制人们的迁徙自由,比如我国的户籍制度。实际上,这些制度都是人为限制人性的做法。只有尊重人性,只有给行为人更多的自由,那些因缺乏自由而产生的犯罪才能渐渐减少甚至消亡。再比如,按照经济一体化的思路,取消所有货物的关税,那么走私罪实质意义上就不存在了;如果两国人员可以自由往来,那么偷越国边境罪某种意义上也就消失了。因此,上述这些消灭国家疆界或者城市与农村疆界,促进国家、社会“相互融合”的制度,都是尊重人性的制度,都应该大力提倡。尽管在短时间内,某些制度还不能迅速做出改变,但是从尊重人性的角度看,赋予人们更多的人身自由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2.财产自由方面。
讨论财产自由,绕不开财产自由权这样一个概念。财产自由权一般是指财产所有人自由地占有、使用和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或公民权,是其他所有权利能否实现的关键。对于财产自由的保护,罗伯斯比尔有过精彩的表述,他说:“如果贫困这个最严厉的法律迫使人民中最健康的和最众多的那一部分放弃权利,那么法律对于权利平等的原则表示假仁假义的尊重又有什么意义呢?”[20]他认为,财产自由的首要权利——财产合法占有权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要求大多数的富人放弃这一权利,那么法律就是假仁假义的平等。我国的立法实际上也已经注意到了对财产自由的保护:比如,我国《宪法》和《物权法》中都有关于个人合法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的规定,从而赋予了国民更多的占有、处分财产的自由。这一自由的获得,不仅调动了公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满足了人们的财富欲,释放了人性空间,客观上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财产安全秩序。再比如,从刑法的角度看,赌博罪等自愿处分财产的行为,基于财产自由原则也应该除罪化。
3.言论出版自由方面。
我们认为语言、思想、意见和纯文字的东西,都不应该由刑法来禁止。“言语并不构成‘罪体’。它们仅仅栖息在思想里。在大多数场合,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意思,而是通过说话的口气表达意思的。常常相同的一些话语,意思却不同,它们的意思是依据它们和其他事物的联系来确定的。有时候沉默不言比一切语言表示的意义还要多。没有比这一切更含混不清的了。”[21]对语言不予刑事处罚,不仅在于语言含义的模糊性,还在于人们无法判断思想和意见的真理性。“法律只能惩罚犯罪行为,因为这种行为表现在确凿的事实上。但法律不能处罚意见、思想,因为同一种意见和思想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在不同场合和不同人眼里会有断然不同的评价。”[22]陈兴良教授同时认为,“不仅言论不能成为罪体,同样,文字也不能单独构成犯罪,因为文字也主要是一种表述思想的工具”[23]。
(三)平等
平等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对人的一种态度,是人类的终极理想之一,主要含义就是同样的情况获得同样的待遇。平等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都有所体现,我们这里无法兼顾这么多内容,现仅探讨刑罚设置的平等与均衡问题。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最严厉的刑罚是死刑,死刑在威慑犯罪的同时也会造成不平等。比如,故意杀了一个人的罪犯和故意杀了一百个人的罪犯只能获得同样的刑罚——死刑。因此,这种没有差别对待犯罪人的方式,可能会促使罪该致死的犯罪嫌疑人继续疯狂地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贝卡里亚对此做过精彩的描述:“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相同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犯罪了。无论谁一旦看到,对打死一只山鸡、杀死一个人或者伪造一份重要文件的行为同样适用死刑,将不再对这些罪行作任何的区分;道德情感就这样遭到破坏。”[24]正是因为死刑是一种极刑,达到了刑罚严厉程度的顶点,人们无法再对死刑进行详细的区别,造成死刑不能区别对待罪犯,因此,废除死刑或者削减死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为了使刑罚的设置更加有区分度和均衡,刑罚就应拉开一定的梯度。在废除死刑的同时,必须对无期徒刑进行详细分类,比如在假释期限上,在减刑条件上,在执行监禁刑的相关待遇上,惩罚的力度要层层递进,以便让犯罪人和群众感觉到刑罚的公平与均衡。正如贝卡里亚所言,“如果说,对于无穷无尽、暗淡模糊的人类行为组合可以应用几何学的话,那么也很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25]。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刑罚的公平性体现在它的区分度,而不在于它的严厉性。以死刑的取消为例,中国民众倾向保留死刑,并不是他们认为只有死刑才足以表达正义,而是认为取消死刑后的替代措施——无期徒刑不足以表达正义。因为中国目前的无期徒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判处“罪该致死”的犯罪分子无期徒刑就有轻纵犯罪之嫌。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在废除死刑的同时,只要细化无期徒刑的设置,使之形成一个轻重有别的刑罚梯度,将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是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这也充分说明了平等欲的满足有利于促进刑罚的轻缓化。
[1]金炳华等.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1184.
[2]罗艳翎.浅谈法与人性 [J].青年科学,2009, (6).
[3][4]圭田畯.人性新论——人性社会学[M].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78,371.
[5][6]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1,22.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26-514.
[8]中外名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72.
[9][英]休谟.人性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11.
[10][23]陈兴良.刑法的启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99-100,27.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0.
[12]赵家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89-190.
[13]邓林格.T.J.Dunning.工会与罢工[M].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565.
[14][法 ]莫莱里.自然法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8.
[15][法]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40-141.
[16][18][19][2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6,83,85, 198.
[17][24][25][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3,65,65. [20][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52.
[22]张宏生,谷德春.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93.
责任编辑:王 瑞
Caring for Human ity in Regulations andM oderating Trend about Penalties
Li Xihui1,Long Tengyun2
(1,2.College for Crim inal Law Science,Beijing Nor m 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The humanity is the inherent needs of human which are based on natural causes and social causes.Humanity is the subject of human nature a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pt of self desires and egois m of idealism by bourgeois.Though a means of achieving humanity can be made value judgments,humanity itself is not good or evil. The ultimate cause of crime is that humanity can not bemetwell,thusour regulations should try to meet the humanity rather than suppressing it.And humanity should be satisfied more fully.A crime are less likely to occurr when people’s response sensitivity level to the penalties are higher.Nowadays in China,the democracy,freedom,equality and the like,which are of universal value as pursuit of humanity,should be further satisfied,in order to create a good a tmosphere formoderating the penalties.
humanity;needs;penalties;moderating trend
D924.13
A
1008-6951(2010)03-0085-06
2010-01-12
李希慧(1957— ),男,湖北仙桃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龙腾云(1981— ),男,辽宁建平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法学系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无穷而又争论不休的问题”[5]。“人性中既具有理性的因素,又具有经验的因素;人性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特殊性,这两者具有辩证统一性”[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