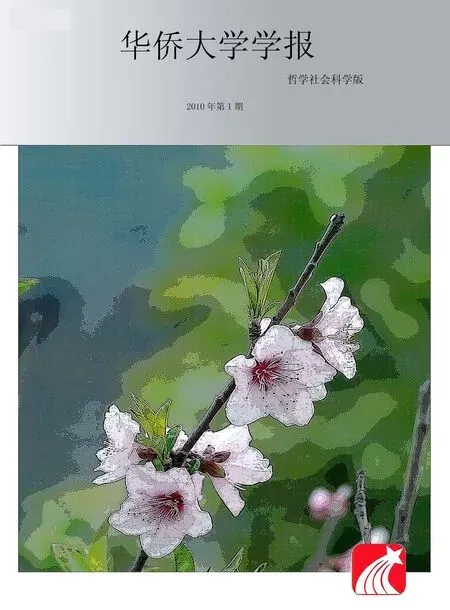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蔡灿津教授的学术品格谈起
2010-04-07吴苑华
○吴苑华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最近30年间,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性研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创新”理论。不过,许多研究不是越来越贴近而是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内涵和科学精神,乃至“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现象”也确实出现了。究其原因,固然有多种,其中,不能不提的是:在当下的学术界,不少研究都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尊重和崇敬之情,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欺世盗名”、“追逐利益”的一种手段,这都成了见怪不怪的现象。问题在于,一旦丢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尊重和崇敬,此类学术研究就难免会陷入功利化、庸俗化、肤浅化之境,乃至滋生某些“恶搞式”研究。因而,摆脱这类学术困境,首先需要我们回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尊重,学会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学者们既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见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内涵和科学精神上,也不要凭借自己的“标新立异”来剪裁、割裂和重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容;它要求学者们在坚持中准确全面地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理论内涵和本质特征,在捍卫中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蔡灿津教授几十年间实事求是地还原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如果不是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吗?!
《濟仕西廬選箋》收录了蔡灿津教授在1978年到2000年间发表的55篇论文,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真理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社会主义辩证法、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问题等,全景式展示了蔡先生几十年间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成就和可贵的学术品格。我们拟从四个方面揭示这一“崇敬地研究”的学术价值。
首先,崇敬地反思了基本理论问题。蔡先生在这方面写下了《重探马克思主义哲学》《单一问题诸多方面说》《论感觉》《真理全面性的真谛何在》《区分真理阶级性中的两个不同的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道德的层次法》等代表性论文,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对诸多基本理论作了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在反思中纠正了以往人们的一些片面认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内涵,创见性地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观点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论”、哲学基本问题的“三个方面说”、真理的“逼近说”、社会基本矛盾新解、“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等学术观点。关键在于,这些学术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原了被人们长期忽视和误解的某些经典思想。与蔡先生的反思不同,一些学者的反思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观点和方法,有过较多的误解和曲解,甚至走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怀疑、否定。这样的反思,是不严肃的,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丝毫的“崇敬之情”了。因而,一旦失去了这份尊重和崇敬,即便做了大量的反思,也难以做到在坚持与发展中创见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
其次,崇敬地探索了辩证思维问题。蔡先生在这方面写下了《从逻辑思想的历史发展看辩证逻辑的对象》《辩证逻辑的制定》《思维方式科学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层因素》《〈资本论〉——矛盾分析的典范》《联系、发展、矛盾——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对逻辑、辩证法、认识论同一问题的简要考察》等代表性论文,着重考察了经典作家们对辩证逻辑思维的理论贡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思想的丰富内容和科学精神,创见性地提出了“联系、发展、矛盾”都是唯物辩证法不可缺少的基本观点、“辩证逻辑作为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制定的”、“思维方式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深层成果”、“真理‘全面性’的真谛在于认识的完整性”、“真理的基本属性是……客观性、具体性和过程性”、“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反作用”、“辩证逻辑方法是研究经济哲学的基本方法”等学术观点。关键在于,这些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被人们长期忽视和误解的某些经典思想。与蔡先生的观点不同,有一些学者却在反思的名义下简单化、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说什么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恩格斯的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因而,恩格斯是自然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甚至说,列宁的辩证法属于黑格尔意义上的,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致的,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很显然,我们看不到这类研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怀有丝毫的“崇敬之情”。这类研究不是着眼于探索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本质内涵,而是着眼于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否定其他经典作家的理论。
再次,崇敬地思考了社会主义问题。蔡先生在这方面写下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辩证发展过程的设想》《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试论人类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波形路径》《社会经济发展在区域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态势》《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观辩证法》《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等代表性论文,揭示了经典作家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本真思想,思考了社会主义的波形发展和非均衡发展问题,创见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优越论也应该是优越发展生产力之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企求是直线式的,而是波动式的”、“就现实的发展过程而论,无论经济或社会,却往往是不均衡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探索性实践”等学术观点。关键在于,这些观点还原了被人们长期忽视和误解的某些经典思想。与蔡先生的反思不同,有些学者虽说也从实际出发,可他们局限于眼前的事实,看不到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波形的历史过程,也看不到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科学再实践也是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要么用眼前的成绩来否定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要么用眼前的发展不足和缺陷来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这都是不正确的做法。我们看不到这类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怀有丝毫的“崇敬之情”。
最后,崇敬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蔡先生在这方面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三次论战》《〈实践论〉之贡献——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色》《〈福乐智慧〉的哲学思想》等代表性学术论文,一方面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始特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探索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应当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进程。与蔡先生的思考有所不同,我们有些学者虽也大讲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但他们只讲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不健全的、也不能说是科学的。
以上分析表明,坚持“崇敬地研究”,就要实事求是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和科学精神。“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十分可贵的学术品格。如果放弃了这一学术品格,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极可能出现一些不良倾向:要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教条化,要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功利化,要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壳化”或边缘化。
也许有人说,坚持“崇敬地研究”,难以做到“客观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任何“崇敬之情”都包含了研究者的某些“主观因素”,它会“稀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性研究。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如果没有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敬之情”,那么有的学者就会纠缠于经典作家的某些理论缺陷和不足,最终又滑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当代价值的怀疑、指责和否定;如果没有了这份“崇敬之情”,那么有的学者就会走向对经典作家的理论的“肢解”和“曲解”,甚至把某些“标新立异”当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如果没有了这份“崇敬之情”,那么有的学者就会倒向对经典作家的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看不到一个全面的、开放的、具体的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没有了这份“崇敬之情”,那么有的学者会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更谈不上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看来,坚持“崇敬地研究”,是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需具备的学术品格。为此,我们拟从如下方面践行“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坚持崇敬地研究,要拒绝“抑此贬彼”行为。比如,学术界从“推广论”到“广义与狭义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作了广泛的探索,但结果并不理想。“推广论”人为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的整体理论“肢解”为机械地构成的两个部分。“推广论”在大多数学者的批评中衰微了。一些学者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并用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可惜的是,这种理解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它最终也被大多数学者边缘化了。更多的学者则走向了“广义与狭义论”的理解,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中,包含了“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是,学者们对“广义的”和“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界说是相互冲突的,这让人们非常犯难,到底哪一种“广义和狭义论”[注]虽然“广义与狭义论”在时下学术界颇有市场,拥有不少“粉丝”,但是它的自身理论的缺陷必然带给它致命的硬伤。因为“广义与狭义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为地设定了两个“历史唯物主义”,这不仅造成了理解困难而且存在了逻辑混乱,因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怎么能包含了本质迥异的两个“历史唯物主义”?!这哪里是实事求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学者们自己理解出来的理论,怎么能把它们直截了当地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理论。按一般道理讲,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内涵上是一致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可是,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却违反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因而,这种研究陷入了一定的理解混乱是必然的。才算是正确的理解呢?!可见,这三种理解实质上都采用了“抑此贬彼”的理解路径。与此不同,蔡先生在《重探马克思主义哲学》(1983)一文中提出了“核心论”理解,虽然它是较早时期就提出的,但在今天依然不失其合理性。蔡先生认为,“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处在核心的位置上。它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别于以往一切哲学学说的关键之所在。这一点,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所决定的。如果没有以对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作为支柱,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从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失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确立了起来。”[1]68-69“核心论”是出于反驳“推广论”而提出的,但它也相对优越于“广义与狭义论”的理解,因为“核心论”在指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又坚定地宣称了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从而合理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三者关系,正如蔡先生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核心的一块整钢。对于社会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对于自然、思维的唯物主义观点应当取得统一的解释与叙述。因之,历史唯物主义不应当成为游离于辩证唯物主义之外的某种‘延伸’部分,而应当有机地统一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内,它的积极成果,应当渗透到、体现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的各个相应的论点之中。”[1]72-73“核心论”没有放弃辩证唯物主义,也没有割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辩证关系,而是站在整个理论体系的高度上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从而合理地界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真正地位和作用。这个“核心论”在一定意义上清除了“推广论”的形而上学缺陷,同时也避免了“广义和狭义论”的混乱理解和附加性。可见,崇敬地研究,应当是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
第二,坚持崇敬地研究,要反对囿于字面的直接性表达。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不论国外还是中国的学者,囿于字面的直接性表达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思想,几乎成为了普天下之惯常手法。可人们也知道,许多误解和曲解都是源于这种“惯常手法”的。法国学者阿尔都塞针对这种理解情形提出一个纠正方案,名之为“症候式阅读”,即透过字面的直接性表达读出作者预留在话语中的“沉默的内容”。他把字面的直接性表达称为“第一文本”,而把那个“沉默的内容”称为“第二文本”,在他看来,“第二文本”是作者的本真思想的居所。我国学者俞吾金教授认为,对于阿尔都塞的“第二文本”,人们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解读”。可实际上,人们对“第二文本”的理解是复杂的,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理解贴近作者的原本思想,有的理解偏差太远,出现了“解释过度”。那么,怎样才能防止这种“解释过度”?我认为,这就需要研究者选择“崇敬地研究”,本着对作者思想的尊重,把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结合起来,一方面实事求是地研究第一文本,另一方面创造性地研究第二文本。如果不是崇敬地研究,那就有可能陷入对第一文本的教条式理解,如果不是崇敬地研究,那也有可能陷入对第二文本的“恶搞”。因而,崇敬地研究,不是拘泥于字面意思,而是创造性地研究。比如,蔡先生在《单一问题诸多方面说》(1985)一文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不仅肯定了恩格斯的经典思想的真理性,而且突破了第一文本的“两个方面”的字面表达,提出了“三个方面说”。在他看来,从字面的直接性表达看,哲学基本问题是由两个方面内容构成的,可是,从恩格斯的文本的整体思想(第二文本)上看,哲学基本问题是由三个方面内容构成的,即“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本原论的问题;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认识论的问题;第三方面的问题,集中地表现为方法论的问题。”[1]87还强调了“世界本原的问题,是其首要的内容,是解决其它方面问题的前提和基础”,[1]87因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的。没有必要硬是把它纳入固定于一、二方面的偏狭框框。”[1]87可见,“三个方面说”没有否定恩格斯的思想,恰恰还原了恩格斯的本真思想,纠正了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缺陷。更重要的是,“三个方面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没有人为地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更没有从某种虚构的“对立”出发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在《濟仕西廬選箋》中,类似“三个方面说”的崇敬式研究,是很多的。比如,真理的“全面性”不应被理解为事物的一切方面的“相加”,而应当合理地被理解为认识的“完整性”,即“把握事物本质规定中多样性的统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应被理解为直线形发展,而应当合理地被理解为波形发展,等等。因而,崇敬地研究,应当是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
第三,坚持崇敬地研究,要反对“撕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学者中,有一种“分裂症式”研究,硬生生地“撕裂”了作为完整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为地制造了“两个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抗”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对抗”,等等,其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局限于马克思哲学之中,否定其他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学说。在我国学术界,也不乏这种研究。有人借口经典作家理论间的差异,制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部对抗和紧张;也有学者提出,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倒退,斯大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代表;甚至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哲学也不是统一的,……诸如此类的研究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尊重和崇敬,这是“非崇敬地研究”。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要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怀有一种“崇敬之情”,有了它,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经典作家思想有机地发展起来的,是不断地深化和丰富起来的科学学说。老实说,一旦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尊重和崇敬,那么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不可能在坚持与发展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研究,唯能看到的是:要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论实施某种激烈的批评和瓦解,要么用他们的“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因此,崇敬地研究,还应当是完整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
第四,坚持崇敬地研究,要提倡创见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教人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思考社会问题,并没有教人直接运用一般的哲学原理去解决社会经济生活的问题。因而,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们解决社会经济生活问题的指导作用,还需要某些具体化的中介环节,这是创见性研究的事务。可见,坚持创见性研究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随意地研究,而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具体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做到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崇敬地研究也是客观地研究。比如,蔡先生在《试论人类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波形路径》(2000)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波形发展”的论断。他说:“整个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是沿着波形路径发展的,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性。”[1]443“我们加以冷静的考察便可发现,制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都存在着形成波动的可能性,甚至是不可避免的。”[1]451无论从物质基础方面来看,还是从经济制度方面、消费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自身之中就包含着波动的因素”,“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程,是曲折波动的过程”。[1]452因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就必须有意识地掌握与运用这一规律性”,[1]460不能企求社会主义经济的“直线式”发展,而要顺应“客观波动的规律性、在波动过程中掌握主动权、驾驭波动发展的经济航船。……实现国民经济‘台阶式’的发展”。[1]460可见,“波动性发展论”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体化了这类思想,使之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既遵循了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又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特征,既批评了那些“直线式发展论”的错误,又合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艰难曲折的历史必然性,既警示了人们应当唯物辩证法地理解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和失误,又启示了人们学会在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发展。很显然,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也是需要人们有一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尊重和崇敬,而不是任由研究者们去臆断或编造,否则,所谓“可操作性”就会成为某些人“谋取私利”之手段,而不是人们“改变世界”的科学方法。
总之,如果一个学者抱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尊重和崇敬,那么他的学术研究就不会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方向,也不会陷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恶搞式”研究之中。我们需要建立在“崇敬地研究”上的创见性研究。
参考文献:
[1] 蔡灿津. 濟仕西廬選箋[M].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