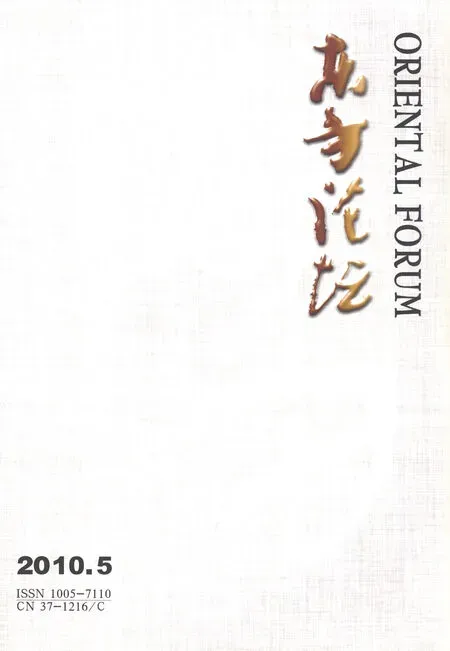论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的关系
2010-04-05张能泉
张 能 泉
(湖南科技学院 外语系,湖南 永州 425100)
论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的关系
张 能 泉
(湖南科技学院 外语系,湖南 永州 425100)
谷崎润一郎和欧阳予倩之间的友谊断断续续维持了三十余年,这在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是较为少见。事实上,20世纪20、30年代的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手法上,也都曾受到谷崎润一郎的影响。与此同时,欧阳予倩戏剧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唯美主义倾向与其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并非矛盾。因此,欧阳予倩在接受谷崎润一郎影响的同时,进行了创造性叛逆。其最为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借鉴谷崎的理论和创作技巧,此来传达作者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
谷崎润一郎;欧阳予倩;关系;影响;变异
一、引言
作为日本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曾两次访问中国。可以说,谷崎的中国之行使之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实,这些作家除田汉、郭沫若、周作人等人外,欧阳予倩也是代表。然而,当前国内学术界对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的关系研究却处于十分薄弱的阶段。因此,研究两者的关系,对我们深入谷崎润一郎与中国现代作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将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深厚的友谊、潜移默化的影响等方面阐述两者的关系,望得到方家的批评和指正。
二、深厚的友谊
众所周知,谷崎润一郎是一位极具中国情趣的日本作家。为了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浓郁情谊,他曾接二连三的以中国为背景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麒麟》(1910)、《金色之死》(1911)、《秘密》(1911)、《美人鱼的叹息》(1917)、《西湖之月》(1919)、《一个漂泊者的身影》(1919)、《苏东坡》(1920)、《鹤唳》(1921)等, 1922年,谷崎润一郎在《中央公论社》发表了题为《何谓中国情趣》一文,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中国的浓厚情趣。这篇文章也被誉为是日本大正时期日籍作家中国情趣的代表。此后,“中国情趣”这个词汇在日本文坛快速传开,成为当时日本作家的争相效仿的创作主题。1918年,首次中国之行后的谷崎带着对中国意犹未尽之意,于1926年再次来到中国。此次之行,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谷崎对中国的初衷,放弃了前往乡村体验的计划,并导致其之后的文学创作出现了中国形象缺失这一特征。然而,此次造访,对于谷崎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中国现代知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两者也因此缔结了深厚的友谊。
1926年1月14日,谷崎润一郎抵达上海,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中国之旅。1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谷崎润一郎出席由内山完造为其举行的欢迎会的情景。“谷崎为日本现代文坛的明星,……此次来沪,内山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设宴为之洗尘,我国文艺家到者有郭沫若、田汉、谢六逸、欧阳予倩等。……”[1]这是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首次见面的最早报道。之后,1月29日,上海文艺家在新少年影片公司为谷崎举行的文艺消寒会可谓谷崎此次中国之行的高潮。为事先宣传此次消寒会,1月27日的《申报》以头条的方式刊登了相关消息。1月28日,《申报》再次对这次消寒会加以了补充。由此可见,谷崎此次来华受到了来自上海艺术界的热情欢迎。1月29日下午3时左右,在田汉的陪同下,谷崎来到了新少年影片公司。关于此次消寒会的具体情形,1月30日的《申报》进行了报道。此外,2月1日上海《新闻报》也以大篇幅的形式报道了此次欢迎会。谷崎在其《上海交游记》中叙述的消寒会情况就是源于《新闻报》的报道。在这次消寒会上,欧阳予倩舞剑助兴给谷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昨今》中对此有详细的叙述。“欧阳氏跟一般的日本演员一样,在白皙的脸庞上加了一副墨镜,但是并没有田汉那种神经质的样子,倒是稳重大方,颇有长者的风范。因此,看上去很有剧团栋梁的派头。”而且“我知道他所作的工作可以说是兼备了小山内熏和上山草人的内容,在当地也非常有名,我国的圈内人士应该也是熟知的。我曾经看见过他舞剑的样子,也就是说他兼备有中国传统戏的素养,还能男扮女装,而且肤色白皙,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个演员的样子。”[2]谷崎在上海期间,在田汉等人的陪同下,体验了上海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结识了许多在上海的中国艺术家。如画家陈抱一、导演任矜萍、作家郭沫若等。然而,最让其铭记于心的事情便是在欧阳予倩家欢度除夕。谷崎在日后的《上海交游记》中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他说:“和那一家人快快乐乐地过年的情形,至今难以忘怀。”[3](P331)为了表达自己对谷崎的热情之意,欧阳予倩这天挥毫写下了一首诗歌赠送给他。现将全诗摘录如下:竹径虚凉日影移/残红已化护花泥/鹦哥偶学啼鹃语/唤起钗莺压鬓低。全诗意境轻盈哀雅,淡雅中流淌着一股忧伤,浓情中流露出一种缠绵,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诗人浓郁的怀念之情。深受此诗感染的谷崎,特将该诗装裱珍藏起来。后来他还在《昨今》中写道:“每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和这首诗相称的季节,我总是从自己不多的收藏品中,取出这一幅字挂上,同时怀念起当年给我写这首诗的中国友人来。”[2]
1927年,欧阳予倩离开新民影片公司,为筹建自己理想的剧团,于12月来到日本东京。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欧阳予倩来访》一文曾记载了欧阳此次日本之行的详情。另外,谷崎润一郎在《昨今》中也详细回忆了欧阳的此次之行。关于欧阳予倩的日本之旅,我们择取两件有代表的事情,以此说明两者深厚的情谊。其一,在谷崎的陪同下,欧阳游历了京都。谷崎对此曾回忆说:“记得曾陪同他去京都看了歌舞伎的首演,还看了已故的梅幸演的茨木,所以想必是在十二月吧。”“那天晚上,我们还去游了祗园,下榻在河原的旅馆。第二天记得他说想去看摄影棚,我就带他去了下加茂和牧野的摄影棚。”[2]其二,欧阳入住谷崎家,并赠送礼物。在陪同欧阳游览京都美景后,谷崎在冈本的家中盛情款待了这位来自中国的戏剧家。众所周知,谷崎润一郎是一位性格怪异,且及其内向的作家。他平日极少邀请他人造访,即使是其良师益友永井和风也很少去过其家中。因此,他的这一行为充分说明两者关系绝非一般。当然,我们所言的绝非一般并非指谷崎与佐藤春夫的关系。(1919年日本文坛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小田原事件”就是代表)而是指两者的友谊情深意切。“欧阳氏也是来去东京的途中住在我在冈本的家里,回去前曾说,回国后想送你一件礼物,有什么想要的请告诉我,所以我就回答说要是有上好的陈年绍兴酒就送我一瓶吧。”[2]12月10日前后,当欧阳予倩回到神户的时候,谷崎的弟弟谷崎终平应此事来神户海关取走了欧阳送给谷崎的两瓶绍兴酒。此事在谷崎终平的《从好文园到梅谷》中有记录。他说:“我接受了哥哥的命令,去神户海关取来了两只装老酒的大土坛子。”[4]欧阳予倩回国后,参加了田汉组织的南国社,并担任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1928年5月,应李济深等人邀请南下广州筹建广东戏剧研究所。1929年2月研究所成立,同年5月创办刊物《戏剧》。然而,欧阳的这一切活动对于远在日本的谷崎却了如指掌。“那以后,欧阳氏从上海移居广东,好像在当地办了杂志。他一直给我寄来,直到事变发生之前。”(这里的事变是指1937年7.7事变)[2]由此可见,谷崎和欧阳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与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关系不同,欧阳予倩与谷崎润一郎的关系一直延续到战后。虽然这期间,两者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彼此都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对方。1956年5月26日,欧阳予倩以中国京剧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和团长梅兰芳等一行访问日本。代表团访问箱根期间,谷崎和欧阳在分隔29年后,终于再次相聚。有关两者的谈话,《中央公论社》以题为《三十年后的再会》(1956年9月号)加以了报道。双方在日本朝日新闻社外报部员冈崎俊夫的主持下,就两人的陈年往事、中国文坛现状、中日传统戏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最后,欧阳还盛情邀请谷崎访问中国。谷崎对此表示感谢,并回答说只有身体允许,一定前往中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谷崎此后的身体一直处在不适状态,直到1965年病逝,谷崎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1957年,谷崎发表了《欧阳予倩君的长诗》,对箱根饭店的重逢情景加以了描述,并全文摘录了欧阳赠送给他的诗歌。“欧阳予倩君和京剧团一行来访时,时隔三十年,我去箱根饭店再次见到了他,畅叙别后之情。”[5]前文提及过1926年谷崎访华时,欧阳予倩曾在除夕之日在自家赠送过诗歌他。可是,该诗不幸毁于战火。因此,对此次赠诗,谷崎有如获至宝之感,特意将之装裱起来,悬挂于家中的客厅,以此纪念两人的深厚友情。1962年欧阳予倩病逝,得知噩耗的谷崎,泣不成声,并撰文《怀旧友欧阳予倩君》(该文刊于《中日文化交流》1962年11月65号)追忆两人的深厚情谊。
三、潜移默化的影响
1910年,谷崎润一郎凭借《文身》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小说以大胆的想象,艳丽的词语流露出作者浓郁的官能欲望和颓废、病态的审美追求。之后,谷崎接二连三地创作了一系列类似风格的作品。从此,谷崎以其独特的官能美、肉体美和感性美蜚声于日本文学界。1923年关东地震后,谷崎移居关西。面对关西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俗民情,谷崎的审美趣味与之前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之前的感性美、肉体美和官能美转向为理性美、精神美和内在美。1948年问世的《细雪》可谓谷崎后期审美趣味的集大成者。那么,谷崎润一郎的文学观念是否对欧阳予倩产生过影响呢?如果产生了影响,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欧阳予倩在接受谷崎文学观念的同时,是否有变异呢?如果有,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将结合相关作品,具体阐述上述问题。
第一,谷崎润一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对欧阳予倩戏剧理论有过影响。1902年,年仅13岁的欧阳予倩赴日本留学。虽然1906年曾因政府问题回国,但次年又回到日本继续学习。他先后入明治大学商科和早稻田大学文科。1910年因护送父亲遗体回国。近8年的留学生活,不仅让欧阳予倩熟知了日本文化,而且还通过春柳社,接触了不少日本作家。虽然这些作家中没有谷崎润一郎,但是欧阳通过藤泽浅二郎之口获知了谷崎润一郎。再加上,欧阳予倩对日本文坛给与《文身》的热烈回应也有所耳闻。这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接触方式使欧阳对谷崎产生了兴趣。回国后,欧阳予倩积极参与戏剧活动。1929年2月16日,以创造“适时代为民众的新剧”为宗旨的广东戏剧研究所成立。在担任所长的同时,欧阳积极撰写戏剧理论文章。1929年欧阳发表了著名的戏剧理论文章《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1929年5月广东戏剧研究所《戏剧》第1卷第1期)。文中,欧阳多次反对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戏剧创作,并认为这种戏剧是专制时代的产物。戏剧是社会的产物,理应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然而,戏剧又非其他艺术,它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欧阳予倩看来,戏剧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综合性。“我们所希望的戏剧,决不是只求消遣闲情,不是仅能作宣传工具的满足,也不是只顾目前的那种功利主义所能的范围。”[6]很显然,欧阳的戏剧理论非常注重戏剧创作的双重性——现实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反对传统戏剧创作的功利主义和文以载道。因此,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所谓综合不是各种艺术简单的拼凑,而是选取各种艺术的精华加以戏剧化的调和与统一。只有这样的戏剧“才能造成浓厚清新的空气(Atomosphere)与美妙谐和的节奏(Tenp and Rhythm)。”[6]好一个浓厚清新的空气!好一个美妙谐和的节奏!虽然,欧阳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但这并不是说他就反对艺术本身。与此相反,他是一位艺术味十足的戏剧理论家。他注重戏剧的艺术美。他强调戏剧是艺术,而非简单的传声筒,更不是知识的播种机。戏剧艺术性的体现不在于向他人介绍和传递了多少知识,而在于能够引起他人的情绪。这种情绪具有永恒性、普遍性、具体性和个性。“所以戏剧要求思想的美化,戏剧的情绪是美的情绪,戏剧所能提供给观众的是快乐。快乐就是美的精神。”[6]强调思想的美化,使之成为快乐的情绪,这是戏剧的根本。戏剧艺术具有独立性和非功利性色彩,它是思想美化的结果,它是快乐情绪的产物。戏剧的魅力就在于讲述美,在于表达美,在于体现美。一句话,美是戏剧艺术的结晶。礼赞美、礼赞艺术的非功利不仅是欧阳的戏剧主张,同样也是谷崎的理论。在《独探》中,他高唱要在独特的艺术世界中寻找令自己醉生梦死的美;在《文身》中,他提出一切美都是强者的体现;在《我做了爸爸》中,认为艺术第一,生活第二;在《阴翳礼赞》中,礼赞美的古典与阴翳。总之,在谷崎的眼中,美就是艺术的本体,是艺术存在的前提,是艺术的精髓,也是艺术的生命。因此,无论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还是谷崎润一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两者都具有诸多相似的地方。
那么,究竟是谁影响谁呢?或许与欧阳予倩同时代的戏剧家——田汉的评论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我早期的文学活动,与郁达夫等人一样,同唯美主义有很深的关联,以至于“几乎走上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歧途”。[7](P447)虽然,田汉的这段话语没有明确指出与欧阳予倩的关系,但是只有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相关知识,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0世纪20、30年代,许多留日作家都或多或少染上了唯美——颓废的情绪。因而,在其文学创作中,他们也都鲜明的表现出这一特征。事实也确实如此。郁达夫就曾是创造社同仁中最具唯美——颓废色彩的作家。对此,郑伯奇曾以知情人的身份公开指出:“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等人的小说是他比较喜爱的。”[8](P859)此外,章克标也是典型代表。他不仅是谷崎文学的翻译者,也是谷崎理论的鼓吹者。在其《谷崎润一郎集•序》中,曾对谷崎理论作了高度的概括。他说:“他(谷崎润一郎,笔者注)有丰富的空想世界,而这个空想像陶醉于鸦片之后,所见的幻美奇怪的梦。”[9](P6)他甚至坦言:“我连续翻译了几篇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头脑中被他的恶魔的色彩,唯美的情调充塞满了。”[10]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持章克标这种论调的作家绝非仅此一人。其实,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曾接受过谷崎的影响。尤其对留日作家来说,这点更突出。因此,处于同时代的欧阳予倩完全有可能受到来自谷崎的影响。更何况,曾两度访华的谷崎润一郎,其作品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文坛曾掀起了一股“谷崎润一郎热”。《文身》、《恶魔》、《美富子的脚》、《麒麟》等作品都先后被翻译到中国。周作人、李漱泉、朱秀侠、谢六逸等也都发表过相关评论,宣扬谷崎理论。这样一来,基于上述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是欧阳予倩接受了谷崎润一郎的影响。
第二,在变异中接受影响。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现代留日作家产生了影响,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留日作家的一员,欧阳予倩也是如此。他不仅在戏剧理论受到了谷崎的影响,而且在戏剧创作上也流露出谷崎的唯美特征。其实,早在其留学日本时,日本文艺界唯美主义的作品和文艺理论有着相当的势力,这对欧阳予倩来说是个不小的影响。以致他在1957年的《回忆春柳》一文中还这样写道:“春柳同人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自觉地走上了艺术至上主义的道路。我们对于艺术形式的完整想得较多,而战斗性不够强……”。[11]甚至在他当任职业京剧演员时,有一阵他也“颇以唯美主义自命”,以至“不信戏剧艺术除掉以美感人之外能够在何种目的之下存在”。[12](P26)这个唯美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他来广东前后,都不时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和演出。1928年,欧阳予倩根据谷崎润一郎的戏剧《无名和爱染》改译成一场两幕三场话剧《空与色》,并在其影响下,创作了五幕剧《潘金莲》。同年10月,上海新东方书店以《潘金莲》为书名,出版了欧阳予倩的上述两部作品。为了更好地阐述在变异中接受影响,我们将以《潘金莲》为文本典型加以具体论述。
《潘金莲》最早刊登在1928年6月10日《新月》第一卷第四期。作者根据时代的要求,改编了《水浒传》中关于潘金莲的描述,创作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浓郁唯美情调的话剧《潘金莲》。首先,我们来看看戏剧唯美主义的情调。谷崎润一郎曾认为艺术不是精神性的东西,而是具有实感的事物。艺术的美不在于你拥有崇高的理想,而在于你拥有令其铭记于心的体验。因此,在谷崎眼中,美不是灵魂,而是肉体;不是精神的言说,而是生命体验的展现。潘金莲如同谷崎笔下的南子(《麒麟》中的女主人公)、照子(《恶魔》中的女主人公》不仅美貌如花、体态丰盈,而且都表现出施虐的倾向。南子夫人凭借自己的美貌和肉体,施展各种伎俩,终于让曾悔过自新的卫灵公再次回到她的身边,忘记了昔日孔子的教诲,背叛了世俗伦理,纵情于女色,过着一种及其糜烂的生活。小说结尾写道:“夫人伸开两臂,长长的衣袖围裹住卫灵公。温柔的手臂在酒力的作用下,如同不能开解的绳索,捆住了他的身体。”以致卫灵公最后发表感叹:“我憎恨你。你是个可怕的女人,你是让我灭亡的恶魔。可是,我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你。”[13]《恶魔》中的照子也是如此。她具有高挑的鼻梁,丰润的双唇,高耸的乳房和圆润的脸颊。体态丰腴、婀娜多姿的照子,为了捆住男主人佐伯,不断施展淫威,使得佐伯为此痛苦的哀号:“照子,你这个淫妇,你杀了我吧,你让我疯狂……”并不时感叹“女人这东西正如世人所说,她会把男人腐蚀成碎片。”[14]由此可见,谷崎笔下的女性不仅具有官能魅力,而且还具有施虐倾向。谷崎正是要在女性营造的世界中表达其对美的执着追求和大胆憧憬。世俗的一切只有在女性肉体中才能升华,才能达到一种永恒。这是谷崎唯美世界的建构,也是谷崎艺术世界的标准。对女性美的演绎和礼赞构成了谷崎艺术世界的核心。受此影响的欧阳予倩在《潘金莲》中也鲜明的表现出这一特点。戏剧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潘金莲的柔媚的语句,但有几处细微的神情描写却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戏剧第三幕主要讲述武松和潘金莲关于武大郎之死的谈话。作者为了表现潘金莲对武松的爱意,有意描叙了她为武松斟茶时的两处细微动作。“眼睛微微向武松那边瞟一瞟,想一想,叹口气,再慢慢地走——很失望的样子。”接着,“一面说着一面收拾茶碗,将茶泼在地下就走,走着回头柔媚地说了一句……”[15]很明显,潘金莲无法向武松敞开自己心扉。因而,她只能借回眸传递欲言又止的心态,借回眸传达自己的万种风情。潘金莲的美媚在两处细微的言行中得到了含蓄的体现。此外,戏剧结尾处,当武松举刀欲杀潘金莲时,潘金莲在生死之间,一改以往的含蓄和柔美,用一种竟似疯狂的举措,脱去自己的衣服,向众人袒胸露乳,跪近在武松身旁,说道:“二郎,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颗赤热的心,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了。你不要,我只好权且藏在这里。可怜我等着你多时了,你要割去吗?请你慢慢地割吧,让我多多的接近你。”[15]多么炽热的表白!多么强烈的心声!沉睡多年的爱情瞬间演变成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激情之歌。委婉、含蓄、柔美刹那间销声匿迹,此时的潘金莲如同火山,终于在喷发之际释放了压抑于内向多年的激情,其力量之强,能量之大,如山崩,如地裂,如海啸,猛烈无穷,响彻云霄。这是美的豪言,也是美的壮语。赤热的心倘若能奉献给自己心仪之人,即便是奉上自己的生命,对她来说,又何尝不是人生一大美事!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这就是美的极致,美的礼赞。
当然,谷崎对欧阳的影响是有限的。换句话说,以颓废、恶魔、怪异、病态著称的谷崎氏文学创作并没有直接给欧阳带来影响。欧阳予倩没有像郁达夫、章克标等作家那样,曾一度沉迷于谷崎式颓废——唯美的理念中。那么,欧阳予倩在接受谷崎的影响同时,究竟进行了怎样的变异?我们认为这种变异是多样的,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我们认为最为突出的变异就在于欧阳善于借鉴谷崎的理论和创作技巧,以此来传达作者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正如郭沫若在评论郁达夫所说:“他(郁达夫)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那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狂怒了。”[8]此外,鲁迅、沈雁冰、朱自清等都相继发表文章,就当时文坛出现的唯美热,发表了自己的评论。虽然他们的观点有些不同,但都肯定这股弥漫于文坛的唯美热是中国新文化界的理想主义时代精神和浪漫主义艺术情绪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欧阳作为中国早期的戏剧家,理应具有这一时代共性。《潘金莲》作为20世纪20年代戏剧的代表之作,在表现女性美的同时,更多是传达一种女性觉醒时的心声。欧阳予倩创作《潘金莲》其目的之一就是欲为潘金莲翻案。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欧阳,将潘金莲视为个性解放的女性。因此,潘金莲强烈的言辞中无不闪烁出作者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控诉和批判。由此可见,欧阳的戏剧创作相对于谷崎来说,少了些颓废,多了些气息;少了些病态,多了些健康;少了些怪异,多了些朴实。此后,欧阳予倩的戏剧创作出现了新的内容。从编《潘金莲》之后,其创作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时代性和现实性成为欧阳戏剧的两大特征,早年的唯美色彩也随之逝去,成为欧阳戏剧创作的历史。
四、结论
以上是笔者对谷崎润一郎和欧阳予倩关系的初步探讨。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谷崎与欧阳之间不仅有着深切的友谊,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谷崎对欧阳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欧阳之所以接受谷崎的影响,其目的并非要成为一位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鼓吹者和捍卫者。相反,其用意在于通过借鉴谷崎的艺术理念和手法更好地感触时代声息,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形成其浓郁的现实主义戏剧理论。因此,我们认为欧阳予倩戏剧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唯美主义的倾向和追求与其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并不是矛盾的。现实主义戏剧理论是他对戏剧总的追求,是他肩负历史使命和社会使命的结果。在他看来,戏剧之所以表现美的事物,为的是让观众在对美的赏析中实现认识社会的目的。用欧阳予倩自己的话讲就是,艺术的目的,在于“美与力”的传达,使观众不仅能“从戏剧里面认识人生”,而且出了剧场“在精神上有所获得”。[6]综上所述,欧阳予倩的唯美主义戏剧创作与其在艺术追求中表现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并不相悖。通过对谷崎润一郎的吸收和借鉴,其戏剧创作既不偏废戏剧艺术本身的特性,又能恰如其分的反映现实社会和时代气息,从而形成欧阳予倩在艺术追求中真实的独特戏剧美学。
[1]唐越石.日本文学家来沪[J].申报,1926,(7).
[2]谷崎润一郎.昨今[J].中央公论,1942,(5).
[3]谷崎润一郎.上海交游记[A].谷崎润一郎全集[M].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1982.
[4]谷崎中平.从好文园到梅谷[J].谷崎润一郎全集[M].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1982.
[5]谷崎润一郎.欧阳予倩君的长诗[J].心,1957,(2).
[6]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J].戏剧,1929,(1).
[7]田汉.田汉选集前记[A].田汉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8]郑伯奇.忆创造社.饶鸿竞等,创造社资料(下)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9]章克标.谷崎润一郎集[M].上海:开明书店,1929.
[10]章克标.做不成的小说[J].金屋月刊,1929,(5).
[11]欧阳予倩.回忆春柳[J].戏剧论丛,1957,(3).
[12]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M].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
[13]谷崎润一郎.麒麟[J].新思潮,1910,(4).
[14]谷崎润一郎.恶魔[J].中央公论,1912,(2).
[15]欧阳予倩.潘金莲[J].新月,1928,(4).
责任编辑:冯济平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nizaki and Ouyang Yuqian
ZHANG Neng-quan
(Hu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ongzhou 425100, China)
Tanizaki and Ouyang Yuqian maintained friendship for over 30 years, something rare in Sino-Japanese ex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fact, Ouyang Yuqian’s dramatic writing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ere influenced by Tanizaki either ideologically or artistically, also. At the same time, Ouyang Yuqian dramatic aesthetic tendency does not run into conflict with his realistic dramatic theory. Therefore, Ouyang Yuqian accepted Tanizaki with some creative treason. The most prominent is that He is good at drawing on Tanizaki theoretical and creative skills in order to convey the anti-feudalism spirit and individual liberation of the times.
Tanizaki; Ouyang Yuqian; relations; influence; variation
book=91,ebook=58
I0-03
A
1005-7110-(2010)05-0091-06
2010-03-25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课题“谷崎润一郎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080604313;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齐崎润一郎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09YBB167。
张能泉(1979-),男 ,湖南株洲人,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中日文学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