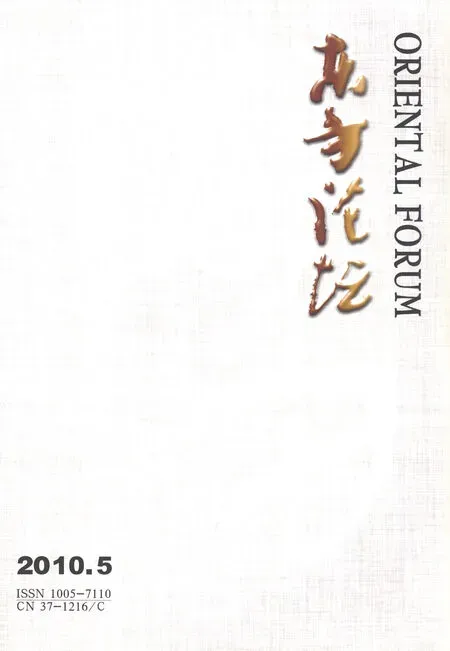勇敢追问真理的反抗与无可奈何的妥协
——卡夫卡小说中的“悖谬”问题之一马 小 朝
2010-04-05烟台大学中文系山东烟台264005
(烟台大学 中文系,山东 烟台264005)
勇敢追问真理的反抗与无可奈何的妥协
——卡夫卡小说中的“悖谬”问题之一马 小 朝
(烟台大学 中文系,山东 烟台264005)
卡夫卡小说中的悖谬问题之一,就是勇敢追问真理的反抗与无可奈何的妥协。正是这种悖谬赋予了作品更复杂、更含蓄的暗示性,从而创造了振聋发聩的警世意义和通往真理的可能性。
悖谬;追问真理;反抗;无可奈何;妥协
在表现主义文学乃至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卡夫卡的小说艺术始终充满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叶廷芳先生说:“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乃至创作特点都与一个哲学术语有关,这个哲学术语就是‘悖谬’(Paradox)。悖谬,一个事物两条逻辑线的相互矛盾与抵消。”[1](P13)由此,破解卡夫卡小说艺术困惑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解读卡夫卡小说的“悖谬”问题,而卡夫卡小说的“悖谬”问题之一,就是勇敢追问真理的反抗与无可奈何的妥协。
所谓勇敢追问真理的反抗,主要指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不轻易接受外在势力的捉弄和迫害,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怀疑精神和自由理想。卡夫卡在《致菲莉斯情书》中说:“哥白尼学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敢于对亲眼看到的事物提出疑问,同样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时,人们仍应该敢于提出疑问。”[2](P110)所以,《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在被宣布逮捕后,先是毫不在乎,因为“他向来不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只有最坏的事发生后才相信世界上竟会有这种事,因此从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甚至危险即将降临时也如此。”[3](P5)约瑟夫•K甚至想“:倘若这是一场喜剧,那么他也应当参加演出。”[3](P6)因此,他敢于理直气壮地告诉监督官:“我猜想,虽然我被控告,但你们却找不到任何指控我的罪证。”[3](P11)坚信自己的无罪的主人公甚至在预审法庭上大义凛然地宣讲:“我所要求的仅仅是公开讨论一下人们普遍蒙受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状况。”[3](P36)“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采取的一切行动——在我的案子里对我的逮捕以及今天的审讯——后面,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在操纵。这个机构不但雇佣了索贿的看守,愚蠢的监督官和至少是不中用的预审法官,而且豢养了一批高等的,甚至最高级别的法官,这些人手下还有一大帮不可缺少的听差、办事员、宪兵和其他助手,也许还有刽子手,我并不忌讳这个词。先生们,这个庞大机构存在的意义在哪儿呢?在于逮捕无辜的人,对他们进行荒谬的审讯,这种审讯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结果,就像我的案子一样。既然一切都是荒唐的,官员们贪赃枉法又怎么能避免呢?”[3](P38)离开法庭前,约瑟夫•K甚至放肆地大笑着喊:“我把所有的审讯都送给你们吧!”[3](P40)同时,约瑟夫•K开始努力不懈地寻找相应的法律机构,为自己无须说明的清白无辜找出一个合理说明。这个过程既是他努力抗争的过程,也是他坚定不移地追问真理的过程。甚至在最后被两个人秘密押解往刑场的时刻,约瑟夫•K还曾想:“我需要用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把它用光吧,他们将发现我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3](P180)总之,约瑟夫•K从被宣布逮捕起就坚信自己的无罪。这其实是表明约瑟夫•K面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驯顺,敢于将人们熟视无睹的正常事情理解为不正常。正如谢莹莹先生所说,约瑟夫•K在千人一面的社会里,“实际上是边缘人,也即尚未被纳入社会整体、被标准化、被同质化的人”。[4]《城堡》中的主人公K偶尔来到一个小村镇,深夜被摇醒过来,要求出示居留许可证。K以对权威的无比轻蔑,声称自己是土地测量员,因而享有居住此地的自由权利。后来,K又怀着坚定的信心,毫不动摇地、时时处处地寻求与城堡长官直接会晤的机会。他在同村长会面时,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不需要城堡的恩赐,我只想讨个公道。”[5](P82)他甚至坚决拒绝城堡长官克拉姆的村秘书的审问,并非常具有尊严感地告诉大桥酒店老板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服服帖帖受人审问,为什么要让别人拿我开玩笑,为什么要让人在我身上使官老爷性子。也许哪天我也来了兴致,开开玩笑,使使性子,那时可以奉陪,可是今天不行。”[5](P127)所以,小说这样写道:“他现在是在千方百计要求一见克拉姆的,却不觉得一个能在克拉姆眼皮底下过日子的人有什么了不起,更谈不上欣赏和羡慕,因为,说实在的,接近克拉姆本人并不是他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而是:他K要亲自(不是别人)带着自己的(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要求去会见克拉姆,会见克拉姆并不是为了在那里歇着而是经过他身边继续前进,到城堡里去。”[5](P121)也正因为此,K使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心甘情愿奉献自己如痴如醉的爱恋,使奥尔嘉推心置腹讲述家庭的不幸遭遇,甚至使小汉斯充满敬意地表示自己长大后要做一个像K一样的人,大概是“在汉斯心中逐渐生出一个信念,就是K目前虽然还地位低下,令人退避三舍,但将来——当然这个将来遥远得很,还在虚无缥缈中——,将来他终归会出人头地的。正是这种虚无缥缈的远景,以及那种可以引为骄傲的、朝着这个方向的步步发展,对汉斯有很大的吸引力。”[5](P164)的确,K作为一个漂泊而至的外乡人,他的身上有一股现代人缺乏的追问真理的傲慢态度,现代人生疏的慌不择路的超验想望。
但是,卡夫卡小说中主人公追问真理的反抗,又往往与无可奈何的妥协交融在一起,从而赋予了作品更复杂、更含蓄的暗示性。尽管这种不自觉的妥协投降里,包含着深长久远的自我谴责与愧疚,但毕竟是放弃了自己面对不合理现实毫不退让的自由理想。《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曾经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大教堂,一位神父给他讲述了一个“法门之前”的寓言。法门是什么?法门大开为什么又不让人进去?为什么不让人进去的法门,却又偏偏专门为想进去的人所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门就是通往真理和意义的象征,也是回答约瑟夫•K不幸遭遇之谜的谜底的象征。世上现成的真理虽然已不存在,荒诞不经背后的现成逻辑虽然已经破碎。但是,作为一个人,只要你坚决去追问,勇敢去闯荡,那么,就一定会有一道为你而敞开的门。你的追问和闯荡也就会为你创造出意义。但问题是,在通往追问和闯荡的门前都有一个守门人,他们命定会阻挠你的追问和闯入。因为,他们作为守门人,其实也只是在履行历史所派定给他们的角色任务。所以,神父告诉约瑟夫•K说:“有人认为,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他用来吓唬乡下人的东西恰恰是他自己害怕的东西。”[3](P175)约瑟夫•K听完神父的寓言和说明后,也终于明白:“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3](P177)既然如此,那位乡下人也就可以无视守门人的存在,大胆怀疑他的职责与使命。约瑟夫•K也可以无视“法庭”的存在,勇敢反抗它的判决与权威。卡夫卡就曾经在其《随笔》中描写一个乡村牧师不能进入两个人守卫着的门时,“忽然他想起了一个念头,又折转身来。这两位先生是否知道他要到谁那儿去呢?他是到他姐姐雷贝卡•措法尔那儿去,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士,跟她的女仆一起住在三楼。守门的这两位果然不知道这回事。现在他们不再反对牧师进去了,当他从他们之间穿过时,他们甚至还向他鞠了个躬。到了过道里,牧师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没想到能这么容易地骗过这两个人。他回头瞥了一眼,他惊讶地看到,这两个守卫正手挽手地离去,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他的缘故才站在这里的吗?”[6](P185)但是,乡下人、约瑟夫•K,以及许多生活在现代社会制度里的人,他们共同的可悲性常常就在于没有那位乡村牧师的自我决断勇气,他们往往不自觉地默认守门人、法庭、社会制度的存在,默认守门人、法庭、社会制度的权威性,也默认守门人、法庭、社会制度对自我制约的合理性。所以,他们只有坐以待毙。比如《城堡》中的普通百姓们,一方面提心吊胆地过着颤颤巍巍、委琐灰暗的日子,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有资格作为城堡的顺民而庆幸。大桥酒店老板娘不是为自己曾经接受过克拉姆那走马灯式的三次召见而引以为自豪吗?她不是尤其为自己收藏有克拉姆第一次召见她的信差的照片,以及克拉姆的手绢、睡帽作为纪念品而得意扬扬吗?她甚至告诉K说:“克拉姆一发话,世界上哪个男人能挡住我跑到他那儿去?”[5](P91)更可怕的是,他们不自觉地甘心接受官方愚弄和欺瞒的同时,还对一切逾规越矩的非驯顺行为皆深感恐惧。这种恐惧甚至成为一种心理疾患,它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隔膜,加剧了人自身的内心的惶惑、困窘,更加强了邪恶势力的张狂、蛮横。比如城堡的一位官员索尔替尼,喜爱上了奥尔嘉的妹妹阿玛莉娅。他派人带给阿玛莉娅一张字条,要阿玛莉娅立即在半小时里到他那里去。因为字条上全是不堪入耳的话,从而使阿玛莉娅毅然拒绝,并愤怒地将字条撕成碎片扔向送信人的脸。阿玛莉娅的举动居然把全村人吓坏了,熟人、朋友看见他们,只急急忙忙几句话便告辞,顾客们纷纷到她父亲的库房里把送来修补的靴子、准备制作的皮料等讨要了回去。父亲的合伙人也要求分手单独干。村消防协会也取消了父亲的会员资格。整个村子里的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们一家子。奥尔嘉告诉K说:“人人都满意能这样干净利索地同我们家断绝关系,即使在了结这些事情时受点损失也不在乎。”[5](P222)其实,阿玛莉娅一家并没有遭受到来自城堡的任何官方的直接迫害,只是村里人由于恐惧而疏远了他们。反过来看,阿玛莉娅一家也不自觉地任自己在这种疏远中越滑越远、越陷越深。奥尔嘉还告诉K说:“现在再说村里的人吧,我刚才说过,要是这档子事最终能得到皆大欢喜的解决,那就最符合他们的心意了。”[5](P228)“只要我们又走到众人面前,只要我们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只要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已经把那件事完全甩开(不管是用什么办法),这样大家就会确信,那件事无论在发生的当时掀起过多大的波浪,以后再也不会旧事重提——,只要情况是这样,那也就皆大欢喜了。”[5](P229)但是,“事情渐渐发展到了这步田地,就是我们几个人自然而然地不断反复讲那封信,横着讲,竖着讲,讲大家都确有把握的全部细节,也讲谁也说不准的各种可能,我们自然而然地每天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一些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办法,一个高招赛过一个高招,一个主意压倒一个主意,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一天不这样也过不去,可是很不妙,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本想从那个泥潭里爬出来,实际上反而在烂泥中愈陷愈深。”[5](P230)同时,“人们发觉我们老是在撕信事件上想不开,庸人自扰,不能自拔,就对我们全都没好气。……如果我们自己摆脱了这件事的阴影,人家就会非常敬佩我们,但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点,人家就往前进了一步,把原先只是暂时对我们采取的态度变成永久性的了:终于把我们排除在每一个社交圈子外面。”[5](P232)更有甚者的是,奥尔嘉继续告诉K说:“我们做了一件糟得不能再糟的事。我们让人瞧不起,原本还有点冤枉,可是一做出这种事,恐怕人家瞧不起我们就理所应当了:我们甩开了阿玛莉娅,挣脱了她那无声命令的束缚,我们感到没法再那样生活下去,那种没有丝毫希望的日子,我们确实过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各显其能,各人按自己想出的办法去行动,去向城堡提出请求或者苦苦哀求,求上头宽恕我们。”[5](P233)父亲“总觉着别人是在瞒着他,不告诉他有什么过失,而原因又是他打点得不够”。[5](P235)一家人变卖了家中的生活必需品,好让父亲有足够的钱财去行贿。后来,父亲还在无可奈何中“想好了一个计划,就是到城堡附近大路上官员们乘车总要经过的地方去站着,一有机会赶紧抓住,向当官的提出希望得到原谅的请求”。[5](P237)父亲每天坐在一个菜园的石头基座上。秋天的雨、冬日的雪使父亲和后来陪伴的母亲,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同时,奥尔嘉为了找到当初替索尔替尼官员送信的侍从,两年多来“最少每星期两次整夜同那些仆人一起待在马厩里”。[5](P243)哥哥巴纳巴斯也不得不撂下成堆通过转接而得到的鞋匠活,跑到城堡去充当似有似无、似真似假的所谓信差。当然,《城堡》中阿玛莉娅的行为所引起的官方迫害,就像《诉讼》中约瑟夫•K所遭遇到的逮捕一样,本就是现代社会时时刻刻皆充溢着难以捉摸阴谋的情感感受。正如奥尔嘉所说:“这里的人也好,城堡的人也好,全都一样,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的人避开我们当然是看得见觉得出的,而城堡方面我们就影子也见不着。”“这种一点动静也没有的滋味是最难受的了。”[5](P227)所以,阿玛莉亚的父亲四处求情也就像约瑟夫•K的四处申诉一样,都面临着一个问题:“想请人家宽恕、原谅什么?”[5](P233)所以,主人公K说:“你们这里的人是天生对官府抱着诚惶诚恐的敬畏态度,出生后又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四面八方不断向你们灌输一辈子这种敬畏心理,你们自己也竭尽全力配合人家向自己灌输。”[5](P200)其实,《城堡》中的主人公K自己亦然。K希望会见城堡官员克拉姆,也就像“法门之前”寓言里的乡下人企图进入法门、《诉讼》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企图逃避法庭一样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妄想。K在酒店曾经假装助手身份与城堡通电话问:“什么时候我的主人可以到城堡来?”城堡回答:“什么时候都不行。”[5](P24)然而,主人公K仍然费尽心机地努力争取被允准作一个当地居民。他卑躬屈膝地到学校当勤杂工,忍受了男女教师的呵斥、辱骂、嘲讽。他甚至为面见城堡官员克拉姆,在严寒的夜晚守侯在雪撬旁,冻得浑身哆嗦。如果说,寻求城堡表现出了追问真理的大无畏精神,那么,反过来,承认城堡对自己居留权的确认,不仍然如“法门之前”寓言中的乡下人一样不自觉地默认了守门人的权威吗?主人公为什么不能彻底蔑视包括城堡在内的一切官方权威和外在证明,只忠实属于人自我的自由本性呢?其实,K在刚来到村子里的那个晚上,当被施瓦尔策摇醒过来,要求出示居留许可证时,K就严肃地声称:“我是伯爵招聘来的土地测量员。”[5](P4)城堡也不得不在电话里认可了K的身份,并且在第二天派来了两个助手。K甚至同克拉姆的情人弗丽达一见钟情而坠入爱河,“当听到克拉姆房间传出一个低沉的冷冰冰的带着命令语气的声音呼唤弗丽达时,至少开始并不惊吓,而是感到一种给人以慰藉的清醒。‘弗丽达’,K凑近弗丽达的耳朵说,算是把这呼唤传达给她了。在那几乎可以说是天生的唯命是从心理的驱使下,弗丽达立刻想纵身起来,但紧接着她想到了自己现在待的地方,便伸了个懒腰,轻轻地笑起来,说道:‘我怎么能走呢,我决不去他那儿。’K本想提出反对,他很想催促她到克拉姆那儿去,开始动手把她散乱的衣衫拉平整,但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拥抱着弗丽达他感到太幸福了,同时幸福与惧怕交织在一起,因他觉得弗丽达一旦离开他,他便失去了一切。弗丽达呢,仿佛有K的默许为她壮胆,便攥起拳头捶门,并大声叫道:‘我在土地测量员这儿呢!我在土地测量员这儿呢!’现在克拉姆倒是不吭声了。K却坐起身来,然后在弗丽达旁边跪下,在凌晨扑朔迷离的光线中环顾四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希望在哪里?现在一切都暴露了,他还能指望从弗丽达那里得到什么呢?”[5](P47)K的迷惘泄露了自己与克拉姆共同分享的色厉内荏,就像“法门之前”寓言中的乡下人与守门人共同扮演的角色使命,谁都拥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机会。正如卡夫卡所说:“藏身处不计其数,可救命的只有一处,但是救命的可能性又像藏身处一样多。”[6](P41)但是,K终归没有坚持住同克拉姆的对峙,没有抛弃对现成社会权威的默认,终归选择了不自觉的妥协投降。如果说,城堡是奥匈帝国摧残人、折磨人的国家机器象征的话,主人公K不就是一个拼命把双手高举在头上,从而向这个机器表明自己驯顺、服从的典型代表吗?正如卡夫卡在《致密伦娜情书》中所说:“诚然,人们对于自身的谜也是无法拆解的。没有别的,唯有‘恐惧’。”[7](P437)“法门之前”寓言中的乡下人、《诉讼》中的约瑟夫•K、《城堡》中的普通百姓、阿玛莉娅一家的无可奈何妥协,无疑揭示了人类社会非常可怕的异化后果,它造成了人性与人自身的分离。这种分离使人难以确证自我的真实存在。所以,他们需要从同他人的比照中,获得对自我的信任。这种惧怕本真孤独的附加值就是相互的欺瞒、麻痹,以至于达到不自知的境地。人们拼命争作“法”、城堡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机器的驯顺奴隶,大家都如此,你不这样行么?
人类社会可怕异化后果制约下的无可奈何妥协性在短篇小说《变形记》里则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小说令人信服地发现,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家庭犹似一个按部就班的舞台剧组,每个人的价值就在于所扮演角色的完美恰切。一旦你失去了对角色使命的良好表演,家庭的剧目就会因你的演砸而陷于崩溃。人们于是不得不抛弃你而重新分配角色任务,以之结成新的舞台剧组。这一切在通常情况下,是人们难以觉察因而也不可能戳穿的人生把戏。家庭主角格里高尔竭尽全力地工作,他在工作上的成就立刻转化成了现金,呈现在惊诧而又喜悦的家人面前。他在承担起全家人开支的同时,还秘密盘算着送妹妹她到音乐学院去学习。[8](P128)然而,格里高尔在一个早晨醒来后,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从而成为一个表演砸锅的倒霉鬼而将整个家庭置于阴郁、痛苦的深渊。家人们一开始面对自己的亲人变为虫子这个事实时,还能出于亲情慈爱,照料这只令人厌恶的虫子,从而表现出某种崇高的同情心和仁爱精神。但是,随着时日的拖延,“妹妹现在再也不考虑怎样才能让格里高尔吃上可口称心的饭食,她总是在早晨和中午去商店上班前急急忙忙用脚往格里高尔的房间里随便推进一点吃的,晚上根本不管这食物是否只是尝了几口,还是——大多数情况下——连碰也没碰一下,她便一扫帚将其扫了出去。”[8](P142)最后,妹妹甚至理直气壮地告诉父母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们也许不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愿意当着这头怪物的面说出我哥哥的名字来,所以只是说:我们必须设法摆脱它。我们照料它、容忍它,我们仁至义尽嘛,我认为,谁也不会对我们有丝毫的指责。”[8](P149)他们终于从厌恶到憎恨到仇视,终于不无轻松地期待着虫子的死去。这其实也是一种惧怕责任、惧怕情感无偿支付的无可奈何的妥协性。这种妥协性往往会转化为一种有意无意的敌视、仇恨,最后变成挤压自己亲人的外在合力,使其不堪最后的重击而扭曲、变形直至死去,然后默默地被永远忘却。这种妥协性使家里人有理由在格里高尔死后,长长地松一口气,而后到郊外去享受温暖的阳光;父母亲也有理由在看见女儿、格里高尔的妹妹“第一个站起来并舒展她那富有青春魅力的身体时,他们觉得这犹如是对他们新的梦想和良好意愿的一种确认。”[8](P156)一个好女婿或许可能填补格里高尔死后留下的家庭空缺,从而重新使家庭人生之戏有滋有味地演下去。家里人将很快忘记那位曾经在家庭剧组里担当主要角色,而后不幸倒楣的格里高尔。尽管这种家庭成员的冷漠,是社会生活本身的残酷异化恶果。但这异化恶果毕竟是源自于人类长期历史文化活动所孕育、所培植;源自于人类社会所不断培养出的无可救药的自私、怯懦。这种家庭伦理关系中所体现出的冷漠,在短篇小说《在流放营》里终于扩展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麻木。所以“行刑前的那一天,整个的山谷里人山人海,所有的人只是来这里看热闹的。”当第6个小时来临时,人人都希望在近处看,司令官命令首先满足孩子门的要求。于是,担任审判长的军官“左右手臂上各抱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军官甚至禁不住神采飞扬地告诉旅行者说:“我们大家看到犯人那备受折磨的脸上焕发出的幸福的表情时,是多么地高兴啊!我们的脸颊沐浴在终于出现但马上消逝的正义的光辉之中。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我的同志!”[9](P92)
卡夫卡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妥协性,其实是卡夫卡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境遇的心灵惶惑和精神恐惧。这种心灵惶惑和精神恐惧在成为卡夫卡小说世界主导氛围的同时,也提供了卡夫卡小说艺术无限创造性的丰富情感源泉。正如叶廷芳先生在卡夫卡《谈话录》的《译本序》中所说:“卡夫卡,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觉着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仿佛站在世界之外,以‘异乡人’的陌生眼光和惊讶神情观察人类社会,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攘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异己的东西,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起初多数人对于这种声音不以为然、充耳不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人们变得清醒些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卡夫卡对那些异常现象的揭示,那种警报性的‘喊叫’,日益领悟了,共鸣了,以至把卡夫卡的作品视为‘现代启示录’。”[10](P278)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小说主人公勇敢追问真理的反抗与无可奈何妥协终归又在新的层次上表现出追问真理的反抗,或者说,卡夫卡的小说通过揭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悖谬,创造了振聋发聩的警世意义,预示了通往真理的可能性。
[1]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卡夫卡.致菲莉斯情书书信[A].卢永华等译.卡夫卡全集:第10卷[M].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卡夫卡.诉讼[A].章国锋译.卡夫卡全集:第3卷[M].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谢莹莹.权力的内化与人的社会化问题[J].外国文学评论.2003,(3).
[5]卡夫卡.城堡[A].赵容恒译.卡夫卡全集:第4卷[M].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卡夫卡.随笔[A].黎奇译.卡夫卡全集:第5卷[M].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7]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A].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全集:第10卷[M].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8]卡夫卡.变形记[A].张荣昌译.卡夫卡全集:第1卷[M].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9]卡夫卡.在流放营[A].洪天富译.卡夫卡全集:第1卷[M].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0]卡夫卡.谈话录[A].赵登荣译.卡夫卡全集:第5卷[M].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冯济平
Resisting to Pursue Truth and Forced to Compromise
MA Xiao-chao
(Dep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264005, China)
One of the paradoxes in Kafka’s novels is brave resistance for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being forced to compromise. It is the paradox that gives his writing more complicated and implicit hints, signals a warning to the world and indicates a gateway to truth.
paradox; pursue truth; resistance; no alternative; compromise
book=68,ebook=102
I109
A
1005-7110(2010)05-0068-05
2010-05-25
马小朝(1954-),男,山西侯马人,烟台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及西方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