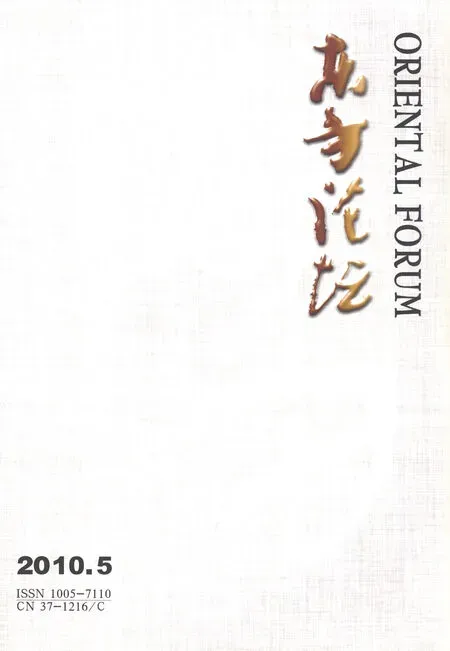《黄鹂声声带血鸣
——孙犁抗日小说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2010-04-05王金胜季美艳
王金胜 季美艳
《黄鹂声声带血鸣
——孙犁抗日小说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王金胜 季美艳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孙犁是个纠缠着诸多悖论的独特存在。从1940—1950年代中国作家构成的谱系上看,他是位《讲话》后成长起来的来自解放区的“中心作家”,其政治身份、政治地位,其写作的合政治目的性,按理说是无可置疑的,但从批评界对其接受来看,情况似乎要复杂得多,孙犁自己也承认:“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具好一点。”[1](P396)进入1990年代后,他甚至又被研究者视为“革命文学中的‘边缘人’”[2]。其前期文学创作只有一本《白洋淀纪事》、一本《风云初记》,外加两个中篇《村歌》与《铁木前传》,但却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且自1990年代以后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在有的学者眼里大有超越曾被称为“讲话旗手”、“解放区文艺方向”的赵树理之势头①这方面代表性著作:如赵建国的《赵树理孙犁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日本学者渡边晴夫也认为:“赵树理的作品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中国得到了不可类比的高度评价,而孙犁的文学具有与之正好相反的特性。这大概就是对孙犁的评价近年有所提高的原因吧。而对孙犁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定会越来越高。”,参见渡边晴夫等的《中国文学史上对孙犁评价的变迁——与赵树理比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1期。)。孙犁晚年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曾公开告白:“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的结合。”[3](P396)但学术界对其“抗战小说”的研究却较为匮乏,且基本停留在单篇作品的艺术鉴赏层面,以泛化的印象式批评为主,缺乏应有的学理含量。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些孙犁研究的专门著作和论文②代表性的著作:如阎庆生的《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叶君的《参与、守持与怀乡——孙犁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这些成果借助现代心理学、美学和西方哲学来探讨孙犁的美学思想、身份建构等问题,但总体上还局限于对孙犁及其作品的内部研究,无法将作家纳入历史结构中大幅度地敞开主体的精神和心灵世界及其美学折光。1990年代初,兼具作家和研究对象身份的孙犁极为少见地表达了对批评界某些研究不足的抱怨:“研究不能老重复过去那些东西,什么孙犁文章行云流水呀,什么富有诗意呀,还有荷花淀流派等等,要拿出一些新东西。”[3]无疑,孙犁及其文本期待着研究者以突出的创新性打破研究成规,尤其是其自期甚高的“抗日小说”的研究常规——这不仅因为孙犁的自我评价,还因为抗战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和精神结构,更因为对“后期孙犁”“新孙犁”的真正有力的理解和阐释无法绕过其抗战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展博士的《黄鹂声声带血鸣——孙犁抗日小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论著)在选题上就体现出研究者的独具只眼和基于既往学术积累所生发出的挑战性。
论著打破了以往关于孙犁的作家状况研究,作品研究,文学史型整合研究等传统研究现状,有针对性地运用传统和现代批评方法,进行了一种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总体性”研究。这种研究不但将孙犁作品的内在结构性呈现出来,而且将孙犁作品纳入一种“历史总体性”中获得整体关联的内在意义,同时揭示出孙犁创作的文化心理基础与历史性含义。
论著采用了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尽管孙犁的小说是一种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鲜明的风景画风俗画描写的“心灵—风景型”小说,但因为孙犁的作品及其本人的生活、思想与其所产生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其小说作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面影和意识形态性,因此要真正了解孙犁小说,就必须“知其人”和“论其世”,唯如此,才能客观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在他看来,所谓知人论世,应当“论世”第一,“知人”第二。孙犁在评论古书古人时有着自己的知人论世的意识:“文人处世,有个人的特征,有时代的样式。历代生活环境不同,政治情况各异,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理想的发生,都不会一样,都有时代的烙印。先秦两汉,盛唐北宋,号称太平盛世,文士众多,文章丰富。而南北朝、五代、南宋、明末之时,文人的生活处境及政治处境,就特别困扰艰辛。反映在他们处世态度和作品之中的,就很难为太平盛世的人民所理解。南北朝时期,是个动乱的时期,北朝文人很少,他们的生活,尤其动荡不安,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都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动乱。”“我们今天谈论魏收,也不过就一篇简短的传记,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论世的试探,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就很难说了。”[5](P68)应该说,以知人论世这一传统批评方法来勘探历经历史风云变幻而又葆有“赤子之心”的孙犁及其文本的精神世界是符合作家实际的。论著对孙犁小说所论,首先是着重于作家个体特殊的身世经历,其次是重视个人的才性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就是说,论著的“知人”不仅局限于革命意识形态为主的“志”,而是扩展到作家的个人生活、性情、才气、身世、立身、行事、情趣,将浅层的才情、意趣深化为作家的人格精神。具体来看,论著对孙犁关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人”,二是“文”,“文”即孙犁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艺术造诣。在对其人其文深度把握的基础上,因文以论人,或因人而观文,较好地做到两方面的结合。这在“孙犁文学创作之心路历程”部分体现得尤其集中。把作家放在所处的时代环境中,以五四新文学(尤其是鲁迅、叶圣陶等)的影响、北平的流浪、抗战烽火的激荡、革命文学及理论的接受、“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讲话》的发表、“冀中一日”运动、婚姻革命、身份革命等对孙犁其人其作产生重大甚至根本性影响的事件为中心,从生活史和精神史两大方面对其文学创作的起源、文学风格形成的心理基础,及其家庭、婚姻、生活经历、思想感情、个性品格、文化修养等进行了通盘的梳理与整合,阐释了孙犁抗战文学美学风格形成的根本原因,论述了孙犁小说与魏晋文学之相似与差异,探讨了孙犁小说兼具审美和革命的功利性的二重性特征,对孙犁文学的主体意志进行了迥异于通常研究对孙犁作品非审美即功利的品格定位,指出:“孙犁文学的主体意志不是个体意志的意义存在,而是所谓革命理想的信念所形成的大写的‘民族’概念,也正是这种大而化之的理想,才为他赋予了一种大化流行的传统伦理感受,而非简单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体意志了”。这种分析和定位,把握住了对象在个体与群体(“民族”而非“国家”“阶级”“政党”等)、功利与审美、传统伦理感受与现代主体意志、革命叙事与伦理叙事之间的复杂性,并以此为基点进行深入探讨,并以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贴合到位,而使论著生发出了诸多前人未道的创新点。
文史互证这一中国文史研究传统方法在论著也得到了较好地运用。论著以孙犁文学创作写作的历史背景为出发点,把前者嵌入历史的深层结构中,从对象的身世遭遇、历史意识和政治态度入手,深入孙犁文学叙事生成的历史环境,依据叙事内容探究孙犁从事抗战活动的经历,同时又借助相关革命史的发展脉络来解读孙犁小说,文学与历史相互参正,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对象的心胸,打开了对象新的心灵世界。论著对1946—1956年间孙犁的心态、创作与当时政治氛围、文学体制之间关系的分析;对延安时代的政治结构、政治规训、女性分配与对孙犁小说“小资情调”的批判、孙犁小说的修改与发表之间关系的分析;对建国后知识分子问题与孙犁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之关系的分析等等,作了一些颇见功底的考据分析,有些判断很有见地。仅举一例,论著对《风云初记》中李佩钟对老革命高庆山表达爱情的一句话“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入手,进行了如下分析:“这句话可以是李佩钟的爱情话语,但却是作家本人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而提出疑问“革命的老干部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恋爱对象,难道他们不喜欢这些有教养的女性知识分子吗?”,论著又结合延安革命阵营的婚姻革命及将女性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祭礼的分配这些革命史料,挖掘出李佩钟此话的深层含义:“难道老干部不讨厌男性知识分子吗?难道老干部不喜欢女性知识分子吗?”一个简单的细节分析,却举重若轻地透露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上述对李佩钟爱情话语下潜在的作者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分析,同时也得益于另一种批评方法的运用:症候式阅读。
论著以对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充分的理论自觉,较合理地运用症候式阅读方法打开了深隐复杂的主体空间。在阐释孙犁及其小说时,论著没有停留于文本的表层空间,而是深入对象的心理和文本结构的深层空间,以文本的断裂、含混、悖逆、反常等为突破口,寻求此类症候出现的原因,重新阐释作品的意义。除了上例,论著对《嘱咐》中“性爱”场景的“缺位”这一症候也进行了深度挖掘,认为,小说讲述的实际上是一个“被‘革命’包装起来的‘性爱’叙事”,“在故事的核心不是革命,而是夫妻对话,而夫妻对话都是性爱叙事的情爱话语”。在文本的叙述过程中,“经过‘革命’洗礼的战士这时已经深陷重围:‘情’与‘欲’的矛盾,欢爱与身体 矛盾,伦理秩序与身份定位的矛盾,革命不过在此提供了一个表演舞台;而当生活一下‘失去轨道’(其父亲去世带来的混乱),革命的锣鼓声声催人急的时候,‘倦意’就来了。”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性爱场景“缺位”的性爱叙事中,革命者和革命叙述因选择“情”分离“欲”而陷入的困境。另外,论著对《荷花淀》中三个关键的文学场景的分析很有意思。从具体场景入手,论著通过对其语言和行为等细节处隐藏的反常、悖逆的探查,发掘人物如何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展现自我和自我变迁,揭示某些甚至不为作家自己所意识到的历史内涵如何在超过场景、细节而形成的特定文化场域中获得表现。
论著对孙犁抗战文学中北方风景描写的阐释是相关领域中具开创性意义的成果。它集中阐释了孙犁作品中“游观”视角、在游动中的人生“邂逅”传奇、对于事件“目击”直观的心灵透入所带来的孙犁小说美学最为深层的心理打动力量,它“将孙犁风景描写有机地结合历史风云与孙犁自身的创作历程甚至将古典山水美学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情景结合起来——这些都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境界,改变了孙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6]。这些都显示了论著的独特研究用心。
总而观之,论著从历史(革命史、精神史、美学史、文学史)的角度进入研究对象,突破了以往的封闭式研究,将对象纳入一个风云动荡的历史空间中,不仅展开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野,而且也使自身获得了深沉厚重的历史感和超越作家论个案研究的普遍性意义。
[1]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A].孙犁文集:第4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2]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3]孙犁.语重心长一席话——孙犁谈文学研究[J].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简报,1994,(1).
[4]滕云.孙犁研究新声息──孙犁创作学术讨论会随想[J].文学评论,1989,(3).
[5]孙犁.买《魏书》、《北齐书》记[A].孙犁文集•续编:第3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6]郜元宝.序[A].李展.黄鹂声声带血鸣——孙犁抗日小说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book=125,ebook=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