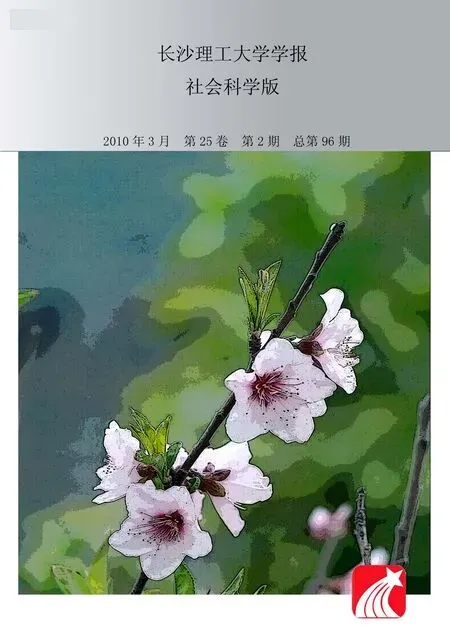王国维的术语学思想
2010-04-03张春泉
张春泉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近代学术大家王国维探赜索隐、通方知类、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由哲学而文学而历史,都极富创见。笔者以为,人们在仰望王国维蔚为大观的学术大厦时,不宜忽视该学术大厦的基本建筑材料——术语。王国维关于术语的研究形成其术语学思想,尽管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值得学界特别关注。
我们今天所谓术语与王国维所说的“学语”大略相当。王国维术语学思想主要散见于《释理》、《论新学语之输入》、《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重要文献,虽然未及集中系统论述,但已涉及关于术语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诸方面,给当今学界以无尽的启示。
一、理性:构造概念之能力
王国维明确指出,“理性者,吾人构造概念之能力也。而概念者,乃一种普遍而不可直观之观念,而以言语为之记号,此所以使人异于禽犬,而使于圆球上占最优之位置者也。”[1](P31),理性是形成概念(concept)的前提,概念通过语词表达出来,显然,王国维已经注意到了概念的符号学性质。理性是构造概念的理据。这从“理”的内涵可以看出。
“理”有相对确定的内涵意义。“则‘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1](P28)“理”与“知”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理”是认知的必要条件。“夫吾人之知识,分为二种:一直观的知识、一概念的知识也。直观的知识,自吾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识,则理性之作用也。”[1](P22)概念是理性发挥作用的结果,是理性的结晶。概念可以推演,可以进行概括和限制。正如王国维先生所正确指出的,“人则有概念,故从此犬彼马之个物之观念中,抽象之而得‘犬’与‘马’之观念;更从犬、马、牛、羊及一切跂行喙息之观念中,抽象之而得‘动物’之观念;更合之植物、矿物而得‘物’之观念。”[1](P27)显然,概念是知识的重要载体,是认知的重要工具。
概念可以在使用过程中拓展主体的认知域,深化主体的认知度,具有抽象性、递归性和概括性。“故所谓‘马’者,非实物也,概念而已矣。而概念之不甚普遍者,其离实物也不远,故其生误解也不多。至最普遍之概念,其初固亦自实物抽象而得,逮用之既久,遂忘其所自出,而视为表特别之一物,如上所述‘有’之概念是也。”[1](P28)这就是说,“概念”必须在“使用”中才有“意义“。因为“用”才有“为”和“行”。“吾人惟有概念的知识,故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先使一切远近之动机,表之以概念,而悉现于意识,然后吾人得递验其力之强弱,而择其强者而从之。”[1](P22~23)“意义”需要载体,也需要生成、传递、理解。
与理性和概念密切相关,人类的言语是“意义”的最重要载体,是传递意义的最便捷形式。“动物以振动表其感情及性质,人则以言语传其思想,或以言语掩盖之。故言语者,乃理性第一之产物,亦其必要之器官也。此希腊及意大利语中所以以一语表理性及言语者也。此人类特别之知力,通古今东西皆谓之曰‘理性’,即指吾人自直观之观念中,造抽象之概念,及分合概念之作用。”[1](P23)“理性”和“言语”是统一的,而“理性”又是构造概念的能力,这就是说,“理性”是构造生成言语的能力,“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2](P101)言语的基本单元是语词,语词与概念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便形成了术语。
二、概念:科学上之所表者
王国维十分重视概念在科学上的重要作用。王国维提出“概念之为物本由种种之直观抽象而得者”。[3](P40)“概念”是“名”和“实”的中介。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导名实关系。
王国维指出,“乏抽象之力者,概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何则?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2](P102)这就是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将“自然之世界”转换为“概念之世界”。“自然之世界”不同于“概念之世界”,前者具体,后者抽象。“概念之世界”是人所认识的世界,“而概念者,仅为知识之记忆传达之用,不能由此而得新知识。”[3](P41)概念记忆传达知识,这是概念的功用,从“用”这个层面上看,概念和术语可以等量齐观。
从功用上看,概念概括现实,术语表征和传播科学知识。“盖科学之源,虽存于直观,而既成一科学以后,则必有整然之系统,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类者,而合其相类者,以排列之于一概念之下,而此概念复与相类之他概念排列于更广之他概念之下。故科学上之所表者,概念而已矣。”[3](P46)概念可以推演其内涵和外延,从而将知识分门别类,进而使科学真正成为分科之学,概念通过推演将“自然之世界”改造为“概念之世界”,然后术语将“概念之世界”外显出来,传播开去。
概念是分门别类的分科之学的重要单元,是说理的最基本的最有效的工具。术语是概念的外显形式,是一种语言片段,通常诉诸文字记录下来,是书面语的片段。书面语是著述的最重要表述工具,一般而言,术语是著述的基本单位,其功用在于沟通著述的作者和读者。“即文字与语言,其究竟之宗旨,在使读者反于作者所得之具体的知识,苟无此宗旨,则其著述不足贵也。”[3](P45)这里所说的“文字与语言”,尤指术语及术语的组合。
三、定名:亦非苟焉而已
王国维在其论著中多次提到“名”。当“名”与“定”一起用时,“名”则可看作是“概念之世界”的具体外显形式,此时“名”、“学语”及“术语”三者的内涵和外延大致相当。“名”在科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2](P102)显然,“名”便于思索,“新名”则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手段和外在标记。
“名”和“新名”如此重要,所以王国维认为“定名”(术语的建构)一定要慎重,能借用现成的就尽量借用,尤其是在翻译外来著述时。“力言翻译者遇一新义为古语中所无者,必新造一字,而不得袭用似是而非之古语。是固然矣,然文义之变迁,岂独在输入外国新义之后哉!吾人对种种之事物,而发见其公共之处,遂抽象之而为一概念,又从而命之以名。用之既久,遂视此概念为一特别之事物,而忘其所从出。”[1](P19)这一表述告诉我们,建构术语不得“袭用似是而非之古语”,不宜抱残守缺;另一方面,既然“用之既久,遂视此概念为一特别之事物,而忘其所从出”,就不必刻意标新立异。这种科学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术语观无疑给当今学界以重要启示。
王国维不赞成用古语翻译西方语言中的术语。他批评道:“又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2](P103)王国维主张国人之于术语,应有分析的“拿来”,且力倡从日本“拿来”。他十分睿智地认识到了从日本“拿来”术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就必要性而言,“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2](P104)讲学说理的形势不断发展,“不能不增新语”,即不能不造新的术语。进一步说来,“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2](P102)“讲一学,治一艺”的“新语”不同于“普通之文字”,而是术语及术语的某种组合。既然“非增新语不可”,则其必要性自不待言。
就可行性而言,有地利之便,有语言文字之通。“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2](P102)无疑,从日本借用术语有其优越性,“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叔本华讥德国学者,于一切学语不用拉丁语,而用本国语,谓‘如英法学者,亦如徳人之愚,则吾侪学一专门之学语,必学四五度而后可’。其言可味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2](P103)王国维将汉语与日语术语之间的关系和英法徳术语跟拉丁语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比,未必恰当,但其关于我国学界借用日本既有术语之便利条件的描述和分析是公允的。
此外,王国维认识到日本术语自身精密,具备被我们“拿来”的“资格”。“余虽不敢谓用日本已定之语必贤于创造,然其精密则固创造者之所不能逮(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2](P104)我们知道,术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质是其精密性,日本汉文术语不仅从自身形式上做到了精密,还从外部主体要求上有“保障”:“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2](P103)王国维在高度评价日人定名“亦非苟焉”的同时体现了他自己关于确定术语必须谨慎的主张,术语的确定需要假以时日,需要多方考究和修定。
如此看来,从日本借用现成的术语是明智之举,可以节省很多学术资源。进一步说来,如何借用?王国维给出了方法。
首先,通过比较互证确定术语。王国维明确指出,不同学科领域的术语不可混用。王氏通过实例说明:“或有谓之(idea——引者注)‘想念’者,然考张湛(《列子注》序)所谓‘想念以著物自丧’者,则‘想念’二字,乃伦理学上之语,而非心理学上之语,其劣于观念也审矣。”[2](P104)即心理学术语和伦理学术语不可混淆。类似地,就“concept”这一术语而言,“然一为名学上之语(指‘概念’——引者注),一为文法上之语(指‘共名’——引者注),苟混此二者,此灭名学与文法之区别也。”[2](P104)逻辑学和语法学这两门邻近学科之间的术语也不可混用。
除了用比较法,王国维有时还并用溯源法。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以“Evolution(进化)、Sympathy(同情)、Space(空间)、Time(时间)、Idea(观念)、Intuition(直观)、Concept(概念)”等为例比较并溯源。首先是“日本已定之学语”与“中国古语”比较,其次是德国学者不用拉丁语而用本国语,跟中国人不用“日本已定之学语”而用本国语类比;再有,就是具体的同一个概念的不同“名”(术语语词形式)之间的比较,王国维以“天演”和“进化”、“善相感”和“同情”、“宇”和“空间”、宙”和“时间”等为例说明比较及溯源等严谨的“定名”方法的科学意义。
当然,借用(含翻译)新术语时,要有分析,要有选择,同时对译者的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即要求译者在能力上“完全”(在当时需要日文、国文、西文兼通),否则,“近人之唾弃新名词,抑有由焉,则译者能力之不完全是也。”[2](P104)
王氏以上关于借用日本汉文术语的倡导,无疑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给我们当今社会以启示:在外语的学习上,与其全国范围内舍近求远且不顾文化(尤指语言文字)上的更大差异去学英语,不如求真务实学习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更近的日语。在“拿来”和“舶来”时一定得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
最后,有必要指出,王国维术语学思想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有其动因。就主体内部动因而言,首先,王国维自身的知识结构有助于其术语学思想的形成。他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学习过自然科学。在其论著中,王氏对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常常信手拈来。例如他在评论《红楼梦》时谈到:“自是而生各种之科学:如欲知空间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空间全体之关系,于是几何学兴焉。(按西洋几何学Geometry之本义系量地之意,可知古代视为应用之科学,而不视为纯粹之科学也)欲知力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力之全体之关系,于是力学兴焉。”[4](P51)第二,王国维在治学上十分注重基本术语的诠释。例如王氏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释史》等文章阐述“性”、“理”、“命”、“史”等他所熟悉的专业领域的核心术语。第三,王国维长于经史小学,重视术语是经史小学创新的需要。我们知道,传统经史小学常在一些十分关键的概念术语上发生混淆,因此要想在该领域有所建树,超越前人,理应重视术语。正如训诂学家陆宗达和王宁所说的,“科学的概念需要明确的术语来表达。术语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基础,又是发展理论的必要条件。术语不仅是消极地记载概念,而且反过来也影响概念,使它明确,并把它从邻近的概念中区别出来。”[5](P15)
就社会外部动因而言,学术时代背景使然。在王国维之后不久,几乎是同一个时代,奥地利著名学者维斯特(E.Waster)于1931年发表了第一篇专门的术语学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提出了现代术语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6](P4)这也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王国维的术语学思想是系统的现代术语学理论的某种雏形。国内,晚清及民国时期,西学东渐,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大量的术语随之而入。“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2](P101)
一言以蔽之,如果说术语是王国维学术大厦的建筑材料,那么王国维的术语学思想即可视为美仑美奂的王氏学术大厦的零珠碎玉,熠熠生辉,值得当今学人玩味。
[参考文献]
[1]王国维.释理[A]王国维学术经典集[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2]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A]王国维学术经典集[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3]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A]王国维学术经典集[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4]王国维.《红楼梦》评论[A]王国维学术经典集[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5]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6]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