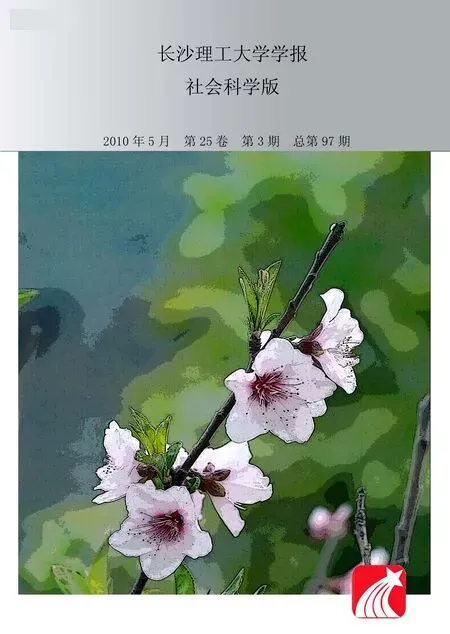“心事浩茫连广宇”
——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感伤情调
2010-04-03郑国友
郑国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湖南 长沙 410205)
19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创作热潮使我们收获了一批颇有分量或饶有趣味的单篇作品。但我们冷静地检视被热销、被影视媒体改编后热播的官场小说文本,发现其表现出来的缺陷也是不容置疑的。模式化概念化、主题先行、消费文化取向的创作倾向相当明显;二元对立的叙事老路,图谱化的官员形象,乌托邦似的“大团圆结局”、“拿揭秘作卖点”的创作取向,都使读者大吊胃口、兴趣索然。由此来看,官场小说需要突破创作困境显然是题中之义。
王跃文的官场书写为突破这种创作困境作出了尝试和探索。在其文本空间里,没有对官场腐败行为的愤激和对官场正义力量的矫情呼喊,也没有为破解官场秩序困局而有意创设的文本价值。王跃文官场小说的美学特色和价值取向显然不在这里。多年的官场生活使王跃文获得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对官场的深切体悟。把官场的生存性体验转化为日常生活景观,将官场讳莫如深的一些游戏规则敞亮为生活化日常化的叙事,这使其官场小说携带着相当丰富的当下官场文化语境的信息量。而在转化和敞亮的表述过程中,浸润着、贯穿着作家对官场、官场生活和官场人物的一种发自肺腑和灵魂深处的感伤情绪的艺术特征。正是这种感伤情调使其官场小说成为世纪之交官场书写中一种独特的美学存在。
一、感伤,作为一种感情基调,鲜明地体现在王跃文官场小说对官场小人物和文人型官员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的深切关怀之中
王跃文“按照百姓的良心去观照形形色色的人物”。[1]其官场小说为我们提供的都是些官场中的小人物或者是不大不小的官员形象,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着作家丰沛的心灵体验和足够的同情性理解。
正是在这种体验和理解的心理前提下,王跃文官场小说表现出对官场人物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关注、关心和关怀。王跃文显然无意于在宏大的叙事空间里展示官员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或政治权谋。他将笔触沉入到纷繁的官场小人物、不大不小人物的生活细节之中,从个人境遇和生存体察,书写官场精神人格取向以及这种取向的可怕之处。这种看似“在场”而又游离于官场之外的官场书写,使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获得了丰富的生活具象依托和当下群体情绪支撑的理解性表达以及写实性观照的美学效果。《蜗牛》中营造的一个意象让人触目惊心又令人叫绝:“人就好比爬行在苹果树上的一只蜗牛,它爬的那个枝丫上是不是最后有个苹果在那里等它,其实早就定了的,只是它无法知道。”这个意象给予了张青染巨大的冲击力,这使他时时生活在诚惶诚恐之中。一把年纪了,他仍然渴望能吃到那个“苹果”,逼迫自己踏上步入官场仕途之路。但是,“这枝丫上有没有苹果”呢?而能不能吃到这个“苹果”又“不在于我们爬行得快还是慢,也不在于我们爬行的步态是不是好看,而是早就注定了”。这是一种尴尬的处境。从吃不到又想吃苹果的忧伤,到似乎闻到“苹果”香而“苹果”又迟迟不见的焦急等待和慌乱,到最终终于没有吃到“苹果”的无望和无奈,张青染冥冥之中是被一种外力主导着,他无法自主,无力主导自己的命运。这似乎陷入了一种宿命论的怪圈。张青染是这样,《秋风庭院》中的关隐达、《旧约之失》中的舒云飞、《天气不好》中的小刘、《很想潇洒》中的汪凡,甚至推及到所有游走在官场中人,哪一个不是冥冥中注定了的,“有没有苹果吃,自己不知道”的那只蜗牛。对官场心存向往,但自己又无法主导,最终导致身心交瘁、欲罢不能,这显然是王跃文官场小说为小人物们吟唱的生命悲歌。
王跃文官场小说中塑造了大批文人型官员。王跃文在《国画》、《西州月》、《今夕何夕》、《秋风庭院》等作品中塑造了朱怀镜、关隐达、陶凡、孟维周等一系列官场人物形象,生动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身陷权力场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和人格分裂。通过这些文人型官员的塑造,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向我们坦露了官场权力对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和理想追求的的侵蚀和异化这一严重的官场现实。权利场对人的不可抗拒的束缚和挤压,揭示出人无可奈何的悲剧性存在。
二、感伤,作为一种创作追求,萦绕在其作品的文字空间里,弥散着的是一种淡淡的哀婉的忧伤,在这种淡淡的忧伤当中照见的是官场中一个个悲凄的灵魂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书写的都是官场的“那些事儿”,文字看似平淡、直白,甚至不无戏谑,但在“就那么回事”的官场表达中见出作家对官场的感悟、了悟和彻悟,字里行间侵润着对官场游戏规则的鄙夷和对官场秩序弊端的深深忧虑。而这种鄙夷和忧虑中流动着的是其对官场亚文化导致人性异化的恐慌以及恐慌中滋生的强烈的无奈的忧伤。王跃文官场小说中的一些主人公,似乎都患有一种官场综合症,敏感、多疑,对官帽有着十分的热情,但是许多时候又是被排除在权利中心之外,仕途不顺或者复杂的官场人际关系使他们常常处在张皇失措、犹疑不定,患得患失的心理失衡状态。于是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便成为了他们行为常态,领导的一句话都可能在他们心中掀起轩然大波,自己偶然的一次情绪的放纵都可能导致他们费尽心思来消除其可能的不利影响。这显然是一种猥琐甚至不无阴暗的人格,而这种人格最终指向的是官场典型的“抱着大树”、“上面有人”的官员依附人格。王跃文将对人的观照视为自己官场小说创作追求,权利场中“超我”和“本我”的不在场,或者说“超我”、“本我”与权利场的价值取向的背离,成为了王跃文官场小说表现的主题。于是,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呈现出这样一种创作特色:从官场中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以写实的笔法,裸露出了官场人物的众生相,而这些人物形象,无所谓好坏,也不见批判,王跃文对这些官场人物怀着的是一种深切的悲悯,弥散着在其作品文本空间里的是一种淡淡的哀婉的忧伤。
对官场人性异化,我们似乎无法从正面价值立场确认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道德风标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我们似乎聆听不到作家对腐败声泪俱下的控诉,体验不到那种自灵魂深处腾腾升起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催人泪下的情感上的震撼。在其作品的文字空间里,萦绕着的是一种淡淡的哀婉的忧伤,在这种淡淡的忧伤当中照见的是一个个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握的官场中悲凄的灵魂。《无头无尾的故事》一开篇就用一种家长里短似的语言诉说着:“偶然的一件小事,没想到竟引出那么多的是是非非来。”市长夫人在市场买衣服差了八块钱,恰巧碰见脸熟的市政府办秘书黄之楚,自然找黄之楚借。但黄没带钱,正手足无措之时,却瞥见了女邻居,于是向女邻居借了八块钱给市长夫人。于是,围绕着还这八块钱演绎了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由于市长夫人忘记了借的是黄之楚八块钱,而黄之楚又身无分文——他的工资都交给了老婆,还钱的压力迫在眉睫。于是黄在鬼鬼祟祟中将机关工会分的三十块钱当作私房钱,结果又酿成夫人对“桃色事件”的无端猜疑。黄之处面临尴尬处境,他自然地把这归结为没能被“提拔个副主任、主任干干”,而这种“人生的失败”,竟然也在家庭的口角中被还算爱他的妻子当成了攻击他的话柄。在一家人巴望着“出人头地”的期待中,黄之楚获得了一个机会,有幸成为陪市长太太的“副官”和为市长家买煤、买米的“家奴”。黄的工作因此获得领导的表扬,并据小道消息,可能提拔在即。在经历了几次波折之后,黄之楚提拔的事却迟迟不见宣布,日子还是在这种等待中流水般地逝去。这多么像贝克特的作品《等待戈多》的意象。黄之楚这个官场中的小人物,在外人看来有身份、有权势,怀着被提拔的美好向往,却又时时处在官场生活的捉弄之中,狼狈、尴尬、焦头烂额,生活有时都好像失去了头绪,无奈而又等待着“戈多”到来。但“戈多”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整篇小说笼罩在作者用语言营造出的淡淡的哀怨之中。朴实、简单的文字,我们无从体验到诸如神圣感、历史感、道德感。王跃文抛弃了传统的那一套话语姿态,以看似温情的怀着淡淡忧伤的笔调,从容不迫、不动声色地讲述着似乎属于官场又似乎在官场之外的故事。在冷静、平实的叙述话语中隐含着作家对官场小人物精神关怀失落的忧虑,照见着的是官场中人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握的一个个悲凄的灵魂。
三、感伤,作为一种美学风貌,比照出王跃文官场小说独特的艺术特质。正是这种感伤性情调,使王跃文官场小说从对官场生活的体验性内涵提升到了价值性话语的表达高度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写的是官场“八小时之内”的人和事,但更多的时候,他的笔又游离于官场之外,在官员“八小时之外”的广阔时空里展示官场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官员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其官场小说也“反腐败”,但他不是鲜明地从权利争斗内幕揭示、具体的官员腐败流程展示的层面,而是从官员生活、生存、生命的层面切入,比较隐性地使我们观照到了官场机制的无孔不入,官场生态的严重失衡、失重,即触目惊心又令人扼腕叹息的状态。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呈现出的这种“美在感伤”的美学风貌,体现了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我独特的文化站位,凝聚了自己对官场进行思索的精神空间。这使许多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包括王跃文自己对这种小说形态陷入了命名的困境和评价的理论失据尴尬。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反腐而又不旗帜鲜明地反腐,谴责而又不愤世嫉俗地谴责,“政治”而又不庄严肃穆地“政治”,“主义”而又不义正词严地“主义”。环顾同时代共存的许多同类型题材的作家,他们都把官场小说都写得很“阳刚”,但王跃文显然开辟的是与之绝然相反的一条创作路径,其官场小说呈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殊途而同归,但王跃文似乎走得更远。
《秋风庭院》很能说明问题。这篇小说的开头写的是地委书记陶凡在自家小院里很惬意地打着太极拳,并对“村野农舍”式的小院进行过细致的描绘;紧接着就讲了地委秘书长张兆林、行政科龙科长以及陶凡本人对于“村野农舍”不同态度。而小说的结尾是退休后的陶凡“终日为这里的环境烦躁。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年老了,本来就有一种飘泊感。这里既不是陶凡的家乡,也不是夫人的家乡。两人偶尔有些乡愁,但几十年工作在外,家乡已没有一寸土可以接纳他们,同家乡的人也已隔膜。思乡起来,那情绪都很抽象,很缥缈。唉,英雄一世,到头来连一块满意的安身之地都找不到了!”这里就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认同,是乡愁式的,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愁,它拓展了乡愁的精神内蕴和情感指涉。而乡愁,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目中,并不仅仅是故乡这一意义,更是人性内在的一种田园回归,自然回归。而现在,无职无权的陶老书记己经无家可归,也找不到归家之路了。这种“官性”对“人性”的暗中掏空与置换,使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蒙上了浓重的悲凉气氛。[2]
我们说王跃文官场小说中有一种悲歌意味弥漫其中,这种悲歌,显现出现今权利场的游戏规则对人植入性的道德观念破环和改写以及官场中人在适应性心理需求下对权利的艳羡和追逐的官场乱相和病相的暴露,这显然是同类型作家都在发力表现的;但是,王跃文官场小说吟唱的官场悲歌,更在于揭示出了中国官场文化对人性的致命性扭曲和伤害,而对这种日积月累有着几千年文化血脉的官场文化——如“官本位”、“包青天”寄望、“集体决定”、“组织意图”,使所有现时代的人都显得渺小和卑微。王跃文官场小说吟唱的官场悲歌,使王跃文官场小说从对官场生活的体验性内涵提升到了价值性话语的表达高度。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官场中人都不配有好的命运,即使他们官员亨通,也无法去除心灵中超乎政治的对理想、对诗意的形而上学追求。于是权利场“到头来一场空”的命运悲歌、官场中人对权利的孜孜以求终改写不了冥冥中“天注定”的人生悲歌,王跃文语言文字中萦绕着的那种淡淡的忧伤就汇聚和凝结成王跃文官场小说独特的感伤情调,成为王跃文官场小说一种艺术特质。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王跃文官场小说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感伤情调,使其作品气韵浓郁丰盈,形成官场小说中一种独特的美学存在。
[参考文献]
[1]王跃文.国画·琐语[J].理论与创作,1999,(5).
[2]王跃文.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 [EB/OL].王跃文博客,2007-01-13.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f402f60100076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