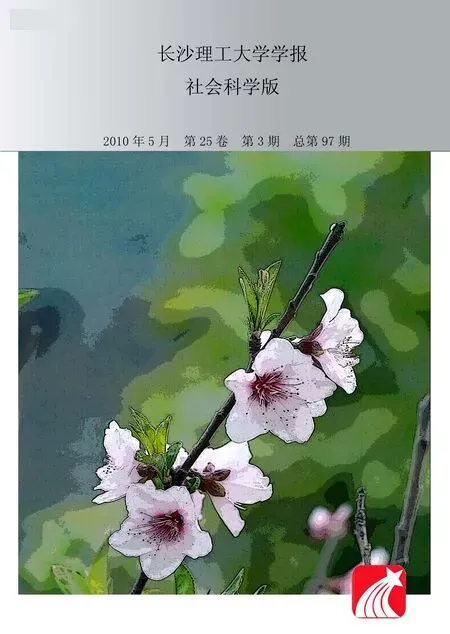词心说
2010-04-03熊开发
熊开发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 570028)
一
“词心”作为一个词学范畴,首见于晚清时期词学家冯煦的《蒿庵论词》: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邪。(清·冯煦《蒿庵论词》)
在冯煦笔下,词心与词才是对立的两个范畴,词心是“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者,词才则应该是可以传之于人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又可具体表现为某种手段或方法。问题是“得之于内”是什么意思?从冯氏之言分析,可知“得之于内”并非是先天禀赋的意思,“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绝尘之才”就是超凡出俗之才,冯氏在暗示它是一种天份,更在强调它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式的单纯品格,“早与胜流”则明确指出了后天环境可能对此品格的影响和熏陶;“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的“寄慨身世”是解释秦观的出尘之才主要指向的对象内容——关乎身世,而“闲雅有情思”是描述其情意特征。总括而言是,秦观以其出尘之才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这些身世的感慨是秦观式的“闲雅有情思”,更具体一点说,是“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的。“情深”是多情,不乱是“有思”,多情而有思,正是人们常说的“雅正”(“悄乎得小雅之遗”)之风。显然,能达到“雅正”诗教标准,决不是凭先天禀赋可行的,一定还有因“早与胜流”(胜流者,高雅之辈也)的后天熏染历练的作用。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冯煦所说秦观 “得之于内,不可以传”的“词心”是什么意思了:它就是指由出尘(出众)的才华和深厚的情思构成的一种雅正的创作心态或精神活动。由此再联想到以“赋心”为赋的司马相如的创作特点正是“曲终而奏雅”,以及晚清词家极力雅化词意的时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冯煦在其《蒿庵论词》首创的“词心”说的主要内涵,一是才华出众,不落俗套;二是情意深厚,其中深是一往情深,厚是“寄慨身世”而非一般恻艳之情,这与作为艳科的早期词情是有区别的;三是有心为之,所谓有心强调的是要心存雅正,“怨悱不乱”,而非肆意肆情之为。由此可见,人们常说的词善于言情,指的是词特别适合处理性、情或情、思的关系,而词这种善于言情的“缠绵悱恻”的特点,又正是根源于词人独特的创作心理,即“词心”的“一往而深”又“怨悱不乱”的心理特征。
二
稍后的另一位词评家况周颐的词心说却极大地丰富了这一范畴的内涵。况周颐在其《蕙风词话》中说: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
吾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霭中来。吾于是乎有词。泊吾词成,则于顷者之一念若相属若不相属也。而此一念,方绵邈引演于吾词之外,而吾词不能殚陈。斯为不尽之妙。
况氏所谓“风雨江山外有不得已者”,或者说,“自沉冥杳霭中来”者,指的是主体在感受对象世界时的一种必然发生或主体心灵深处的某种忽然而生的感动。这种开始只是隐约存在的感应或感动的心理状态,一旦进入意识中,也就成为具体的情感和情绪活动,将其诉诸笔端,“于是乎有词”。而这种通过词表现出来的具体的情感、情绪,与最初感受到的内心状态(顷者之一念)是一种“若相属若不相属”的关系。而那最初忽生的“匪夷所思之一念”或“万不得已者”,不仅成就了当下的词情,甚至还“绵邈引演”于词外,引申出“不能殚陈”的无限韵味。由此可见,况周颐所谓词心,其实包涵了三个内容,一是触物而生的“万不得已者”或“自沉冥杳霭中”忽来的“匪夷所思之一念”;二是由此心念转化而成的当下的词情;三是此心念通过当下词情进一步“绵邈引演”于词外的更多“不能殚陈”之情。如果说第一“心念”还仅是词作者之词心,后二者则不仅是词作者的词心,也是欣赏者的词心。
三
与冯煦强调“一往情深”、“寄慨身世”和“怨悱不乱”等内容相比较,况周颐的词心说则有一种“心灵化”,“神秘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他强调的“万不得已者”。 冯煦的出尘之才在他笔下被解释成了一种“匪夷所思”之念和“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这种念在不是因江山风雨之感而后生的一种情怀,而是能与江山风雨必然发生感应引发情怀的一种“万不得已者”,它适时呈现但又令人“匪夷所思”,不可捉摸,它更多地属于先天禀赋而非后天熏陶所得。
作者另有一段描写词境的材料,则将这种神秘化的心灵活动明晰地表述为一种禅念式的心境:
人静帘垂,镫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1]
况氏描写的“万缘俱寂”状态,与禅定的状态十分相似。其中“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正是说明主体如何才能回归到“我”的感受的自然性之中,它几乎可说是禅宗层层剥芭蕉似的开悟方式①的另一种表述。这种冥思方式,其实质不过是使人排除外在的观念,甚至也排除因种种观念而产生的虛假的情感激动本身,使主体凝神于自己的真实感觉之中。只有在心成为自然之心的时候,才能以其灵敏的感受力,回应着对象世界的存在变化的本质。
词境中描写的“词心”与词心中描写的“词心”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又互相补充。具体地说,“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与“匪夷所思”之一念、万不得已者及万缘俱寂后莹然开朗之心,显然描绘了不同层次的心理过程。每一念起之念是指各种随缘而起或无端而生的杂念,这是第一层次,是所谓六识纷纭之时。
其次是排遣杂念以归心凝神的层面。用于排遣杂念的是“理想”,所谓“理想”,既指对未来正确的展望和想像,又指“合理契道之念”,前者是现代语汇中的解释,后者则是古典语辞的含义。不论何种意义,有一点是共通的,即“理想”是思想者自设的一种念头,它的作用就是为了排遣纷扰人心的杂念,在它澄清杂念的同时,也必然因其为自设性理念而具有的个体有限性,反过来成为某种障碍并遮蔽内心。这是第二层的心理活动。
最后一层则是念想无碍的境界。那种“匪夷所思”、“ 莹然开朗”之“万不得已者”,不招自来,不设自成,而且不仅与往思旧念“若相属若不相属”,还能诱出无限的后续之念,“绵邈引演于吾词之外”,以至“不能殚陈”。
这就是况蕙风 “词心”说的内涵。比较诸家“词心”之论,当以况周颐的词心说最能显示这一范畴的理论魅力,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也是“词心”说如此突出为一个独特理论的主要原因。那么,它是否真实地描绘了词人独特的创作心理的普遍特征,或者只是况蕙风等人的自说自话甚至于是“禅语”的某种意义上的翻版?
清·王拯《龙壁山房文集忏盦词序》云:
唐之中叶,李白沿袭乐府遗音,为菩萨蛮,忆秦娥之阕,王建,韩偓,温庭筠诸人复推衍之,而词之体以立。其文窈深幽约,善达贤人君子恺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论者以庭筠为独至。
四
窈深幽约,正是词独特的艺术风格或词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一种审美境界,而词这种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又是源于一种独特的词情,即“恺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所谓贤人君子不能自言的窈深幽约之情,至少包含这样三个意思:其一是羞于启齿,怯于自言;其二是因其窈深幽约恺恻怨悱而确实没有能力表达出来。其三是,这种不能自言之情,是与贤人君子的社会、道德等价值观相悖的,但它又确实是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是一种不得已之情,是一种不能言而又不能不言之情。这种不能自言之情就是早期词人心中独具的情意,是促成独特的词心得于产生的内在根本,当然更是只有象温庭筠这样真正的词人才能把握好并加于表述达成的境界。
这种“恺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及其反映出的那种独特的词心,在其他花间词人的身上和作品中也同样有所体现。下面是关于曲子相公和凝的两段材料:
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北梦琐言》)。
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这种不可面对,不敢承认的艳词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并不仅是艳情,而是一种用异样的表达方式说出的特别的(很私人的——个人化的)情意:
况周颐《餐樱庑词话》[2]:“和鲁公江城子云:‘轻拨朱弦,恐乱马嘶声。’二语熨贴入微,似乎人人意中所有,却未经前人道过,写出柔情密意,真质而不涉尖纤。又一阕云:‘历历花间,似有马蹄声。’尤为浑雅,进乎高诣。”况氏选择的两句,所谓真质不尖纤,所谓浑雅高诣,并不是和凝词的重心所在,倒是熨贴入微,道出人人意中所有而并非人人能道出、人人敢道出这一点,才可能使和凝成为“曲子相公”,也才使他在成为“贤人君子”后突然有几分羞涩,不敢面对这曾经有的“柔情密意”及其熨贴入微的话语方式。无论评论者和词人自己如何“弃恶扬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和凝的词心,与其他花间词人的词心是相一致的,而花间词人这种普遍相通的词心,便是一种熨贴入微地呈现人人意中的“柔情密意”的创作心态。
况周颐《餐樱庑词话》还有另一则材料:“顾夐艳词,多质朴语,妙在分际恰合。……工微丽密,时复清疏。以艳之神与骨为清,其艳乃益入神入骨。”顾夐有一首《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沈,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清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顾太尉,‘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自是透骨情语。”况氏发挥了《花草蒙拾》的观点,而其所评顾夐词境之妙在分际恰合及一种入神入骨之艳,同样也是“花间”词心之普遍所为。
如韦庄《思帝行》: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决绝语②
尹鹗《菩萨蛮》:陇云暗合秋天白,俯窗独坐窥烟陌。楼际角重吹,黄昏方醉归。荒唐难共语,明日还应去。上马出门时,金鞭莫与伊。——痴绝语③
牛峤《望江怨》:东风急,惜别花时手频执。罗帏愁独入,马嘶残雨春芜湿。倚门立,寄语薄情郎,粉香和泪泣。——艳情语④
毛文锡《醉花间》: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鸂鶒还相趁。 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絶边庭信。——清淡语⑤
在这些词中,无论是说的是艳情语、清淡语也好,决绝语、疾绝语也好,都呈现出相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一种情语透骨、分际恰合的表现方式,这种入神入骨既艳而又清疏之情,是“花间”词人集体的词心吐露,其表现都侧重于心理单纯,多一往情深,而少寄慨身世之情思和怨悱不乱之雅意。
花间词人以外,南唐词人的词心表现最突出的当属李后主。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赤子之心又是什么心呢?从另外几条材料中可得到旁证:“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人间词话》一七条)⑥赤心与阅世多少、涉世深浅有关。阅世愈少愈浅则性情愈真,赤子之心即纯真之性情。对李后主来说,这种赤子之心,还表现为“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很显然,李后主词心的特征表现与冯煦词心说强调的“一往情深”、“寄慨身世”和“怨悱不乱”等内容是基本相吻合的。
对于“词心”同样能做出说明的是关于晏几道的几则常被引用的材料:
《彊村丛书》本《小山词》引晏几道自序云:
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考其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抚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序中所记创作的心情,与况周颐对词心的描摹精神更多相通之处。而黄庭坚所云小山之“四痴”,则同样揭示出晏几道“词心”所具有的一往情深而又单纯诚挚的内在特征:
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彊村丛书》本《小山词·序》)
这种以“痴”为特征的词心,与王国维所说李后主式的赤子之心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以赤心、痴心为基本原素构成的词人词心的最典型的表现。
在此基础上,苏东坡辛弃疾等豪放词人的词心表现内容又更为丰富。
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韩岳,变则即桓温之流亚,故词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模,适形粗鄙耳。[3]
这里所说的东坡心地、胸襟,稼轩气概,指的就是东坡稼轩的词心——作为词人的一种主体精神特征。这一特征又主要指他们的性情和精神素养,它包括先天禀赋和后天积累。就东坡而言,所谓光明磊落的心地及其忠爱之情,是植根于“性生”——也就是生性如此,所以唱出的是超旷和平之音。就辛弃疾而言,则吞吐八荒之概原是天性禀赋,这禀性在现实中郁勃积累,未得机会泄放,则转成一种悲郁的意绪。如此则有东坡词,有稼轩体。
范开《稼轩词序》又云:
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知夫声与意之本质,则知歌词之所自出。是盖不容有意于作为,而其发越著见于声音言意之表者,则亦随其所蓄之浅深,有不能不尔者存焉耳。
……
坡公尝自言,与其弟子由为文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之所为。公之于词亦然: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是亦未尝有作文之意,其于坡也,是以似之。[4]
上一段指出,声意的本质在于心器或心志之高远宏大,也即词文声韵之意皆源于词人内心的身心器质,而身心器质又有一种不依他物而自在自为之存在者在,所谓“有不能不尔者存焉”。苏辛之创作,皆非有意勉强之作,而是得之于嬉戏行乐、醉墨淋漓之中,所谓“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
这种“不能不尔”者,刘辰翁则进一步解释为:“陷绝失望,花时中酒,讬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而或者以流连光景,志业之终恨之,岂可向痴人说梦哉!……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处,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
刘辰翁虽然将这种不得不尔的心情充之以英雄感怆的现实内容,但并未因此否定它的“不能不尔”的内在属性。每个人心中都有不能不尔者存焉,但都通过不同的现实事象表现出来,词心的深刻之处,便在于它总是指向人心中的“不能不尔”之处。花间词人如此,欧阳修、晏殊被讥为或自己不敢承认的创作如此,苏轼一面嘲讽柳永,一面又不能不为之的词作冲动,同样反映了词心独有的一种“不能不尔”的特征。
张耒在论贺铸词时,同样也指出了词心词情有不能不尔的特点:“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⑦
那种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正是“虽欲巳焉而不得者”,是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张耒认为,东山词正是这样一种“直寄其意”,不“费心而得之者”,是天理之自然而然者,是性情之至道极境者。这种不得己而发之的性情,正是贺铸的词心,也是其他词人的词心可能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
《蕙风词话》卷一·五五《织余琐述》云:“蕙风尝读梁元帝荡妇思秋赋,至‘登楼一望,唯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呼娱而诏之曰:‘此至佳之词境也。看似乎淡无奇,却情深而意真。求词词外,当于此等处得之’。”
情深意真,真者,如实显现也,意真,主观之识如实显现,主观之识乃触物觉知,以心会物,以心觉物,以心识物,以心显物。在心如实显现中,物(对象世界)亦如实显现,物这意义亦当下如识所知,如实显现。情深,最能见出词境之妙,词人之识见,往往以情出之。识化为情——感动之呈现,与智识之判断识别不同,呈现感动乃是情绪活动的过程,情绪之感动,是主体精神活动全部化作生理、心理活动的自我呈现,它超越智识有限的区别可能造成的遮蔽(一己之见),而有一种当下澄明的真实。
周济在论词的“寄托”时,曾对词人创作心理有一段独具慧眼的描写,他说:
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旁通。驱心若游丝之挂飞英,含毫若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颏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5]
“驱心若游丝之挂飞英,含毫若郢斤之斫蝇翼”,最是形象化地再现了主体的感受与对象物触及的一刹那最微妙的状态;“意感偶生,假类毕达”和“赋情独深,逐境必寤”则描述了主体的体验活动的过程及其运思状态。作者在此颇为准确地道出词人创作时特有的感受和体验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独特的词人创作心态,奠定了词这一艺术形式独特的主体属性和审美特征,并为后来各时代不同风格词人一脉相承。
“词心”作为一个重要的词学范畴,出于晚清诸家词论,但并非出于这些词论家们的主观臆造,此前虽无人明确提出“词心”概念,但词的不同时期的创作和理论实践,却无不昭示了词的这一独特属质的存在。
[注释]
①参见铃木大拙与弗洛姆合著之《禅与心理分析》。
②清贺裳《皱水轩词筌》:“小词以含蓄语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牛峤:‘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抑亦其次。”
③刘承干《历代词人考略》卷五:“尹鹗《菩萨蛮》词,由未归说到醉归,由‘荒唐难共语’想到‘明日出门时’,层层转折,与无名氏《醉公子》略同。‘金鞭莫与伊’,尤有不尽之情,痴绝,昵绝!”
④况周颐《餐樱庑词话》:“昔人情语艳语,大都靡曼为工。……《望江怨》云:‘惜别花时手频执。……倚门立,寄语薄情郎,粉香和泪泣’。繁弦促柱间有劲气暗转,愈转愈深。”
⑤同上:“余只喜其醉花阴后段,情景不奇,写出正复不易。语淡而真,亦轻清,亦沉著。”
⑥《人间词话删稿》四四条,王国维还曾以“忠实”一词来说明词人的创作心理:“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⑦《彊村丛书》本《东山词》。
[参考文献]
[1]况周颐.蕙风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2]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第166页,1959、10,第1版。
[4]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