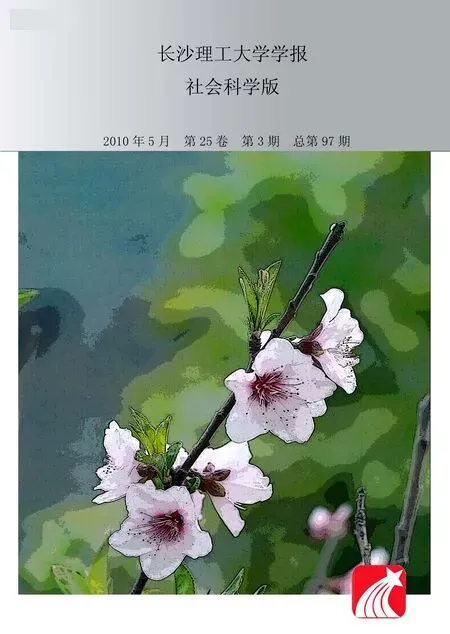缛旨星稠 繁文绮合
——西晋诗歌创作成就论
2010-04-03张鹏飞
张鹏飞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30)
继建安、正始之后,西晋诗坛群英荟萃,创作兴盛,前有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太康诗坛,后有以石崇为核心的“贾谧二十四友”诗人群体,其后又有郭璞、刘琨等永嘉诗人群体,故钟嵘称之为“文章之中兴”。西晋诗文在选取题材的多样性、创作技巧的丰富性以及对文辞的锤炼上可以说传承并进而发展了建安文学,不仅传承了建安文学崇尚“风骨气象”的美学风尚,又开创以“韵”取胜的新的美学风尚,并进而呈现出文雅化、士族化的倾向。西晋诗风在总体上虽 “力柔于建安”,但是却以“清、韵”取胜美学风尚上超越建安风骨。
一、“渐为新变”的泰始诗坛
对于西晋的建立时间,有以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晋受魏之禅让为始的,也有以武帝太康元年,晋灭吴,统一全国为真正建立之始的。本文则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以泰始元年为西晋建立时间,而对于西晋诗坛的研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往往只关注太康诗坛,而对于太康之前,泰始这长达十六年的诗歌发展状况,则所提甚少,而作为从建安、正始诗坛向太康诗坛转变的过度阶段,这一时期的诗歌对于西晋整个诗歌发展史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并逐渐显现出了与建安、正始诗坛不同的诗歌风尚。
武帝泰始年间凡十六年,即公元265到280年,这是西晋诗歌发展的初期。在泰始诗坛上,活跃着诸如傅玄、张华、荀勖、冯沈、成公绥等松散的诗人群体,其中以张华、傅玄两人成就最高。他们大都依附于当时的权臣贾充门下,并进而发展为后来的“贾谧二十四友”。泰始时期的诗歌虽然仍受建安、正始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就其内质而言已大为衰落了,不仅建安诗人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已成古风,而且正始诗坛那种反抗权势、嫉世鄙俗的忧愤已不复存在了,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歌缺乏那种强烈的现实感和峻烈的气骨。西晋诗歌正是在这种力柔于前代的情况下趋向于采缛的。
在泰始初期的诗坛上,以傅玄影响最大,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傅玄应算做曹魏时期,他与嵇康、阮籍同时,其诗也大多作于魏末。但是,傅玄虽历仕魏晋两代,却为晋初重臣,又是泰始初期的文坛之主,对西晋诗坛影响很大,可以说是西晋诗坛形成之初的代表诗人。
建安时代,诗和乐府的界限还不很清楚,很多乐府也可以看作五言诗,但到了西晋,诗和乐府的界限已较为明晰,这时的文人乐府诗创作丰富,但与建安文人乐府诗有很大的不同,建安的文人乐府诗以乐府古题写当时的时世或为阐发个人的感怀,而西晋文人乐府诗则完全以乐府古题单纯的咏古事,并进一步引发了西晋诗坛的拟古之风。[1](P142)傅玄大量创作乐府诗,一方面与他精通音乐有关,但主要是因为他在艺术上无创新精神心中无必抒之情,无必作之诗,所以只好模仿汉乐府民歌之作,掇拾前人的题旨情事,敷叙成篇,以逞才性,而这种模仿进一步演变成为西晋诗坛流行的一种创作程式,即“缘情而绮靡”,而这个“情” 与现在的情不完全相同,是前人作品中的情事,或他人的情事,而非诗人自我的诗情,傅玄的乐府诗创作,突出表现了这种创作程式,如他的《艳歌行》、《秋胡行》、《青青河畔草》大多模仿汉乐府民歌,《善哉行》、《苦相篇》代人抒情,思想平庸,一味追求典雅丽则的语言,而对美缺乏自我的感受,内心无激情,后来许多诗人比如陆机、石崇等都有大量的拟古乐府之作。傅玄的诗作一方面具有拟古倾向,开启了西晋诗坛的一股拟古诗风,是西晋诗风的开创者,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建安诗歌那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这正体现了其作为从建安、正始诗坛向太康诗坛转变时期代表诗人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风貌。
而同处于魏晋之际,而在年岁上较傅玄晚一些时间,诗风处于傅玄与太康群英之间的张华,从西晋诗歌发展史上看,是由傅玄诗风向太康诗风发展的中间环节。张华与傅玄同为晋室重臣,而且自泰始年间乃至太康时期,一直处于文坛领袖的地位,对太康、元康诗坛影响更为深远。
张华博学又善于诗文,他像傅玄那样写下了诸如《轻薄篇》、《游猎篇》等模仿前人的乐府诗,但是他又与傅玄不同:一方面他的诗歌不再像傅玄那样保留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张华的诗没有悲郁苍凉的情怀,也没有尖锐激烈的指陈时弊,他的诗缺乏一种深沉的情感和高峻的气骨,《晋书》本传称其“辞藻温丽”[2](P1069),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评价张华之诗:“五言流调,则清丽居中,茂先得其清,景阳振其丽。”[3](P42)其诗不像傅玄那样质直,而是颇事华辞。张华的整个诗风,钟嵘评其曰:“其体华艳,兴托不寄。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尤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4](P89),也就是说,张华诗的特征正是力柔而采缛,其诗作,皆好用排比对偶、堆砌典故、雕琢辞藻,后人对此评价,褒贬不一。但正是这些表现“儿女情多”的作品代表了张华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如其《情诗》五首艺术性较高,写情真实动人,语言也清新流丽,而其诗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低回婉转的情韵,则对潘岳的《悼亡诗》影响很大。
总之,在张华身上,建安诗风的影子日益淡远,而太康诗风就是在张华这种“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诗风的基础上张扬和发展而来的。西晋诗歌走过傅玄、张华相续而成的阶梯,来到了“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太康时代。
二、“勃尔复兴”的太康、元康诗坛
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为西晋诗歌发展的繁盛期,当时的诗坛,除张华仍在世外,又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4](P6)等人,以及后来元康时期以石崇为核心的“贾谧二十四友”诗人群体。一时间才俊云蒸,各竟新声,大有曹子建所谓“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其中,尤以陆机、潘岳两人在当时评价最高,并称为“潘陆”,代表了太康诗坛的主流。太康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刘勰把它总结为“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并呈现出与建安、正始诗坛不同的诗歌风貌:抛弃了建安诗歌那种梗概多气与正始诗歌的深邃哲思,转而向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形式技巧方面发展,形成了“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缛旨星稠,繁文绮合”[3](P42)的太康诗坛特征。
而作品多、影响大,能够代表太康诗坛风貌的是被钟嵘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作为“太康之英”的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其中尤以诗歌成就最大,钟嵘《诗品》谓陆机诗“其源出于陈思”[4](P69)。可以说,陆机是曹植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以“缘情绮靡”(《文赋》)的准则,将诗歌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引导了华丽雅致的诗风,流播久远。
陆机现存诗作104首,分为乐府诗、拟古诗、奉制应和之诗三类。其中大多为拟古诗。而表现陆机主要诗歌风貌的是其《拟古》诗十二首。 拟古诗,顾名思义,就是模仿古人诗作风格形式所作之诗,它发轫于魏晋,盛行于南朝,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西晋诗坛拟古之风颇为盛行,从泰始年间的以傅玄为代表的文人拟乐府诗的盛行,到太康年间以陆机为代表的拟古诗的大量盛行,一时间,西晋诗人大多以写作拟古为时尚,所拟内容,上至《诗》、《骚》,下至乐府古诗,都有大量的仿作。陆机作为这一模拟诗风的集大成者,不但在创作实践中广泛地模仿借鉴了乐府、古诗的各种题材及表现手法,更在理论上总结了“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文赋》)的经验。而其《拟古》组诗共十二首,集中体现了陆机在诗歌的表现技巧和语言风格上的追求:文辞繁缛、语言华美典雅、多用排偶。[5](P137)
与陆机齐名,同样为太康诗坛代表诗人的潘岳,其在追求绮丽、喜欢铺写等方面与陆机文风一致。南朝人论潘、陆之别,多认为“潘文浅而静,陆文深而芜”[6](P70)。这是因为潘岳的作品用语较浅,不像陆机那样深奥,文句的连接也比较紧密。但是,他也很少写出陆机那样精美工致、深于刻炼的句子,在语言的创造方面显得比较平庸。潘岳一生作过不少哀诔之文,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晋书》本传称岳“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2](P1501),又称“潘著哀辞,贯人灵之情性”[2](P1501)。在潘岳的诸多诗作中,最能展示其才华与性情的,便是他的哀诔之文,而在这些哀辞中,最为感人、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悼亡诗》三首,是他追悼亡妻之作。
与潘陆不同的是,出身于寒门的左思一反当时绮靡华艳之诗风,卓然自成一家,其代表作《咏史诗》八首是对“建安风骨”的直接继承,反映了太康诗歌成就中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一面,被钟嵘称之为“左思风力”,对其诗作,钟氏评为:“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2](P67)。就左思的《咏史诗》而言,史为诗用。诗人并非象潘、陆等人单纯的拟古,而是很巧妙地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摄取、加工,做了文学的典型化处理,从而融进了时代感、现实性,融进了个人身世遭遇之感,升华了历史的深意和诗歌的境界。左思正因为深切地感受到了门阀制度的不公,愤怒地喊出了一代寒门志士的心声。建功立业,功成不居;致力典籍,名垂后世;不干富贵,着意山林;蔑视豪右,推崇寒人。这是左思《咏史》组诗的主要内容,并开拓了“咏史”的艺术领域,“把咏史、咏怀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写成规模宏大的组诗,对后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P138)
三、“变创新体”的永嘉诗坛
从惠帝永康元年,即公元300年,赵王伦诛贾后、废惠帝,接着发生了“八王之乱”,从此,西晋走向了衰亡,而西晋诗坛也走向了最终的衰变时期。
永嘉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即公元307—312年,为两晋之交的过渡时期,也是西晋诗歌发展的衰变时期。这一时期,正是西晋政局极为动荡的时代,先后发生了所谓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变”,西晋政权迅速走向了灭亡。社会又一起陷入动乱之中,而太康、元康诗坛的许多诗人都死于这场战乱之中,如张华、陆机、潘岳、石崇等诗人在八王之乱中死于非命,侥幸逃到江左的,则远离现实,重新陷入清谈玄理之中,使玄言诗继正始之后得到迅速的发展,钟嵘《诗品序》言:“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4](P10)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趋向于衰落,但在衰落中同时存在着新变——玄言诗的兴起。
这一时期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郭璞和刘琨两位诗人,其内容风格与当时盛行的玄言诗极为不同,“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重我寡,未能动俗。”[7](P1742)郭璞的诗,打破了当时玄言诗蔚为成风的局面,开创了游仙这一特殊的诗体,并借《游仙》以抒怀,歌颂高蹈遗世的精神,从而给玄言弥漫的永嘉诗坛带来一股清新的诗风。而经历了西晋灭亡全过程,并饱受战乱之苦的诗人刘琨,则继承了建安风骨以及左思之风力,以描写战乱之苦、亡国之痛为主要内容,反映了当日的士人在动乱危难的环境中不同的人生态度,并表现了一个爱国志士的热情与悲痛,从而呈现出与当时诗坛不同的以慷慨悲凉为美的诗风。
在西晋“中兴”的诗坛上,除了上述几位外, 其他诗人,据丁福保、逯钦立所搜集,还有将近百人,而被列入代表诗人之列的,还有傅咸、陆云、潘尼、张载、张亢、张协等人。
四、“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西晋诗歌艺术之新变
对西晋诗风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云:“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连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P27)而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评价为:“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7](P1743)从此两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晋诗坛更注重诗歌修辞技巧,自建安时期产生而发展于正始诗坛以追求辞藻华丽为尚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在西晋时期发展到极致,从而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一种文雅化、贵族化的倾向。
但是,在注重诗歌技巧的同时,西晋诗歌仍以表现人生的伤感为中心主题,诗歌的抒情性,在主观意识上甚至比前代更为受到重视。然而面对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诗人往往选择逃避,而寄情于山水、玄远,所以在当时的诗文创作中,往往充斥着一种无奈、悲凉乃至于绝望、颓废的情感。简而言之,对于西晋诗风,可以“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和“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概论之。
综上所述,从“渐为新变”的泰始诗坛到“勃尔复兴”的太康、元康诗坛,最后到“变创新体”的永嘉诗坛,西晋诗坛群英荟萃,创作兴盛,前有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太康诗坛,后有元康时期以石崇为核心的“贾谧二十四友”诗人群体,其后又有郭璞、刘琨等永嘉诗人群体,故钟嵘称之为“文章之中兴”。 西晋诗歌一方面继承建安诗歌“风骨气象”和正始诗坛“缛密深邃”美学风尚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在选取题材的多样性、创作技巧的丰富性以及对文辞的锤炼上传承并发展了建安、正始诗坛,并开创了以“韵”取胜的新的美学风尚,呈现出文雅化、士族化的倾向,从而形成“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文学特征,并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可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在中古诗歌发展史上开创了继往开来的诗歌艺术风尚。在中古诗歌发展史上可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总体而言。
[参考文献]
[1]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唐]房玄龄.晋书[M].中华书局,1974.
[3][南朝·梁]刘勰著,郭晋稀注.文心雕龙[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4][南朝·梁]钟嵘.诗品(徐达《诗品全译》本)[M].贵阳人民出版社,1990.
[5]葛晓音.八代诗史(第四章.西晋诗风的雅化)[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6][南朝·宋]刘义庆(柳世镇注).世说新语[M].巴蜀书社,1991.
[7][南朝·梁]沈约.宋书[M].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