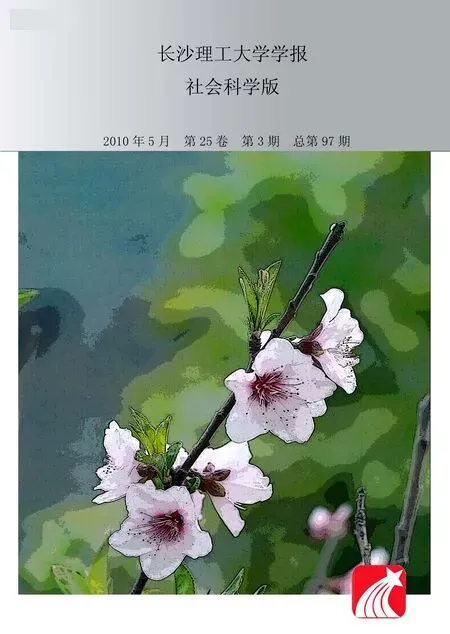中西理性概念差异及其对传统法理念的影响
2010-04-03周雪峰
周雪峰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然相异的两种文化类型,尤其是法律思想文化更是大相径庭。传统中国文化注重现世性的道德修为和建功立业,强调学以致用;传统西方文化注重超越性的精神思辨和批判意识,强调学以致知。正因为西方文化学以致知即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使其往往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生活而遨游于永无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倾向。西方哲学所独具的这种追求形而上学理想的超越性倾向和将知识本身作为终极目标的学术特点,是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哲学理解大相径庭的。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就培养了一种深厚的“实用理性精神”,重实际而轻玄想,崇现实而抑超越,正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朱熹)”,说到底,在中国,哲学和其他学术中的一切深奥思想都必须满足于为政治实践和道德服务的现实需要,形而上学必须落实到道德教化和日常事功之中。
一、西方理性发展的简要脉络
1.理性的源头:逻各斯(logos)。
理解西方法律文化的关键,首先要理解西方的理性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性是贯穿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轴,即便是后现代思潮,也是内涵着西方理性的基因的,流淌着西方理性文化血液的,不了解西方理性文化,而妄谈后现代只是隔靴搔痒,只知皮毛,无法知晓西方文化的精髓。要了解西方理性文化,首先必须要厘清一些概念,尤其是理性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概念辨析主要以理性的起源和开端进行的,正因为“开端的确定所依据的,是在持续的往昔中始终被重复的事情”。[1]
“逻各斯”出自希腊语λoyos(logos)的音译,它含义丰富,汉语里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词。著名哲学史家格思里在《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中详尽地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纪及之前这个词在哲学、文学、历史等文献中的用法,总结出十种含义。①逻各斯一词的原意是“话语”,也由此带来了规律、命运、尺度、比例和必然性的意思。为什么在逻各斯意义上的理性含有规律、命运、尺度、比例和必然性的意思呢?这就需要考察逻各斯的产生的历史发展过程。
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中的第一句话所说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2]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发展是全人类所共有的,逻各斯正是基于这一人类共性而被提出的。泰勒斯之所以因为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而被誉为哲学之父[3]。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是第一次突破传统的神话宇宙论而用自然物质本身来说明万物本原;第二,他将万物的变化统一为一个事物实体,从个别事物上升到一般的事物,即提出了事物的本质问题;第三,他第一次用哲学的方式而非神话的方式表述了关于本原(即万物由以产生的源泉和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的思想。[4]
泰勒斯的学生阿纳克西曼德进一步提出始基(即本原)这个概念。到了毕达哥拉斯派,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进一步朝着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发展。该学派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数”。他们认为“无形性的东西”连自己都是无定形的,怎能给世界万物定形呢?所以万物的本原应该是万物共同的有定形的东西即“数”。 在他们看来,“‘数’是构成事物实体的基本元素。②赫拉克利特综合米利都派和毕达哥拉斯派提出了“火本原说”。赫拉克利特说:“这个世界,对于其他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5]火本原说虽然也是用某一自然元素来解释万物的本原,但是他特别提出了这种转化的方式是按照“一定分寸”进行的。火的燃烧本身是无定形的,但是它燃烧的方式却是有定形的(一定分寸,如“火苗”、“火舌”),这样就“表现为一个无定形和有定形相统一的过程,即无定形的火在燃烧中自我定形”,“火是变化无常的,始终处于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但其‘分寸’、‘次序’、‘周期’、‘必然性’等却是永恒不变的,是万物所遵循的普遍法则。这种永恒不变的普遍法则被赫拉克利特表述为逻各斯”。[3](P20)这样从“火本原说”中赫拉克利特明确提出了“逻各斯”这个概念。正如邓晓芒教授提出的:“逻各斯”概念的提出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创举。从此,规律、确定性、逻辑、理性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轴。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这里不仅具有客观规律的含义,同时也具有主观理性的含义;并且在这里,逻各斯的客观含义(规律或秩序)与主观含义(理性或智慧)是统一的,所谓理性或智慧就在于对客观规律或秩序的认识和把握。到了巴门尼德,他最终完全抛弃了感性,提出只有存在才能作为世界的本原。巴门尼德的“存在”抽掉了一切感性特征和数量规定,要把握世界的本原只能由理性思辨和逻辑来把握,而不能由感性直观来把握。
从这个历史发展脉络中,我们能清楚的看到逻各斯、理性是如何蕴含着普遍性、规律、命运、尺度、比例和必然性的深意的,是如何一点点的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具体走向一般的,从偶然走向必然的。这就是西方理性思想的最初源头:逻各斯。
2.理性的起源:古希腊自然宇宙观。
古希腊哲学通过对自然事物进行抽象概括解释世界,从而将自己从宗教和神话思想中解放出来,实际上是人第一次从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的压迫和屈从中超脱出来,人第一次把自己从自然的宿命中解放出来。古希腊哲学经过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人的论述已经显示了理性发展的一个最初脉络。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达到了古希腊哲学的高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最终奠定了古希腊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苏格拉底提出著名的口号:“认识你自己”的口号,实际上是要人们的注意力从自然界转向自身,主张通过研究和审视人自身的途径来研究自然。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提出“理念论”。理性是关于纯粹理念的知识。亚里斯多德将探索世界的本原问题归结为第一哲学,他认为现实世界仅仅是具体的多变的不确定的,而实体是不变的,是第一因。要把握真理就是要找到事物运用的原因,第一因不能通过感性,只能通过理性的概念、逻辑、范畴才能把握。
古希腊哲学的特点就是寻找世界的本原,而世界的本原是不能靠感性发现的,只有运用理性才能真正找到,因为理性才具有确定性、恒定性、必然性和客观性。所以古希腊理性是一种自然理性或客观理性。
3.理性的回归:文艺复兴以及近代理性主义。
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是一种客观世界的哲学,即自然哲学和本体论,而此时的理性是自然宇宙论即客观理性,那么中世纪哲学主要是主观精神世界的哲学,即心灵哲学。而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代替了对宇宙理性的崇尚,宗教理性取代了宇宙理性。当宗教理性无限地抬高上帝之时,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便遭到了外在力量的扼杀。启蒙理性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它旨在把理性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使人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在这次启蒙中,理性、科学、个性得到了充分发展,人类恢复了自己的尊严。
近代关于理性的集大成者是两位思想巨人:康德和黑格尔。
康德将理性与感性做了严格的区分。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就叫做感性。所以,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且只有感性才给我们提供出直观;但这些直观通过知性被思维,而从知性产生概念。”[2](P25)也就是说康德认为所谓“感性”,指人的认识的“接受性”即一种被动接受的认识能力,也就是“直观能力”。 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人的认识能力还必须往高处提升,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知识。所以和感性相比,知性和理性都属于“高级认识能力”。 感性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能力,知性则是一种主动地产生概念并运用概念来进行思维的能力,所以知性的特点就是在于自发性和能动性。理性是比知性更高一级的认识能力。知性一般是产生概念(范畴③)来进行判断的能力,理性则是进行推理的能力。判断总是一次性的,它离不开经验对象,所构成的是一个个单个的知识;理性比知性更高一层次,知性要应用于经验,而理性是超验的,知性产生概念或范畴,而理性是运用概念进行的推理,推理则不和经验对象直接打交道,只和知性已构成的知识打交道,因而是可以向上或向下连续推下去的,作为一条法则,则是要通过理念(理性概念)而获得完备性的整体知识。[3](P211-215)
继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将康德的德国唯心论和理性主义发展到了最高点。黑格尔也必须回答感性材料与纯粹概念推理得出的理性知识的真理性之间的关系。黑格尔提出了“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观念。他认为,一方面,事物的本质只有在思想中才能得到规定。另一方面,人的主观意识在其发展中会上升到客观精神,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认为感性和理性不存在两个领域的划分。二者的联系在于思想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使感性经验能上升到纯粹思维(理性)。理性知识是感性经验知识上升,而这种上升是一种自我否定。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有两个基本构成要素:一个是逻各斯(logos)即理性,一个是努斯(nous),这个词本意是“灵魂”,具有能动性和超越性的意思。逻各斯精神即理性精神注重逻辑和规范性(对此方面的强调就发展出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努斯精神注重个体的超越性和个体的自由(对此方面的强调就发展出西方的自由主义)。黑格尔认为逻各斯和努斯都是理性,努斯即超越性,超越性首先是超越感性的东西。那么如何超越感性就是靠努斯精神,即能动性、自发性、自由的精神,跳出感性的束缚。所以黑格尔讲理性一方面是逻各斯即作为一种规范的理性,理性一旦成了一种规范,那就是一种规律、一种必然命运了。但是理性还有一种能力那就是超越,超越感性。这里似乎就有了一个矛盾:逻各斯要规范,努斯要超越,要打破规范。这恰好是黑格尔整个辩证法的精髓:正因为它们是对立的,所以它们是统一的。也就是说真正的规范要靠超越建立起来,感性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规范的,而超越或自由并不是任意的超越,自由也不是任意的自由,必须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超越。两者是辨证统一的。反过来,如果逻各斯离开了努斯,它就会偏向一种形式化,成为一种“铁的必然性”,一种限制性的东西,一种束缚人的东西,后现代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因为它束缚人;另一方面,努斯如果抛弃了逻各斯这个形式,就会陷入一种神秘主义,一种相对主义,主观主义,那一切都是偶然的、完全主观的等甚至都会容易倒向虚无主义。[6]而黑格尔认为理性辩证地包含着这两个精神(逻各斯和努斯)。
4.理性的怀疑和解构:后哲学时代。
传统哲学和理性在黑格尔的庞大理论体系之后因现代哲学和非理性的兴起而走向解体。许多哲学家提出哲学应由研究外部自然界转向研究人本身的内心世界,由倡导理性转向否定理性,鼓吹神秘主义的直觉,导致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另一些哲学家虽然主张哲学可以研究自然界,但是反对探索事物的基础,本质,而只是描述和整理感性事实,声称要把哲学变成实证科学,也就是所谓的实证主义哲学。[7]后现代思潮以反对理性和解构理性而走向非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
理性似乎也无法逃脱辩证法的命运,理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停止过的在矛盾的运动之中,这个矛盾就是黑格尔所讲的反自身或自否定,在古希腊时期,理性从感性和盲目中挣脱出来,发展出人类的一个轴心时代,到了中世纪理性主义发展了极端,通过自否性和反自身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了绝对理性主义即宗教理性,然后这个绝对理性主义又要反自身和自否定,历史进入了理性的回归—启蒙运动的发展。启蒙运动之后,18世纪的法国哲学机械论又将理性变成技术理性主义,束缚了人的发展,出现了经验主义的对抗,休谟的怀疑经验论打断了理性主义的独断梦,康德又重新树立起理性主义的大旗,到了黑格尔又走向了“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又一次将理性主义体系化、封闭式和绝对化。理性又一次走向了反自身和自否定,非理性主义兴起。后现代高举“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解构和否定理性,而弘扬非理性主义。
三、西方理性与中国的“理性”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对西方理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里我们要谈谈西方的理性与中国的“理性”的区别。在西方哲学中,“理性”对于自然规律而言,被看作是万物的运动规律或世界的本原,对于人的实践能力而言,是一种符合逻辑的规范要求,即人类活动的基本规范。理性的精神就是,一切思想和行为都需要符合规范,需要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行事。那么在西方哲学中就最基本的方面,“理性”就是一种规则要求,而这种规则要求是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这种必然性和普遍性最终是由人的自由决定的,而自由又是规范的基础上一种能动性和超越性。
理解中国文化中的“理性”,要将“理”和“性”分别进行分析。中国的“理”通常是与“道”联系在一起的,俗称“道理”。“道”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一章就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道”即恒道、永久的道,也就是天道、天理的意思,就是探索世界的本原、始基是什么的问题,这一点与古希腊哲学家探讨世界的本原的意图上是一致的,差异之处只是在于他们认为的世界本原或本体之内容的不同。“道可道”中的第一个“道”是常道、恒道的“道”,后面的“道”是言说的意思。这句话意思是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道”,即“恒道”是不可言说的,可以言说的是“名”,而这个可以言说的“名”是 “非常名”。“常”就是恒久的意思,也就是说可以说出来的就不是永恒的。“道”是不可言说的,所以是“常道”,“名”是可以言说的,所以名就是“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就是讲天地的开始或始基是不可命名的,而万物是可以命名的。[6](P74-86)因为“道”是不可言说的,是最高境界,只能靠体悟。但是国家的治理要有标准,不能靠个人的体悟,个人的体悟是没有标准可言的,所以要命名,正所谓孔子所说的“为政必先正名”。正名了一个国家就有了等级次序了,有了这个次序国家才好治理。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在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有了名,刑罚就有了标准,人民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才有法可依了。所以“名”虽然与“道”相比是次要的,但是因为“道”不可言说,所以“命名”对于国家的治理来说就很重要了,那么命一些什么“名”呢?这个“名”的内容是什么呢?简单讲就是“名分”,这里就涉及到伦理纲常。 “理”最初的涵义是按照石头的纹路把玉解开(“王”字边意指治玉即玉匠把璞按照玉石的纹路解开)。理即玉石中的纹理,纹理就蕴含着一定的条例和规律。[6](P94)后来韩非子解释理就是道,意指规则、规范。到了宋明理学“理”上升为宇宙的本体、最高的宇宙规律,是与人心相通的,但是却体现为对个人欲望冲动的一种压制,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这里的天理与天道不一样,天理是可言说的固定的天道,由“天子”命名实施,这就是伦理纲常,就是道德规范和政治规范。
在中国哲学中,“理”既作为一种哲学本体和统治正当化根据既可以被理解为“天理”、“天道”,也可以作为个人日常行为被理解为“理由”或“根据”,而“理由”又包含着“原因”的涵义。中国哲学的“性”主要是指“性情”、“秉性”或“性格”,或者是用作把形容词、动词加以名词化的助词,这样, “理”与“性”结合就具有“说理”的涵义,即“讲道理”,设法解释某种行为(这里主要就是讲的个人行为)的理由和原因。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理”与“性”是一对矛盾的范畴。“性”正如孔子所说:“食色,性也”主要是指人的一种天然本性,而自然本性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中是应该压制的,用什么压制呢?主要是用道德和政治规范即“理”,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但是如果“理”与“性”结合起来用,就是用“理”来教化(说理)“性”,达到“克己复礼”,那么“性”就是一种有道德的“性情”、“秉性”、“心性”。
这样的“理性”主要不是寻求普通的、形式的、客观的规律或规则,而是满足于能够用同一文化共同体所接受的理由去解释具体的行为。当然,中国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并不完全排斥普遍的原则或规范,有时甚至把某种普遍原则确立为理性的最高标准,把这种原则看作是先在于并超越于具体的道德规范。然而,这种作为普遍原则的“理”之形而上学的规定是事先不容违背的预定好了,使其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原则,所以,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概念,就是说,它不是出自于人们内心的理性要求,而是强加于人们的外在要求,更准确的说,是一种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要求。可以说,中国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基本上是一种道德规定,因为他要求的是对人们的行为给出理由,但是这个行为的理由的正当根据却不是由作出这个行为人的绝对的,而是由外在的已经预设好的伦理道德决定的。而这个道德规定或标准又是“天道”、“先王”定下来的,是不容许个体自由选择的,至于“天道”、“先王”为什么定下这个道德标准,那是不能言说的,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中国的“道”、“理”“名”、“言”这些概念和相应的范畴都是有内在勾连的,呈现“太极”图形。
中国哲学理解的“理性”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如果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理是根据其他的因素而不是他的行为理由,那么,我们又当如何理解“合理”就是“有理由”、“有道理”呢?[8]这个矛盾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哲学理性概念的内在逻辑矛盾造成的,即理和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理与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理,作为天理,是由道决定的,但是道却不可言说,只能靠体悟,那么每个个体的体悟当然是有差异的,那么中国文化理应强调个体的差异性,但是个体的差异性正是需要天理压制的,或者如果个体体悟到的道应该符合本体意义上的普遍性,那么这种差异性倒是可以上升为普遍性,但是既然道是不可言说的,那就没有判断的标准了,也就是说哪个个体的体悟是正确的呢?有没有标准呢?其实在中国文化里是有这种标准的,那就是先王所定下来的伦理道德,那么这就抹杀了个体的能动性和自我规定性,个体的自由就被取消了;另一方面还由于没有分清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意义上的理性(实践理性),从而混淆了对合理性的判断标准,继而取消了判断标准之“合理性”的怀疑。在西方哲学中,理性既是本体论意义的概念也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认识归根到底是一个“求是”、“求真”的过程。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识中的“求真”,即关于人们的认识如何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的规范要求,“合理性”首先就有一个认识论上的求真,即对个人行为的一个客观的认识判断而非完全的主观价值判断。但是,在中国哲学中,合理性概念却更多地是一种价值判断:说某个人的行为是合理的,就是说,这个人的行为是好的,是值得肯定的,这样,理性的标准就变成了一个价值的标准,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有理”就变成了看它是否符合这个人所处的社会或文化共同承认的价值规范,所以,团体或局部的价值标准自然成了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理的最终尺度。这样理性就等同于已经预设好的道德价值判断,至于这个价值判断是怎样的或何以可能,这个价值判断的认识能不能真实的反应人类社会规律的要求,这是不能追问的。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在中国是缺乏的。把理性的标准看作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哲学一切以“人”为基点的认识论,这恰好抓住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根本目的即人自身,这就使认识活动本身具有更为明确的目的性和指向性。另一方面却忽略了认识论的客观方面, 消极后果就是完全取消了人类认识活动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更重要的是在本体论上取消了个体的自我规定性,个体被抛入被决定的宿命中。
四、 中西理性概念之差异对传统法理念的影响
从对中国理性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理与性本身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并且理性在取得表面上的和谐(用理来教化性,性便是具有道德的性情、心性)之后,在实践中仍然陷入矛盾之中,即自我行为的合理性不由自我行为的根据决定,而由外在的因素决定,那么自我行为的合理性的问题实际上转化为一种外在因素的合理性问题,而外在因素的合理性却又是无法言说的也不能言说的(没有道理的)。这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矛盾。在这个矛盾的表象里隐藏一些中西方对于终极关怀、道德和价值判断的差异,甚至也隐藏着中西方对主客体关系的颠倒性认识。中国的终极关怀似乎是主体的人,但这个人又被自然决定的,虽然在表面上看是被君王决定,但是君王是天之子,所以连君王也是由自然、由天决定的,而天即天道,天道却是不能言说的或不能认识的,那么主体最后是由一个不能被普遍认识的客体决定的,而这个客体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虚无决定的。这样主体(人)就陷入了虚无的宿命了。
虚无毕竟是虚无的即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客体如何决定主体(人),于是就有了“理”,有了“名”。那么这个“理、名”由谁来确定呢?天子即天道的代表者。这就使天子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才行,这个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既然天子代表的是天,天道,权威因此就具备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天子本身是主体(人),也就是他只是一个代表,而不是真正的天,权威也就具备了必然性。权威的绝对性的天然对敌就是怀疑。也就是要毫无怀疑的服从权威。对权威毫无怀疑绝对服从的就必然有了两种需要,一个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或自我决定性的取消,二是神秘主义的文化。所以孔子有一句教导君王的话:“民可使其由之而不可使其知之”(《论语、泰伯》)。故孔子推崇“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④,而反对晋铸刑鼎。但神秘主义对于主体来说毕竟是外在的,这个能由天子们外在的控制,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怀疑,你一怀疑就没有信仰了,也就没有权威。而自我意识的一个首要精神就是怀疑,自我“意识到自我”(即主体要认识主体自身)的第一步就是要问一句:我是谁?怀疑才能觉醒,怀疑意识的觉醒使得君王的外在控制根据受到动摇。所以为了避免它,就必须将“我是谁”的问题在意识到之前就把它解决掉,用什么解决呢?名分。那就要在等级次序中为“我”划定一个位置,然后通过名教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韩非子杨权》),故孔子说“为政必先正名”(《鲁论》),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可以看出,没有“名”的后果就是“民无所措手足”。民是谁?民是名即是由名决定的。所以在中国名分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它是决定你是谁的问题。既然名分都决定了,那就不能犯上作乱。个体就被固定了或被决定了,那就自然服从那个决定自身的东西了。
梁治平先生认为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表达了两个命题:第一,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第二,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9]这种社会的特色就是法律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与承担是由个人的身份来决定的,名分构成了伦理纲常的根本。法律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⑤“父而赐子死,尚安敢复请?”⑥到了唐宋律,虽然父母杀死子孙皆处徒罪,但如果子孙系犯教令而杀之,需要较故杀罪减一等。[10]再比如,子女对父母须以恭敬顺从为本,常人相骂不为罪,但是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总之,家族高于个人,名分终于责任,依此原则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如容隐制度,如复仇制度。[9](P20)不但在家中身份关系是承担法律义务的根据,在封建社会中的身份关系(贵贱等级)也构成了封建关系的基础,如“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⑦贵贱等级的差异区分是非常繁杂细致的,从饮食,服饰(甚至到了衣料)房舍到车马等等事无巨细的详细规定。生前如此,死后(丧葬)也不例外,“同是一死而有崩、毙、卒、死、捐馆等不同的名称”[10](P179)而“丧葬的用器和仪式,自始丧以至埋葬无一不指示阶级的差异。”[10](P179)
“中国的政教以纲常为本……为政者以政治的力量来提倡伦常,奖励孝节。”[10](P85)所以我们通常称呼的“国家”一词就带有深厚的家国一体的中国文化内涵。“在古人的观念,忠孝相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同,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11]在家用孝作为最高原则来制定各种律令,在国以忠为最高原则来制定各种律令,而两者在通常的情况下是相通的即家国相通,君父相通。正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⑧以孝悌为根本原则的伦理纲常是与代表国家权力的皇权相统一的,“忠”本身就是最高的孝,忠孝在最高原则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一般的孝和最高的孝(即忠)之间发生冲突。[12]也就是说家与国、忠与孝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矛盾产生了,怎么解决呢?“据历代法律,凡罪涉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直接危及皇权、国家的情事,什么容隐、子孙不得告父母、子报父仇,都化作乌有,犯者定严惩不贷。本人身首异处还算是侥幸,弄得不好还要株连三族、九族。”[9](P22)可以看出,家的伦常构成了名分的基石,构成了国之律法,但是这一切都是手段,都是为了君之统治,国是谁之国?“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⑨所谓家国一体只是用以纲常名教以及相应的律令来服务于“王”。瞿同祖将以此为基础的社会阶级(阶层)分为:贵族官吏、良民、贱民。[10](P197-222)名分对在身份社会中的民的意义在终极上甚至是关乎他作为一个人的根据,违反名分其实就是违反对自己的界定,那民也就是失去了其在这个家国中的根基,从内在意义上讲他是失却了自我(这个自我当然不是由自我决定的自我)的存在价值,为家族社会不容;其次,名分对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来讲,是关乎制度的稳定,违反礼治,也就是违反了以纲常伦理为皈依的宗法礼教,为国不容。
总之,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说:“社会也好,法律也好,一切都围绕着这个‘名分’,它是纲常名教,是富于差别性的礼。所以,社会乃是身份社会,法律乃是伦理法律。”[9](P26)中国的礼法包罗万象,举凡伦理纲纪、礼仪习俗、法律政令、典章制度,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礼法这个概念与舶来品法律其实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法”概念有广义与狭义有两个不同的词表示:拉丁文:Jus和Lex,德文中的Recht和Gesetz,法文中的Droit和loi,而JUS、Recht、Droit本身含有公平、正义、权利等内涵。也就是在西方法本身就内涵有正义、公平、人权等理念,而中国的“法”的概念并没有内涵着这些理念,相反“法”只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术”,那么这里就一个出发点的不同,西方的“法”及“法治”本身内在的要求正义、权利等理念(理性的概念),而这些内涵不断历史演化,发展成“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权力制约”、“分权制衡”等自然法的理念,甚至西方现在的“实证法学”也是内涵着自然法的基因。而中国的法的理念的出发点不是正义、权利等这些理念,中国“法”理念的出发点是“君权”,是巩固统治的一种工具,本身并不具备正义公平权利等内涵。“法的工具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走出“法的工具主义”。“法治”是治国手段,“手段”(如“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即“工具”,表明“法”本身并不具有“目的性”或“本体”的意义。[13]
对西方而言,从法的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法律与理性就联系在一起。苏格拉底将法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性因素影响的理性”。[14]斯多各学派认为支配世界的原则就是理性,自然法就是理性法,在服从理性命令的过程中,人乃根据符合其自身本性的法则安排其生活,即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就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西塞罗说:“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吻合的正确之理性,它对所有的人普遍适用,稳定持久地存在,它通过命令召唤履行义务,经由戒律防止作恶……限制这种法律的影响,有悖于上帝之法,部分废除它也不允许,完全取消它也不可能。但我们既不通过元老院,也不能经由人民解除这种法律对我们的约束……法律是永恒不变的法律,将适用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同样将有一个超越一切的共同的导师和主宰:谁不服从这种法律,谁就是逃避自我,因为他违反了人的本性,为此要遭受最严厉的惩罚。”⑩古希腊时期法哲学认为万物和一切行为受世界法则、世界理性统制。古典自然法学的创始人格老秀斯认为成文法源于自然法,自然法源于人的理性。康德将法的原理归于权利,而将权利的原则又归于自由,而自由又是理性推导出来的。所以康德的法的理念就是自由的理念,就是理性的理念。康德认为法权分为自然法权(即自然权利)和实证法权,自然法权是建立在先天原则之上,实证法权则来自于一个立法者的意志。自然法权是实证法权的根基,而自由权是衡量一切具体法权的标准。康德正是通过追溯自然法权内在的道德根基,康德把自然法权与自然法则区别开,同时,也正因此,自然法权是把自然法则引向其道德内核的桥梁。他要把自然法权的唯一基点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以便从中引申出道德的内涵。[15]而这种道德内涵就在于道德命令本质上立足于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即道德自律。黑格尔认为:“法的观念就是自由,即意志的自由。”黑格尔说:“人间最高贵的事情就是成为人”,但人却不总是高贵的,唯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是高贵的。”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呢?他说“法的命令是‘作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16]这样黑格尔把法提高到人之成为真正之人的命令。唯有遵守这种命令,人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任何一种包含着自由意志的存在,就叫做法”。[17]这种法(命令)就是作为人的意志的自由。
总之,古老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然相异的两种文化类型,尤其是法律思想文化更是大相径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自古以来是缺乏西方这种理性文化的,由此造成了中西法理念的巨大差异,西方的理性精神主要是逻各斯和努斯精神的辩证统一,而中国的理性主要是两个单词的组合,理和性,即用理来教化性,以形成以忠孝为皈依的宗法礼教制度。其实这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人、人性、人格的认识的差异:西方强调人以及人格的独立性,人的自我决定性,倡导自我意志;而中国强调人以及人格的依附性,人的被决定性,最后是取消自我意志。
[注释]
①(1)任何讲出的或写出的东西;(2)所提到的和与价值有关的东西,如评价、声望;(3)灵魂内在的考虑,如思想、推理;(4)从所讲或所写发展为原因、理性或论证;(5)与“空话”、“借口”相反,“真正的逻各斯”是事物的真理;(6)尺度,分寸;(7)对应关系,比例;(8)一般原则或规律,这是比较晚出的用法;(9)理性的能力,如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逻各斯;(10)定义或公式,表达事物的本质。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一卷:《早期苏格拉底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剑桥,1971:420-424,转引自张廷国:《“道”与“逻各斯”:中西哲学对话的可能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1):125.
②作为一切数之根本的‘1’是第一本原,而‘1’表现为点,由‘1’派生出其他的数乃至万物的过程则被表述为:点(1)产生线(2),线(2)产生面(3),面(3)产生体(4),体(4)构成水、火、土、气等四种元素,这四种元素则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结合和转化,从而产生出世界的万事万物。”参见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18页。
③范畴这个词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提出来的,他在《范畴篇》里提出“十范畴”到了康德提出十二范畴表。范畴简单讲就是纯粹概念(区别于一般概念),纯粹概念是指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概念,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东西都要用范畴加以考察,比如因果性,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因果性,那么因果性就是范畴。哲学的范畴之应用是最广泛的,当然在法学领域也应该有自己的范畴。比如有法理学的教材将正义、权利与义务、人格、责任等概念归于法学领域的范畴。参见李龙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④《左传》(昭公六年礼颖达疏语)。
⑤《清律例》二八。
⑥《史记》八七,《李斯列传》。
⑦《左传》恒二。
⑧《论语·学而》。
⑨《诗经·小雅·北山》。
⑩西塞罗,《论共和国》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与埃米尔·诺埃尔的谈话(冀可平,钱瀚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6.
[2][德]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
[3]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14.
[4]参见邓晓芒.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7.16.
[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7.
[6]邓晓芒.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208-211.
[7]王春梅.对经验与理性关系的一种解读[J].法制与社会,2007(4):804.
[8]江怡.论时间推理中的非理性悖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80-83.
[9]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20.
[10]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8.
[1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法学出版社,2008.8.
[12]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J].学海,2007(1).
[13]周雪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生命力:开放性[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0(1).
[1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3.
[15]邓晓芒.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J].哲学研究,2009(4):4-6.
[1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启泰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5-46.
[17]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