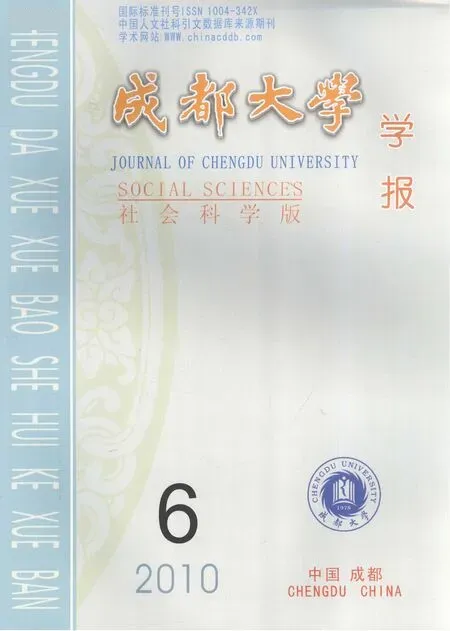浅析汉晋时期汉文化对南中地区的影响
2010-04-03陈芳
陈芳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41)
浅析汉晋时期汉文化对南中地区的影响
陈芳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41)
通过对比南中地区在汉政府开发西南夷前后的考古学文化,探讨汉晋时期南中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特征。
南中地区;汉晋时期;考古学文化
一 南中地区的界定
“南中”这个地理名称最早出现于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中。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南中地区是指包括今天云南省、贵州省大部、四川省西南部以及广西、缅甸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范围。时代不同,“南中”所包含的区域也不尽相同。南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一部分为农耕民族,一部分是半农半牧民族,还有一部分是游牧民族[1]。秦国并蜀以后,开通五尺道,设置官吏对该地进行管辖[2]。西汉建立之初,南中地区便不再臣服于中央政府。直至汉武帝时,重新设立郡县进行管理,南中地区才再次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分犍为郡置牂牁郡[3];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以滇池为益州郡,分牂牁、越嶲郡部分县并入益州郡[4];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孝武帝置朱提郡[5];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明帝置永昌郡[6]。经过两汉政府的长期经营,到东汉末年,南中地区主要包括四个郡:益州郡(以云南滇池地区为中心,包括今滇中和滇东地区,治所在今滇池一带)、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省保山一带,包括今滇西、滇西南地区和缅甸部分地区)、牂牁郡(包括今贵州省大部、云南省东南部部分地区和广西省西北部部分地区)和朱提郡(郡治在今云南昭通,包括今云南昭通、大关等地以及贵州威宁、赫章、宣威等地)。
三国时期,南中地区属于蜀汉的管辖范围。建兴元年(公元223年),朱褒、雍闿、高定等人造反。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亲率大军南下,平定南中。南中平定之后,诸葛亮分益州、永昌、牂牁、越嶲[7]四郡为建宁、永昌、牂牁、越嶲、云南、兴古六郡[8]。延熙年间,蜀汉政府在南中设立南广郡,任常竺为太守[9]。建武元年(公元304年),该郡被取消。
晋代,南中地区的建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设立宁州,对南中四郡(云南、兴古、越嶲、永昌)进行管辖,庲降是其都督府的所在地。宁州设置之后,分出西边七个县另外设置了益州郡,后益州郡又改名为晋宁郡。太康五年(公元284年),西晋政府罢宁州,置南夷府。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冬十一月,又重新设置宁州,统管云南、兴古、越嶲、永昌、牂牁、益州、朱提七个郡,史称南中七郡。晋元帝时期,刺史王逊分牂牁郡鄨县的一半设平夷郡,夜郎以南为夜郎郡。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刺史王逊分建宁郡新定、兴迁二县,加上重新设立的平乐、三沮二县设置平乐郡。除此之外,刺史王逊分兴古县设立梁水郡,又分云南置河阳郡。王逊死后,刺史尹奉平定盘南地区叛乱,分割兴古郡的盘江、南零、来如三县,加上漏卧县设置了西平郡。建武后[10],朱提郡被取消,改为犍为郡下属的国。
二 南中地区汉代的考古发现及主要特点
南中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大相径庭,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差异比较明显。为了能更好地对该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结合现代的行政区划将南中分为以下几个区域进行讨论。
除了南中地区,此章节的讨论还涉及越嶲郡的西昌地区和犍为郡的宜宾地区。这是因为,尽管依据《华阳国志》的记载,越嶲郡和犍为郡在汉代属于蜀地范畴,但是,三国两晋时期越嶲郡已划归南中范畴,加之诸葛亮南征作为南中历史上一个避不开的重要历史事件,西昌和宜宾又是诸葛亮南征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地区[11],为了使讨论有一个延续性,所以将这两个地区纳入讨论范围。
(一)东南地区(主要包括牂牁郡,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指除黔北地区以外的贵州省大部分地区)
1、西汉时期
目前,该地区发现并公布的两汉时期考古资料,主要有遗址和墓葬两类,已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赫章可乐、安顺宁谷、贞丰者相等处,墓葬主要分布在赫章、威宁、毕节、安顺、清镇、平坝、兴义、兴仁、道真等县。该地区西汉的考古学文化以西汉中期为界,西汉中期以前的墓葬,大多是自先秦以来便繁衍盛行的夜郎民族文化墓葬,以赫章可乐、威宁中水等墓地的乙类墓为代表。这类墓葬通常规模不大,墓葬形制绝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无墓道、无封土,埋葬方式有“套头葬”、排葬和乱葬等。随葬器物普遍不够丰富,带有浓厚民族色彩,包括陶器、青铜器和铁器。陶器多为手制,有的刻划有各种特殊符号[12],烧制火候较低,质地松软,易碎,常见的器形有碗、罐、杯、觚、瓶等,纹饰以刻划纹为主,有的器底有叶脉纹;青铜器中数量最多的是扣饰、发钗、手镯、戒指、铃铛等装饰品,其次是戈、剑、箭镞等兵器和釜、鍪、洗等生活用具,另有少量生产工具(锄)、乐器(鼓、铃)和贮贝器;铁器有铜柄铁剑、柳叶形铁剑和带钩。
西汉武帝以后的墓葬,以汉文化风格为主。此类墓葬的规模普遍比夜郎文化墓葬大,地面均有高大的圆形封土堆,除少数地面因多年耕种封土不太明显,一般高约2米左右,直径10-30米不等[13]。曾有学者对这类汉文化墓葬作过专题研究,将这一阶段的墓葬分为同一期下的两段:第1段,墓葬数量较少,主要分布在赫章可乐[14],包括赫章墓地的M16、M92、M165、M182、M281、M283、M284等,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以陶器和铜器为主,陶器有罐、釜、壶、豆等,铜器有釜、鍪、提梁壶、蒜头壶、盘、铜镜等,钱币有西汉高后所铸半两和《洛阳烧沟汉墓》中所分的一型五铢,年代大致为西汉中期;第2段,墓葬数量增多,仍以赫章可乐为主要分布区,墓葬形制主要是竖穴土坑墓,但墓坑形状更丰富,包括长方形、凸字形、方形和不规则形,随葬器物主要是陶器和铜器,陶器有罐、釜、豆、碗、甑、井模型和房屋模型等,铜器有釜、鍪、洗、壶、碗、钱币等,钱币均为五铢钱,年代大致为西汉晚期[15]。
结合上述分析,综合研究这一地区西汉时期的汉文化墓葬,我们发现,西汉时期,这一区域汉文化墓葬的形制主要是带封土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主要为各类生活用具,除此之外还出土金、银、玉、玛瑙、琥珀以及大量的琉璃佩饰等。西汉晚期与西汉中期相比,出现了几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首先,墓葬数量增加,墓坑形状更加丰富。其次,虽仍有部分当地民族的夹砂软陶,但火候高、质地坚硬的泥质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泥质陶器以灰色居多,兼有红、黄二色,同时开始出现釉陶。制法以轮制为主,少数手制。陶器上的纹饰以绳纹、刻划方格纹为主,还有附加堆纹,新出现拍印或模印方格纹加几何图案戳印,少见篮纹,不见前期的叶脉纹和刻划符号。随葬陶器以矮圆的罐为主,其次是壶、釜、钵、盆、灯、盂、豆、碗、房屋模型、井模型等,器形与中原汉文化同类陶器基本相同。当地民族常用的带状单耳罐明显减少,不见觚、杯。第三,铜器种类增加,且以中原地区常见的器形为主,如壶、釜、洗、碗、瓶、盉、熏炉、熨斗、耳杯、灯、各式铜镜、带钩等,尽管也出土了一字格曲刃剑、靴形钺、立耳釜,手镯、铃等夜郎青铜文化风格的器物,但数量甚少。第四,出土的铁器多为汉文化风格,有三类,一类是铁剑、环首铁刀、矛等兵器,一类是锸、斧、斤、凿、锤等生产工具,还有一类是釜、交股剪、脚架、削、钎等生活用具。
2、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该地区的考古发现以墓葬材料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已清理和发掘的东汉时期墓葬主要有清镇平坝汉墓、赫章可乐汉墓、安顺宁谷东汉墓、威宁中水汉墓、安顺市宁谷汉墓、贵州兴仁、兴义汉墓、贵州黔西汉墓等,总数约百余座。墓葬规模有大中小三类,小者长3米、宽2米左右;中者长5米、宽3米左右;大者以多室墓居多,面积均超过20平方米[17]。
西汉末—东汉初年的墓葬,主要集中在威宁中水和清镇平坝等地,赫章可乐和兴仁交乐有少量发现。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以竖穴土坑墓为主,约50余座,砖室墓数量较少,约有8座,主要为单室。墓坑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刀形、铲形、凸字形等,还出现了带甬道的砖室墓。随葬陶器主要有罐、壶、碗、井等,新出现了动物陶俑和水塘陂田模型;铜器主要是洗、釜、碗、豆等生活用具,也出有部分钺、矛、镞等兵器,新出现了摇钱树;铁器以环柄刀、剑等兵器为主,另有少量釜、锄等生产生活用具出土;钱币种类比较丰富,多出王莽时期钱币,有大泉五十、货泉、大布黄千等。
东汉早、中期的墓葬分布范围较广,赫章、威宁中水、清镇平坝、安顺、兴义、兴仁、黔西等地均有发现。墓葬形制主要是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偶有砖、石混合墓。竖穴土坑数量锐减,仅发现十余座,砖室墓和石室墓的数量增加,已发掘或清理的砖室墓约18座,石室墓约33座。墓坑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刀形、凸字形、铲形、“大”字形等,分单室、双室和多室墓,墓顶基本为券顶。随葬陶器有罐、动物俑、人物俑、屋、井、水塘陂田模型等,生活用具中以罐最为普遍,几乎每座墓葬都有出土,偶见釜、豆、瓮;铜器比较丰富,有釜、碗、盘、壶、豆、洗、灯、 斗、摇钱树、车马等,以釜、盘、摇钱树最为常见,除此之外,还多出手镯、带钩、泡钉、铺首、动物俑等小件铜器和少量铜兵器;铁器出土数量不多,一类是以环首刀为代表的兵器,另一类是釜、交股剪、棺钉、铁三脚等生产生活用具;钱币种类更加丰富,有五铢、剪轮五铢、大泉五十、货泉、中泉三十等;金、银、骨、琥珀类装饰品也有较多出土。
东汉中、晚期的墓葬分布于安顺、兴义、兴仁、黔西等地。墓葬形制依然是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又分单室墓和多室墓。石室墓数量最多,约14座,砖石墓次之,土坑墓少见。墓坑形状有长方形、刀形、凸字形、“十”字形等,以长方形和刀形数量最多,最为常见。随葬陶器主要有罐,水塘模型,各种动物俑如鸡、羊、猪等,各类人物俑如庖厨俑、吹箫俑、抚琴俑、舞俑等,新出现灶、圈;铜器有釜、壶、碗、摇钱树、车马器等,实用器的数量减少,明器的数量增多;铁器仍然以环首刀等兵器为主;钱币有大泉五十、剪轮五铢、 钱、东汉五铢等,东汉五铢多晚期形制;饰品出土较为普遍,仍然是金银铜琥珀等材质制成的饰品。
归纳起来,该地区带封土的竖穴土坑墓是从西汉中期(武帝之后)开始出现的,流行于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东汉中期便开始衰落;砖室墓大约是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开始出现,盛行于东汉早、中期,东汉晚期开始衰落;石室墓的出现不早于东汉早期,东汉中期开始盛行,一直持续到魏晋南北朝[18]。
和西汉相比,东汉时期汉式墓葬分布的区域不断扩大,到东汉中期以后,各个地区均有汉式墓出土。葬具多为红漆髹漆过的木棺,亦有极少的瓦棺和石棺,这可以从墓葬中普遍发现的漆残片、铁抓钉以及它们的出土位置得到印证。随葬品几乎都是汉文化风格的物品,西汉后期还有少量出土的一字格曲刃剑、靴形钺、立耳釜等夜郎风格的物品已经完全不见[19]。陶器主要是质地坚硬、表面施釉的泥质陶。西汉末—东汉初,随葬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罐、壶、釜等生活用具,明器种类增加,新出现了摇钱树、水塘模型、动物陶俑等明器;到东汉早、中期,随葬品种类日益丰富,但各类生活用具的主导地位已经有所削弱,明器比例上升,车马器、摇钱树等的数量增多;东汉中、晚期,尽管还出土有各类生活用具,但是明器开始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陶明器,该时段的墓葬中往往出有各类人物俑、动物俑、水塘稻田模型、镇墓俑等,还新出现了灶、圈,而且这类陶器往往呈组合形式出现[20]。
当地土著中,习带各种小饰品,好身体装饰,此风颇盛[21]。纵观东汉墓葬,虽多经盗扰,仍出土了手镯、琥珀饰、料珠等各种装饰品,而且数量较多。说明这一土著遗风在东汉时期仍然盛行。
(二)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包括永昌郡、益州郡和朱提郡,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主要是云南省)
1、西汉时期
以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为界,汉代云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两个大的时期: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以前,以青铜文化为主;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以后,跨入了铁器时代。云南的青铜文化早起于商周,春秋战国至西汉最为发达,按照区域特点大致划分为五个类型:滇池地区的滇文化,红河流域青铜文化,洱海区域青铜文化,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下游青铜文化。这些区域出土的墓葬大多数为竖穴土坑墓,但是在洱海以东地区的宾川、祥云、弥渡、姚安等县,还存在一种以“大石墓”为特点的青铜文化遗存。众多区域青铜文化中,尤以滇池地区的滇文化最为发达。目前,已经发掘和清理的滇文化墓葬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昆明羊甫头墓地最具代表性,延续时间较长。西汉时期,滇文化墓葬的形制以竖穴土坑墓为主,随葬品的数量、种类和质地根据墓葬的规模大小差异明显。总的来说随葬品以具有浓厚地方民族色彩的滇文化器物为主体,典型器物主要有铜鼓、贮贝器、壶、尊、觚形杯、葫芦笙、执伞俑、狼牙棒、啄、各类扣饰、杖头饰等,基本不见铁器。到西汉中晚期,各类滇文化的墓葬中出现了不少具有“汉文化”风格的铜铁陶器,如铜盉、耳杯、釜、镜、钱币,陶壶、平底罐、豆等,但是,由于这类器物数量不多,并没有改变其滇文化墓葬的性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前期。
2、东汉时期
东汉以后,特别是东汉中期以后,汉族“大姓”势力及汉文化在云南各地日益兴盛,取得了主导地位,云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该阶段发掘或试掘的遗址较少,截至1999年,一共3处[22]。发掘和清理的墓葬主要集中在昭通、大关、大理等地[23],数量不多,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约50余座(注:因版面所限,此文附表“南中地区东汉、三国魏晋墓葬表”从略)。
东汉早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在昭通、江川李家山等地。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砖室墓主要为单室。随葬陶器较少,有罐、鼎等;铜器比较丰富,有釜、洗、盘、案、耳杯、甑、镜、熏炉、尊、俑等,某些墓葬还出有杖头饰、镦、钏等土著风格的铜器;铁器以刀、矛等兵器为主;钱币有五铢钱、货泉等;还出有金戒指,银手镯,金、玉、玛瑙、绿松石制成的管、珠等。
东汉中期的墓葬分布于昭通、昆明等地,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竖穴土坑墓发现较多,集中在昆明羊甫头墓地,墓坑形状均为长方形,砖室墓出现了双室形制。随葬器物比较丰富,陶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罐、甑、钵、碗、盆、壶、瓮等生活用具,另一类是楼、井、仓、灶、牛、龟、鱼、水田模型等明器,新出现了摇钱树座;铜器更加丰富,有釜、案、提梁壶、耳杯、盆、洗、釜甑、盉、镜、动物俑、带钩等,出现了车马器;铁器变化不明显,仍以兵器为主;饰品出土较为普遍,包括金、银环、琥珀珠饰等。
东汉中晚期的墓葬分布区域较广,昭通、呈贡、大理等地均有发现。墓葬形制均为券顶砖室墓,有单室、双室、多室几类,墓坑形状有长方形、凸字形、不规则形等。随葬陶器有罐、釜、甑、盆、钵、盘、碗、灯等生活用具,也有灶、井、楼、仓、池塘、水田、人物俑、动物俑等明器。明器的种类和数量都较之前增加,特别是人物俑和动物俑。该时段的人物俑有庖厨俑、吹箫俑、抚琴俑、听琴俑、持刀俑等,动物有子母鸡、雄鸡、鸭、鱼等,往往呈组合出现。随葬铜器较少,釜、案、甑、壶等大型铜器少见或基本不见,出土较普遍的是耳杯、灯、铺首、动物俑等小型铜器,摇钱树也常有出土。
综上所述,东汉早、中期,该地区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竖穴土坑墓占较大比例,砖室墓从东汉早期开始出现,多为单室,到中期出现了双室形制;东汉晚期,几乎不出竖穴土坑墓,墓葬形制以砖室墓为主,墓坑形状丰富,出现了多室墓。随葬品方面,东汉早期无论陶器还是铜器都以各类生活用具为主,偶见鼎等仿铜礼器,也出有少量土著文化器物如杖头饰,玛瑙、琥珀、绿松石等制成的饰品、“珠襦”等;东汉中期,随葬陶器、铜器虽然保留了各类生活用具,但模型器、车马器、摇钱树也占有相当比例;东汉晚期,陶器数量增加,但生活用具数量减少,模型器、明器盛行,特别是人物俑、动物俑种类非常丰富,往往以组合形式出现,铜器基本不出壶、甑等大型生活用具,多出灯、耳杯、带钩等小型器类。东汉中期以后,土著文化器物基本消失。
东汉,除各地普遍存在的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滇东北还出有崖墓[24]。崖墓系凿山而成,包括墓道、墓门、墓室几个部分,墓道通常较为平直,墓室分为单室、双室、多室及带耳室几类,墓顶多为券顶,墓门用石块封堵,是汉至六朝广泛流行于四川以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的一种极具地方特点的墓葬。云南崖墓是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的一种墓葬,多见于滇东北的几个县,已发掘的崖墓有昭通象鼻岭、大关岔河和鱼堡、昭通小湾子、盐津燕儿湾和漆树湾等,时代都在东汉。以大关岔河和昭通象鼻岭两地为例,两地崖墓包括人字形顶、圆顶、拱形顶,有单室、双室以及带耳室几类。随葬陶器较少,主要是罐、碗、壶、甑、熏炉等;铜器也不丰富,有釜、釜甑、洗、壶、鐎斗、耳杯;铁器以环首刀、镞、剑等兵器为主;其它还出有少量的漆奁、漆耳杯、金银琉璃饰品;钱币主要是东汉五铢、货泉、大泉五十等。借鉴罗二虎先生对四川崖墓的分期[25],两地的崖墓多人字形和圆形顶,陶器组合基本为罐、碗、壶、甑、熏炉,铜器组合为洗、釜、甑、壶、鐎斗、耳杯,时代应在东汉晚期。但是,从目前出土的情况看,云南崖墓中随葬的陶人物俑、动物俑、模型器极少,也不出摇钱树,与同时期的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区别明显。
(三)北部地区
1、西昌地区
(1)西汉时期。以四川省凉山州安宁河流域为中心,包括相邻的云南省北部地区,分布着一种以大石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这种墓葬系大石垒砌而成,顶部以大石覆盖,流行二次葬的多人合葬,其文化面貌除了本地土著文化特征外,还受到了北方草原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和滇文化的影响[26]。这种以大石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延续时间很长,上限可以到中原地区的商代至西周中期,下限可至东汉早期[27]。西昌地区是目前大石墓发现最多最集中的地区,现存大石墓近百座,北端以冕宁浸水湾为界,沿安宁河两岸向南分布,南端以西昌西河、西溪为界,向东与邛海四周的大石墓连成一片[28]。目前,已发掘的西昌地区两汉时期的大石墓主要分布于西昌西郊、河西、洼垴、黄水塘、小花山等地[29]。
西昌地区两汉时期的大石墓仍然以土著文化因素为主,原有的巨石结构的墓室、二次捡骨多人合葬的葬俗、随葬制度和一些主要随葬品的风格等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化。随葬陶器仍然最发达,有单耳罐、双耳罐、杯、带流壶、无耳罐等;铜器以发饰(发钗、发笄等)、环、镯、铃等小型装饰品为主,还出有刀、矛、镞等兵器,但数量较少;石器有斧、凿、簇、条形石器等;还出土骨玦、骨璜、玛瑙珠、绿松石珠等饰品。保留原有文化特征的同时,两汉时期的大石墓已经明显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出土了诸如环首刀、削等铁兵器和五铢钱、大泉五十等汉式器物。
(2)东汉时期。东汉前期,大石墓在安宁河流域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流行的汉文化墓葬。目前,西昌地区公布的东汉时期墓葬材料较少,主要包括西昌、西昌礼州、西昌杨家山等几处有限的材料[30]。通过上述几个墓地出土情况,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东汉早期的墓葬数量极少,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砖室墓均为单室。随葬器物中陶器发达,一类是罐、钵、壶、釜、甑等生活用具,一类是灶、井、水田、水塘等模型器;铜器出土较少,包括釜、洗、带钩、斧等;铁器有刀、剑等兵器和凿、锛等生产用具;钱币主要是五铢钱和莽钱,莽钱有货泉、大泉五十、契刀五百等。
东汉中、晚期的墓葬数量相对较多,几乎都是券顶砖室墓,少见竖穴土坑墓,砖室墓有单室、多室等类,墓坑形状较早期丰富,有长方形、“十”字形等。随葬陶器仍然丰富,但生活用具类数量减少,以釜、罐居多,模型器等明器数量增加,以房、田、塘、动物俑、人物俑如农夫俑、劳作俑、庖厨俑、舞俑、抚琴俑为基本组合;铜器出土数量不多,但种类丰富,有釜、案、耳杯、洗、壶、甑等,摇钱树、车马器较为盛行;多出五铢钱和金、银、琥珀类饰品。
2、宜宾地区
宜宾地区公布的汉代考古材料甚少[31],从目前收集的东汉墓葬材料分析,该地区东汉的墓葬形制大致分为四类:土坑墓、砖室墓、石椁墓和崖墓。土坑墓数量最少,仅发现翠屏村M10一座,年代在东汉初年;砖石墓、石椁墓数量较多,几乎都为单室,结构较为简单,仅合江出土的一座单室砖墓年代在东汉早期,其余年代均在东汉中晚期;崖墓数量最多,有单室、双室和多室墓,除真武山93ZWM5年代为东汉初期,其余墓葬年代相距不远,多为东汉中晚期。由于材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宜宾地区东汉早、中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变化规律,但是从出土数量较多的中晚期墓葬来看,东汉中晚期墓葬形制主要有砖室墓、石椁墓和崖墓三类,已基本不见竖穴土坑墓。尽管墓葬形制多样,但随葬器物及其组合却大体相似,以陶器最为发达,数量较多,占主体的一类是罐、钵、釜、甑等生活用具,另一类是人物俑、动物俑和其他与生产生活相关的明器,而东汉初期还有少量出土的陶礼器如鼎已消失;铜器出土较少,主要是带钩、铺首等小件器物,釜、甑等大型生活用具少见或基本不见;铁器数量不多,主要是环首刀等兵器;钱币有五铢、货泉等。
三 南中地区三国两晋时期的考古发现及特点
南中地区发掘并公布材料的三国两晋时期墓葬较少,东南地区仅贵州安顺和平坝两县有少量发现,中部和西南地区只在云南保山坝、昭通、姚安等地有出土,北部地区也仅发掘了西昌和江安两处[32](参见附表二),约30余座。
三国两晋时期,南中地区的墓葬形制与东汉大体相同,变化不明显。相较而言,东南地区比较丰富,有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和石室墓,石室墓的数量最多,是主要墓葬形制,其他各地以砖室墓为主,基本不出竖穴土坑墓,昭通地区出现了壁画墓。墓葬结构趋于简单,仅见单室和双室,多室墓基本不见。
与两汉相比,三国两晋时期墓葬的随葬器物的种类和数量都明显减少:铜器以鐎斗、豆、镜、灯等小型器物为主,数量较少,仅有少数墓葬出有釜;陶器以罐、碗为主,常出黄釉和绿釉的陶罐,有系,其他如釜、人物俑、动物俑、模型器等所占比例较小,新出现了鹤、马等动物俑;新出现了青瓷器,主要是各类青瓷罐。此阶段东南地区的墓葬还出土有数量较多的装饰品,包括金、银、玉、玛瑙、琥珀、琉璃佩饰等,据统计,占到所有随葬品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33]。
四小结
由上可知,南中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汉代发生了质的转变。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牂牁郡开始,南中各地陆续经历了一个“汉化”的过程。已有许多学者对“汉文化”进行过探讨,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蒋晓春先生将“汉文化”的特征总结为六点[34],笔者在此就借鉴其中的一些标准来考察“汉文化”在南中各地的确立和发展。
1、厚葬。判断墓葬是厚、薄葬的标准主要根据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丰寡。前面,我们在分区对南中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进行论述时已经谈到,东南地区西汉中期之前的土著文化墓葬无论规模还是随葬品数量都比不上西汉中期之后的“汉式”墓。再根据东汉南中各地的墓葬状况,除了被盗特别严重的,其余各墓随葬品均比较丰富,普遍在二十件左右,个别墓葬更多达六十多件,贵州兴仁、兴义汉墓还出土了精美的铜车马[36]。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地处西南边隅的南中地区也深受汉代厚葬之风的影响。
2、开通型墓代替密闭型墓[37]。以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东南地区为例,汉代该地区有密闭型墓(竖穴土坑墓)和开通型墓(砖、石室墓)两类,直至西汉末—东汉初,都以密闭型墓为主,但是从东汉早、中期开始,开通型墓的数量远远超过密闭型墓,成为主要墓葬形制。墓葬数量相对较少的其他各区域,发现的密闭型数量远远少于开通型墓葬(砖室墓、崖墓、石椁墓)。由此可知至迟在东汉中期,南中地区的墓葬以开通型为主。
3、生活实用器、明器代替礼器成为随葬品的主要内容。东南地区,在西汉之时,尚有少量铜礼器或仿铜礼器的残余,如中原礼器组合中常见的鼎、盒、壶都有单独出现,至东汉时,除壶外,鼎与盒近乎绝迹,从西汉晚期开始,生活实用器如罐、釜、灯、铜镜、钱币、带钩等大行其道,到东汉中晚期,仓、灶、井、水田等模型明器以及各类人物俑、动物俑则成为随葬品之大宗。其余各地,东汉初期仍能见到如鼎这样的仿铜礼器残余,但占主导地位的已经是罐、釜、耳杯、甑等生活实用器,到东汉中晚期,各类模型明器和动物俑、人物俑成为了最重要的随葬器物。
由上可知,南中各地开始接受汉文化的时间并不一致,东南地区更早,到西汉中期以后,已基本融入到汉文化中,其余各地直至东汉初期才开始汉化,但是至迟到东汉中后期,汉文化在南中地区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三国魏晋时期,南中各地在考古学面貌上更是呈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各地的墓葬形制大致相同,随葬品的构成、组合方式、风格甚至变化规律都已非常相似。
由于地区差异、建立郡县的时间差异以及各种历史因素,南中各地在接受汉文化的方式上各不相同。总体而言,西汉中期以后南中地区土著文化变迁呈现出两种情况:其一是土著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但在尚未融入汉文化之前便突然消失[38],这种变化不是渐进的,而是一种突然的剧烈的变化,以川西南、滇北的“大石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和贵州地区的夜郎文化为典型。其二是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后,土著文化迅速变化,最后融合于汉文化之中,这种变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云南的滇文化为代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滇文化墓葬中铜器所占比例特别大,且均为实用器,基本不见铁器,民族特色浓郁;西汉中期,有民族特色的生活用具减少,兵器和生产工具增多,铁斧、铁剑等铁器开始出现,出现了“汉式”铜镜和“半两”铜钱,与汉地联系增多;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汉文化风格的随葬品大量出现,出现陶明器,说明土著文化已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冲击,滇王族的生活习俗开始发生变化;西汉晚期以后,铜器数量锐减,土著文化风格的随葬品较少,汉式陶礼器成组出现,滇文化完全衰落;东汉中期以后,土著文化最终融合于汉文化中,民族特色的器物基本不见,汉文化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墓葬风格及变化规律与四川、中原等地几乎一致。
应该指出的是,在“汉文化”的扩张及其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中还存在比较大的缺陷,尤其是在像南中这样的多民族聚居区。由于资料的局限,研究者往往只能把着眼点置于“汉化”墓葬和部分生产、生活用品的流通等领域之上,这样的视角必然会使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如何通过“生”与“死”的结合,通过具有“汉化”和“非汉化”特征的物质文化的空间结构来探讨南中地区的“汉化”进程将是笔者今后关注的问题。
注释:
[1]《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榞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厓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厓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2]《华阳国志·南中志》:“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頾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华阳国志·南中志》:“牂牁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
[4]《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牁、越嶲各数县配之。”《华阳国志·南中志》:“元封二年,……。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
[5]《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本犍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属县四。建武后,省为犍为属国。”
[6]《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永平十二年,……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
[7]诸葛亮南征的区域包括越嶲郡,但《三国志·蜀书》和《华阳国志》都没有明确记载三国时期越嶲郡属于南中地区,仅提到它位于成都南面,即“诸葛亮南征四郡”。直至晋代,“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为宁州”,“冬十一月丙戌,诏书复置宁州。增统牂牁、益州、朱提,合七郡。”(《华阳国志·南中志》),才明确指出越嶲郡属于南中地区。
[8]《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十二月,亮还成都。”
[9]《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南广郡,蜀延熙中置,以蜀郡常竺为太守。”
[10]建武这个年号,曾被四个朝代使用:东汉光武帝、西晋惠帝、东晋元帝以及后赵。刘琳注《华阳国志·南中志》认为此处可能有误。
[11]宜宾古称僰道,是诸葛亮南征中马忠率领的东路军行军路线中的重要一站;西昌所属的四川凉山是诸葛亮南征的重要战场。
[12]参见《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13][17][19][33]宋世坤:《贵州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14]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15][21][36]罗蓉晖:《贵州汉墓初步研究》第22—23页,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16]a.熊水富:《贵州平坝金家大坪古墓清理简报》;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59年第1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平坝天龙汉墓》,《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4期;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b.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赫章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c.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安顺宁谷发现东汉墓》,《考古》1972年第2期;严平:《贵州安顺宁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4期;刘恩元:《安顺宁谷古墓》,《贵州文物》1983年3、4合刊。
d.贵州省博物馆:《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黔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8期。
e.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第二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1987年第10期。
f.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汉墓》,《考古》2004年第3期。
g.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安顺市宁谷汉代遗址与墓葬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6期。
h.贵州省博物馆:《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唐文元:《黔西甘棠汉墓群》,《贵州文物》1982年第1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黔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第8期。
[18]宋世坤、罗蓉晖等学者对贵州地区的汉代墓葬做过系统的研究,他们认为石室墓盛行于东汉晚期。本文不涉及黔北地区,而从黔东南地区来看,部分时代推断为东汉的墓葬,如安顺宁谷、黔西赶棠等,并未发现明确为东汉晚期的随葬物品,其特点反而与东汉中期墓葬的特点更为接近,所以笔者对这部分墓葬的年代做了调整,认为石室墓的出现与盛行应在东汉早、中期。
[20]部分学者曾对贵州地区汉墓做过系统性的研究,对于汉文化墓葬丧葬习俗的整体变化趋势研究者间有较多的共识。参见宋世坤《贵州汉墓的分期》、《贵州两汉魏晋南北朝墓葬形制的演变》、《贵州两汉魏晋南北朝随葬器物的演变》和罗蓉晖《贵州汉墓初步研究》。
[22]孙太初:《云南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23]a.曹韵葵:《云南昭通专区东汉墓清理》,《考古》1957年第4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8期;曹吟葵:《云南昭通县白泥井发现东汉墓》,《考古》1965年第2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象鼻岭崖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昭通地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昭通市鸡窝院子汉墓》,《考古》1986年第11期;张兴宁:《昭通小湾子崖墓发掘简报》,《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大关、昭通东汉崖墓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3期。
b.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大展屯二号汉墓》,《考古》1988年第5期;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市下关城北东汉纪年墓》,《考古》1998年第4期。
c.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归化东汉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3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七步场东汉墓》,《考古》1982年第1期。
d.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盐津燕儿湾崖墓发掘简报》,《云南文物》总第48期,1999年。
e.王桂蓉:《禄丰汉代砖室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9)。
[24]除上述墓葬形制外,云南地区还有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梁堆”墓。“梁堆”墓是云南这时期有高大封土堆墓葬的俗称。分布于云南东北部、中部及滇西大理、保山等地。墓主是中央委派的外来官吏和任命地方豪族充任的官吏以及他们的亲属。这类墓封土堆高3-10米、直径10-20米,少数有墓碑。墓室随时代早晚而形制不同:东汉初期仍沿袭青铜时代的主要墓制,为竖穴土坑墓;东汉中、晚期演变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券顶砖室墓,一般单室,少数有前、后两室,还有前后室带耳室的,均有墓道。本文不对这类墓葬做单独讨论。
[25]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26]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第25页,天地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27]刘世旭:《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6期;罗开玉:《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考古》1989年第12期。
[28]刘弘:《川西南大石墓和邛都七部》,《文物》1993年第3期。
[29]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30]a.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凉山西昌发现东汉、蜀汉墓》,《考古》1990年第5期。
b.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发现的汉墓》,《考古》1980年第5期。
c.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杨家山一号东汉墓》,《考古》2007年第5期。
d.黄承宗:《西昌东汉、魏晋时期砖室墓葬调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31]赵希铭等:《四川宜宾市郊发现东汉砖墓九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匡远滢:《四川宜宾市翠屏村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四川大学历史系七八级考古实习队等:《四川宜宾县黄伞崖墓群调查及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宜宾市博物馆:《四川宜宾真武山发现一座东汉崖墓》,《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宜宾横江镇东汉崖墓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泸州河口头汉代崖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谢荔等:《四川合江县东汉砖室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32]a.刘恩元:《安顺宁谷古墓》,《贵州文物》1983年第3、4合期;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4期;熊水富:《贵州平坝金家大坪古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6期。
b.耿德铭:《保山坝蜀汉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孙太初:《云南姚安杨派水库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56年第3期。
c.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凉山西昌发现东汉、蜀汉墓》,《考古》1990年第5期;崔陈:《江安县黄新乡魏晋石室墓》;黄承宗:《西昌东汉、魏晋时期砖室墓葬调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34]本文所说的“汉化”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汉文化”在丧葬制度上的体现。
[35]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37]对于密闭型和开通型墓葬的定义,研究者间有所差别。笔者赞同蒋晓春的观点。参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38]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第25页,天地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On Influence of Han Culture in Nanzhong Area in the Han and Jin Periods
Chen Fang
(Zhuge Liang Memorial Hall Museum in Chengdu,Sichuan,Chengdu 610041)
This paper,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the Nanzhong reg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Han government developed the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probes into th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nzhong region during the Han and Jin periods.
Nanzhong region;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archaeological culture
K234.235
A
1004-342(2010)06-117-08
2010-08-23
陈芳(1977—),女,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