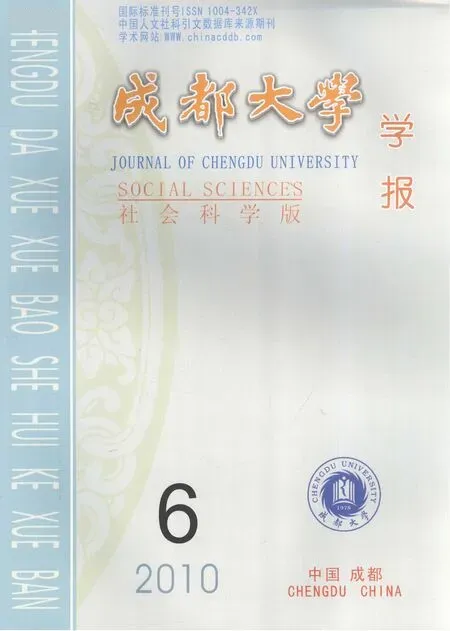成都武侯祠塑像沿革与保护
2010-04-03李兆成
李兆成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41)
成都武侯祠塑像沿革与保护
李兆成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41)
自唐代武侯祠中塑像之后,历代逐渐增多。清康熙年间武侯祠重建后,两廊塑像已成规模,道光年间调整后沿袭至今。各尊塑像具体塑制年代的考述。1971年至今的塑像维修保护。对塑像保护不利因素的讨论。
塑像沿革;《昭烈忠武陵庙志》;宋可法;刘沅;移塑
塑像是成都武侯祠文物之一大宗,年代久远,特色鲜明。祠内现有的50尊塑像中,47尊为清代所塑,具体塑制于1672~1849(清康熙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九年)年间。全国其他寺庙祠观等文物遗迹中的塑像所塑多为神佛、罗汉,偶有塑历史人物的数量也极少。而武侯祠塑像除6位侍者以及周仓外,其余40尊所塑人物均为见于史籍记载的蜀汉历史人物(周仓见于《三国演义》)。如此众多的历史人物塑像,在诸文物胜迹中实为翘楚。因此,成都武侯祠的塑像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此前,已有文章论及成都武侯祠塑像的沿革等相关问题,但尚欠系统和全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塑像进行了一系列的维修和保护工作,其得失也需要认真总结。
一 618~1644(唐初至明末)年间塑像情况概述
蜀汉王朝至南北朝时期,安葬刘备及其夫人的惠陵、纪念刘备的汉昭烈庙和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相继建成于成都南郊,武侯祠初具规模。那时的祠庙内或有塑像,但唐代以前塑像情况因无文献记载,相关情况待考。
祠庙内塑像有诗文记述的,始自唐代。由裴度撰文,镌立于809年 (唐元和四年)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中,就谈到作者拜谒武侯祠时所见塑像的情况。碑文称:“随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谒。有仪可像,以赫厥灵”。“有仪可像”的“仪”,就是指武侯祠内塑有供人瞻仰的诸葛亮像。这是有关武侯祠内塑像最早的记载。该碑碑阴镌有835年 (唐太和九年)杨嗣复《祠祭毕题临淮公(裴度)旧碑》诗,称:“谋猷期作圣,风俗奉为神。酹酒成坳泽,持兵列偶人。”又,杨汝士《和前(即杨嗣复)诗题韵》:
古柏森然地,修严蜀相祠;
一过荣异代,三顾盛当时;
功德流何远,馨香荐未衰;
敬名探国志,饰像慰甿思;
昔谒从征盖,今闻拥信旗;
固宜光宠下,有泪刻前碑。
诗句所言武侯祠内有供人拜谒景仰的“饰像”,自然也是指诸葛亮像。
通过上述诗文,可确知唐代武侯祠内已有诸葛亮像,同时祠内还有“持兵”的“偶人”。自公元三世纪建立起直到十四世纪的漫漫一千多年中,武侯祠与昭烈庙各为独立的祠庙,建筑虽邻近却又彼此分立,明代初年昭烈庙与武侯祠始合为一庙。故裴度所撰《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中,就只字未提昭烈庙。这些执兵器的“偶人”既在武侯祠内,当是诸葛亮的侍卫而非蜀汉武将或卫士。同期昭烈庙中的塑像情况,仍不详。
自北宋初年始,祠庙中蜀汉历史人物塑像增多。据修撰于976~984年(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太平寰宇记》载:北宋初年昭烈祠中“左右侍侧者”塑有刘禅、刘谌、关羽、张飞、诸葛亮、诸葛瞻等像,“俱合为一祠”。祠庙中既塑有“侍侧者”,则昭烈祠主要的祭祀对象——刘备的塑像,自然就肯定存在。也就是说,北宋初年时祠庙中已有了7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刘禅像在祠庙中存在的时间并不久,约于1041~1042年(北宋庆历初年)就被益州知州蒋堂拆毁;北宋初年惠陵旁同时有昭烈庙(亦称昭烈祠、先主祠)和武侯祠、后主祠三座祠庙,而其建筑各自独立。[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蜀先主祠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挟即武侯祠,东挟即后主祠。蒋公堂帅蜀,以(刘)禅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蒋公堂即蒋堂,北宋庆历初年任益州刺史。《宋史·蒋堂传》载当时蒋堂是为了修建铜壶阁而拆去刘禅祠并毁其像的,可见当时昭烈庙之东的刘禅祠的建筑是自成一体的,否则撤除刘禅祠则必将毁损昭烈庙的建筑,而祭祀蜀汉皇帝刘备是北宋朝廷的既定政策,相关诏令载于《宋史》,毁损祭祀昭烈庙的事,无论如何蒋堂也不敢造次。昭烈庙之西即“西挟”的武侯祠,也当是自成一体的独立建筑。大约“东挟”、“西挟”的建筑规模卑小,并与昭烈庙紧邻,甚至可能在同一院落中,《寰宇记》也就将这三座祠庙视为同一建筑了。总之,北宋时祠庙中塑有7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刘禅像被拆毁后,仍有6尊。
从文献中可知,到南宋初,大约1158年(南宋绍兴二十八年)之前,刘禅像又出现在了祠庙中,其他的6尊塑像的状况仍同于北宋初。1160年(南宋绍兴三十年)任渊主持重修武侯祠工程竣工,祠庙内的塑像亦无改变,仍同于北宋时。约30年后,爱国诗人陆游至成都,有《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诗,咏赞游览陵庙时所见,称陵庙中“画妓空笙竽,土马缺羁鞚。”画妓当指壁画上的乐妓,五代以来成都各祠庙中多绘有壁画,当时武侯祠内壁间亦绘有演奏器乐的歌伎;“土马”即泥塑之马,这种泥塑的马自然不能放在墓道等露天处任日晒雨淋,风蚀雪侵,故土马当在祠内的塑像旁。马以泥塑,塑像或亦为泥塑。从有关情况看,不独宋代,唐至清各代祠庙内的塑像均应为泥塑。
1380年(明洪武二十三年),蜀献王朱椿“就藩”到成都后,重建昭烈庙,同时废除了成都南郊惠陵旁的这座武侯祠,将武侯祠中的碑碣迁入昭烈庙中,诸葛亮像也塑入了昭烈庙中。当时“帝(刘备)位中”,居大殿上之主位;“而(武)侯与关、张祔左右”,分列两旁。也就是说,明初祠庙内共塑了四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到明弘治乙口年时,庙内又增塑了刘谌、诸葛瞻、诸葛尚和傅佥等四尊像。按,明弘治年间有两年的天干为乙,或乙卯即1495年,或乙丑即1505年。因此,增塑刘谌等四尊像应在1495年或1505年。此时祠庙内共有八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
这种情况延续到明代(1368~1644年)末年。
二 1672~1849(清康熙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九年)年间的塑像状况
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重建武侯祠,在昭烈殿后建诸葛亮殿,形成成都武侯祠现存君臣合庙的基本格局。当时在四川的清廷大员如湖广总督蔡毓荣、四川巡抚罗森、四川布政使宋可发等等,或“倡事”,或捐款,或主持修建,并各自镌碑以记叙重建武侯祠的相关情况,这些碑文同时也就反映了当时祠庙中塑像的有关情况。
具体主持重建武侯祠工程者为四川布政使宋可发。宋可发撰写的《重修忠武侯祠碑记》中,就谈到了祠庙的塑像情况,说:
今以前殿祀昭烈,两庑列从龙诸名臣;后殿奉侯,配以子瞻、孙尚。
文中所称“侯”,即指武侯诸葛亮。
四川巡抚罗森所撰《重建武侯祠碑记》,对当时塑像有关情况记载得更详细:
奉昭烈正位于前殿,而左庑则祔以伏魔帝、北地王,右庑则祔以张桓侯、傅将军,堂帘以肃,如朝廷礼。特建后殿,奉武侯于中,子若孙昭穆—堂,如家庭礼。
文中的“伏魔帝”,指关羽;“北地王”指刘谌,“张桓侯”指张飞;“傅将军”指傅佥。
稍后,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对武侯祠又曾有修葺,而祠庙内塑像并无改变,王渔洋《秦蜀后记》载其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奉使成都时所见:
(五月)初七日渡锦江谒武侯寺……两庑祀北地王刘谌及关、张、蒋、费诸将相。
上述碑文和文献记载,反映了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重建武侯祠后祠内塑像基本布局:诸葛亮殿中塑有诸葛亮像,还塑有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等像。刘备殿中塑有刘备像;刘备殿前两廊庑中,左庑(东廊、文臣廊)塑有关羽、刘谌等像,右庑(西廊、武将廊)塑有张飞、傅佥等像,两廊内还塑有蒋琬、费袆和其他的“从龙诸名臣”,但这些文臣武将塑像的具体位置,碑文和文献中未曾述及。
上述碑文还告诉我们,1672年在祠庙内塑像时,不同塑像的具体位置,是按一定的礼仪确定的。刘备殿与殿前两廊“从龙诸名臣”的塑像,其礼仪“如朝廷礼”,也就是说,刘备殿及殿前两廊的塑像的位次排列,是按朝廷中朝会的礼仪进行安排的,有尊卑之分,以之确立塑像的位次,皇帝刘备地位最尊,塑于刘备殿正中,而蜀汉的文臣、武将,包括关羽、张飞、刘谌、庞统等等,一律排列在殿堂之下,分塑于殿前两廊,犹如当年蜀汉朝廷朝会议事时的状况,皇帝刘备要找某人议事则宣其上殿,文臣武将有事禀告则经皇帝同意后再上殿。诸葛亮殿内塑像,其礼仪“如家庭礼”,也就是依长幼为序,诸葛亮塑于殿之正中,其子诸葛瞻塑于诸葛亮像前东侧,其孙诸葛尚塑于诸葛亮像前西侧,氛围如家庭,上下一堂,似天伦之乐。
1672年及其后,祠庙内的塑像均为泥塑。
两廊中究竟有哪些塑像呢?
编纂于1829年(清道光九年)《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一《祀典》中,保存有《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辩误》一文。这是我们弄清清代康熙年间两廊塑像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辩误》记载了1829年(清道光九年)时,刘备殿前东、西两廊的塑像的具体情况。两廊当时各有塑像十二尊,东廊由北至南,依次是:吕凯、关兴、费祎、庞统、邓芝、陈震、蒋琬、董允、法正、刘巴、秦宓、许靖;西廊由北至南,依次是:张苞、马超、张裔、姜维、黄忠、赵云、傅佥、向宠、李彪、廖化、张虎、张嶷。
《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辩误》的题目之所以称“原列”,是因为《昭烈忠武陵庙志》的作者潘时彤已对两廊塑像的人物选择、人物介绍和位次排列,很是不满,于是提出了自己调整塑像的设想,“以备采择”。实际上,潘时彤拟议的调整并未实施。不过相对于他提出的调整设想,潘时彤将当时祠庙内实际存在的塑像状况称为“原列”。《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辩误》一文后有“按”,称:“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均系康熙间宋臬使(即布政使宋可发)修庙时肖像、书牌”。也就是说,潘时彤认为1829年(清道光九年)时两廊塑像及其位次排列,很大程度上保持了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的旧貌。潘时彤对《昭烈忠武陵庙志》的纂修态度是审慎、认真的,他称当时两廊的塑像均为1672年时的旧貌,当有所据而言,基本可信。但必须指出,《昭烈忠武陵庙志》的“祀典”和“艺文”等部分的记载中,已反映出1672~1829(清康熙十一年至道光九年)年间两廊的塑像已有少量的调整。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塑在两廊的关羽、刘谌、张飞等像,1829年(清道光九年)时已“移塑”到刘备殿上;《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辩误》中还载明西廊中的黄忠塑像是“移塑”到张飞塑像原来所在的位置上,黄忠塑像原来的位置又重新补塑了张裔像;两廊塑像是对称的,东廊既未出现关羽、刘谌移走后的空位,那么东廊也应补塑了两像。
需要指出的是,《昭烈忠武陵庙志》中使用的“移塑”一词,是指将祠庙内原有的塑像移到别的位置上。由于塑像系泥塑,塑制的工艺程序都是先用木头搭成骨架,并固定在座墀上,再在骨架上进行泥塑,最后上色贴金。这就决定了泥塑像无法搬迁。因此,“移塑”实际上并不只是简单的塑像位移,塑像位置的移挪变动,实际上必须在新的位置上重塑。因此,关羽、张飞、刘谌和黄忠、张裔等曾经“移塑”的塑像,其塑制年代须从“移塑”之时重新算起。
关羽、张飞等像“移塑”到刘备殿上,是在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时。这一年曾修葺祠庙,维修工程的主要项目是扩建刘备殿,按照四川布政使司的《重修工程禀批》,这次维修改变了1672年(清康熙十二年)时所建刘备殿的格局。修葺后,刘备殿的开间由原来的五间扩增为七间,正殿由正中的明间和东、西两次间共三间组成,左右两边间分置钟鼓,在边间与正殿之间分别形成了东偏殿和西偏殿。扩建后增加的东、西两偏殿,就是为将与刘备“恩若兄弟”的关羽、张飞的像塑到大殿上。于是,关羽像被塑入东偏殿,张飞像被塑入西偏殿。刘谌像塑到了刘备殿正殿的东北角,具体位置在东次间的东北角。从文献记载看,1788年时刘备殿东偏殿除塑有关羽像外,另外还塑有关羽之子关平和周仓等2尊像。
《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辩误》中又称:“按桓侯(张飞)久升祀昭烈殿西,今因移祀刚侯(黄忠)以补其位。”也就是说,黄忠像塑于《昭烈忠武陵庙志》成书时或稍前,也就是1829年(清道光九年)时或稍前。在黄忠原来的位置上补塑的张裔像也应在同时,即塑于1829年时或稍前。
《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辩误》还记载说,1672~1829年(清康熙十一年~道光九年)时,刘备殿前的东、西两廊的塑像群均分作上、中、下三部分。我们知道,张飞移塑到刘备殿上后其处“移塑”了黄忠,可知1672年时张飞像是塑在西廊中部的,以张飞在蜀汉武将中的地位和他与刘备“恩若兄弟”的特殊亲密关系,张飞塑像的位置无疑应该处于西廊最尊的位置。当时与张飞同处西廊中部的赵云,也是最著名的武将之一,与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并称为“五虎上将”。赵云像之北为姜维塑像,张飞像之南为傅佥塑像。姜维是蜀汉后期的军队统帅,傅佥官阶虽不太高,但因为蜀汉死节而在封建时代被推崇,清代以前如北宋、南宋和明代,祠庙中仅只塑了几尊像时,就必定塑有傅佥。赵云、姜维、傅佥与张飞在1672年塑在西廊中部,可知当时是以两廊中部为尊的。再说东廊,1829年时中部的塑像为庞统、陈震、邓芝、蒋琬等4人。陈震、邓芝在蜀汉时的地位、名望远不及庞统、蒋琬,却塑在正中最尊处,这是什么原因呢?据本文前引罗森《重建武侯祠碑记》载,1672年(康熙十一年)时关羽、刘谌是塑在左(东)庑中的。关羽在封建时代极受推崇,至明末追封为帝,清代各地更是关庙林立,虽然在汉昭烈庙中关羽仍作为刘备之臣子被塑在廊庑中,但他必处于廊庑中的最尊处;刘谌是皇孙,又哀国亡家丧而自刎殉国,在廊庑必然处于最尊处。也就是说,1829年时东廊塑有邓芝、陈震像之处,在1672年时(清康熙十一年)塑的是关羽、刘谌像,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关、刘两像移至殿上,才在那里补塑了邓芝、陈震像。
刘备殿前的庭院,也就是由北面的刘备殿、南面的二门、东面的文臣廊和西面的武将廊所围成的院落,自1672年建成后迄今基本无改变。庭院中除了二门通往刘备殿的主道外,从东西两廊的中部各有一条小道与主道相连接,小道与两廊的连接处,正是1672年时塑有关羽、刘谌(东廊)和张飞、赵云(西廊)之处。当然,在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刘备殿扩建之前,殿基的宽度还没有达到与庭院同宽的地步,两廊与刘备殿的建筑之间有缺口,并未以建筑物完全封闭。其实,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刘备殿扩建之后到1829年(清道光九年)时,这一缺口仍未封闭。从《昭烈忠武陵庙志》卷首所附“陵庙全图”可知,那时联结刘备殿山墙与东西两廊的各是一条回廊,分别通向东面的官厅和西面的道院,回廊有柱无墙,刘备殿殿前两廊并无现在的北首第一间,因而那时的两廊与刘备殿并不能直接相连。
因此可知,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时汉昭烈庙中的塑像“如朝廷礼”,两廊中所塑蜀汉文武大臣,在这种礼仪所示的“朝会”中“奉召上殿”时,显然须经由廊庑中部的小道到主道后再上殿。这种建筑格局,正是与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塑制两廊塑像时以中部为尊的排序方式相配合的。
三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塑像调整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对祠庙内的塑像曾有一次较大的调整,此次调整所确定的塑像格局,至今无改变。主持这次塑像调整的,是当时成都的名儒刘沅。
这次调整中,两殿的情况比较简明。其中:诸葛亮殿并无调整变动,仍为诸葛亮及其子诸葛瞻、孙诸葛尚等三尊像;刘备殿的东偏殿中增塑了关羽之子关兴和赵累等2尊像,西偏殿中增塑了张飞之子张苞和张飞之孙张遵等2尊像。
两廊塑像调整变动较大,东廊(文臣廊)由北至南依次是:庞统、简雍、吕凯、傅彤、董和、费祎、邓芝、陈震、蒋琬、董允、秦宓、杨洪、马良、程畿等14尊塑像;西廊(武将廊)由北至南依次是:赵云、孙乾、张翼、马超、王平、姜维、黄忠、廖化、向宠、傅佥、马忠、张嶷、张南、冯习等14尊塑像。
两廊塑像在这次调整中情况比较复杂,需要我们作较详细的讨论。
前已述及,早在刘沅这次调整之前20年,《昭烈忠武陵庙志》的纂修者潘时彤就提出过一个调整塑像的设想。他在《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辩误》后“按”称:
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均系康熙间宋臬使修庙时肖像、书牌,不据史书,半从小说。位次既未妥协,官爵亦多桀。讹久相沿,未经辩证。兹妄参末议,附录于前,以备采择焉。
潘时彤“祔录于前,以备采择”的“末议”,包括载在《庙志·祀典》中的《原列两庑陪祀将佐位次官爵辩误》、《位次》和《祔拟增升前后殿配享并增改两庑陪祀位次官爵议》等文献中,这也就是潘氏提供“采择”的、对塑像调整的规划。从这些文献中可知,潘时彤调整塑像的主要意图有两廊分塑文武和两廊塑像的位次排列以一端为尊。两廊分塑文武即东廊全塑文臣,故拟将东廊中穿战铠的邓芝须移至西廊;而西廊则全塑武将。两廊塑像的位次排列以一端为尊(如能实现,自然应是两廊庑北端靠近刘备殿处),是指按所塑人物地位、官爵、影响,依次从一端依序排列。总之,潘时彤的这一调整规划要付诸实施,显然必须推倒两廊原有的塑像,全部重塑。
主持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这次塑像调整的刘沅,又有自己的调整标准。塑像调整事毕后刘沅曾镌有《汉昭烈庙从祀功臣记》碑,今存于武侯祠内。碑文在述及此次调整情况时说:
惠陵之侧为武侯祠。两庑祀诸臣,旧有李彪、张虎,于传无稽;而法正报怨于睚眦,刘巴、许靖之辗转而轻生,皆不得为昭烈纯臣,特僭为正之。且揭其事略,以便观者。书缺有间矣。存者表表,惟此数人,而砆玉杂揉,使人疑信参半,可乎?故叙颠末,以告将来。
刘沅认为,武侯祠两庑中的塑像,有的并非历史人物,“于传无稽”,有的又非“昭烈纯臣”。 刘沅于是“特僭为正之”,即在塑像调整(撤销、增塑)中,加以纠正。这段碑文没有说以“纯臣”的标准汰选了两廊全部塑像,也未说这次在两廊是全部重塑的,恰恰相反,它调整的对象只是“砆玉杂揉”中的“砆”。 从刘沅调整后的实际情况看,也确实如此。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塑像调整中,刘沅并未全部按潘氏的规划进行调整,两廊塑像并非是全部调整重塑的,而只是局部调整。
潘时彤关于两廊以一端为首排列塑像的意图,在刘沅主持的塑像调整中有所体现,例如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诸葛亮的庞统、五虎上将之一的赵云,分别被塑到东廊和西廊的北首,即为明证。但令人奇怪的是,东廊的蒋琬、费祎等,西廊的黄忠、马超、姜维等蜀汉文武重臣仍处在廊庑中部。刘沅主持塑像调整后,两廊以北首为尊、按所塑人物地位、官爵、影响的依次排列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位次很乱,不成体系。再则,潘氏对两廊分塑文武的意图,这次调整中仍未实现,东廊仍有穿战铠的武将,邓芝既未移走,另又增加了身着战铠的傅彤。若刘沅能将两廊塑像全部推倒重塑的话,那么无论按潘氏规划还是刘沅自己的意图,形成以北首为尊的有序位次,两廊分塑文、武,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断乎不会如此错乱。这些情况,都充分说明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对两廊的塑像不是全部调整重塑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庙志》卷首所载道光九年时的“陵庙全图”,那时联结刘备殿山墙与东西两廊的各是一条回廊,东面通向武侯祠主体建筑之东的官厅(今锦里前端),西面通往主体建筑之西的道院(今香叶轩、碧草园),回廊有柱无墙。即是说,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两廊北端第一间房屋,在1829年(清道光九年)时尚不存在。由于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在两廊北端各增修了一间房屋以与刘备殿相联接,并在该处各塑了两尊像,东廊是庞统、简雍像,西廊是赵云、孙乾像,两廊塑像才从1672年时的2尊增加至14尊。
我们可以对1829年(清道光九年)和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两个时期两廊塑像排列情况进行比较。在认识到两廊建筑上述区别之后,我们须将1829年(清道光九年)东、西廊北首第一尊像分别放至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北首第三尊像的位置上,依次比较各尊塑像。我们会发现下列塑像在调整前后位置毫无改变,包括:东廊的吕凯、费祎、邓芝、陈震、蒋琬、董允和西廊的马超、姜维、黄忠,共计9尊。这绝不是偶合,而是因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的调整并未涉及到这9尊像,故这些1829年(清道光九年)前的旧塑仍处于原来的位置上。也就是说,清道光二十九年在两廊调整重塑的,是除上述蒋琬等九尊像之外的其他19尊像。
上述情况,对我们弄清两廊现存塑像位次错乱原因,弄清两廊每一尊像塑制的准确年代,无疑是极重要的。
不同时期的塑像,它们之间就可能有某些差别。从两廊塑像的有关情况来看,两廊塑像若分别塑制于不同年代,确实有一些相异之处。较有代表性的,是两廊各尊塑像的“通高”,也就是从座墀的上部平面到塑像头顶的高度。在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调整中并未涉及的蒋琬等9尊像,已测通高数据的7尊,其中186厘米以上者6尊,另一尊也在180厘米以上;另外19尊调整后的塑像中,达到180厘米以上者仅9尊,不足半数,而达到186厘米以上者仅五尊。两批塑像在通高数据上的差异,反映出不同年代中工匠在塑像时的工艺差别,蒋琬等未调整的旧塑像都较高大(旧塑中陈震、邓芝、黄忠虽年代稍晚,但因是个别调整,工匠当然要参照康熙时两廊塑像的尺寸去塑制),而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的新塑像普遍均稍矮一些。
再看另一个情况。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调整后,两廊各自形成了两个较高的塑像群,分别在两廊的北首和中部。两廊北首头两尊塑像均为新塑,通高都较高,这是此次调整中欲以廊庑北端为尊的反映;然而两廊中部又存在一个较高的塑像群,中部这些塑像都是1829年(清道光九年)或之前的旧塑。两个较高的塑像群,在同一廊庑中形成了两个中心(为尊处),很不协调。这恰恰反映了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刘沅欲以两廊北端的塑像为尊,但实际并未办到,正因这次塑像调整是部分调整所致。
两廊塑像座下的座墀也说明了这个情况。现两廊座墀高低不一,最高的恰恰在中部,即东廊陈震、邓芝并坐的一墀和西廊黄忠、廖化并坐的一墀。如前所述,这里正是1872~1829年(清康熙十一年~道光九年)时两廊塑像位次最尊处,那时此处东廊塑的是关羽、刘谌,西廊塑的是张飞等。也就是说,两廊中部座墀相对较高大的现象,仍然保留了以旧塑中部为尊的旧貌。刘沅虽然把庞统赵云分别调整到了两廊的北首,已经表现出虽欲改以北首为尊的倾向,假如是全部推到重塑,座墀高低的调整,自然不成问题。正因是部分调整,陈震、黄忠等像既仍其旧,其座墀当然也无法改动,刘沅也就无法统一安排座墀了。
刘沅学识渊博,对于武侯祠中的塑像调整,自有其主张。这种看法在刘沅所著《明良志略》一书中有所揭示。如,刘沅认为,刘备殿上的塑像除了刘备塑像外,应当还有4位侍臣,即庞统、赵云、孙乾和简雍;“北帝王”(按当作北地王)刘谌虽作为“附祀”,其塑像置于刘备殿正殿之东北角,却不恰当,需要“更正”:
按,王之义烈,当祀于昭烈庙后,别为一宫。今因后为丞相祠堂,地隘,故祀于昭烈殿左,退后别为一龛,俟后更正。
按刘沅的主张,庞统、赵云、孙乾、简雍都应当塑到刘备殿上。蜀汉文臣中除诸葛亮外,自然首推庞统;武将中除关羽张飞,赵云亦为首选;孙乾、简雍虽无卓著功勋,但自始至终追随刘备,是刘沅最看重的“纯臣”。“由士元亚于诸葛,子龙亚于关张,孙(乾)、简(雍)相从最久,故正殿以之为侍。”(据刘沅所著《明良志略》载)刘沅还主张在刘备殿后专为刘谌另修一建筑,在其内塑像,单独放置。不过我们看到刘沅对塑像调整后的实际情况,庞统、简雍被塑在东廊北端,赵云、孙乾被塑在西廊的北端,刘谌仍在刘备殿东北角。也就是说,刘沅对塑像调整的主张,并未在其主持的调整中体现,必因有所制约,使其并不能如愿调整塑像。刘沅受到制约的因素,或当为经费不足。按武侯祠清代以来历次较大修葺的工程经费,有的为官府供给,如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刘备殿的改建,有的为官员募集,如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重建、1825年(清道光五年)对惠陵及其附属建筑的修葺,或见于竣工后相关碑文,或见诸文献,总之都有相关记载。以1825年(清道光五年)培修惠陵工程为例,由布政使董淳牵头,各藩司衙门和地方官员均参与捐资,其中“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董淳捐银二百两,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兴科捐银一百两,四川通省盐茶道周之琦捐银八十两,四川通省盐茶道花杰捐银一百二十两”,以下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尹济源等地方官员捐资情况,包括捐资人姓名、官职、所捐银两数量,清清楚楚。此次“共捐赀二千五百五十两,其捐赀职名均照是年藩署档册所载录入”。然而1849年这次塑像调整却未见记载,当非官府资助或官员募捐,经费或由驻庙道士筹集,或由刘沅募资。由刘沅募资的可能性也不大。尽管刘沅非常关心武侯祠,对祠庙内文物的保护很热心,但当时他正在募资修建成都西郊的黄忠墓,刘沅及其门人所筹经费只够买下土地,“别为棺敛,树碣修茔尚需工费数百”,只得“布告同人捐助,以完盛举”,于1850年凑够经费修成黄忠墓,至于规划黄忠墓旁的黄忠祠,则又在刘沅过世后由其子建成。塑像调整若纯由驻庙道士筹资,所能筹集自然很有限,难免捉襟见肘,不可能实现将塑像全部重塑。
由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肯定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对两廊塑像的调整,只进行了部分重塑,调整中保留了蒋琬等9尊1829年(清道光九年)前的旧塑。由于道光廿九年调整时准备改以两廊北首为尊,而保留的道光九年前的旧塑多在廊庑中部,以中部为尊的旧貌也基本被保留下来,故形成现在两廊塑像位次错乱、不成体系的排列。因而,现在俗称武将廊的西廊中既有身着袍服的文臣简雍,文臣廊即东廊里也有穿战铠的邓芝、傅佥等像。
通过上述考述,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武侯祠内塑像的塑制年代。
两殿塑像的塑制年代:刘备殿的刘备及其两侍者塑像,诸葛亮殿的诸葛亮及其两侍者、诸葛瞻、诸葛尚8尊塑像,塑于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刘备殿东次间东北角的刘谌以及两侍者,刘备殿东偏殿的关羽和关平、周仓塑像,刘备殿西偏殿的张飞塑像等7尊塑像,塑于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刘备殿东偏殿中的关兴、赵累塑像以及刘备殿西偏殿的张苞、张遵4尊塑像,均塑制于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
两廊塑像的塑制年代:蒋琬、费祎、董允、吕凯、马超、姜维6尊塑像系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所塑;邓芝、陈震2尊塑像系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所塑;黄忠塑像为1829年(清道光九年)或稍前所塑;其余19尊塑像,包括东廊(文臣廊)的庞统、简雍、傅彤、董和、秦宓、杨洪、马良、程畿像,西廊的赵云、孙乾、张翼、王平、廖化、向宠、傅佥、马忠、张嶷、张南、冯习,系1849年(清道光二十年)所塑。
上述47尊塑像,除随侍刘备、诸葛亮、刘谌的六位侍者和周仓外,其余40尊所塑的人物,也都见载于记叙三国时期历史的重要史籍《三国志·蜀书》,是真实的蜀汉历史人物。(《三国志·蜀书》中无传者,则见《三国志·杨戏传》中之《季汉辅臣赞》所载。)周仓见诸戏曲和《三国演义》。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塑像调整之前,每尊塑像前有介绍该像所塑人物的“书牌”,主要为其姓、名、字、爵位、官职等,因其“不据史书,半从小说”,被潘时彤诟病为“官爵亦多桀。讹久相沿,未经辩证”。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塑像调整完成后,原来的各尊塑像前的“书牌”一律改为石碑,刘沅为两廊的28尊塑像逐一撰写了碑文,共计28通小碑。这些碑文行文简洁,其内容主要介绍该人物的有关情况,如姓氏、名字、生卒、里第、官爵、事功等等。作为一代名儒的刘沅在介绍这些蜀汉历史人物时,非常注意尊重历史,其碑文内容主要摘自《三国志·蜀书》该人物的传记,以及《三国志·杨戏传》中《季汉辅臣赞》和裴松之注文的有关记载。在黄忠像前小碑中,刘沅还记叙了清道光年间成都近郊黄忠墓的发现等情况。此外,刘沅撰写了《汉昭烈庙从祀功臣记》碑,记叙这次塑像调整的有关情况;另外还撰写了《关夫子考辩》碑、《汉昭烈庙偏殿祀张桓侯及其子孙记》碑、《周苍赵累》等碑,介绍和考述相关人物的情况。以上32通碑的碑文以及刘沅关于塑像调整的一些设想,后来由刘沅的学生结集刻版印行,书名为《明良志略》。
关于塑像的外貌和衣着。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武侯祠内现存塑像分别塑制于清代的康熙、乾隆和道光等不同时期。依照廿五史等历代史籍的惯例,除非是记载中的相关人物外貌有异于常人的特别之处,如身高特高,如诸葛亮“身长八尺”,刘备“身长七尺五寸”等;或有其他特征,如刘备耳朵特大,可“顾自见其耳”,手特别长,“两手过膝”,等等,需要在传记中反映外,一般对人物外貌并不做记叙。《三国志·蜀书》亦如此,也只对少数人物特殊的外貌特征有记载。由于无据可凭,因而后代塑制这些蜀汉历史人物时,主要是参考戏曲、演义故事和传说等艺术渲染后的形象,再由工匠艺术加工而成。据说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塑制庞统像时,就是参考川剧中的庞统扮相塑成的。当时活跃在成都戏曲舞台上的一个太洪戏班中,有位叫何二胖的演员,以扮演庞统而驰名,工匠们就是参照何二胖的扮相,塑制了今天我们在东廊中看到的面部较黑的庞统像。历史上并无庞统面黑的记载,但是何二胖扮演庞统时扮相的面黑,可以说,工匠们较为严格地依照何二胖的舞台扮相塑成了这尊像。不同时期的工匠们都遵循此道,因而塑成的像,风格也就能基本一致。同样,塑像的衣着也都是参考戏剧服装而塑制的,文官的衣袍冠带,武将的战铠头盔,都参照明清时期的戏装塑成。以武将的头盔为例,出土文物中有西晋时期战时防护的头盔,仍然是用金属整体浇铸的,而远非武将塑像头上那种用金属片联缀而成、加工精细、戴着舒服的头盔。
四 1971年至今的塑像维修保护
本文所谓“塑像维修保护”,一方面是指直接实施于塑像本体的维修,即对塑像上色、贴金、补贴胡须,以及对塑像受损部位的修补,等等。另一方面,是指对塑像所处环境的改善,包括对塑像和壁画保护条件的改善和塑像参观环境的改善。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塑像调整后,迄无变动,沿袭至今。1849~1949年之前的塑像维修,因无文献记载,情况不详。1949~1970年间未维修。1971年之后,塑像曾多次维修,进行了修补、上色、贴金和补贴胡须,等等。同时,也进行了多次改善塑像环境的工程。具体有:
(1)1966~1970年间,武侯祠闭馆。因英籍华裔韩素因女士回成都省亲时要来祠参观,武侯祠将于1971年8月重新开放,1971年1月~6月,对祠内中轴线道路、文物稍作整修。
由于本祠1966年“破四旧”时曾遭红卫兵冲击,匾联、塑像均有损失,部分塑像的胡须被扯掉。其后虽然闭馆未遭继续冲击,两殿、两廊却又被征用为“抄家物质”的堆放场所,主要堆放较大的木制家具,家具搬运进出时对两廊的塑像撞伤、擦伤。此次整修前塑像的损失主要有:刘备殿西偏殿张苞像头部脱落;两廊塑像大部分胡须被扯掉或脱落,两廊塑像约三分之一有手指断脱和碰伤、擦伤,等等。本祠因特聘成都著名泥塑世家“泥人蔡”的传人——蔡婆婆来祠,对塑像修补。蔡婆婆参照已脱落的张苞头像予以恢复,非常接近原貌,手指断脱的也一一修复,碰伤、擦伤等情况也做了修补。当时,因无补贴胡须的原材料,暂搁置。
(2)1976年5月~1978年1月,武侯祠文管所特邀新都县万和村民间艺人王义元师傅对塑像上彩。王师傅当时在祠内做漆工,主要用土漆漆宫灯、对联和家具,同时他对祠庙塑像上彩等也很有经验。此次上彩是在开放游览的同时进行,只罩蔽正在上彩的塑像,先两廊、次刘备殿、最后诸葛亮殿,所用颜料完全用矿物颜料,逐一对47尊塑像上彩。1980年前后,王义元师傅托人购得为塑像粘贴胡须所需原料,仍由王师傅为47尊塑像中缺损胡须的,进行了补贴。
(3)1979年,武侯祠文管所为刘备殿的刘备塑像、刘谌塑像,诸葛亮殿中的诸葛亮塑像、诸葛瞻塑像、诸葛尚塑像等5处像龛安装了玻框。1980年底~1982年秋,在维修文武两廊建筑的同时,增添了有利于塑像保护和便于游客观览的设施。原两廊为隔蔽游人的触摸塑像而造成毁坏,自距塑像正面座墀前端约1.7米处建有矮墙,高约1.2米,墙上再以7厘米见方的方木作木栅,直封至将近屋顶处,以方木的两角与墙体平行,另外两只角分别朝向游人和塑像,方木之间均间距35厘米,犹如城隍庙中的神像廊的形制。这样的设施只能防止游人直接触摸塑像避免损害,并不能防尘,对塑像的保护力度远远不够,同时因墙栅距塑像较远,墙栅内光线不足,影响游客的观览。此次维修中将原墙栅和矮墙拆去,将矮墙朝塑像座墀方向后退约1.30米,在距座墀前0.4米处重建矮墙,矮墙上改设仿古式玻窗,直封至顶。这样就大大有利于塑像的防尘,减少了因除尘的清洁工作对塑像的损坏,同时改善了两廊中的采光条件,加宽了两廊的游览线,使游客更接近塑像而便于观览,既有利于塑像的保护,也便于参观游览。
为了解决塑像玻框所需大量平板玻璃,1978年武侯祠文管所曾派人专程到距成都最近的平板玻璃生产厂家——洛阳玻璃厂订购。刘备殿、诸葛亮殿安装玻框所用,两廊改设玻框所用,均为该次从洛阳采购回的玻璃。
(4)1981年,西廊(武将廊)后墙倾斜严重。由于墙上有清代的水墨壁画,不便拆除墙体重建,于是武侯祠文管所在壁画墙后建一厚墙支撑危墙。当时是以钢筋混凝土建一保护墙,一边建保护墙一边填实与危墙之间的空隙,因保护墙仍在游览区内,又再将保护墙外建为长廊。这一保护方案既消除了西廊危墙的隐患,保护了廊中的壁画,增添了新景点——长廊,还解决了消防断火的问题。该方案由何赐秉同志提出,经国家文物局专家认可后实施,效果甚佳。
(5)为解决塑像和匾联补贴金箔所需,经多方争取,1985年秋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特批给武侯祠博物馆5两黄金(当时除首饰外黄金尚不允许自由买卖)。武侯祠博物馆特邀有金箔加工特殊技艺的成都剧装厂师傅2名,在馆内加工金箔,金箔的制作历时约三月,约于1986年春节前完成,制成了一寸见方的金箔达10000多张。1986年春节后至同年年底,由王艺元师傅对塑像和匾联补贴金箔。
(6)1996~1998年,武侯祠博物馆邀请成都市轻工研究所为两廊安装冷光源灯具,既增强了两廊光线,又避免灯具发光时所产生的热量直射塑像。
(7)2001年,再邀新都县万和村民间艺人王义元与其子为塑像维修上色。具体包括为塑像除尘、清洗、修补、上色、补贴金箔、补贴胡须。维修上色历时半年。稍后,又邀请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曾中茂研究员为两廊后墙的水墨壁画除尘清洗。
(8)2001年2月,对两廊建筑大修。两廊建筑系清代所建,因年代久远,屋面漏雨,白蚁蛀蚀,建筑、泥塑、壁画都面临危险。1999年本馆组织专家论证并制定出维修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2001年2月,武侯祠博物馆投入94万资金,对文武两廊的建筑进行了揭顶性的全面维修,工程包括屋面维修、蚁害治理、墙体加固、壁画保护(清垢和重建着色)、维修排水沟、地坪铺设石板、参观线路改造等保护措施。此次维修,修旧如旧,施工全过程采取开放式施工,维修工程由成都市晓初建筑责任公司负责施工,于2001年7月竣工。
五 对塑像保护的不利因素亟待消除
尽管近四十年来已为塑像的保护做了不少的工作,但仍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例如,成都地区常年的高湿度,空气中既有较多的粉尘,还含有一些对塑像保护不利的物质,对塑像的保护就极为不利。
对塑像威胁最大的,首先是湿度问题。由于成都处于盆地之中,四周环山,空气流通不足,加之地势低洼,地下水位较高,因而湿度很大。同时,成都地区自古以来光照就较少,有“蜀犬吠日”之谓。在以上种种因素影响下,成都地区长时期以来都是终年潮湿。从实际监测的数据来看,刘备殿前东西两座塑像廊内,3月份最低湿度为63%,7月份最高湿度为97%,总的说来湿度太高。虽然这些以泥为主要材料塑制而成的塑像,其表层也作了防潮处理,这就是在泥塑像的表面加有一层以石灰等物质做成的表层,便于上色,同时也有一点防潮作用。不过这种简单的防潮隔离层远远不足以抵御常年的高湿度的侵害,对塑像的保护极为不利。其次空气中的粉尘和有害物质,也不断侵蚀着塑像。
在上述不利因素的持续危害下,泥塑像像体日益粉化、酥碱,表层起甲、剥落,彩绘褪色,像座开裂,壁画褪色、剥落,尽管针对这些不利因素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对塑像保护有害的这种趋势迄今尚未得到根本的扭转。以塑像的外观为例,本文前已载明,自1976年~1986年,曾对两殿和两廊的塑像进行了系统的修补维护,包括上色、贴金和补贴胡须等保养维护,但仅仅约20年后,塑像的腐损状况又日益突出,两廊因屋脊时有漏雨,塑像曾遭受雨水侵蚀,文臣廊的程畿、马良等两尊像损坏最严重,色彩剥离;武将廊廖化的脚破损严重;黄忠、赵云的白胡须几乎掉完;其余塑像布满灰尘,色彩黯淡,污迹斑驳。于是武侯祠博物馆于2001年再次邀请王义元父子上色贴金。而且上述保护措施还局限于塑像的外观,最多能对彩绘褪色、金箔脱失作一些修护,并不能解决像体日益粉化、酥碱,表层起甲、剥落之类对泥塑像产生根本性危害的问题。
针对对塑像危害严重的常年高湿度等问题,武侯祠博物馆的文博干部曾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对进入刘备殿前两塑像廊的空气作除湿和过滤粉尘处理。具体的设想是:将两座塑像廊塑像前端的以砖木和玻璃组成屏蔽墙作封闭处理后(其余三面均已有砖墙封闭),在廊庑的两端高处设置抽风机,一端抽入,一端抽出,对抽入的空气用木炭或除湿剂进行除湿,用多层窗纱过滤粉尘,这样一来,可以有效地降低湿度,减少粉尘。但这种方案若付诸实施,势必对塑像长期以来所处的环境发生很大改变,环境的骤然改变会不会对塑像产生新的、更大的危害?由于存在着上述顾虑,该方案并未实施。
这些对塑像保护的不利因素亟待消除。相信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消除不利因素的难题在不久的将来或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J317.G264
A
1004-342(2010)06-72-09
2010-05-27
李兆成(1949—),男,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