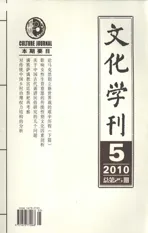试论池田大作人类和平思想中的佛教哲学渊源
2010-03-21张云江
张云江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在《我的人学》中文版序言中,池田大作自称是“一个祈求和平的佛法者”,是“站在祈求和平、以佛法为基调而行动的立场上,思考和谈论如何坚强地对待人生”。[1]池田大作的佛教“日莲宗”信仰背景人尽皆知,佛教信仰是其内在精神支点与人生终极关怀,祈求、推进人类和平则是他一生追求的志业,二者共同构成了池田人生内外之两极。所以池田所自称的“一个祈求和平的佛法者”,是对自己平生理想、志业最为精炼、准确的概括。
纵观池田几十年来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祈求、推进人类和平始终是一条主线。他所倡导的人类和平思想,并不仅限于国际社会能够和平相处,也非仅指一个族群或者国家内部的和谐稳定,而是针对当代社会出现的种种“现代性”问题,诸如人自身价值丧失、环境恶化、教育异化、伦理观念蜕变等,追求一种“人性革命”的“创造性转化”,使个体以“内发的力量”为精神生活的源泉,并以由此所锻炼成的自律产生“外在的规范”,以期达到人与自身、社会、自然和平共处、持久发展的目标。“最高的和平状态其实就是我们所倡导的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繁荣,每个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是成功幸福的终极状态。”[2]
有鉴于池田大作深厚的佛学素养与信仰背景,在他论述人类和平思想的诸多言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深厚的佛教渊源。佛法智慧既是他观察、思考社会问题的坐标,又是他矢志不渝地追求理想时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池田关于人类和平的言论,也可以说是古老的佛教智慧针对现代社会种种问题与弊端所发出的、现代人包括西方人士所能听懂的一种“福音”,是在现代文明时代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境界言诠。
下面从四个方面探讨池田大作人类和平思想中的佛教哲学渊源。
一、肯定个体自身价值
池田大作充分肯定个体自身价值,认为这是人类和平的前提。这和佛教“个体本位”哲学思想有着甚深的渊源关系。
池田在评述俄罗斯“新思维改革设计师”雅戈布列夫时说道,雅氏崇信佛教,是因为佛教要在自身之中发现自我的神,而不像其他宗教那样承认外在有创造者。池田认可这一观点,认为“每个人之中都隐藏着自我完成的可能性,自己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要相信自己的可能性,不要期待从权力或其他方面得到恩赐”。[3]“佛法主张自体显照,重视各个人从内部发挥出自身本来的个性。”[4]
池田重视个体价值,强调“个人对人生的责任”,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正如他在和儒格对话时所说,当今时代,人们已习惯随波逐流,不再追问存在意义,丧失了生命原动力,人的精神变得衰弱被动。现代文明中,那种无限提高人、使之向上奋进的精神推进力量,正消磨殆尽。物质、机械、技术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人主体心灵、精神的力量却越来越虚弱。这是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推进人类和平的最大障碍。池田认为,如果没有个人内在的变革,不能消除个人内在的恶,外在的任何组织性的斗争、运动都是徒劳无益的,“有外在的‘恶’,同时也有内在的‘恶’——若不看到这一点,一切改造世弊的革命,是不能脱离单纯的权力斗争、政权更迭的范围的”。[5]甚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并非只是军备和政治体系的问题,它要求我们必须从人类的根本立场来审查问题”。[6]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池田才主张:要解决现代社会种种问题与弊端,需要从根本上改革人的精神、生命,除此之外,没有解决途径。人性自身的革命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组织和社会的变革。[7]“一切行动都应该立足于正确的精神基础之上。个人的生命比地球还要重。”[8]“让每个人能直接接触到终极的精神实在,给人类带来同现在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诸恶作斗争并克服它们的力量。”[9]
池田凸显人的个体价值的优位性,与佛教的“个体本位”哲学思想有着甚深渊源。佛教“个体本位”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个体对善恶业果的承担,二是鼓励个体追求还净寂灭的解脱之道。佛教要人承担自己所造业果,即便亲人也无法替代。池田以现代人的视域来谈论佛教的业果思想,如在与汤因比的对话中,池田将佛教的业果比喻为“银行存折”,“一个人作为一个身心统一体,要重新在银行存折上填写自己在现世这一世的支出与借入”[10]。为善还是为恶,个体有抉择的自由,但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行为的业果承担者只能是个体。
“佛教解脱论也是以个体本位为基石。”[11]小乘佛教灭除内心烦恼,证入清净寂灭涅槃,其求道、修行是个人的事情,别人无法替代;大乘佛教为成就菩提,六度万行,上求下化,突出的是个体对于众生救渡的责任。池田大作充分肯定个体自身价值,是因为个体实际上是一种“永久性”、“终极性”的精神存在,因为幻象、欲望的遮蔽,人们已经习惯忘记这一点。而要想使自我与终极存在(佛境)合为一体,个体“需要通过严格的精神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它,唯有这种每个人的精神努力,才是导致社会向上的唯一有效的手段”。“除了每个群众都成为贤明者之外别无他法,每人都成为圣贤,拥有明确的是非观,从而可以校正社会的动向和前进的道路。”[12]池田大作在哈佛大学论及大乘佛教担负的任务时,曾强调这一信念。而各种制度的变革,不过是这种精神努力的后果而已。[13]
二、重视个人内心和平
池田大作重视个人内心的和平,认为这是人类和平的基础。这和佛教“心为法本”的哲学思想有着甚深的渊源关系。
在《心灵的容器》中,池田大作写道:“美的心灵必然有美的人生,坚强的心灵则必然有坚强的人生”,并引用《华严经》“心如工画师”一语,说人的内心能够创造出善恶、美丑等一切之法,时刻累计,便会形成独自的人格。在《忠实于自己》中,池田大作说,“从无常的世界向常住世界的转换——可以说这正是有史以来,人类所追求的最大课题”,也是“人生的最大事”,“我之立足于悠久的生命观,走上信奉佛法的理由也正在这里”。[14]
可以说,在池田大作的著作中,我们会发现非常多的重视人内在心灵的话语。这自然与佛教所谓“心为法本”的传统有甚深的渊源关系。如佛所说偈云:“心为法本,心尊心使,心之念恶,即行即施,于彼受苦,轮轹于辙。心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行即为,受其善报,如影随形。”[15]
佛教哲学所谓“心为法本”,即是说,世间、出世间的一切理事,无不以心为本。池田大作重视人的内心和平,认为人“找到内心的和平,才能和人生、和社会泰然相对”。[16]人“内心和平”之实现,首先要学会“约束欲望”,这要靠个人的自觉和意志来进行:“给欲望以无限制的自由,就等于压制了崇高的精神自由。只不过这不能靠社会的外在力量,而是要靠个人的自觉和意志来进行。”[17]
佛教认为,以欲望为主导的贪瞋痴等烦恼,是人身心不得安宁和平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种种苦难的来源,这些负面精神作用的扩张,使得人类争夺、仇恨不已。佛教要人们通过修行、磨练去除贪欲之心,净化心灵,这样才有善法可言。池田大作认为,现代社会“恶缘不绝”,所以更有“讲求不断磨练生命的修业的必要”,“对人来说,只有通过战胜自己那无聊的贪念和狭隘的自我,才可能得到更大、更高尚的境界”。[18]只有磨练过的生命,才能引导人走向内心真正的和平。个人内心和平是人类和平的基础。这和佛教“心为法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池田强调要达到内心的和平,需要“修业”,亦即不断磨练自己。他与世界各地的闻达、贤哲展开对话,谈论天下是非,衡定世间得失,推进人类和平,从其对话中的表现及立场来看,他自身是首先达到了内心和平了的,然后才能与对方平心静气地进行探讨,也才能真正推动和平理念的普及与推广,而不是在强制兜售自己的思想。池田大作此种内心和平的人生境界,不妨视为是佛教“心为法本”智慧之学的一种实际践行,而他所说“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教诫,也可以说是自身经验的结晶。
三、强调人间信赖关系
池田大作认为人类和平必须以人间信赖关系为基础,所以需要认同差异,互相尊重。这和佛教的“缘起”哲学思想有着甚深的渊源关系。
在与金庸的对话中,池田说道:“人有善友是多么重要啊,这使我想起阿难向世尊请教的问题……释尊说道,……我们有好朋友,又有好伙伴,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已成此佛道的一切。”[19]池田认为,佛教所说的好朋友、好伙伴,就是“共步于人的精髓之道的同志”的意思,实际上是个体层面意义上的一种深刻牢固的信赖关系,而“和平的实质经常是存在于人与人的信赖之中”。社会的根本是信赖,“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必须以人间的信赖关系为基础”。[20]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是人类和平的基石。
池田以人间信赖关系为人类和平的基石,其中的佛教哲学理念当是“缘起”思想,而从好伙伴、好朋友这样的伦理之常层层扩展到国际关系,则明显有华严哲学境界“重重因陀罗网无尽缘起”的思想渊源。池田大作在莫斯科大学和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谈到佛教的“缘起”思想:“万物存在于相互的‘由缘而起’的关系性之中,独自能单生的现象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佛教的世界观。”[21]“宇宙的森罗万象都处在‘缘起’,即相互依存的关联性之中。”[22]一切事物互为因缘,皆无自性,要依赖于其他部分或他人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故佛教立论,多强调人、事、物之间的和合,此即池田所谓“佛教不把如神一般的超越之存在置于首位,而宣传内在的万物的相互关系性、相互依赖性这一点”。[23]从这一哲学理念出发,在对待人际关系时,必然以平等、慈悲为出发点,突出事物成立的“结合”一面,而视一切差异相为成就一体的必要存在因缘。“秉持佛法的本意,就不能不把和平摆在第一位。”所以池田大作认为,“要抛弃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等造成的人的固执于差异,而对一切人予以爱,亦即大爱、博爱,也就是慈悲之心”。“平等和慈悲的确是成为国际人、世界人、二十一世纪人的条件,慈悲之心愈是扩大,和平也就更接近了。”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及由之造成的人生态度,必然是倾向于消弭对立、追求和平的。这种思想能消除现代社会流行的自我中心主义及人类中心主义,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和生态的亲和关系,从而促进人类和平的福祉。
池田所领导的“创价学会”,引导平民阶层的“精神变革”,在与金庸先生对话时,池田曾举了两个例子,说明普通百姓精神世界发生变革之后的事情。这是一种微观层面上的“缘起”;池田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人类和平理念,这是一种宏观层面上的“缘起”。如果按照华严宗哲学“因陀罗网重重无尽缘起”的思想来看,二者理事一致,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百姓的精神变革与人类和平的进程,二者所含有的道理是一样的,需要投入的真诚与努力也是一样的。一位平民的“精神变革”并不是一件小事,人类和平理念的推广普及也不必是一件大事,二者小中见大,大中映小,相互交映,隐映互彰,重重影现。池田所领导的人类和平推进及人的精神变革工作,就其影响及内在理念而言,是有《华严经》这种“因陀罗网”重重涉入的甚深缘起之思想渊源的。这也正如同池田所说:“在人类所进行探索的各种领域之中,都必将看到佛法闪动着的耀眼的智慧之光。”[24]
四、积极倡导文化对话
池田大作一生积极倡导文化对话以促进人类和平,这一形式自身即具有佛教特色,同时和佛教菩萨道积极入世的慈悲救世精神又有着甚深的渊源关系。
池田大作所采取的推动人类和平的策略,即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著名政要、学者、文化名人进行文化对话,认为“人的交流与对话是克服文化、思想的差异的关键,促进相互信赖与理解对争取持久和平是必要的”。[25]这一方法本身就充满了佛教特色。在不同文明、文化对话方面,佛教有着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明相遇,就是在不断的对话中互相融摄,和谐共存,取长补短,最后形成了三教鼎立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佛教传入日本,日本的神道与佛教也没有相互排斥、对抗,而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神佛合一”思想。佛教由印度传播到亚洲各地并生根、开花、结果,在遇到与本地文化冲突时,其消弭矛盾、争端以达致和平的主要方法就是开展文明对话。因此我们应当看到,池田大作采取这一策略,是有着深刻的佛教思想渊源的,同时也得到了如汤恩比、金庸等人的高度认同,如汤因比曾对池田大作说:“要开拓人类的道路,就只有对话了。”[26]
池田奔波于世界各地,多次与各国领导人、著名学者等进行诚挚而认真的对谈,除了佛教自身源远流长的文化对话形式的影响之外,还有取于大乘佛教开展文化对话时的宽厚兼容的胸怀以及哲学解释、辩难的高度机巧。楼宇烈教授认为:大乘佛教宽容的精神,表现在对于不同文化、理念有着同情的理解。这是佛教能够与其他文化开展对话、和平相处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佛教在坚持、维护自身教义立场的同时,对于其所批评的理念能有一种肯定、认可的态度,并通过“判教”的方式给予一定的地位。正是有鉴于佛教文化对话的成功经验与宽厚兼容的胸怀,池田大作在与世界各地的二十几位社会贤达人士对话以促进人类和平时,才能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理念、思想、理想解释给对方听,以使对方能明白进而认可自己的观念。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对对方的文化背景有着极为熟稔的了解与掌握,这样才能在解释自身立场、辩解对方疑难时具有针对性;开展文化对话同时又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能吸纳对方的合理意见,以完善自身思想,这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对话心态。“所谓对话,可以说首先并不是改变他人,而是一种改变自己的巨大挑战。”[27]池田大作积极推进文化对话以促进人类和平,在形式、内涵的胸怀、心态等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发现与佛教哲学解释、辩难方面的甚深渊源关系。
另外我们从池田大作奔波劳碌的身影中,不难感悟出佛教所赞扬、推许的菩萨慈悲救世的伟大精神。池田这样理解“菩萨”:“所谓菩萨,即以慈悲为怀的、为世界和人类服务的人类生命的状态。”菩萨具有一种“在自己灵魂深处能够深深体念到所有人类同胞苦恼的人格”,这是充满慈悲精神的人性,[28]池田大作曾以一百步与一步之对比说明“平凡而非凡”的菩萨精神,“一个人走一百步”所追求的是个人的卓越,“一百个人走一步”则“需要大乘佛教的菩萨”团结民众,与之交流,耐心地组织民众参加社会活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可以说是池田对当代社会之佛教菩萨慈悲救世精神的独特理解与诠释。
佛教大乘菩萨慈悲救世,六度之首是“布施”,《华严经》中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法供养”即是以佛法去化解人们的烦恼,消除人们内心的焦虑不安,其主要内涵是帮助人们建立“正见”——对于生命存在价值的正确见解。尤其现代社会,阻碍人类和平的障碍更多来自人们精神上的不安、心灵上的苦恼,如果进一步追问根由,则缺乏正确的生命存在观、价值观是主要原因。池田称我们正生活在“一种与精神的深度无缘的时代”,古今之隔使得人们面临着迥异于古代的社会生存环境,古老的道德伦理资源在现代人看来已经过时,人们在面对种种人生困境时难免会无所适从,因此精神堕落,多以追求欲望的满足为人生目标。青年人心灵荒芜,自暴自弃或反叛社会的行为形成风气,人类正在遭受着“以贪欲为动机、由技术所造成的种种恶果”。[29]要改变这一切,需要实现“人类心灵的变革”,要实现心灵的变革,则必须引导人们建立“正见”——池田大作称之为“正确的哲学”——“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随着感情、欲望的漂流,像浮萍似的生活态度,是不可能治愈心灵的冷却和干渴的,生存的活力也会削弱的。”[30]“要改变这种神死与心死的状况,池田认为必须从人这一原点出发,首先实现人自身的革命,继而以人自身的改变带动社会的变革。”[31]
从这层意义上说,池田大作所推动的、以促进人类和平为目的的文化对话及社会活动,可以视为一种以佛法为背景而向世界普及生命、生存智慧之正见的“法供养”。也因为他充分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所以能以现代人可以接受的言说方式、直接针对现代人的心灵困境诠释佛法,因此,池田大作所秉持大乘佛教菩萨慈悲救世的精神而作的此种“法供养”,可以说是古老的佛教智慧在现代文明时代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境界言诠。
[1][14][16][24]池田大作.我的人学[M].铭九,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4.63.91.619.
[2][31]曲庆彪,等.回归与超越——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M].大连:辽宁师大出版社,2007.27.20.
[3][5][12][19][20][26][28]池田大作,金庸.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3.366.156.156.158.71.135.
[4][9][22][25][27][30]池田大作,杜维明.对话的文明[M].卞立强,张彩虹,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80.70.195.74.68.91.
[6]池田大作,保林.生生不息为和平[M].周伯通,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87.
[7][8][10][13][17][29]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M].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143.57.3.4.55.52.
[11]林国良.出入自在——佛教自由观北京[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34.
[15][东晋]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大正藏2[M].827b.
[18][21][23]池田大作,戈尔巴乔夫.20 世纪的精神教训[M].孙立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59.226.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