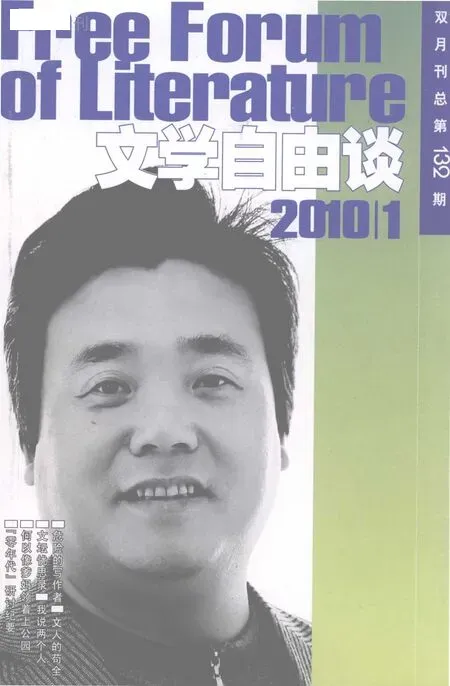散文可以是“诚实的谎言”
2010-03-21文高为
●文 高 为
文学写作的要求首先是求美,求善。文学的本质是虚构,求美,独创。小说是“庄严的谎话”,同样作为文学体裁的散文,为什么就不能是“诚实的谎话”呢?用真实、规范、格式、套路来要求文学作品就无异于方枘圆凿,南辕北辙。如果承认散文是文学的一种,用真实来要求散文甚至作为散文的标志,那就有些自相矛盾了。
冰心先生在《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中,以她的三篇散文——《尼罗河上的春天》《一支木屐》《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为例,详尽解释了其中的虚构成分。通过适当地更改事实,使文章更合理、更美了。“笔补造化天无功”(李贺),大自然或现实情况不完美,写作时靠修辞使其完美。
苏联理论家维·什克洛夫斯基于1925年和1982年分别出版了内容不同而书名相同的著作——《散文理论》。两书虽然用散文笔法写成,谈的却是小说、戏剧、民间故事、神话、圣经,惟独没有“散文”。如果上述文体都可虚构,为什么独独散文不能虚构呢?
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叔雅找到陈寅恪,请陈代拟大学入学国文试题。陈寅恪出对子之题为《孙行者》,作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象。……若应试者不被录取,则成一游园惊梦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高考作文当然是散文,可以看出考生的“史才诗笔议论”,想象当然是虚构,谁说散文不能虚构?
一篇动人的散文,当我们知道了其中有虚构成分时,顿时觉得其价值就打了折扣。其实大可不必。恰恰相反,我们应当为作者的巧夺天工而加倍喝彩。“不以人废言”,不也可以指这种情况吗?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那我们欣赏作品就行了。钱钟书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为什么非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作为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的《左传》,它到底是左丘明的真作,还是刘歆的伪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区别吗?三百篇的作者是谁,荷马到底有无其人,对我们欣赏《诗经》《伊里亚特》《奥德赛》有什么影响呢?如果作者是谁都不重要,作者是善是恶也不重要,那么,作品有一部分虚构就那么重要吗?这是不是在采用双重标准?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钱钟书《管锥编》)《左传》《史记》等书中的对话,基本都是后世史学家的想象、拟言、代言。史书尚可虚构对话,散文有部分虚构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17世纪法国戏剧家莫里哀有一个剧本《贵人迷》,其中的哲学教师说:不是散文的,就是诗;不是诗的,就是散文。一个人说话,就是散文。他说的散文应当包括公文。散文易写而难工,能把散文写得富有诗意,才见真功夫。散文的自由体现在没有格式,没有目的,收放自如。下笔时的无心失真或有意弄虚,可能都有助于散文的美。说到底,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只是用文字营造一种貌似的真实或现实,只要“像”真的,就可以了,不必“是”真的。动人的散文不一定都有真情实感。景不必是亲历(可以看风光片或宣传画册),情未必是真有(可以抄写情书或“誓词”“出师表”),可以造景,造情,只要能使散文有魅力。真实并不是散文成功的惟一源泉。散文可以真实,但不能要求散文处处真实,事事真实。真实的可以是散文,但不一定所有的散文都真实。
如果小说可以“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整体虚构,部分写实),那为什么“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整体写实,个别虚构)就是大逆不道呢?
《忏悔录》“是凭记忆写的,有些事时常想不起来,或者只留下一些不完整的回忆,所以只好用我想象出来的可以作为这些回忆的补充的细节来填补……我爱对一生中幸福的时刻加以铺叙,有时又以亲切的怀念作为装饰来予以美化。对已经遗忘的事,我是根据我觉得它们应该是那个样子,或者它们可能当真就是那个样子来叙述的……我有时在真实情况之外添上一点妩媚……我在隐善方面时常是比隐恶下更多的功夫的。”(卢梭《漫步遐想录》)
作为散文名著的《忏悔录》,其作者卢梭承认写作时运用了“想象”“铺叙”“美化”“添上妩媚”“隐善隐恶”等手法,而这些都是“散文真实论者”所不能允许的。卢梭如此写,在他们看来就失去了真实,《忏悔录》也就不能算作散文。
散文所追求的真实,其实是一种真实感,使读者读起来觉得是真的。有时,不真实比真实更真实。眼见都未必为实。如《开国大典》那幅画,有一段时期就抹去了某些人;萧伯纳访华同鲁迅等人的合影,有一段时期就抹去了林语堂;井冈山会师,朱毛握手变成了毛林握手;几十亩地的麦子集中到一亩地里,愣说是亩产几万斤;把不相干的男女的照片合成一张,愣说两人关系暧昧。面对上述画面、场面,如果我们心潮澎湃,激情满怀,或怒不可遏,义愤填膺,那就抒错了情,恨错了人,用俗话说就是:哭了半天不知是谁死了,一笔糊涂账。面对假象,不真实的写作是否比真实的写作更接近真实,更接近真相?所谓歪打正着、负负为正,是否也包括这种情况?
雅各布森说:散文是换喻的艺术。其实归根结底,任何艺术都是提喻的艺术。艺术家、作者不可能把全部素材一次都用上,七情六欲同时都写出来,他们必须对材料进行选择——提取,而有选择就有了倾向性,就有了舍弃,就同真实(全面)有了距离。
散文一般分为写景散文、抒情散文、说理散文、叙事散文,不管哪种散文,都是“过去的事”——事已发生,理已存在,情已具有,景已观毕,我们写的都是“回忆散文”,每写一篇散文都是在“追忆逝水年华”,而回忆总是靠不住的。“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钱钟书《<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我们是把大脑中的事、理、情、景用文字表现出来,而人的表达能力各不相同。“我手写我口”是一种高超的能力,非普通人能办到。“眼中有神,碗下有鬼”,说的是眼高手低,面对同一种事、理、情、景,由于能力的差异,就会有不同的真实出现。
散文写作有点像小学生的看图说话,但要复杂得多。图是固定的,图中有几个人、几只鸡、几条狗、几头猪,大家都能说出来,但要讲清人与这些动物的关系和故事,肯定言人人殊。只要不是故意歪曲,尽管能力不同,每个人讲的就都是真实的,虽然每个人讲的都不可能全面。散文写作之所以比看图说话更复杂,是因为我们要写的景不会是一处而是一片甚至多处;我们要写的事是动态的、已经发生的;我们要写的理和情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这些全靠我们用文字来追述,来表现。“修辞立其诚”,有多少人写,就有多少种真实。
即便是同一景、同一情、同一理、同一事,由同一个人来写,写十次肯定是十样,因为时过境迁,经历不同了,角度不同了,观点不同了,“前推”(突出)的部分不同了,表达能力也不同了,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了。卢梭同朋友们绝交后,以前朋友们对他的善举都变成了恶行,都被解读为给他挖坑、下套、使绊,为的是让他出丑。绝交前后写同一件事肯定是两种面貌。《列子·说符》:“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 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让这个人来写丢斧,找到斧前同找到斧后肯定是两种写法。
即使是同一件事,立场不同,也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沦为难民这事,如果干得好,叫出国深造。不得人心这事,如果干得好,叫曲高和寡。回家蹭饭这事,如果干得好,叫看望父母。虐待儿童这事,如果干得好,叫望子成龙。前言不搭后语这事,如果干得好,叫跳跃思维。脚踩两只船这事,如果干得好,叫慎重选择。摆架子这事,如果干得好,叫有气派。装傻这事,如果干得好,叫大智若愚。木讷这事,如果干得好,叫深沉。鬼混这事,如果干得好,叫恋爱。掐人这事,如果干得好,叫按摩。跑龙套这事,如果干得好,叫友情出演。……”
所以,对同一件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真实;写多少次,就有多少次真实,除了上述个人的诸种不同外,还得加上各人的表述能力差异,这还不包括故意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秘鲁—西班牙大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有一部著作《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写大他14岁的表姨妈与自己恋爱、结婚的经过(后离婚)。胡利娅认为此书不真实,改编成电视剧后离真实更远,于是写了一部《小巴尔加斯·略萨没有说的话》来回应。他俩说的都是真实的,也都不是真实的,永远不会有全部的真实。
有些罪犯对自己的同一宗罪行供诉十次,如果不是事先背诵了第一次的供词,十次肯定十个样,他们倒不一定是为自己开脱,前后矛盾,而是因为是事后回忆,而回忆是靠不住的。这有点像散步,虽然每天走的是同一条路,但谁能保证踩着的永远是同一排脚印呢?如果是团伙犯罪,分别审理犯人,然后比较矛盾之处,有时能得出真相,但有时却制造冤案,道理就在于此。
散文真实论有点像自然主义论。虽然莫泊桑同左拉是好朋友,但莫泊桑对左拉的自然主义颇不以为然,并当面质问左拉:你哪一部小说是自自然然自己流出来的?写作既然是一种主观行为,那怎么可能完全客观地反映现实?绝对的真实论就像绝对的自然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就像“写作的零度”或“零度写作”——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的写作。
古文或外文译成现代汉语就会部分失去原有的真实;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就会失去更多原有的真实——两种艺术形式越不相同,改编(改变)后原有的真实就失去的越多。用散文表现现实,是把生活“改编”(改变)成艺术,是比两种艺术之间的改编更难更远的事情,怎么可能百分之百地保留原有的真实而毫无损失呢?
散文当然也可以写未发生的事,那就是预言了(计划、规划、前景),而预言有对有错,有能实现有不能实现的,需要未来去验证。这种散文离真实(真实感、真实性)就更远了。
从附录《近代散文钞》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可以说主要讲的是散文的变迁。周作人把中国文学大体分为两派:言志派与载道派。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国的文学统称为言志派文学;两汉、唐、两宋、明、清的文学统称为载道派文学。乱世言志派文学占统治地位;国家统一则载道派文学是主流。他自己更赞赏言志派文学。
事实上,言志与载道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区别。有些人的言志就是载道,有些人的载道也是言志。道无所不在,所谓“道在屎溺”。在受到钱钟书的质疑后,周作人修订了自己的表述:“凡载自己之道即是言志,言他人之志亦是载道。”这样一来,言志与载道之分就成了自己与他人之分。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 檄》,既言志又载道,就不好归类了。自己的道自己载,自己的志自己言,别人的事让他们自己干。尽量别代言别人,以免受累不讨好;也努力不被他人代言,省得代言人得便宜卖乖。从这个意义上说,捉刀人、影子作家,都挺不容易的。要揣摩上意,代上峰立言,版权还得归上司所有,何苦来哉?!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不摆架子,不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是言志派的标志。言志派的文学,也可以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称为“赋得的文学”,或者说命题作文。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但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仍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如果把“无用的”散文当做实用的公文来写,把自选动作作为命题作文来做,那就会离文学、艺术、美越来越远,离规范、公式越来越近,但也未必离真越来越近。等而下之的就成了八股文——既不美,也不真,光剩下了套路和套话。套路的僵化导致话语的趋同,话语的趋同源于思想的统一。“反正我并不相信统一思想的理论。”“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
好散文除了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之外,还应注重时代性,不能制造假古董,文章要有鲜明的时代特性,虽然传之久远的可能终归是“永久的人性”。我们是活在当下,应勇于在场。除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还要拓宽自己的眼界,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拓宽眼界的便利。写颂扬文章时参考一下反对意见,以堵塞漏洞;写批评文章时了解一下辩护观点,免得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