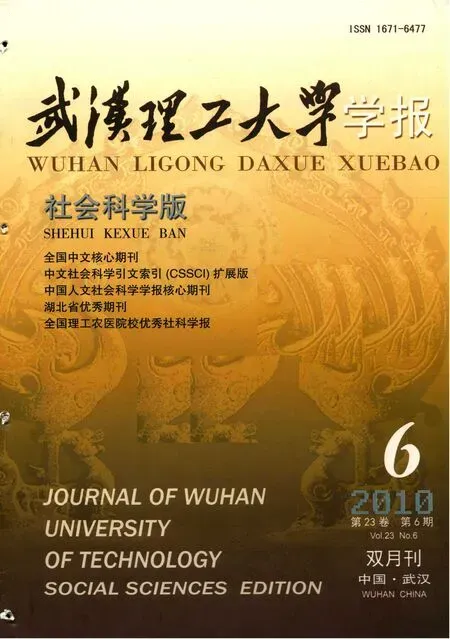河洛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文化突围*
2010-03-20刘保亮
刘保亮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471023)
河洛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文化突围*
刘保亮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河南洛阳471023)
河洛文学是地域、文化、文学三者的共生互创。河洛作家研究要探寻创作主体的情感地理,从“地方亲属关系”中呈现地域文化人格与原型意象。河洛作品研究重在解析文本的地域文化品质,揭示河洛理学文化、宗教文化、王都文化等对河洛文学的“深度构成”。河洛文学史的书写要凸显长河意识、多元意识、当代意识。对河洛文学的研究,既是对文学传统的追忆与眷恋,也是对今天的聆听、关注、阐释与反思。
河洛文学;河洛文化;情感地理;文化视阈;史学意识
河洛文学作为河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始,以先后在洛阳、郑州、安阳、广州召开的十届国际研讨会为标志,已有近20年的历程,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既为这一充满生机的学术增长点而欣喜,同时也不无忧虑地发现“热闹”背后尚缺乏有价值的学术沉淀。
正如克罗纳将一部哲学史看作一部“问题史”[1],或如马克思所言“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2],我们有必要对“何为河洛文学”,“何为河洛作家”这一原点问题重新追问。无论是早期的三集《河洛文化论丛》,还是新近出版的《河洛文化通论》,论者一般以地域为判定标准,把那些或为河洛人或长期游宦居住于河洛地域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毫无置疑地归属于河洛文学。然而,地域文学是地域、文化、文学三者的共生互创,这就决定了河洛文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对作家出生地和居住地的溯源考证,河洛文学史的书写不能仅仅只是河洛作品的堆砌,如果我们不能解析出河洛文学里那种地理与人文相互依赖的生命密码,那种千载轮回的欢乐与悲哀所积淀生成的集体无意识,那种穿越历史时空的地域文化精神印记,那么,我们就不能回答“河洛作家的文化个性何在”以及“河洛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学意义何在”之类的问题。难道“河洛”只是一个不具备人文地理价值的标签式冠名吗?
一
研究河洛作家,首先要着力探寻创作主体的情感地理。任何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成长的母地,正如屈原之于荆楚,李白之于巴蜀,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州。河洛地域就是河洛作家特别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河洛人的精神母地,那自小接受并长期濡染的山川景物和人文传统,都会有意无意地以各种方式进入作家视野和作品文本,无论是“自然的人格化”,或是“人格的自然化”,在作家与自然人文环境的相互创作和被创造的关系流程中,不断地形塑着河洛地域文学的斑斓色调和情致灵韵。正因为河洛作家不是从虚无开始而是历史地存在着,他们生活的河洛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观念习俗等,或如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或如海德格尔“前理解”理论,将必然影响着艺术创作主体。这样,当作家进行“灵魂还乡”的写作时,从文学发生学理论出发,从荣格“自主情结”观点看,我们总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氤氲弥漫的母地泥土气息。
河洛作家与河洛地域文化血脉相连,他们的欲望和创伤都根植于这块古老的土地,尤其是在经历了四方漂泊或人生磨难之后,其笔触游荡于河洛山水人物,无论是“金谷二十四友”饮酒赋诗的酬唱之歌,还是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黍离之悲;无论是杜甫“三吏”和“三别”的痛苦愤怒,还是元结《次山文集》的“危苦激切”;无论是白居易终隐香山的吟咏性情,还是元稹《连昌宫词》的盛衰感叹;无论是邵雍《伊川击壤集》的快乐诗学,还是李绿园《歧路灯》的理学伦理,那唤回和流淌着的爱恨悲欢无不深蕴着地域文化基因,即便是感性的山水风情描摹,也沉潜着人文诗思,从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河洛作家精神气息和土地文化的内在关联。
深化河洛作家研究,重要的在于揭示河洛作家的“地方亲属关系”。“每个社会群体都感到自己与他所占据的或者将要迁去的那个地域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土地和社会集体之间存在着互渗关系,等于是一种神秘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不能让与、窃取、强夺的”[3]。这说明地域与人的关系已经越过生活居住的物质层面而直达精神信仰的深度。河洛作家与河洛地域——特别是地域文化——血肉相联,但这种人地关系表现于文学并非都脉络清晰。从先秦到明清乃至当代,有一些河洛作家,我们似乎在作品里嗅不到原本应有的地域气息,这也许因为作家已将它巧妙地遮蔽,也许出于对自身存在的现实超越。而不符合常规的文学现象,既给河洛文学研究者带来心理的困惑,同时也激发其探索的热情。
深化河洛作家研究,要着力开掘河洛地域的文化人格。文化人格是以历史地理为载体和基础的。由于河洛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人文传统塑造了地域性的文化生存形态,影响并制约着河洛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生活其中的人们形成一种心理定势,进而最终形成独特的河洛文化人格。如李准对中原人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的“侉子”性格的概括,李佩甫对豫中平原“有气无骨”的“绵羊地”人格的刻画。对河洛文化人格的发掘,既包括作家这一创作主体,也包括作品里的人物这一创作对象。
深化河洛作家研究,要解码历代河洛作家共同呈现的原型意象。荣格认为,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的系列的意象和模式。在河洛大地,从“河图洛书”、“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到阎连科《日光流年》里现代版的回响;从黄河水患的遥远记忆,到当代文学对水旱蝗灾的苦难反思;从“中原干戈古亦闻”的洪荒逐鹿,到历代诗文的乱离哀音;从十三王朝的光荣梦想,到今日河南作家的权力书写,透过悠久而丰厚的河洛文学典籍,追踪“易象”、“黄河”、“战火”、“帝都”等反复浮出的原型意象,我们不难发现河洛群体“种族记忆”的碎片,那重复了无数次的心理体验的结晶,我们理应沿着一道道深深开凿过的原型河床,勾勒出河洛人生命之流如何从远古走来又怎样奔腾成一条大江。
二
河洛文学是描写不同时期河洛地区的自然环境、现实生活、生存状况、价值取向、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等具有特定文化品格的地域文学。如果说对河洛作家的研究意在认知主体的文化身份,那么对河洛作品的研究则重在解析文本的文化品质,因为地域文学总是有意无意地坚守和捍卫一种地域文化,河洛文学既然是由河洛文化所孕育生成,其文本就必然是对河洛文化的书写、表现和凝聚。
河洛作品研究的现状是:多为资料整理性和粗线条评述性的著作,缺乏综合性和整合性的成果;局限于就文学研究文学的牢笼,缺乏地域文化视阈的观照,致使河洛作品中品味不到其赖以滋养成长的“泥滋味、土气息”。如果仔细审视历年来河洛文化研讨会成果,以杜甫为例,可以发现对他的诗歌研究似乎克隆着《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我们看不到这位土生土长的河洛诗人留存有多少地域文化的印痕。想必诗人的童年一定会有许多身边的欲望梦想,也许还有闭锁于黑暗意识里的心理创伤,它们都有可能转化为情结而在成人诗作里悄然流露;想必诗人青年时代游历繁华似锦的神都洛阳,耳闻目睹近在咫尺的权力舞台,是否激发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想必晚年寓居浣花草堂,凄风苦雨、纵酒啸歌之中,那故园情思是否拨动着生命黄昏的琴弦,促使他最终携家出峡踏上漫漫回乡之途?读着“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的诗句,我们由衷地被游子乡愁感动着,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仍未绘制出杜甫与河洛文化的指掌图。
河洛作品研究的另一硬伤是欠缺文化比较,大多满足于孤立封闭状态下的自我独白,甚或自大与自恋。而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透过理解他者来扩大对自身的理解。怀海特曾说:“人需要邻居具有足够的相似处以便相互理解,具有足够的不同之处以便激起注意,具有足够伟大之处以便博得敬仰。”[4]这里“人”、“邻居”与“文化”、“文学”是隐喻同构的关系。按照怀海特的有机哲学,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离开他者自我表现既是不可能也是不可理解的。这样,我们对河洛周边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的“注视”与“倾听”,既借助文化他者多视角地返观自身,避免井底之蛙的独断,又在差异参照中获得丰赡生命,抛弃“简单位置“的思维,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研究的园地。
对河洛作品进行文化研究,一些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独特关系值得关注和追踪。如河洛王都文化与河洛文学的苦难叙事和权力情结,如河洛易学文化与唐代河洛诗歌的神秘奇异风格等等。这里主要探讨两点:
一是河洛理学与河洛文学之关系。河洛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礼乐的始兴之地,也是程颢、程颐“伊洛理学”的发源地,仅从民谣“嵩县伊川到洛阳,村村立着石牌坊”就可见理学的民间“播撒”程度。在河洛“理学名区”,从元结、白居易、韩愈最初倡导道德文章,到邵雍、二程讲义式的“理学诗”和“理学古文”,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文学主题,都留下了理学的烙印。特别是清代李绿园的《歧路灯》,“籍科浑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劝戒世人“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达到理学家所谓的“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的目的[5]。无论是“伦理范世”“正人心”“淳风俗”的小说基调,还是浪子谭绍闻、贞妇孔慧娘、义仆王中等人物形象,无不深深契合于“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理学名言,无不昭示着程朱理学是人生歧路明灯的道学圣训。同时,由于河洛理学文化有着自身庞大的思想体系和漫长的演变历程,这就要求我们仔细辨析和呈现它不同阶段既细节鲜活又芜杂碎片化的“原初景观”。
二是河洛宗教文化与河洛文学的关联。河洛地区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被后世尊为教主的老子长期在洛阳担任周朝的守藏吏,并在此完成道教经典《道德经》。之后,无论是黄老道的传播,还是太平道的发展;无论是嵩山道士寇谦之的改革,还是唐代道教的走向颠峰;无论是北宋王朝的崇奉,还是金元全真教的布道,河洛地区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河洛地区也是佛教在中国内陆的初传之地,白马寺曾被尊奉为“释源”和“祖庭”。从东汉至唐代,河洛地区既是主要的译经场所,也是大德高僧辈出之地,特别是少林寺禅宗的出现,是佛学与道家及玄学相激荡的产物,它有着深刻的河洛地缘因素。时至今日,在河洛地区还保留着龙门石窟、白马寺、少林寺、中岳庙、上清宫、吕祖庙等大量丰富的宗教遗存,这些文化景观不仅是昔日佛道兴盛的历史铭碑,也是解读现实社会尤其民间信仰的活化标本。就在这千年不衰的香火缭绕之中,在河洛文人雅士的吟唱与凡夫俗子的跪拜之中,佛道释放出巨大的浸润能量,河洛文学以其对社会生活的摹写和思想情感的表达,自然而然地记录和贯穿着佛道身影。从魏晋的玄言诗到唐宋诗文再到明清小说,我们不难发现河洛文学与佛道故事的渊源,作品主题中的出世忘世哲学,以及作家审美情趣、心理结构、艺术思维、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有机关联。同时,佛道作为两种影响整个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宗教,虽然在总体线性时间上它表现为“大一统”结构,但这种整体结构与空间形式的地域相遇,由于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殊异,使其在不同地域文化里的“弥散结构”并不均衡。因此,我们对河洛文学与佛道文化的考量,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放之四海的普世知识的翻版与微缩,而应与周边秦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里的文学宗教因子,进行比对与参照,以此细致入微地发掘佛道对河洛文学的“深度构成”,呈现河洛文学对佛道的独特书写。
三
对河洛作家及作品的研究,为河洛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坚实的基础,它使我们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中触摸文学的脉搏,感受文化传统,既获得时间层面继往开来的方向定位,又找到空间层面自我识别的文化坐标。而一旦进入对河洛文学史的思考,便会有问题意识随之产生。
一是长河意识。河洛文学史是一条流动不息的长河,它有源有流,古今是一体贯通的。而目前无论是河洛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还是河洛文化著作的文学专题,大凡涉及河洛文学研究时不言而喻地将分期截止于晚清,由此把20世纪的现当代文学排除于视野之外。这种做法无疑把河洛文学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拒斥了文化和文学的历时互动功能,既造成学术观念的严重缺陷,也不符合文学的经验事实。如果我们仔细研读新时期以来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李佩甫的《李氏家族》和《羊的门》,张宇的《活鬼》及《晒太阳》,阎连科的“耙耧系列”小说《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刘震云的“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等,不难感受到来自于中州理学名区的不绝如缕的孝道妇道规训,滋生于河洛“王者之里”的难以割舍的政治集体无意识,熏染于河图洛书文化并与李贺、韩愈、李商隐等一脉相承的神秘奇异文风。这种河洛文学“今”与“古”内在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积淀-生成”式的建构特征,说明现当代河洛文学与地域历史文化的源流关系。所以,文学分期不应是简单分割,更不应是彻底断裂。同时,“长河意识”也启示我们研究深厚、绵延的河洛文学,要尤其关注名胜古迹如嵩山、龙门石窟、白马寺、相国寺等文化高地,考察不同时期文学对同一空间景观不断进行的描述、表现、题咏,发掘历代迁客骚人为景观所增添的人文附加值,从而在变化的时间与假定不变的空间之中剖析层累的序列化的文化岩层,不断追忆一山一寺、一草一木的悠久生命,感悟江山胜迹超越人事代谢的历史沧桑。
二是多元意识。目前各种区域文学史和省籍文学史层出不穷,也许是受地域的限制,或许是主体身份的遮蔽,在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研究中存在不同程度与方式的“自恋”情结,在对自身的过度张扬而对他者的有意矮化中,形成了理论的“冒险”与虚假的学术泡沫。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蓬勃兴起与文化多元主义时尚流行的语境里,河洛文学史研究理应与时俱进地弹奏多元文化的“格调”。一方面,在河洛文化、文学与周边地域的比较中,对自身评价应保持一种谨慎与警惕,防止惟我独尊的话语霸权,因为在多元文化价值观里“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6]。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关注弱小群族的文化诉求,善于发现并认同主流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这一意识形态要求我们避免对河洛文化与河洛文学的本质化叙述,而注意倾听其内部的“杂音”和“异调”,如曾经侵入,后被同化的各种胡夷文化,如北宋灭亡后“文化塌陷”期被边缘化的文化。同时,我们还要以多元开放的思维方式,以海洋般的心胸,推进不同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内部或外部的平等对话,着力构建地域文学的生态乐园。
三是当代意识。“当代”,被内在地赋予一种视角高度,因为过去的本质可能并不存在于过去,一个阶段的最大特征在那个阶段往往并不知晓,一个阶段的本质常常是由后人所决定的。有了这种视角高度,“当代”意味着我们正以一种前人不可能有的时间和空间方式进行思维,意味着以跨越时空的旅行者的优越身份进行观照,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对文化和文学传统进行鸟瞰式的零度聚焦,使其无法锁定而总是处于流动的、开放的、反思的状态。所以,在文学史的叙述中,我们重视当代河洛文学,因为它不仅指向“当下”,也指向过去;它不仅是现实生活的逼真再现,也是历史传统的陈列缅怀。这正如当代河洛作家的“权力情结”,无论是阎连科、李佩甫还是刘震云、张宇,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热衷于描写“乡村政治”,对权力充满欲望与想象,这不仅是“河南最大的问题确实是对行政权力的迷信”[7]的真实写照,而且也是漫长的河洛千年帝都历史文化的缩影与折光,是流转千年的贾谊、杜甫等政治集体无意识的遥远回应。因此,当代河洛文学对伦理道德、民俗风情、文化精神的书写,是当代与历史的双重映像,从中可以看到历史传统如何穿越时空的雾霭走进当代文学世界,哪些被敞开而进行表现与阐发,哪些被遮蔽而导致忽略与压抑,进而寻找历史与现实的“视阈融合”,管窥河洛地域沉潜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规范。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河洛文学不无“温情与敬意”的回眸研究,不仅仅是对文学传统的追忆与眷恋,而且也是对今的聆听、关注、阐释与反思。
[1]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
[3] 赵 园.回归与漂泊[J].文艺研究,1989(4):56-65.
[4] Whitehead.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313.
[5] 栾 星.歧路灯研究资料[M].郑 州:中州书画社,1982:94.
[6] 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M].叶兴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7]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641.
The Existing Question and the Cultural Breakthrough of the Heluo Literature Research
LIU Bao-l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He'nan,China)
The Heluo literature is three symbiosis creates mutually of the geography,the culture,and the literature.The Heluo writer studies explore creative writers on the main emotional geography,presents the regional culture personality and the prototype image from“local family ties”.The Heluo work research in the analysis text of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quality,revealed the Heluo Neo-Confucian culture,the religious culture,the national capital culture and so on to“the depth constitution”of the Heluo literature.Heluo history of literature's writing must highlight the long process of awareness,the multi-dimens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The research of the Heluo literature research,in fact,are not only to memorize literary tradition,but also tolisten respectfully to today with the explanation and the reconsideration.
Heluo literature;Heluo culture;emotion geography;culture threshold;historical awareness
I207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29
2010-06-10
刘保亮(1968-),男,河南省新野县人,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课题(09BZW066)
(责任编辑 文 格)